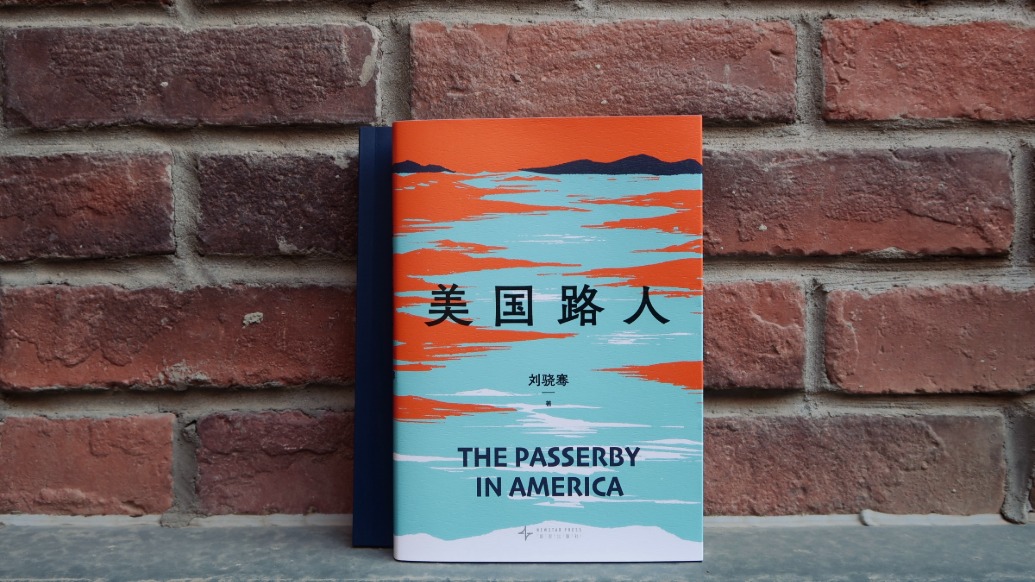- +151
我們家“過年”要花兩個月,從東歐到浙江
有孩子前的圣誕節,我們過得馬虎;有了孩子之后,大多數時候去安在斯洛伐克的老家和公公婆婆一起過。有幾年不去歐洲,外出旅行都是安排在12月24號、25號、26號之前,獨獨這三天是一定要在家里過的。安就地取材,做簡易版的圣誕晚餐;我和女兒則早早地把房間裝飾好。可是,在與誰的故鄉都不搭邊的現在的住處過,怎么也不如去婆婆家過來得有氛圍,就像中國除夕,要是一家三口在自己家里過,即使做了一桌的菜,那味道總是缺了一點什么,再燈火通明也冷冷清清。
所以,我們經常從十二月中開始“遷徙”,先往西,去東歐過圣誕節;再往東,回江南過春節。
外出務工者返鄉
2018年12月22日早上,我帶著女兒和在德國出差一個多月的安一起乘火車返鄉,從科隆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
這是我第一次在歐洲乘火車出行,以為購買了車票就能高枕無憂,可以舒服地坐在溫暖干凈的車廂里看風景,卻在出行前一天才被安提醒還要去購買座位以保證上車能有位置坐。
“外出工作的人都會趁這最后一個周末趕回家去過圣誕,明天沒準會很擠。”他告訴我。
于是,我去火車站的乘客服務中心買座位。
一位戴著厚厚的圓形黑框眼鏡的上了年紀的工作人員盯著屏幕查了很久,然后有點艱難地用英語告訴我:“沒位置了。”
“沒位置了?我買的是一等座,麻煩你查查一等座車廂。”我不相信,我明明買了一等座的車票,現在卻要站著?
“所有的座位都被預訂了,你還是可以上一等座車廂,只是沒位置坐。”她又盯著屏幕查了好一會兒后,肯定地對我說。
誰讓我想當然地認為買了火車票就有座位呢?!
牽著女兒走出客服中心時,女兒一個勁兒地問:“那我們要站8個小時?”
“沒事,我們可以坐行李箱上,8個小時很快就過去的。”我安慰她,雖然心里有點忐忑,但又有些許興奮,很想看看東歐“民工返鄉”的情景。再說了,我是經歷過數次中國春運的人,站過從天津到浙江近30小時的綠皮火車,還怕區區8個小時!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坐上了回家的火車。站臺上果然都是推著行李箱的人,不少拖家帶口的。不過上了火車,竟幸運地看到了沒有標“被預訂”字樣的座位,所以女兒便被安頓好了。車上當然也沒有人擠人,寥寥數人——包括我和安——站在車廂連接處,標著“被預訂”字樣的座位即使空著,也沒人坐,等著預訂者前來認領。
我既慶幸又失望,慶幸的是后半程車程都是有座位可坐的,失望的是沒看到大規模的集中人口遷徙。想想也是,他們人口這么小,怎能成規模呢?!
只有最后一段從維也納到布拉迪斯拉發的行程,才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許多人一般,火車上坐得滿滿當當。突然周圍人說的話是我聽得懂的——這聽懂也不是真的懂,而是那語音語調是熟悉的,一熟悉便有回到家的感覺。一路懸著的心終于放下來,很快就到家了。
天賜的假日
晚上7點多。我們的車駛進婆婆家所在的街道,在熟悉的窗前停下。一邊的窗臺上亮著蠟燭狀的小燈,這是每年圣誕期間才拿出來的;另一邊擺著盛開的蝴蝶蘭,那是老人家精心伺候著特意在圣誕時開的。
我聽到咔嚓的開門聲,和樓梯上的腳步聲,最后樓梯口的大門開了。婆婆張開雙臂迎我們進屋。暖意濃濃。蘭姆酒已經倒好放在茶幾上,此時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下行李,端起酒杯。干杯、擁抱、行貼面禮,我們才“被放過”去做其他事。
房子里四處都是圣誕裝飾。桌上、茶幾上鋪著圣誕桌布,桌布中間擺了圣誕松環,松環中立著圣誕紅色的蠟燭。墻上、門上也掛著大小不一的松環。這些擺飾是在12月6日“圣尼古拉斯節”就拿出來的,到1月6日“三王節”這日才收起來,包好,等下一年再拿出來用。
圣誕樹通常在12月24號早上才拿出來,樹上的掛飾也是有年頭的,很多玻璃吹出來的天使、小鳥和彩球,都是從安小時候就有。不過這次,我們到的時候,圣誕樹已經裝飾好了,可能是老人家實在閑來無事。

23日星期天是圣誕前最后的購物日。TESCO超市前已經擺出了臨時魚池賣活鯉魚。不同于我們熟悉的英美國家以烤火雞為主食的傳統,斯洛伐克人的圣誕晚餐主食是鯉魚。23號到24號早上,大超市門口都會擺出臨時的魚池賣活鯉魚,買魚的人排長隊。不過把活鯉魚炸成魚排是項繁瑣的活兒,所以很多家庭都改吃加工好的魚排,我們也是。
對了,超市——即使像TESCO這樣的大型超市——在24號早上賣完鯉魚之后就要關門三天,直到27號才開門營業。這樣天賜的假期,連周末都不愿意多干點活的懶人們自然是要拿來享受的。我們恰好在23號晚上去了TESCO,一邊超市的廣播里不停地播當晚的打折信息,新鮮面包1歐元可以買10個,另一邊采購的人們恨不得一手推一輛購物車,那規模,跟我們過農歷新年沒什么兩樣的。不過,我們的超市365天全開放,在城市居住的人倒也用不著為過年存多少貨。要在圣誕期間大吃大喝的斯洛伐克人,不把后備箱反復裝滿是過不了超市不開門的三天的。
家人的聚會
雖然斯洛伐克的官方宗教是天主教,但是許多人不過是名義上的天主教徒,比如安和他的父母。安雖說小時候受過施浸禮,長大后卻是徹底的唯科學論者。公公婆婆也是多年不上教堂,所以圣誕節對于他們來說,只有世俗意義。
就像我們的年夜飯一樣,平安夜的圣誕晚餐自然是圣誕節的重頭戲。前菜、沙拉、湯、主食、甜點樣樣俱全。
婆婆在頭天傍晚就把土豆和雞蛋煮好,這兩樣要晾涼了切成丁放到沙拉中。紅豆腰豆也是提前泡好,用來做甜點。24號當天,老人家很早就起床,開始煮酸菜臘腸湯。這一天,我可是被酸菜湯的咸香味喚醒的!酸菜原本就是頂頂開胃的東西,湯里又加了各式臘肉和臘腸,以及秋天在山上采來曬干的蘑菇,真是鮮上加鮮!這一整天,哦不,整個圣誕節,房子里都彌漫著酸菜湯的香,因為湯的分量,是夠一家人喝三天的,而且這湯越放越入味,吃到最后一碗時,恨不得把碗舔個干凈。主食魚排是開餐之前才煎的,因為用的是加工過的魚排,反而沒什么特別之處了。
忙完廚房里的,公公婆婆在下午洗頭洗澡,把自己拾掇清爽,又要拿出襯衣和裙子熨妥帖了。等天黑后,速速煎了魚排開餐。不過別急,開餐前還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在桌布下放上錢。這是安最積極的,他把世界各地收集來的貨幣各取幾張放到下面去,仿佛放得越多,來年他就能賺得越多——果然,錢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語言!
一家人都坐好后,坐在主位的公公先發言,當然是祝大家“圣誕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之類的。大家碰杯飲酒,這時喝的是朗姆酒。第一道菜,吃的是圣誕薄餅。這種餅薄薄的一片,上面印著圣誕樹或鈴鐺或星星的圖案,只在圣誕節期間有賣。餅上涂一層蜂蜜,再夾一瓣兒生大蒜一起吃。這酒和餅的意頭,想來必定是來自于基督教傳統。

晚飯后,圣誕老人就悄悄地來了!12月6日,有個叫圣尼古拉斯的老爺爺會給小朋友們送糖,這圣尼古拉斯和圣誕老人其實是一個人,他并不會在平安夜再來。圣誕老人的概念,也是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結果。總之,圣誕禮物不是我們通常熟悉的圣誕日早上起來才拆的,而是平安夜當晚就拆。這就要求我們給小朋友編個故事,要有人負責在晚飯后把她從客廳里引開,又有人迅速把禮物放到樹下去。9歲的女兒至今還未懷疑圣誕老人的存在,她總是在圣誕節前給他寫信,說自己想要的禮物。只有在今年,她問了幾次“這個禮物是不是你們誰給我的?”問她怎么會這么問,她說:“包裝紙看起來很眼熟。”我和安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要讓孩子相信圣誕老人的故事。作為唯科學論者的他說:“因為我們要她相信這世界上有奇跡。”
圣誕節當日,我又在食物的香味里醒來。這次是一種特殊的烤肉,只在12月25日早上吃。
同樣的,各人洗漱完畢,穿戴整齊——與前一晚一樣的正裝。婆婆把一大盆新鮮出爐的烤肉放到桌上,旁邊放了一籃子面包片,還有一壺剛泡好的紅茶。每個人面前的餐具和茶杯也整齊地碼好了。待大家坐下來后,公公點上蠟燭,給每個人都倒上茶。他上了年紀,又因前幾年動過手術,手抖得厲害,可是盡管顫巍巍的,他也是不愿意讓我們代勞的。他們還習慣在當天早餐的茶里加蘭姆酒,我不習慣在早晨空著肚子飲酒,便省去了這一步。早餐的主要內容是烤肉就面包。
早餐后,這一天剩下的便是走親戚和吃吃喝喝了,26號也是類似的作用。婆婆家互相走動的親戚朋友似乎并不多,核心家庭之外的表親們都是打個電話問候而已。公公的弟弟一家住在南方靠近匈牙利的區域,來回開車將近兩個小時;婆婆有個姐姐住在附近的一個村子里,但是他們也不在圣誕節期間上門。有一年,遇到過安的弟弟楊的教母來,那是一個為了照顧母親終身未嫁的老人,還給我女兒送了當地中國超市買的玩具。另外有一年,安的一位堂弟和他太太上門過,他們都在維也納工作,所以都會英文,和我聊了一會兒。
安偶爾也帶我和女兒去他的朋友家。有趣的是,他們從來不給客人準備正餐。招待客人的都是火腿片、芝士片、腌黃瓜片之類的小食。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吃過別人家做的家常菜。有點遺憾,但是千萬不能被婆婆知道。
走親訪友的下午,除了吃小食,還能干什么呢?喝酒啊!以及聊天。他們會一本正經地圍坐在客廳里,聊個不停。坐在一邊什么都聽不懂的我有點無聊,不過他們似乎會意識到我無聊,時不時地問我問題,而我呢,聽多了便能歪打正著地猜個大概。
到了26號下午,寂靜的空蕩蕩的、只有金色的街燈閃爍在街的轉角,突然有一兩家屋里的燈亮起來,那是終于從節日的慵懶里蘇醒過來的酒吧,開了門供人換一個地方暢飲閑聊。從此,小鎮從平安夜的天賜安眠和萬籟俱寂中舒緩過來,積聚著力量,奔向新年的熱烈和狂歡。
歸來、回去
圣誕、元旦之后,我們回國,短暫地回歸正常的日常之后,開始準備另一個方向的遷徙。
我在更年輕時雖說也有過不愿意回老家過年的時候,現在有了孩子、年紀漸長后,卻很樂意帶孩子回去湊湊熱鬧。一來孩子既需要了解和經歷父親的文化傳統,也需要熟悉來自我的另一脈傳統;二來如今的浙江農村,除了冷點兒,實在沒有什么不如我所居住的城市舒適的。
我對擁擠的返鄉人群比依舊空蕩蕩的圣誕節前的歐洲高鐵要有準備得多,方便面的氣味更是熟悉得下了火車許久還留在心頭。平時不怎么吃方便面的女兒一定要在坐火車回外婆家的時候買上一桶,坐定后就急急忙忙地撕開泡上。我坐著看窗外,從廣東經過湖南,右轉進入江西,最后到浙江。一路山丘起起伏伏,一棟棟新建的西式洋房座落其中,若不是割成井田狀的土地不同于歐洲延綿的田野,恍惚中真有置身歐洲的錯覺。


一家人坐在年夜飯前,桌上的菜式幾十年都沒有多大變化,都來自本地的自然,同東歐圣誕節里的“農夫之菜”異曲同工。我的家鄉不靠海而多河流多池塘,所以年夜飯里只有河魚并無海鮮,紅燒鯉魚取的自然是“年年有余”之意。從前一年一度的白切雞和白切肉也是取自自家養了大半年的雞和豬;最最新鮮的要數青菜,剛從菜園里摘的,意為“清潔無災”。如今大部分人直接去市場買了雞和肉,但是如果有外地回來的年輕人買了山珍海味來,大家并不買賬。
年夜飯的菜式和習俗一代傳到另一代。爸爸接替了從前爺爺做的事情,點蠟燭點香、在門前朝拜;從前不給自家孩子發壓歲錢的媽媽給孫子孫女發了紅包,還加上已經成年的我們。那些年令人操碎了心的弟弟已經成了慈愛的父親,嘰嘰喳喳的小孩換成了另一批。
正月初一的早飯,是我最盼望的菜羹。奶奶將豬肉、雞血、竹筍、豆腐干等切成丁,用前一夜的高湯,在柴火灶上熬一大鍋。盛滿滿的一碗,撒上胡椒和蔥,就著嘴里冒出的寒氣一起服下,再冷的冬天也暖和了。這羹只是我家的傳統,“羹”與“耕”同音,不外乎是“年年吃羹,年年有地耕”的農耕思想。從前的鄰居家正月初一吃泡飯,泡飯與方言里“賺萬”相諧音,人家果真早早地進城做了生意賺了許多個萬。我們開爸爸的玩笑說他守錯了正月初一的傳統。
盡管爸爸依舊沉默寡言,我卻學會了開他的玩笑。這個從前壓抑得我迫不及待地要遠離的家,也隨著我們的長大生出了溫暖。我們終于不用再叛逆,父母終于不用再嘮叨。我東兜西轉,見識過不同的家的樣子,終于明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頓年夜飯,即使不怎么說話,也是過年。
回家過年,和回家過圣誕一樣,成了我的傳統。
【 About us 】專注于普通人的非虛構寫作,旗下設有三明治寫作學院,以及媒體平臺“中國三明治”。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三明治”(微信ID:china30s)。如需轉載請至公眾號后臺留言,未經許可,禁止一切形式的轉載。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习近平访问越南
- 习近平抵达越南河内
- 多地代表团近期走出国门

- 101家沪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报喜比例超九成
- 行动教育:2024年归母净利润2.685亿元,现金分红总额2.67亿元

- 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代表作之一,取自曹植的同名辞赋
- 缅甸的第二大城市,又名“瓦城”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