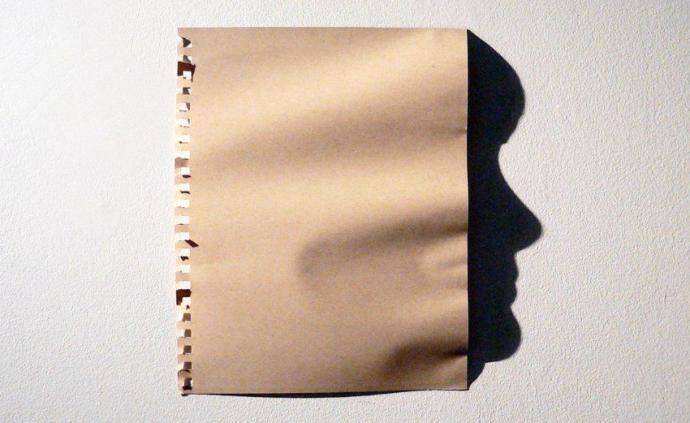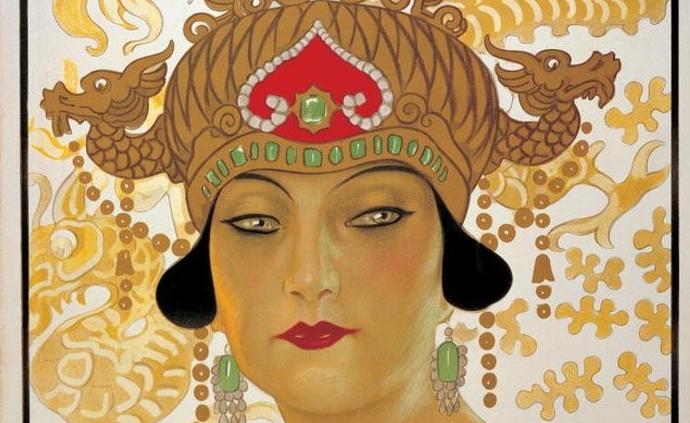- +1175
西風不相識︱大西洋變窄了嗎(二):辛納屈主義
對美國而言,聯合盟友來制定對華戰略,是其對華思路的重大改變,這種改變乃拜大選換屆所賜。對歐洲而言,聯美對華也并非其天然選擇,同樣是經過了反復思考、討論、權衡的結果。
四年前特朗普剛上臺時,歐洲受到劇烈的戰略沖擊,聯中抗美、西方抗中俄、觀火漁利等種種觀點散見于戰略界的討論之中。到2020年下半年,隨著歐洲對全球格局、自身定位的認識加深,歐洲的大國戰略日益明確。歐盟對大國關系的新認識,要言有三:
其一,走“自己的路”。
2019年12月隨著新一屆歐委會走馬上任的歐盟“外長”博雷利(Josep Borrell)是73歲的老政治家(僅比拜登小一歲),曾官至歐洲議會議長和西班牙外長。此公乃奇人也,生于西班牙邊遠村莊,少年在家自學,后靠獎學金游學巴塞羅那、馬德里、加利福尼亞和巴黎,所拿學位涵蓋工程學、經濟學和數學,最高學位是馬德里大學的經濟博士。
“走自己的路”,正是博雷利的貢獻。
如果說在歐洲之內,法國總統馬克龍是最會“敘事”、最懂話語之于重整政治秩序之重要性的政治家,那么博雷利可排第二。
2017年上臺的馬克龍,曾任法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助手。利科為解釋學泰斗,給語言(尤其是詩性語言和隱喻性語言)賦予了極高的政治地位。正是在馬克龍力推之下,“主權歐洲”“歐洲戰略自主”成為主流話語,錨定了歐盟的航向。
年邁的博雷利甫一上任,就遇到“大變局疊加大疫情”,無法周游列國,卻正好“指點江山”。他在歐盟官網開辟個人博客,經常在媒體“一稿多投”并接受媒體集體采訪,不斷發出振聾發聵之聲。
“走自己的路”正是博雷利在2020年6月提出的。面對如何在中美之間做選擇的難題,博雷利對媒體說:“我們必須像辛納屈一樣(Frank Sinatra),不是嗎?走自己的路。”辛納屈是何許人也?中國人不太熟悉,但西方人很熟悉。他是美國著名的爵士歌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他的歌聲估計伴隨了博雷利的青蔥歲月。而“走自己的路”(my way)正是辛納屈的代表作之一。博雷利以辛納屈歌名“走自己的路”來比喻歐盟的戰略抉擇,令人過目難忘。很快,英國《經濟學人》將博雷利的這一思想冠名為“辛納屈主義”,令其廣為人知。
其二,在中美間“不選邊、非等距”。
到2020年7、8月間,博雷利對其“辛納屈主義”又有新發展。他說:“獨立性并不意味著與中美之間距離相等。我們與美國漫長的共同歷史和共同價值觀意味著我們離華盛頓比離北京更近。”
這個立場顯然不僅僅是博雷利個人的立場。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9月中聯合國大會上講話時表示:“自從我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以來,經常有人問我一個既簡單又殘酷的問題:‘在中美之間的新競爭中,歐盟站在哪一邊?’我的回答如下:我們與美國息息相關……我們不同意中國政治和經濟體系所依據的價值觀……我們站在民主、人權、法治與合作的基本價值觀的一邊。利益是我們的指南針。歐盟是一支自主的力量,它是決定我們選擇的主人,也是我們命運的主人。”
歐洲民意在中美間的搖擺似乎與政治家同步。德國科爾伯基金4月進行問卷調查,在回答“德國應該跟美國還是跟中國保持更緊密的關系”這個問題時,選擇“美國”和選擇“中國”的人幾乎持平。但到9月份再次進行調查時,結果則發生了明顯變化:認為應與中國更緊密的人從36%降至27%,而認為應與美國更緊密的人則從37%升至56%。
選前,歐盟實際上已做好了無論誰入主白宮,都要與美改善關系的心理準備。9月1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其任內首個盟情咨文中表示:“不管今年年底發生什么,我們都準備好了要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議程。”更耐人尋味的是德國女防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11月2日美國大選前夕在媒體上發文《歐洲仍然需要美國》,稱“在一個以權力競爭加劇為特征的世界中,西方只有保持團結,才能站穩腳跟并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此時美國大選結果其實并未揭曉。
待歐洲確定拜登勝選后,歐洲人爭辯的焦點,與其說是在中美間如何站位,莫不如說是在親美與自立間如何站位。法國總統馬克龍對德國女防長“歐洲仍然需要美國”的言論心懷不滿,表示“只有在歐洲嚴肅地看待自己的時候,美國才會尊重歐洲這個盟友”。最終,歐委會在《歐盟-美國應對全球挑戰的新議程》中是這么“和稀泥”的:“一個團結有為且自立的歐盟,對歐洲有好處,對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有好處,也對多邊體系有好處——此三者相互加強而非相互排斥。”
其三,將對華政策協調作為改善美歐關系的鑰匙。
這種想法最早曾于2018年4月浮現。當時歐盟為力避特朗普對其征收鋼鋁關稅,醞釀對美提議簡化版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與此同時與美國聯手對付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由于特朗普堅持征稅且在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上毫無與歐合作之意,歐盟未能施展此計劃。
媒體后來甚至披露,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8年4月訪美期間曾試圖“禍水東引”,但未得到特朗普回應,相反特朗普稱“在貿易問題上,歐盟比中國還差”。更有甚者,特朗普問馬克龍為何不離開歐盟,并允諾如果法國離開歐盟,將給法國更好的雙邊貿易協定。地區一體化是歐洲戰后的生存關鍵,特朗普對歐洲一體化的傲慢與驚人的無知,恐怕是讓歐洲精英無法真正與特朗普展開合作的更深層次原因。
然而,到2020年,呼吁美歐聯手制華的聲音不斷增多。2020年2月,美國智庫亞洲協會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項目舉辦大型網絡研討會,匯聚43位美歐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探討對華關系。美歐學者召開這樣規模的會議來共同研討對華政策,為近年罕見。此次會議的一個出發點是:特朗普的做法侵蝕了美歐互信,中國利用美歐分歧來“以夷制夷”,“對中國的擔憂”也許能成為修補美歐裂痕的“一個主要機會和催化劑”。
也許是看到美國反華共識之深,也許是看到地緣政治爭奪之烈,也許是認為中歐關系已難回舊好,總之,歐盟官員似乎將上述觀點聽進去了。2020年6月15日,美歐舉行了外長視頻會議。會談僅僅一個半小時,主要談論三大問題——中國、中東和歐洲的“東部鄰居”。除烏克蘭問題外,美歐或各執己見,或歐方言之諄諄而美方聽之藐藐,可謂忠實反映了美歐冰冷的關系。相比之下,此前6月9日的中歐外長視頻會議舉行了3個小時,“坦誠而有用”;而此后6月19日的中美外長會則閉門談了7個小時。正是此次美歐外長會上,博雷利提議歐盟與美國就中國問題啟動雙邊對話。事后博雷利在其博客提及當時的場景:“我給了(蓬佩奧)許多例子,其中一個是當美國懲罰空客而我們準備懲罰波音的時候,中國正在補貼它的大飛機,打算以后把它賣到世界各地,也包括賣給我們的私營企業。這是需要我們在對話中討論的。”
然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博雷利的提議不置可否,更未進一步探討細節。博雷利略顯尷尬,降調處理,會后對記者稱這僅是一個“建議”。但在美歐外長會10天之后,蓬佩奧卻在一個智庫論壇上出人意料地表示對此建議很感興趣,并稱已派大隊人馬設計美歐協商對華政策機制的細節,將在數周內盡快啟動。有分析稱,此間6月22日中歐領導人會晤舉行、特朗普選情不利等因素或許刺激蓬佩奧改變了心意。
10月23日,也即距美國大選不到兩周之時,博雷利與蓬佩奧通電話,雙方決定建立美歐論壇(US-Europe Forum)討論“所有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并在美國大選結束后立即啟動。兩天后,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寫道:“有些人可能將(美方的對華戰略側重)視為其會自動削弱跨大西洋之間的關系。但是,我認為,我們對中國關系的積極方式是重新開展跨大西洋合作的機遇。”
最后宜指出的是,歐洲與美協調對華關系,并不意味著歐洲想“慫恿”美國對華強硬,恰恰相反,歐洲認為自己能在中美間居間協調,借力打力。歐盟委員會在12月2日發布的《歐盟-美國應對全球挑戰的新議程》中委婉地指出了歐美對華看法的差異:“對于歐盟來說,中國是合作的談判伙伴、經濟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歐盟和美國都認為中國日益自信地擴展其國際影響力構成了戰略挑戰,盡管我們不總能就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達成共識。”一些歐洲軍事部門的人甚至認為,歐洲的戰略自主有助于阻止中美爆發軍事沖突,因為歐洲擁有“公認的、完整的工具——包括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可以采取真正的綜合方式”。
-----
作者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