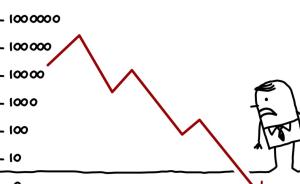- 21
- +140
三個學術民工〡緩解匯率沖擊的外部思路
匯率的大幅波動,肯定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劇烈的波動————嗎?對這個問題的肯定式回答,帶來了對浮動匯率制度的恐懼。而否定回答,則帶來了更為樂觀的預期,以及更具野心的匯率改革方案。
不管是恐懼、還是相對樂觀,人們往往從國內經濟因素來尋找佐證。這篇文章關注緩解匯率沖擊的另一個視角:改變我們的外部環境。
廣場協議:德國幸存指南
1985年9月,西方五國達成了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廣場協議”:日元與馬克大幅對美元升值。事實上,從1985年9月至1989年12月,兩者分別對美元升值了42%和46%。同樣經歷了大幅升值,歷史卻對日本、德國給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
相對于日本經濟,德國經濟何以能夠在廣場協議之后幸存?原因很多,根據作者的不完全總結,主要有三點原因:
其一,廣場協議之后,日本過度依賴擴張的貨幣政策刺激內需,德國則更多地使用了財政政策,對擴張的貨幣政策保持了非常謹慎的態度。具體可以參見學術民工的另一篇專欄《擴大內需:靠財政還是貨幣?》。
其二,廣場協議前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順序出了問題,具體參見學術民工的舊文《1980年代,日本金改的錯與莫》。
其三,正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內容:廣場協議后,日元對美元的升值是單打獨斗;而德國馬克對美元的升值,則是以“鐵索連船”的集體行動來應對的。
廣場協議之后的1986年至1990年間,日本出口貿易增速明顯偏弱,年均增速僅為4.1%;德國的出口貿易則維持了強勁增長勢頭,年均增速仍然高達16.7%。對美元升值更多,而德國出口表現卻更為強勁:
一方面,這與德國貿易方向多元化有重要關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在當時的德國出口當中,美國市場僅占8%,歐共體成員國占比則高達70%;另一方面,德國與歐洲貿易伙伴之間的匯率,多處于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安排之下,德國和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都在較窄的范圍內釘住歐洲貨幣單位(ECU),互相保持著較穩定的匯率水平。這種穩定的匯率安排,與歐共體的內部貿易又有一種雙向的強化關系。
相反,日本的出口有30%到40%集中于美國市場,而且東亞其他國家的匯率對日元大幅波動。因此,同樣對美元的大幅升值,日本就悲劇了。
日本的自我救贖
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機,讓東亞大部分經濟體都體驗了貨幣危機的夢魘。日本也在其中看到了機會——像德國那樣,建立起東亞匯率協調體系,為日本和東亞經濟提供外部穩定機制的時機似乎成熟了!
此后,日本學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或者應該說一直以來),主導了東亞貨幣合作的研究,其中伊藤隆敏教授、小川英治教授就是兩位代表性人物。前者曾經在東京大學任教,在安倍晉三的上個任期(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曾任首相經濟顧問,在安倍的第二任期當中,也曾經與黑田東彥并列,成為日本央行行長的熱門人選。小川英治教授曾任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也曾任日本一橋大學的副校長。
2000年,小川英治和伊藤隆敏設計了一個貨幣籃子,如果能夠共同釘住這個貨幣籃子,那么東亞經濟體就能同時實現雙邊匯率、以及多邊有效匯率的穩定。這時候,東亞國家不但能夠穩定區內貿易,也可以緩解外部因素帶來的沖擊,從而將匯率波動帶來的成本最小化。
2006年,小川英治與清水順子共同提出了亞洲貨幣單位(AMU)的概念,并且計算了這個貨幣單位。這使得東亞經濟體的匯率釘住一籃子有了具體、清晰的目標。此后,在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相當于我國的商務部國際貿易研究院,但研究范圍更廣)的支持下,AMU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拓展,AMU及其衍生指標每個月都在RIETI的網站有更新和發布。
關于AMU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但是受到中、日雙邊關系等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以及后來國際金融市場保持了一段時期的風平浪靜,在實踐上,東亞匯率協調機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匯率協調機制進入北京時間?
當國際金融市場面臨狂風駭浪,除了個別大型經濟體之外,大部分開放的經濟體都是一葉扁舟。通過錨住一個共同的貨幣單位,區內各國可以建立起匯率協調機制,從而避免或緩解外匯市場、以及匯率沖擊帶來的壓力——這是廣場協議德國生存指南對中國的啟發之一。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要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帶來的影響,一種辦法就是推動東亞區域的匯率協調機制。那么中國主導、推動東亞匯率協調機制的時機是否成熟?
我們傾向于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首先,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充滿動蕩和風險。歐央行、日本央行等五國都在強推負利率,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取向撲朔迷離,外圍市場如俄羅斯、巴西、阿根廷、哈薩克斯坦等等,都已經或仍在面臨著巨大的經濟、金融沖擊。
從扣動金融危機的扳機來看,亞洲新興市場面臨的外部風險也正在上升。在美聯儲加息正式啟動之前,從2015年5月開始,東亞區內普遍出現股指大跌、匯率快速貶值的現象,同時一些經濟體也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外流和外匯儲備的下降,一些東南亞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的外債甚至還在快速攀升。
今時已不同往日,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悲劇未必重演,但從目前的國際金融形勢來看,區內國家的貨幣與金融合作,尤其是匯率協調機制的合作具有現實需求。
其次,中國已經成為大部分東亞經濟體的最重要貿易伙伴,成為東亞經濟生產網絡的核心樞紐。以東盟為例,10年前,大部分經濟體的最重要貿易伙伴當中,中國基本上都排在前三名之外。到了2015年,東盟6個主要經濟體當中,中國已經成為其中5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只有菲律賓例外(中國是其第二大貿易伙伴)。整體而言,中國也是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國,這一地位已經維持多年。在此基礎上,東盟國家貨幣匯率的波動,也開始更多的考慮人民幣匯率因素。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兩位研究者,Subramanian和Kessler在2013年的研究表明:在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以及2010年7月至2013年7月,這兩段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升值的時期,東盟10國釘住人民幣的節奏明顯加快,其中7個國家的貨幣與人民幣的緊密性甚至超過美元,當人民幣升值1%,東南亞7國匯率則上升0.5%,但如果美元上行1%,上述7個貨幣匯率的上行幅度僅為0.3%。作者甚至驚呼其為“人民幣在美國后院的崛起”。
相比較而言,徐奇淵和楊盼盼在2013年的研究,則沒有這么樂觀:美元在東亞地區的錨貨幣地位相當穩固。不過他們也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日元已經基本上失去了在東南亞各國貨幣當中的駐錨作用,同時人民幣的地位顯著上升,在東盟6大經濟體的貨幣當中,人民幣權重大致在20%到30%之間的水平。
過去10年,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力量對比發生了大反轉。2005年,中國的GDP是日本的一半;2010年,中國與日本持平,時隔4年之后的2014年,中國GDP已經成為日本的2倍!以此為背景,中國在東亞區域匯率協調中的話語權、影響力也日益增強,同時為地區金融穩定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也在上升。因此,在我們關注匯率沖擊對國內的影響時,我們也要更多關注這一問題的外部解。
提到的文章:
Eiji Ogawa, Takatoshi Ito (2000), On the desirability of a regional basket currency arrang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00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Eiji Ogawa, Shimizu Junko, 2006, “AMU Deviation Indicators for Coordinate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East Asia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Effective Exchange Rates”, The World Economy, 29(12), 1691-1708.
Subramanian, Arvind and Kessler Martin, 2013, "The Renminbi Bloc is Here: Asia Down, Rest of the World to Go?", PIIE Working Paper WP 12-19.
徐奇淵,楊盼盼,東亞貨幣轉向釘住新的貨幣籃子?,《金融研究》,2016年第3期(該文初稿完成于2013年,我們所在機構與小川英治教授每年舉辦一次雙邊的學術研討會,主題聚焦于中日的金融合作。2013年末,在東京RIETI的研討會上,雙方也討論了這篇論文)。
-----
您正在關注“三個學術民工”第2期工程:本專欄關注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金融問題,由徐奇淵、楊盼盼、熊愛宗倒班為您特供。事實上,“三個學術民工”已經完成第1期工程——《抓住碎片:三個學術民工玩中國經濟拼圖》,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即將上市,敬請關注。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