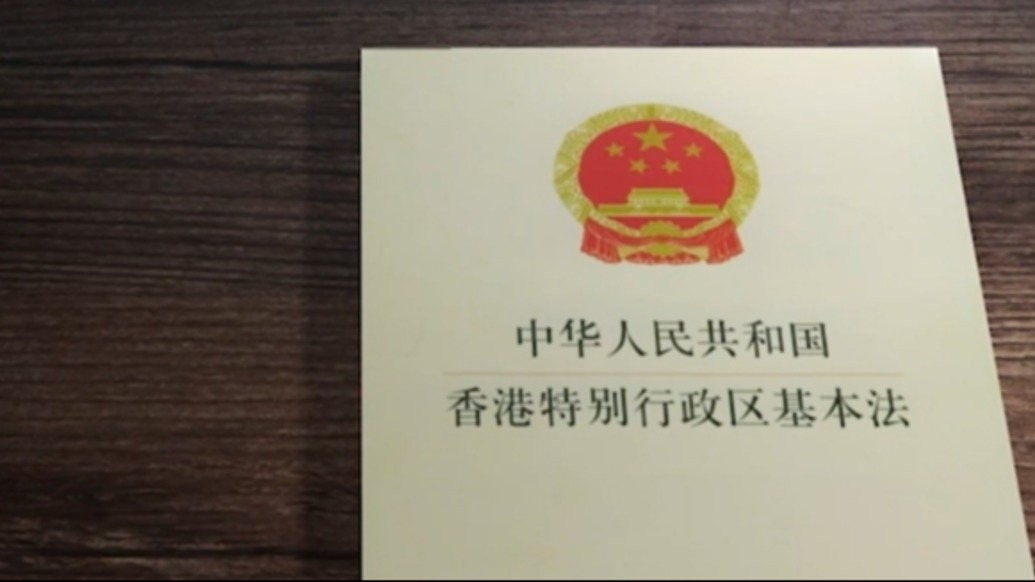- +1129
李小江讀《唐虢國夫人:文本與日常生活》︱守史學之根,尋歷史之“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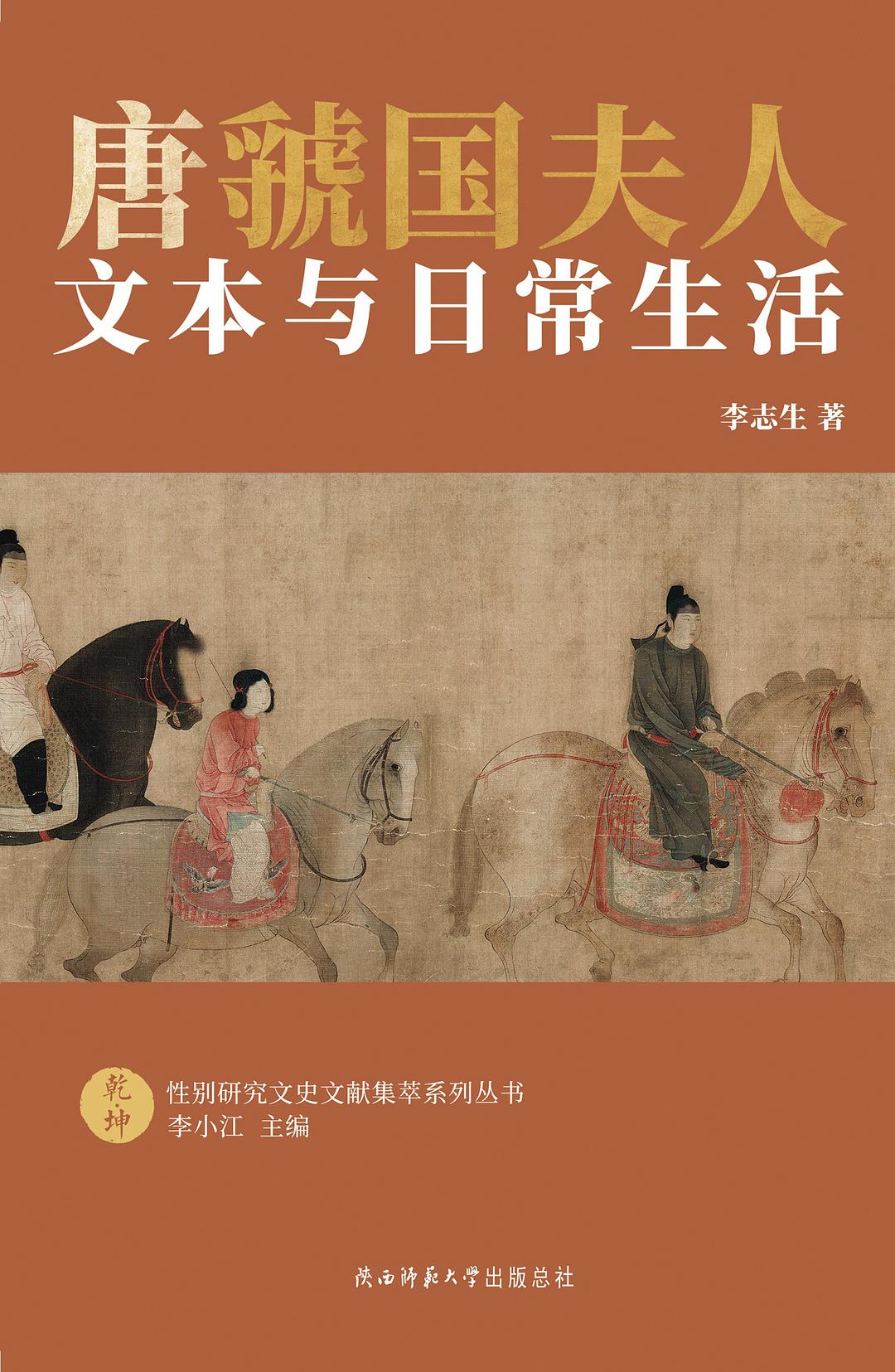
《唐虢國夫人:文本與日常生活》,李志生著,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266頁,78.00元
史學的根本是什么?
是史料。無論新史學還是傳統修史,“任何歷史研究都應當從分析原始資料開始”([法]埃馬鈕埃爾·勒華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中譯本前言,許明龍、馬勝利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頁)。史家追尋的終極目標是歷史真相,一代接一代,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再現論”([美]詹明信:《馬克思主義與理論的歷史性》,張旭東譯,載《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38頁)中,為人類世世代代身心健康發展構筑“接地氣”的精神家園——如此高貴的境界,與唐虢國夫人有什么關系?
虢國夫人,楊貴妃三姊,宰相楊國忠堂妹,驕奢跋扈不可一世,因盛唐時期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和歷代文人著述而名在史冊——遺憾,其名不善,與“紅顏禍水”同步相傳。她本人的身世面目也并非自在清朗,“自其文本出現之始,就是以唐玄宗時期的政治和帝王個人生活的附屬而存在,長久以來被‘封裝’在男性知識和權力精英的各種敘事文本中”(《唐虢國夫人:文本與日常生活》,38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從宋代歐陽修到明清的戲文傳唱,惡評如潮……直到李志生的《唐虢國夫人》面世。
作為“性別研究文史文獻集萃”系列叢書主編,早在2020年我就讀過此書的初稿,看好它做文本考據的真功夫。近期新書面世,再讀,有意外的收獲:在傳統史學的根脈上不期撞見了歷史之“真”的精髓:它若隱若現,一脈相承,無論彌漫到哪里,都會牽扯出有關女性的意識形態問題。
整個文明史中,作為群體的女性長久未載史冊。婦女史的浮出,得益于女性主義史學“披荊斬棘”的開拓之功。歷史文獻中關于女性的信息多半出自男性筆下,無不攜帶著父權制意識形態的印記;不披不斬,難見“女人”的真相。迄今呈現于世的歷史,隱含著一部男性主導的性別觀念史;要想做好婦女研究,不得不從“剝離”(批判)歷代即成的“史實”開始——因此,女性主義史學一總附著在傳統史學的根脈上,手心手背,兩面一體,在難以撼動卻不能信賴的史料面前翻云覆雨。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的舞臺幾近成為兩性對弈的戰場,這與兩性和諧共生的歷史事實并不相符——對此,早有認識,卻苦于沒能找到走出困境的門道;有前衛的史學理念,卻一直缺乏有說服力的史料認證。我總以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沒有以扎實的考據為基礎的史料做臺基,任何理論都是無根的,難以有序地傳承。因此,數十年下來,我將希望放遠在有專業根基的后學身上,把心思和目光篤定投向歷史深處,一邊徑自全力以赴創業奠基(自1980年代至今,我在婦女研究領域的主要工作都與奠基有關:主持二十世紀婦女口述史、籌建婦女博物館;創建女性/性別研究文獻資料館、女方志館、新列女文庫……將散失在歷史縫隙中的碎片匯聚成有形的文獻,為女性的知識傳承建成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基地),一邊期待著同仁同道相向掘進——終于,黑暗的巷道里不期而遇,我在李志生的研究中看到了那一縷“真”的光束。
李志生,女,中國古史專業,本碩博均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追隨“鄧廣銘、王永興等老一代學者”,學生做得畢恭畢敬,學問做得戰戰兢兢,筆下文字顯露的盡是考據派修煉出來的慢功夫,與當下學界急吼吼的張揚喧囂判然兩個世界。滔滔學海,新潮洶涌,為何耐得住寂寞?尋求歷史之真,坐冷板凳就是硬功夫。《唐虢國夫人》面世后,我和李志生曾就“真”的問題有過討論,數十篇文本考據下來,問她“哪個是真”?她的回答讓我吃驚:“沒有哪個是‘真’的,歷史的真相就是‘不真’。我們必須抽絲剝繭地尋找可能的歷史真相。”
分明是流傳至今的真文本,何以全都“不真”?
所謂文本,無不出自文人之筆。筆隨腦至,所有的歷史文本無不留下了記錄者的思想印記,從初本到近世,概莫能外。就以虢國夫人為例,對其歷史文本逐一羅列考據,李志生總結:
唐代虢國夫人文本呈現了如下特點:一是文本形式多樣,既有詩歌,也有筆記小說,還有對國史的引用。二是諸文本對虢國夫人事跡的記載零散,每一文本僅是對個別事例的記載……三是對虢國夫人的記載重點不在她的個人生平經歷,而在與政治人物或政治局勢的關聯上,即玄宗的特殊寵待、奢靡生活、楊家的威勢、私生活放蕩等幾方面,而這些方面也成了其后虢國夫人文本衍變的諸方向。(91頁)
從最早的史料開始,真功夫用在刀刃上,甄別和分析提前到位:
《舊唐書》對虢國夫人的記載有如下特點:首先,此書雖未為虢國夫人立傳,但其事跡在書中大致是首尾相接的,這也是《舊唐書》編纂特點……其次,此書對虢國夫人的記載,當是對唐國史、實錄進行整合后的結果。而作為第一部將虢國夫人事跡進行整合的正史著作,它通過虢國夫人事跡的選擇性記載,實為虢國夫人做出了定性,那就是她的奢靡、跋扈、違禮及玄宗為寵她而對法度的僭越等,都是致使天寶政治走向昏暗的重要緣由,而這也為后代文本以虢國夫人為禍首做出了重要指向。(104頁)
將原作中兩段話長錄于此,是想強調它的重要性,面對“第一部將虢國夫人事跡進行整合的正史著作”,作者的立場清晰可見:不是盲信盲從,而是必要的提醒和質疑:“即便是最早記錄的文獻史料,即便是出自官方史家之手的正史”,只要經由“選擇”,呈現于世的就未必是歷史的全部真相。它們攜帶著(當時)現實社會的塵埃,不由分說地落定在被記載的歷史人物身上——抑或,“塵埃”就是歷史之在的部分真相?歷代塵埃累積疊加與時俱進的品質,或許就是歷史文本不斷被后世修訂、篡改或重說的前提?如是,接下來的問題很重要:那些去之不盡的“塵埃”究竟是什么?它因何出現、由誰攜帶、何以成為求真路上難以去除的歷史障礙?這類問題古今同質,長久橫亙在史家面前,讓歷史研究深陷在求真的兩難困境中:去除它,如西西弗斯推動巨石,去之不盡,周而復始;不去除,它即成為歷史真相的遮羞布,讓史家在“半遮面”的史料面前踟躕不前——于此宿命,史家要么繞行而過,要么坐而論道,少見有人迎難而上。
李志生知難而上,因為她有據史料而作為的底氣。將新史學的視界帶進古舊文本,讓塵封的故人故事重新煥發生機。讀過《唐虢國夫人》,高世瑜(唐史專家、新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先行者)看它可作范本,在舊學新用的方向上“對于年輕人日后做學問有一定示范作用”(高世瑜:“《唐虢國夫人》讀后感”,2023年4月1日在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示范,重在展示,此書的重點不在追究虢國夫人生平細節的真實與否,“主要觀照的是文本的出現及所載事件的生發與衍變”。“虢國夫人的歷史是在文本的衍進中逐漸增飾而成的”,這不是特例,一切被記載的人事都有可能在文本的歷史演變中不斷被改寫,在不同立場和觀念的剔抉取舍中逐漸成為今天可見的樣態。以虢國夫人為例,李志生在傳統的敘事軌道上逆向而行;所謂“逆”,針對正史而言,可見四個不同尋常的面相:其一,女人,除非個別有政治地位的,古代女性少有專論;其二,惡人,紅顏禍水,蓋棺定論,翻案困難;其三,邊緣人,其生平脈絡隱含在顯赫的人際關系中,她本人并沒有主導或參與重大事件;其四,物化人,奢靡的日常用品展現的多是物質生活,在正史中少有正面描述——四個面相疊加,尋真是難的。最難的不是尋找史料,是面對層層增飾的史料取舍困難;所謂真相,在歷史文本的衍變中真假難辨。
如何通過文本尋找歷史的真相?《唐虢國夫人》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它用全書一半篇幅陳述艱難的尋真歷程。依次分解,三個步驟,排序不容置換;環環相扣,步步不可或缺。
首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語),盡可能搜尋乃至窮盡相關文本。此事李志生做得漂亮,在虢國夫人名下遍攬眾說,“幾乎將千年以來的相關史載和文史作品搜羅殆盡”(高世瑜語)。書中,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并行的,在歷時分類的基礎上對具體的文本逐一辨析,時代特征和書寫者的個人立場在李志生的解析刀下清晰地展現出來。照通常的做法,接下來該做的,是在甄別真偽的基礎上解讀資料——李志生有所不同:在新史學的光照下,確信“一切歷史的再現都不可避免地含有想象和虛構的成分”([美]海登·懷特:《后現代主義歷史敘事學》,陳永國、張萬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292頁);吸納女性主義史學研究成果,認定既有的歷史文本都留下了男權社會意識形態的烙印。因此,她并不打算在既有的議事平臺上評判是非,而是將所有文本都回歸放置到它們生成的時代背景中——這一來有趣了,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個別事件的表述差異,更多的是不同文本在同樣的意識形態環境中顯現出的相似性:
在虢國夫人問題上,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所有文本均由男性撰寫而成。而在中國歷史上男性文人掌控話語權的語境下,很多時候,當男性君主的統治出現問題時,男人們下意識地尋找禍根緣由的路徑就是指向女人。在他們的描述中,舉凡妲己、妺喜、褒姒、趙飛燕,都成了歷史上著名的“女禍”。(50頁)
經由文本考證,可見兩個分期:第一階段(第四章)是唐、五代和北宋,第二階段(第五章)是元以后直到清末。唐至北宋期間,但凡漢人主政的地方,文本的性質大同小異,沒有偏離女禍這條主線。難得作者在眾口一詞的“女禍說”中理出了它特有的演進路徑:盛唐社會風氣開放,虢國夫人的出現順理成章;安史之亂雖然終結了她的性命,卻沒有將女禍的帽子直接扣在她頭上。“儒學有待復興的唐代后期,以儒家女禍觀來衡評虢國夫人者,尚不多見”。但是,到了“儒學復興的北宋,士人則警省于唐時后妃、公主等在政治與社會中的顯見與作用。故此,楊貴妃被歐陽修等貼上了‘女禍’的標簽”,虢國夫人即被描述成了重要幫兇。到了元明清時期,雖然還是儒家主導的意識形態,士人對虢國夫人的書寫態度卻有了很大轉變,他們“不再僅執著于虢國夫人的禍國與誤國,轉而將她的另一面——素顏美提煉出來”:在清人洪昇的《長生殿》中,虢國夫人成為引發李楊愛情沖突的重要人物;在明末清初褚人獲的《隋唐演義》中,虢國夫人與安祿山、楊國忠等人的多層關系被編撰成好聽的故事和好看的劇目。“這一時期的虢國夫人,雖依然在女禍論的檢視之下,但在很大程度上,她已一變而成為審美、愛情、戲劇沖突中的主題人物。”(本段引文均出自30頁)歷代士人對女禍論的輕重研判,可見儒家道德意識的寬嚴和不同時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將隱身幕后的“意識形態”推向真假難辨的議事前臺。問題因此接踵而至:既然所有的歷史文本無不銘刻著意識形態的印記,那么,意識形態本身抑或就是“歷史之在”的天然要素呢?
答案是肯定的:越是深入歷史深層,越是在歷史書寫中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意識形態這一特征就會越發強勢地顯現出來。隨著整個人類社會進程由遠及近,由上古先人走進高科技含量的現代社會,各類文本文獻中的意識形態不是漸趨消弭,而是越發明顯、普遍和壯大……終有一天,它突破歷史地表,從幕后走上前臺,當仁不讓地成為改變歷史走向和主宰歷史敘事的操刀手,讓眾多史家在積流成海、其勢洶洶、難以超度的“意識”面前止步不前。
關于意識形態和歷史乃至史學的關系,早有話想說;不期走到虢國夫人名下,是因為李志生對歷史文本的處理有意無意間開啟了一條可能見光的通道。經由她的廣泛搜尋、歷時分類、具體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關于虢國夫人的歷史記錄和對她本人的評價,歷時數百年,所有相關文本無不浸染在執筆人身處的時代和主流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中。顯而易見,意識形態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非多余的事項)存身在歷史之中,隱身嵌入歷史敘事——既然如此,與其在真假問題上躑躅徘徊,不如直面意識形態“在史冊中”這一客觀事實,讓抽象的概念下沉,接地氣,入時序,認真析出意識形態自身的歷史面貌。
意識形態的歷史與意識形態史學不是一回事,在學理上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學術走向完全相反:前者必須去政治化,讓意識形態確實成為可能被研究的客體;后者的基本品質就是政治性的,相應的意識形態是闡釋文本的精神指南。探究意識形態的歷史,面對史料會有全新的使命:在起點上為意識形態去政治化,讓它以“中性”品相進入史家的視野——惟此,它的三個基本屬性才可能在具體的文本分析中各顯神通:(一)歷史性,有史以來,它與“歷史”同在。(二)地域性,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邊界,只在族屬(政權/主流文化/精英階層)管轄統治的范圍內是有效力的。(三)實效性,其歷史壽命通常是“長時段”的,與(某一地域族群)文明的盛衰周期密切相關——從屬而至的,有兩個重要特點,如下,不妨分頭說來。
其一,正因為意識形態是歷史性地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與地緣政治格局密切關聯,因此,它在世界版圖中既是相對穩固的,也是可變的。如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中,每個長時段(古代、近代、當代)都有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統領社會人心,每次改朝換代也會有相應的觀念調整:變的是枝葉,是附在主桿上的“意識”;不變的是“形態”,即主流社會的價值導向——變或不變,女性都是在場的:女性的生存狀態以及兩性關系,既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也是人世間的道德標桿。如虢國夫人,在李志生的文本分析中,其變,清晰可見:唐末與政治盛衰聯姻,宋代被理學嚴苛批判……到了明清時期,隔岸觀禍,與權力和道德的糾纏少了,娛樂空間應時開拓——這一趨勢成為(某)意識形態走向末路的歷史常態。尤其今天,當娛樂已然成為大眾消費的廉價市場,歷史人物的發掘或重述直接迎合的是市場需求。它有兩個特點首先被商家看中推廣:一是知名度,便于傳播傳銷;二是去神圣化,走下神壇的同時也是娛樂化的開始。可見,為歷史人物(事件)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遠不只是學術研究自身的需要,更有市場經濟推波助瀾,萬民大眾在歡快的消費中成為史學變革的共謀。
其二,意識形態屬于思想領域,在精神上可以統領世間萬物,存在方式卻是依附性的,其歷史的載體主要是文字,依次為:選擇性的記錄(如《史記》)、歷史評價(如唐虢國夫人)、政治批判(如女性主義史學)、分析解構(如后現代史學)、重釋重述(如新文化史),周而復始,是輪回性的。如果認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那也可以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意識形態的歷史。因此,面對史料,史家不能簡單地信以為真,必須對藏身其中的意識形態成分做必要的分析和解構。就像處理一艘遠航的船舶,要想看到船的真實模樣(本事),首先要清除那些附著在船體上的雜質;越是航程久遠的,就越是需要細致操作,用足夠的耐心和專業技巧遞進剝離。如虢國夫人的文本,其中不乏“明顯的張冠李戴、虛構情節”之偽,剔除偽裝的同時,李志生關注的重點是“虢國夫人的歷史是如何層累地造成的”(36頁)。面對層層累積,她的工作是層層剝離,至少有兩件事要做:一是剝離主流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因素,作者在文本的歷時分類中做成了這件事。二是析出文本書寫者的立場和主觀意向,這是第二章后半段的工作。接著,李志生給出了一個嶄新的個案:作為《唐虢國夫人》的作者,她本人已然走進了歷史書寫(再造)的隊列,在解析虢國夫人的說辭中加入了個人的立場和認識。走到這里,書寫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意識形態因素不再全然是歷史性的,更是當下的。面對新文本的公然僭越,讀者和當世的歷史工作者不得不接手一個全新的使命:剝離。
繼續剝離,這是我的讀后感理當完成的任務。
書中第三章,李志生在“自我感受”和“能動性”名下,將虢國夫人作為主體性的女人帶進現代世界,讓“長久以來被‘封裝’在男性知識和權力精英的各種敘事文本”(苗延威:《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譯者的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頁)中的故人面貌一新,有兩點格外耀眼。
一是行為張揚,跨越性別藩籬任自炫耀:
虢國夫人……并不低調,更不受男女有別、女居于內的儒家禮教的束縛,所以她:“每入謁,(與國忠)并驅道中,從監、侍姆百余騎,炬密如晝,靚妝盈里,不施幃障。”唐代禮教要求“婦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她們的身體和面部是不能為外人窺見的。所以,虢國夫人……除有沖破“男女有別”的豪情外,更有著“讓別人看”的強大心理驅動。(40頁)
二是心理活動:“那種沒落士族人家姿貌甚好但自感不得志的女子,有太多的抱憾與欲望,急于去填補與滿足。”缺少父家夫家的支撐,欲壑難填,只有倚仗自己去爭取或攫得,于此,作者的辯詞過甚有加:“她的風流放蕩、蠻橫霸道、奢侈驕縱等,都是她使自己暫時逃離男權社會的彰示。”
在逃離時,她的“無所顧忌”多少帶上了雄性化戰爭文化的英勇特質,它是赤裸裸、缺乏羞恥感的,而母性的英勇則不同,它總是有所顧忌,一向尊重尺度和界限。所以,虢國夫人的所為,終究是不會為男性社會所接受的,指斥她為安史之亂的禍因,也正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42頁)
恰恰在這些言辭中,我們看到了意識形態的身影:不再隱匿幕后,儼然成為一副親臨前臺參與表演的面具——這樣典型的現代面具,直接戴在歷史人物臉上是否合適?由此引發出兩個相關聯的重要問題,正好卡在當下中國史學研究難以回避的理論命脈上。
第一個問題,因為虢國夫人是女性,相關理論首先是女性主義。顯而易見,李志生接受了女性主義的立場和價值導向,但她并不打算跟在其后亦步亦趨,而是轉用了一個新概念“近女性”。這個概念出自中國年輕學人王虹的專著《“近女性”與“流”的藝術哲學實踐》,嚴格地說,它并不是一個界定清晰的學術概念,而是一種個性化的理念表述,說到底,不過是以德勒茲為代表的解構主義的分蘗,附著在諸多互不相關的現代/后現代理論的軀干上,連自圓其說的基盤都尚未生成——納悶,分明有眾多成熟的女性主義論說,為什么會走到這里?我曾問過李志生,她的回答不出所料:“為了與西方女權主義保持距離。”只因為王虹全書開篇第一句話聲稱“‘近女性’是一個非女性主義的‘女性’理論”(王虹坦言,“‘近女性’的理論是建立在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所說的‘無組織軀體’”/‘無器官身體’”和‘生成女人’概念基礎上的”,《“近女性”與“流”的藝術哲學實踐》,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頁),并且多次強調“它根本不是一個概念,而更像是解構女性主義一個近乎藝術化的裝置”(同上,引言第2頁),李志生便選擇了這個裝置——李志生認同王虹的觀點:女性有一體性(oneness)的傾向,即女性從來就沒有將自己和他人及環境絕對地分開來看,她們感覺自己不是和它們/他們生活在一起,而是他們/它們的一個部分。女性認為:“我不解決問題,我和問題生活在一起。”她們的無意識更傾向于同萬事萬物的“融合”,而不是“分離”,她們不將自己與其他人和物對立起來,而是認為自己就是在這一切之中存在著的(43頁;引自王虹:《“近女性”與“流”的藝術哲學實踐》,191頁)。借助德勒茲的“游牧”精神,一步跳過現代(主義)跨進了后現代的陣營——走到這里,她“邂逅”(李志生語)的就不單純是一個女性主義,而是今天中國所有歷史學者置身其中的學術境況,即必須面對的第二個問題:當華夏古學遭遇現代西學和后現代新史學,史家該如何應對?如何自處?
李志生的處境很有代表性。站在傳統舊學的臺基上迎候八方來風,她是有取舍的:取的是新文化史觀的理念和敘事方法,舍棄的恰恰是她受之恩惠的女性主義史學方向。書中多次提到新史學理論和女性主義倡導的性別觀念(參見第二章第一節和第三章),前者強調文本解析的重要性,意在析出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因素:
如在虢國夫人的問題上,我們就特別需要關注“資料提供者”的儒家性別導向。內外有別與“三從”是儒家性別理論的兩大支柱。在內外有別的含義中,牝雞無晨、美女誤國的思想又占有重要地位。而這些都與對虢國夫人的認識與評價直接相關。(30頁)
后者試圖呈現現代視野中的虢國夫人,有一段話耐人尋味:
社會性別理論強調關注婦女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能動性(agency),側重她們的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這在虢國夫人的研究課題中,同樣是一個需要更多揭示的重點……她的所作所為,其實是有諸多的自我背景與自我導向的,其中明顯蘊藏著她的主體性與能動性。(38頁)
這里引用的分明是女性主義的核心概念,卻偏偏沒有出現“主義”這個字眼。作者本人也是在女性主義的光照下覺悟了現代性別意識的,卻在文本分析中決絕地與之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感似乎是本能的,并不是因為新舊時代或東西方之間存在差距,而是出自堅守史學根性的歷史學家們不約而同的選擇:有意回避強光的照耀,拒絕與意識形態史學同流合污。
毋庸諱言,女性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術語,女性主義史學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史學。意識形態史學的基本特點是排他性,只在一束光照下長驅直入。其優勢,在它的純粹和單一,簡單易行,普及面廣泛,極具戰斗力。借助它的批判力,可以穿透層層歷史屏障,直擊癥結之要害。女性主義史學的主要方法就是批判,針對父權制難以撼動的社會根基,秋風落葉,橫掃史冊,迅速拉開了長久被遮蔽的女性世界的帷幕,為我們客觀地認識人類社會存在已久的“性別制度”開辟通道。其問題,就在它的意識形態品質,同男性中心的歷史觀一樣,單一的性別立場必然導致客觀判斷的錯位,在起點上就可能偏離“真相”:一縷過強的光束難免會遮蔽其他色彩,致使“本事”失真失色。一元化的認識論不僅窒息了自由的人類精神,也極大地制約著原本是活生生的人間生活。生活的常識告訴我們:人世間的兩性關系在社會結構上是互補的,并非單方面的剝奪和壓迫。做歷史研究,任何時候都不能置常識于不顧,先驗地置身于(單一)理論的羽翼之下。具體到婦女史的開拓和精進,最需要的不是“主義”,而是可信且可以傳承的史料。只有通過史料進入歷代在地的女性生活場景,我們才會發現,真正左右歷史進程的不是哪一個帝王將相,也不是虛擬化的人民群眾,而是相似的人性和身處社會關系中的無數個不盡相同的人生。比如虢國夫人,在李志生的文本梳理中,我們看到的不是“個人”,而是層層盤結的“關系”。虢國夫人身上附著的“塵埃”不是一次落定的,而是多次疊加合成的結果。意識形態的時代印記與書寫者的個人觀點糾纏一處,該如何處理才好?李志生的做法值得效仿。在“文本的衍進”(第四章、第五章)名下,她將兩種品性不同的分析路徑合二為一:每每開章,介紹時代的意識形態概貌;章落結尾,適時歸納出若干特點。俯瞰有大勢,落地見個性,在紛呈各異的文本中梳理出清晰的脈絡,涇渭分明,豐富多彩。
有趣的是,書中(搜尋、分期、解析)三部曲在三個步驟的演進中逐一到位,結果卻不善:我們看到的不是真相,而是對“真”的質疑。顯然,研究走到這一步,不能止步,三加一,第四步是我追加的:我看它是通向“真”的最后一搏:剝離,從意識形態浸染的文本中剝離出“本事”——這第四步,該是史學批評暨書評人的責任;除此,還有另一種選擇:作者自檢,如微觀史名家卡洛·金茨堡在《奶酪與蛆蟲》新版前言中所做的,對自己的主觀偏好自查自檢:“與我的成長環境緊密相連的民粹主義,和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所做出的選擇,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聯系,這些驅動力讓我犯下了一些錯誤,有時候還會過甚其詞。”([意]卡洛·金茨堡:《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2013年版前言viii,魯伊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由此可見,“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只說出了部分事實,“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似乎更能擊中要害,因為它道出的不只是歷史的時代性和實用價值,更是觸到了歷史的本質:思想。思想與意識形態,兩者不可等約。思想一總是個體的精神活動,未必付諸行動;意識形態則是一系列社會行為制造的集體意志,與權力運作和集團利益互為表里。思想,可以去政治化,是開放的和多元的。意識形態不同,它本身就是政治工具,不僅有明確的立場和目標,而且有一整套話語體系結構生成的價值判斷,是排他的。現代社會里,意識形態日漸占據了跨疆域的宗教領地,在集群化的基礎上與信仰結盟,服從并服務于(某個)社會階層或群體的現實利益;女性主義也不例外。因此,在處理史料的時候,僅僅完成文本分析還遠遠不夠,自覺地去除“塵埃”將成為史家修史必需的功課。在這個方向上,新史學功不可沒。在新史觀的引領下,以女性個體為主角的史學專著近年火熱,有四部引人矚目:《王氏之死》(史景遷著)、《公主之死》(李貞德著)、《漫長的余生》(羅新著)和李志生的《唐虢國夫人》。史家不拘性別,不計國別和民族身份,將女性當作新史學開疆拓土的突破口,不由人不好奇:為什么他(她)們會不約而同地匯聚在“女性”名下?
依照新史學的政治理念,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沒有主體地位,“講述”就是解放。依照新社會史觀,歷代女性的生存空間集中在日常生活領域,“拓展”就是創新。依照新文化史觀,邊緣化的女性身份輕而易舉就突破了“階層/等級/民族”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為多元化的場域提供了多視角的闡釋空間。依照女性主義史學理論,女人浮出歷史地表,既是對傳統史學的挑戰,更是完善人類自我認識的必經之途。整個父權制的歷史長河中,女性的社會地位不高。但是,在新史學視界中,婦女史的研究價值驀然彰顯,收獲是雙向的:突出(普通)“人”的主體身份,無意中凸顯了女性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去除意識形態沉積的層層塵埃,歷史中的“本事”顯露出來,在女性身上別有風景。本事,即事物原本的樣子,諸多事項中,“兩種”和“兩極”引人注目。
所謂“兩種”,一種是對歷代性別制度的深層解構,一種是物質生活和生產水平的即時呈現。以《唐虢國夫人》為例,前者體現在“關系”中,貫穿全書(如:上唐令規定,在“從夫”或“從子”的前提下,相關婦女可受封為國夫人至鄉君的不同等級外命婦封號;而不依夫、子受封者,則在外命婦封號前加“某品”,17頁),需得專門研究逐一析出。后者即日常生活,是全書下編討論的主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為“交往”設立專章。在“交往”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持續拓展的人際關系,還有各色人等進行交往的場合、交通工具和階層差距。毫無疑問,虢國夫人的交往和她的生活與尋常人們的“日常”有很大距離,與其說它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不如說它展示的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可能企及的物質生活水平,從中可見女性“身體”的負載能力(許多民族用鍛造的金銀首飾裝飾女性)究竟在以怎樣的方式承載起了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和愿景。
所謂“兩極”,指的是女性的生存品質。王氏(《王氏之死》)和王鐘兒(《漫長的余生》)的故事觸到了底層女性求生的底線;而在陳留公主(《公主之死》)和虢國夫人的生活場景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追求物質欲望的極致,從數量到質量,在奢靡華貴的財富中窺見到主流社會的審美觀念和手工制作精美絕倫的技藝水平(虢國夫人衣食住行所顯現的遠不止在日常生活這一層面,“它更多滲入到了等級、技術、工藝等人類精神生產領域或人類知識領域,如其衣服的蹙金繡、障泥的組繡、犀頭箸的平脫技術等,代表了唐時工藝技術發展的高超水平”,257頁)——于此種種,本書最后兩章有充分的描述和展示,細膩,飽滿,無微不至,在“本事”面前顯露出考據派的真本事,沒有給思辨留出太多的議事空間。
廬山·秀峰
2023年3月28日-4月8日初稿
2023年4月11日修訂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