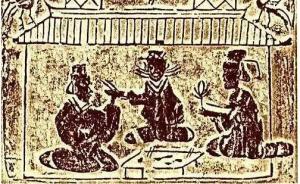- 12
- +136
饕餮中國︱中國發明的面條如何在日本風行
在歷史上,稻米曾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日本人曾經認為食物就是大米,吃飯無非是把米飯加上鹽而已。日本甚至有句俗語,“米鹽之資”,指的是只要有米有鹽就有了生活。但如今,根據NHK(日本放送協會)做的一個調查,“ラーメン(ramen,拉面)”卻成為日本人在新年里最愛吃的食物——面條在這個大米國度站上了美食之巔。
古代的日本人為何不吃麥子?
日本有一個民俗傳說,“狐貍從中國偷來一根稻穗,把它藏在竹筒中帶回日本”,這樣日本就有了稻子。通過這個傳說,我們知道,日本的稻作文化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傳播的途徑大抵有兩條:一是經現在的江蘇、山東,自山東半島越海傳入朝鮮半島的南部;另一是經華北至東北從陸路傳入半島北部,再輾轉擴展到南部。兩者殊途同歸,通過對馬海峽傳到日本。這從日本早期的水田遺跡——發現于最靠近朝鮮半島南端的九州島北部福岡一帶沿海地區的考古發現——就看得出來。隨后,稻作技術以九州北部為中心,逐漸向南和向東擴展,到了公元3世紀左右,已經傳到了四國島和本州島的大部分地區,在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7世紀的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的遺址中出土的谷物都是大米。


由于日本列島的水、熱條件都適宜稻米的種植,加上較之種植旱田雜糧,水稻種植省力省時又高產。因此,數千年來,日本的水稻產量一直是各類農作物之首。故而日本人稱大米為食品之王,水稻則是上天給日本的饋贈。日本人吃慣了大米,所以在古代日本農業史中,大、小麥均不太多見。古代日本民間甚至認為吃面食費時間,而流傳“窮人吃麥”的說法,對面食有抵觸情緒。雖然遇到荒年,日本的官府往往鼓勵種植麥子以緩解饑饉,還發放種子;但農民卻不買賬,即使是被政府所逼,無奈種植了麥子,也不肯作為糧食食用,而是在成熟之前割下來,作為馬的飼料銷售,以至天皇不得不在公元715年頒布法令宣布,如果把未熟的麥子作為馬飼料銷售,將予以重罰。
真的是麥子的滋味不合日本人的喜好么?其實并不是,抵制小麥種植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是當時日本缺乏制作面粉的技術。機器化大生產時代之前,古代人制作面粉用的是石磨。隋唐時期的中國,先是用人力或畜力推動石臼加工面粉,后來用水車轉動碾磨,從而降低了面粉的價格,使一般人也有了條件食用面食,進而使得面食得以大量出現和推廣。按照日本史書《日本書紀》的記載,早在公元610年,一個名叫曇徵的高句麗和尚就把石磨帶到了日本,結果日本人卻仿造不出來——要制作石磨,就必須對堅硬的石頭進行精密加工,偏偏古代日本石工技術不發達,生產石磨實在是力所不能及之事。當時的日本老百姓只能用木制的臼和杵磨面粉,但是木制的臼和杵只適合搗米,遇到有硬麩皮的小麥,搗起來就相當費力,制作面食也就變得非常不容易。與需要磨成粉才能吃的小麥不同(小麥種皮堅硬,直接煮粒食是很難吃的),谷子只要洗凈就能直接煮著吃,甚至食用糙米反而意外地彌補了日本人日常飲食中缺乏的維生素及礦物質。明治維新后,日本軍隊普遍食用精米,反而大規模出現了因維生素缺乏而導致的腳氣病。結果,與“窮人食麥”的民諺恰恰相反,在很長時間內,日本的面食成了一種為公卿貴族與高級僧侶所獨占的珍貴食物。

素面、烏冬面、蕎麥面
說到面食,不能不提面條。2002年,在今青海省新石器時代的齊家文化層(甘肅地區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新石器文化)內,考古工作者發掘出了4000年前用谷子和黍子混合做成的面條,長約50厘米,寬約0. 3厘米,粗細均勻,顏色鮮黃,這大概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面條了。中國對于“面條”的發明權,因此也顯得毋庸置疑。

在唐代以前,一切用小麥粉制成的食物都叫“面”,像面條這樣把小麥面團放入滾水里加熱的食物被稱為“湯餅”,而到了宋代,“面”才與“餅”分家,用以專指“面條”。在吳自牧撰寫的記述南宋臨安(今杭州)繁華景象的《夢粱錄》中,已經專設了“面食店”,有“絲雞面”、“三鮮面”、“炒雞面”等等,與今天已無什么區別。
宋代中國與日本雖然沒有國家層面的交往,但雙方的文化、經貿往來依舊頻繁。與唐代官方的“遣唐使”不同,入宋的日本僧人在雙方交流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彼時,正值佛教的禪宗于中土大興,大部分日本僧人也有來華留學的意愿,他們一邊將禪宗引入日本,一邊也將當時中國寺院的飲食文化(當然都是素食)帶回了日本,面條就是其中之一。后世有人總結,“日本大部分具有劃時代念義的食品都來自寺院,一般是由有中國留學經驗的僧人傳播開來的”。
公元1241年,今天京都南部東福寺的創建人圣一國師從中國學成歸國之時,帶回了一幅“水磨圖”(一張利用水車和齒輪做成磨粉機的設計圖),終于使日本制作面粉的技術趕上了中國的水平。從這時起,日本老百姓才可以品嘗到面食這種從前僧人和貴族專享的食物,并逐漸改變了對面食的看法。


古代日本人吃什么面條呢?最先受到日本人歡迎的是素(索)面。素面是最早的日本面條。當時的素面,都是將面團反復揉捏了以后手工拉長的,就像手工拉面一樣,它的特點是長而細,吃口清爽,主要用作冷食。接下來是大名鼎鼎的烏冬面,當時的烏冬面是將薄面團切片制成熱湯面。據說,日本戰國時期著名的“甲斐之虎”武田信玄的部隊,就以烏冬面作為行軍作戰時的兵糧。按理說,烏冬面只需要用搟面杖把面團搟薄然后用刀切就能做成,不像制作素面需要先將面團拉成長條需要很高的技術,但實際上烏冬面在日本的出現卻晚至15世紀。究其原因,竟是因為當時日本人的技術水平太差,做不出砧板!做砧板需要刨刀,而刨刀在日本直到公元16世紀的江戶時代才開始普及;在此之前,工人需要將刀刃裝在棍子前端,一點一點地削平木頭才能做出砧板,非常費力。
比烏冬面出現更晚的是蕎麥(そば)面。蕎麥本身沒有黏性,容易斷裂,并不適合做面條,傳說是1659年東渡扶桑,寄寓在水戶藩(今屬茨城縣)的明遺民朱舜水(1600-1682年)教會了日本人在蕎麥粉中摻上小麥粉,使其具有黏性和彈性,于是,這種被稱作“最富有日本特色的”面條才面世了。蕎麥面受到歡迎的一個原因是討口彩。據說日本的金箔師傅,在工作時,常用蕎麥面團沾起飛落在各處的金箔碎片。為此,日本民間認為蕎麥是聚金收銀的物品,便借其吉利之說,在訂婚、結婚或吉慶活動時,都準備蕎麥面條。除夕的晚上吃隔年蕎麥面,也是為討個吉利,祈望金銀進家,與中國的“年年有余(魚)”是一個心態。到了公元19世紀,擁有100萬人口的江戶(今東京)城居然出現了100家蕎麥面店的排名榜,足見當時日本人對于這種面條的熱衷。


“拉面”的誕生
同樣是面條,無論是烏冬面還是蕎麥面,近代之前的日式面條與中式面條的一個重要區別是,日本面條在制作時不加堿水。小麥面粉遇水,就會產生一種網格狀的組織,俗稱“面筋”。堿水則是一種含有碳酸鉀和碳酸鈉的呈堿性的天然蘇打水,中國面條在制作時加入了堿水,如此揉捏出來的面團,能使面粉中的蛋白質發生變化而增強黏性和彈性,口感更加舒適。
正宗的中國面條遲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進入日本。1893年時,日本橫濱的外國人居留地中居住著約5000名外國人,其中中國人約為3350人。而在甲午戰爭之后,清朝開始向日本派遣官費留學生,以后自費留學生的規模也急劇擴大。在1905年前后,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人數達到大約5萬人。與此同時,無論是梁啟超這樣的立憲派,還是孫文這樣的革命黨,都將日本作為重要的活動據點,如此眾多的中國人在短時間內來到日本,勢必又一次將中國的飲食文化帶入東瀛四島。
大約在20世紀初期,中國面條出現在了橫濱的“南京町(唐人街)”,并從這里出發,迅速征服日本人的脾胃。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日本一心脫亞入歐,斷發易服之外,連飲食也恨不得一日西化,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撰文鼓吹要像西洋人一樣“應該吃肉”(此前受佛教影響,日本人幾乎不吃魚肉之外的肉類)。明治天皇帶頭喝牛奶吃牛肉,當時的日本宮廷膳食干脆就是法式大餐。相反,對于傳統的文化母國,日本則是一副鄙薄心態,印度古籍用于指代中國的“支那”一詞正是在這一時期,在日本人的口中出現了貶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面條在日本的傳播,完全是出自食物本身的魅力。


盡管這種中國面條毫無蕎麥的成分,但比起粗粗圓圓的烏冬面,形式上更接近固有的細長的蕎麥面,被日本人稱為“南京蕎麥面”,并以其價格低廉、滋味鮮美而受到日本中下層市民的歡迎,逐漸走出“唐人街”,在日本主流社會中流行開來,名字也變成了“支那蕎麥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迫于作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壓力,日本官方不得不下令禁用“支那”一詞。結果,不知從何時起,“支那蕎麥面”又變成了“ラーメン”。這個假名的讀音“ramen”極似普通話的“拉面”,顯系晚近從漢語里直接借入的外來詞。

拉面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日本的國民美食,主要是長長的拉面可以搭配各種不同的蔬菜、動物的肉類作為主要的材料,以及加入醬油、姜、蔥、麻油以及各種干貝或者蝦等海味,能夠滿足各個社會階層對于飲食的需求。因此,在福岡有“中華湯面中心”,橫濱有“株式會社新橫濱拉面博物館”,甚至有個“日本拉面研究會”,專門出有拉面雜志……拉面成為在日本流傳的中華料理中當之無愧的王者。

參考文獻:
(韓)李旭正等,洪微微譯:《面條之路:傳承三千年的奇妙飲食》,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
徐靜波:《東風從西邊吹來:中華文化在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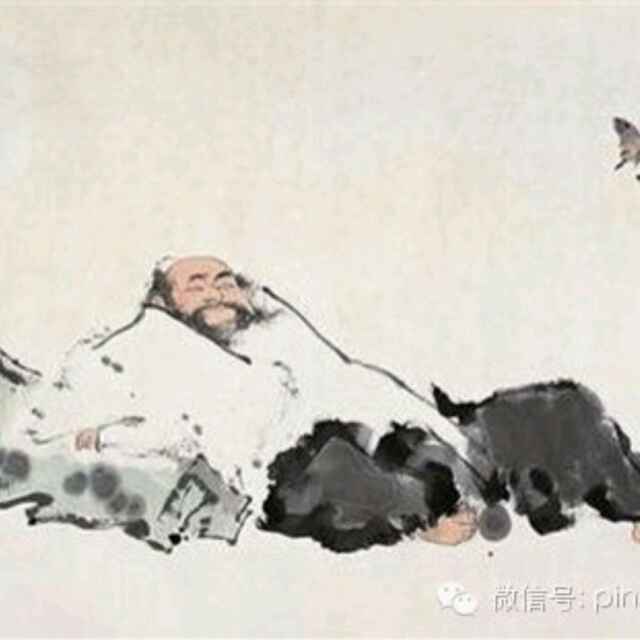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