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鄉民生活世界的“細描”——讀劉永華《程允亨的十九世紀》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永華教授的新著《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在史料整理和分析上下了大工夫,整體設想宏闊,實際操作扎實,允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一部力作。志在樹典范、示軌轍,本書提出了“個體層次的整體史”之類的概念,不過其目標能否達成,恐怕見仁見智,有待時間的檢驗。粗粗瀏覽,即可知本書議題豐富,條分縷析,極盡榨取史料之能事,表面上看似波瀾不驚,實則靜水流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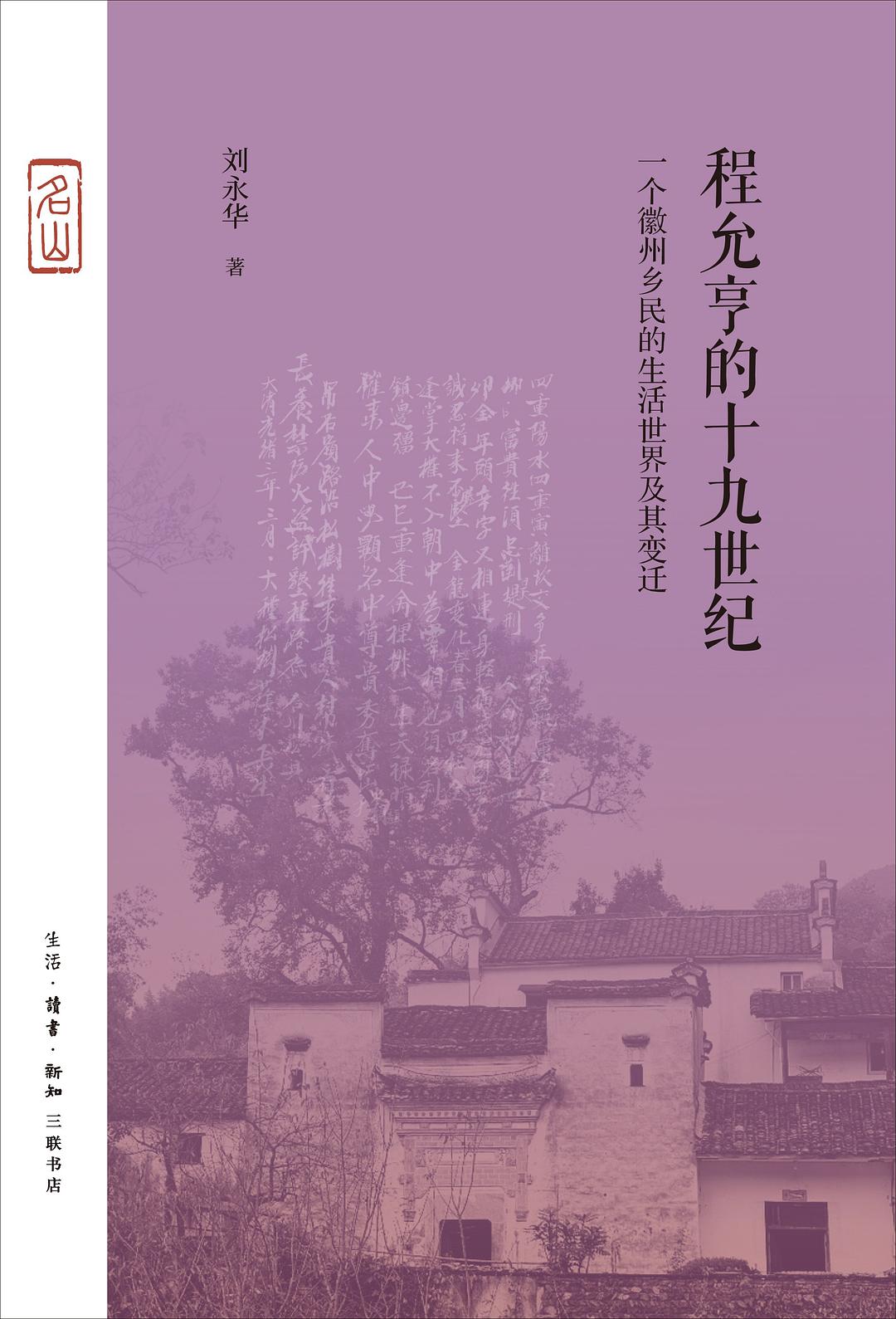
通讀本書,感觸最深的一點是鄉民為了維持生計而付出的種種辛勞。書中有大量表格、各種統計數據,大都跟生計有關。說到生計,在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以說,生態環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當地人的生計方式。本書主人公程允亨所生活的徽州婺源,山地、丘陵眾多,當地流傳著“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莊園”的說法。這種生態意味著“豐富的林木資源成為當地重要的生計來源”,“此外,森林中的野生經濟作物,是鄉民采集的重要物資,在其生計中也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35頁)。由于耕地很少,“婺源生產的糧食不足半年之需”(徽州其他地區大致也是如此)。因此,徽州很早就形成了經商的傳統,“至明后期,經商已成為當地重要的生計手段之一”,故明末謝肇淛《五雜組》有“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之說(41頁)。
本書所利用的主要材料是排日賬,而排日賬最詳盡記錄的當數各種生計活動的內容。為此,書中花了大量篇幅討論程家的生計,比如第五章“勞動安排與階級關系”就涉及農田耕作、茶葉生產、山貨采賣,第六章則對生計模式作了精細的統計和分析。書中指出,“從總體看,程家投入各類生計活動的勞動量,占所有日常行事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66.64%)”(134頁)。第七章“生活水平、商業化與交易形態”也是“沉甸甸的”生計估量,精心制作了程家歷年收入一覽表、歷年開支結構表、歷年收支比較表、不同時期最低消費表等。第九章則從行動空間的角度考察種種生計模式(糧食種植、茶葉生產、集市貿易與食鹽販賣等)。其他章節間或也會涉及生計方面的內容。此外,附錄三至六還提供了糧價、豬肉購買、銀錢比價、耕地與糧食產量等方面的數據。
由此,我們不難體會維生的艱難困苦和維生的堅強意志。畢竟,人作為生物,“生”是第一位的,于是產生了“民以食為天”之類的俗語,以及“天地之大德曰生”這樣意蘊深長的哲言。可以說,“生”是本書的第一個關鍵詞。“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生計,二是生育。
關于生計,上面略微作了一點梳理,接著看看生育。書中關于生育的內容明顯不像生計那樣豐富,但其重要性卻絲毫不差。道理很簡單,沒有生育,生計也就無從談起,“生”之意義也無所附麗。第四章第一節“出生”介紹了不少婺源地區的生育習俗。出于對新生命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風俗,禁忌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妊娠期間的女子有諸多禁忌。如忌參與紅白喜事,不宜接觸做豆腐、做屋上梁等事。又忌吃兔肉,否則孩子豁唇;忌吃姜,免胎兒生六指;忌吃甲魚,恐難產。”(75頁)此外還有種種習俗,如“算胎命”“洗三朝”“望娩婆”“接外甥”,等等。
生育是男女兩性合作的結果,所以婚禮“可說是傳統中國社會中最為重要的一種人生禮儀”(121頁)。婺源的婚禮儀節大致包括討生庚、論八字、踏家地、訂婚、討禮單、下定、送日子單、納采、迎娶、拜堂、三朝、謝媒等。第六章第一節“成親”對此有較為詳細的描述。
如費孝通所言,“一個孩子要長成一個社會分子須有長期的教育。生育制度中就包括著生和育的兩部分”,生殖本是一種生物現象,而人類為了繁衍生息,遂采用種種文化手段干涉、控制生殖作用,“使這生物現象成為社會的新陳代謝作用”。而“婚姻是人為的儀式,用以結合男女為夫婦,在社會公認之下,約定以永久共處的方式來共同擔負撫育子女的責任”。(《生育制度》,《費孝通全集》第四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226、234頁)
總之,“生育”和“生計”的“生”構成了本書的第一個關鍵詞。
現代漢語有“生活”一詞,在某種意義上,“生”就是“活”,“活”也就是“生”。不過,這里強行略作分隔(實則“生”和“活”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相互糾纏、緊密相聯的),以“活”作為本書的第二個關鍵詞。
“活”指靈活性和流動性。雖然處于農業社會,但徽州鄉民為了謀生,并沒有也不可能死守耕田種地一條路,而是多種經營,竭力拓展營生。書中對程允亨的父輩的生計有如下一段小結:
總而言之,自19世紀30年代后期至太平天國前期,允亨的父輩在從事農田耕作的同時,投入大量時間往返于休寧、婺源、黟縣等地,從事食鹽、布匹、麻袋等小商品的販賣,此外也進行茶葉、灰蒻、葛粉等農產品的收購與銷售。發開敏銳地感覺到當地茶市變動帶來的商機,適時購入茶園,開始進行茶葉的種植與生產。(73頁)
從中可以提煉出兩個描述鄉民的形容詞,一是“勤懇”(55頁),二是“精明”(62頁)。可以說,這二者都是應付“生”“活”所必需,也是“生”和“活”的結果。
關于“活”,書中提到的“行動空間”值得稍作討論。要“活”下去,自然不能滿足于田間地頭,何況婺源這樣山多田少的地方。“生活的基礎是生物性的,溫飽是生物基礎給人規定下的生活最低水準,因為饑寒會使人的生命不能維持下去。但是生活卻不等于生命,比生命還要多一點,那是因為人有理想,要活得更好,更有價值,在追求更有價值的生活,使人不肯停留在一種生活水準上……”(費孝通《鄉土重建》,《費孝通全集》第五卷,123頁)
要“活得更好”,出外闖蕩無疑是一條法子,因此排日賬中留下了大量地名。第九章便對排日賬中的地名作了詳細的統計,并制作了路程距離和出現頻次表(217頁,表9)。書中指出,“在出現次數最高的26個地名中,距上灣十華里以內的有14個”(上灣是程家居住的地方),但似乎更強調“在距離上灣100華里以上的地方中,溪口、莊前和休寧在排日賬中出現次數均在200次以上”(217頁)。——對照216頁的地圖,可知大連和莊前是比較近的,大連距上灣將近20華里,莊前在表9中則被列入距離超過100華里的區間,我懷疑是不是將莊前列入了錯誤的區間,要么地名有誤,即不是莊前,而是別的超過100華里的地方。
這個疑似的失誤之外,我比較在意的是溪口,排日賬中提及546次,且距上灣超過100華里。根據222-223頁的說明,可知溪口屬于休寧縣,對程家而言,溪口最重要的意義,一是購買食鹽(既是自家消費,也是營生),二是由此可以前往徽州中東部地區,相當于中轉站。再根據227頁排日賬所見地名歷時性變動表,可知在高峰期(1838-1858年)程家去溪口的頻率為月均2.2次(仍然是較高的頻次)。
其他地名,像婺源北部的重鎮清華,距離上灣有30華里,排日賬中出現763次,書中已作了妥當的解釋:對于沱川一帶鄉村來說,清華承擔了基層市場的功能,程家去往清華,主要是做買賣(221頁)。參照227頁排日賬所見地名歷時性變動表,可知程家在1838-1858年、1872-1885年、1891-1901年前往清華的月均次數分別為1.44、1.59、1.86次。

徽州建筑
另外,“在排日賬中被頻頻提及的地名中,苦竹山高居榜首,總共出現了2600次,比出現頻次排名第二的西坑高出兩倍多”(219頁)。西坑距上灣在10華里以內,出現809次,不難理解;而“苦竹山位于婺源與休寧交界處,距離上灣約有十七八華里的路程,因需翻山越嶺,徒步前往需兩個半至三小時”(143頁)。那么,苦竹山何以高居榜首呢?這是因為程家在那里建了茶園,而后搭建了臨時住宅,再后來建造了更為長期的住所(343、345頁)。有了棲身之地,采摘茶葉、種植玉米就更方便了,苦竹山在排日賬中出現次數如此之高,也就不成其為疑問了。實際上,苦竹山儼然成了程家另一個生活空間(238頁)。
關于程家的活動范圍,書中作了如下說明:
程家從事生產活動的大致范圍,位于以上灣為中心,半徑約二十華里的范圍內。這一范圍可能較我們理解的傳統鄉民的生產空間要大一些,不過若放到當地的生態環境中,這個現象不難理解。由于當地山多地少,單憑耕種水田是無法糊口[的],因此,必須開發、利用村莊周圍的丘陵、山地,種植玉米、茶樹等。……(219頁)
這個解釋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本書卻著意強調程家的行動空間比黃宗智、施堅雅所討論的華北、四川小農的活動空間更大,進而主張:“程家的個案顯示,無論是從生計活動、社會圈子還是儀式活動看,傳統中國鄉民在空間方面都比我們過去認為的更具流動性。……在這種意義上說,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概念,似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傳統中國的鄉民,遠非我們想象的那么‘鄉土’。”(234頁)
可是,在我看來,這個主張有失偏頗,似難成立。就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的概念而言,本書的探討非但不構成挑戰,反而大體上是支持這一概念的。根據217頁表9,粗略統計可知,10華里以內各地點的頻次總和為4439次,再加上苦竹山(考慮到帳篷和長期住所,相當于零距離)的2600次,可以說這基本上就是程家的生活空間(書中對此似不甚措意,而過于強調出遠門的頻次)。實際上,書中明確指出理坑和上灣構成了程家最基本、最核心的生活空間(334頁)。換言之,本書試圖用非日常的“行動空間”去挑戰“鄉土中國”概念下的日常的“生活空間”,似有偷換概念之嫌。比如,在我看來,齊云進香之類的活動就不屬于“日常生活”(當然這涉及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和介定)——“在排日賬有記錄可查的近四十年中,程家家人共進香五次”(347頁),其“非日常性”一目了然,無需多言。
另外,書中強調黃宗智、施堅雅依賴的調查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其所依據的史料可能是“扭曲”的(214、232頁),然而這種說法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實際上,人們同樣可以質疑,本書使用的排日賬在史料上存在諸多不足(30-31、235-237頁),其所呈現的恐怕只是“個案”(234頁)。再則,書中所列的幾點理由(232-233頁),諸如經濟(商業化、區域貿易)、政治(戶籍、賦役制度)、宗教(進香活動)等方面的因素,都有“空對空”之嫌。相反,根據書中的統計數據,程家的日常生活空間基本上在20華里的范圍內。畢竟,在前工業時代,沒有自行車(更別提汽車、火車了),也沒有馬車(徽州山地恐怕不宜騎馬),單靠步行,普通人一天行走8小時,距離一般為60到80華里之間。考慮到往返、天氣、路況等因素,鄉民“日常”的活動范圍頂多30華里左右,也就是書中提到的清華到上灣的距離。換言之,鄉民確有流動的必要性(主要為了謀生),但在出行距離上必有限制(時代條件使然),即鄉民的活動總體上是地方性的(盡管存在地域差異)。
總之,本書通過扎實的統計數據活脫脫地勾畫了鄉土中國的面貌,加深了人們對傳統農村社會的理解。為了寫這篇小文,時隔多年重溫《鄉土中國》,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筆者仍感到“鄉土中國”論的獨特魅力。當然,《鄉土中國》的行文是隨筆式的,有些說法可能會給人武斷之嫌。比如,“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大旱大水,連年兵亂,可以使一部分農民拋井離鄉;即使像抗戰這樣[的]大事件所引起[的]基層人口的流動,我相信還是微乎其微的。”“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一個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變更。一度一年,周而復始。”(《鄉土中國》,《費孝通全集》第六卷,109-110、111、149頁)
這類表述在《鄉土中國》中俯拾皆是,整體而言,我感覺是妥帖、到位的,盡管“孤立的社會圈子”、“安土重遷”可能引起爭議。也許正是在這些細微的表述上,我和本書作者對《鄉土中國》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我看來,“鄉土中國”的鄉民當然會走出村莊,甚至會出遠門,對外界也有好奇心(尤其是青少年時期,“山的那邊是什么地方?”),但他們的人生是有“根”的,長年最經常活動的區域大約就在方圓二三十華里以內,其所面對的基本上是“熟人社會”。而本書作者大概更追求精確,更強調鄉民的流動性,傾向于認為他們見過“世面”,因此主張重審“鄉土中國”。
“生”“活”這兩個關鍵詞之外,本書還蘊藏著非常豐富的內容。比如,“小姓”與大族的關系(277-281頁)、沱川的出臺閣(320-322頁)、理坑的打五猖儀式(338-339頁)、程允亨的涂鴉(376-377、387頁)……單是這些細節,就惹人浮想聯翩。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書中也無法深入探討。
在“導論”中,著者亮明了本書的敘事策略,即以鄉民的生命歷程為經,生活世界為緯,具體而言,一方面試圖再現鄉民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舉凡生計活動、物質文化、人際關系、儀式實踐、時空觀念、讀寫能力、政治體驗等,另一方面,將鄉民的生命歷程置于十九世紀的歷史事件中加以探討(23頁)。這充分反映了著者的治學抱負,從詳實、細膩、嚴謹的討論中也可管窺其精湛的史學技藝。但綜覽全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仍屬生計方面的描述和分析,其他方面則不免意猶未盡(有些議題如讀寫能力,別有意義),而這基本上可以歸因于材料——作為史料的排日賬存在莫大的缺陷,因此,非史家不能也,實在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盡管如此,單憑書中詳確的數據和五花八門的表格(大概我是所讀歷史著作中表格最多者——這背后無疑凝聚著著者的無量心血),及其所蘊含的精義(值得社會經濟史專家研討),本書無愧為一部“充實而有光輝”的匠人之作。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