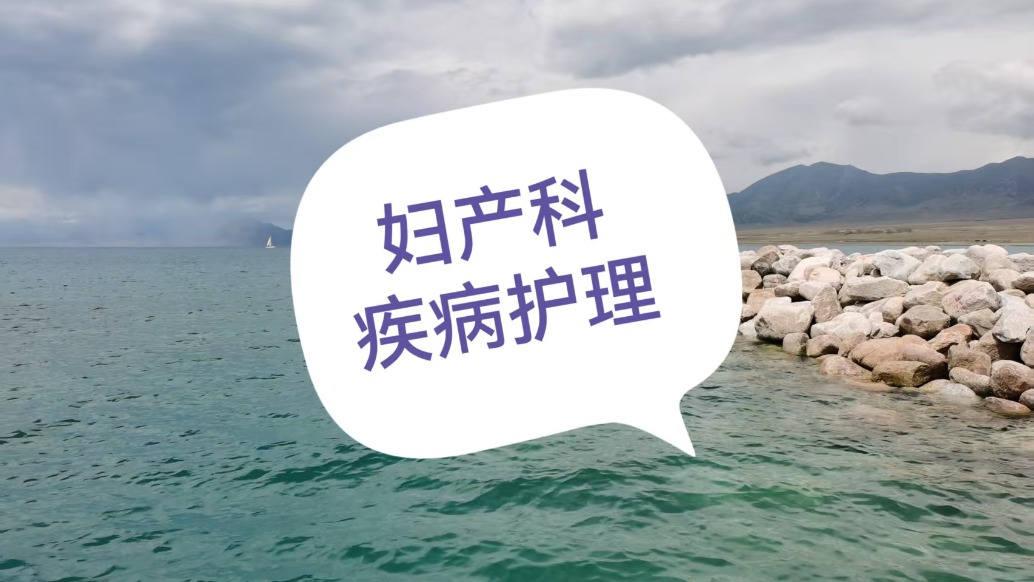- 53
- +1689
在蛋殼上動刀的男人
在袁家釗眼里,每只雞蛋都是獨一無二的,有不同的形態、顏色、手感,就像人的臉,富有生命力。
一個脆弱易碎的蛋殼,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一個可以包羅萬象的“乾坤”。
今年63歲的袁家釗是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淞南蛋雕技藝”的唯一傳承人,他的蛋雕作品曾代表上海搬上世博會的展覽臺。
榮耀背后,是所謂“玩了一輩子”的功夫。40年來,袁家釗的夜晚大多是和蛋殼一起度過的。
方形寫字桌上一個紙箱操作臺,里面擺放著五把刻刀、一只鉛筆、一根牙刷和打磨用的橡皮。扎著一頭長發的袁家釗拿起刻刀,左手握蛋,神情肅穆。燈光打在蛋殼上,袁家釗沿著鉛筆線條,緩慢地將黃色的蛋殼刻出白色的紋路。
工作室寂靜無聲,只有刻刀和蛋殼的摩擦聲在窸窣作響。

專注雕刻的袁家釗。受訪者供圖
“蛋殼怎么會不碎?”
1980年,在上海手帕廠工作的袁家釗到大連出差。他在火車站門口拿著地圖張望時,發現一位體格結實的中年貨郎坐在小凳上,正在雞蛋殼上刻畫著什么。他一下被眼前的新鮮事物所吸引,路也不問了,就盯著貨郎的手看。
蛋殼一碰就碎,怎么會不碎呢?他感到既神奇又納悶,也不敢問,在旁邊默默看了一下午,一直看到太陽下山,車站沒人,貨郎也要回家了,問他:“小伙子,看夠了沒有?”他才回過神來:“能不能教教我?”
貨郎答應了,拿給他五個蛋殼和一把小刻刀,讓他試試。結果一刻就破,五個蛋殼全壞了。
第二天,貨郎師傅又來了,告訴他握蛋的正確手法,左右手怎么配合,刀怎么移動,然后又給了他五個蛋殼。
按照師傅的技法開始練,果然就不“壞”蛋了。他在大連待了6天,便刻了6天的蛋。
熟練之后,袁家釗就開始發揮“小聰明”了。他覺得師傅將字體設計得太大,雖然易刻,但欣賞性欠佳。他壓縮了字體的大小,將一個“和”字陰刻成白色,并在外圍刻了兩個顏色較淺的圓作為點綴,無論從哪一面看,都能看到字的全貌。
貨郎見到袁家釗改良后的作品,滿意地點點頭。

袁家釗蛋雕作品“手拉手”。馮佳倩 圖
從大連回上海后,袁家釗繼續磨練技藝,慢慢嘗試各種花樣,還花了兩年時間研究蛋殼上的色彩。起初他因為緊張,雙手一直繃著,不敢過于用力,使得手腕經常酸疼。手被劃傷了,他拿布隨意包扎止血,忍著痛繼續刻,至今他的左手上還殘留著大大小小的疤痕。
蛋雕需要全神貫注,稍一分神,也許就前功盡棄了。但他喜歡的恰恰是這種微妙的刺激感。有次弄堂里的孩子在袁家釗房間外打架,吵得雞飛狗跳,但別人問起來,他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深夜是他最好的雕刻時間。早年間,母親曾生病臥床十個月,他徹夜守在一旁,安靜地刻蛋殼。每當母親發出疼痛的呻吟,他正在用勁的手就會一抖,蛋殼就壞了。幾年前,他習慣早上睡覺,晚上雕刻,常常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一眨眼就凌晨四點了。
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家人購買雞蛋的數量有限,用完了自家的蛋殼,袁家釗就去問鄰居要。“只要是蛋,我都討來雕。”
雕刻前,他將麥稈伸進蛋殼表面的開孔中,吹出蛋黃和蛋清,“這下子吃不到水煮蛋和荷包蛋咯!”他打趣說,從此家里只能吃炒蛋、燉蛋、蛋花湯。
實現購蛋自由后,他每周在市場里挑蛋,一挑就是幾個小時,大的、光滑的、顏色深的、蛋殼厚的、沒有黑點的……一籮筐的雞蛋一個個地挑,為此他會多給點錢。
早期,他雕刻的圖案較簡單,像十二生肖,一兩天就能完成。后來,他試著將其他工藝的手法運用到蛋雕上,例如竹雕的留青、玉雕的薄意,加上設計的時間,完成一個作品要好幾個月。
這難不到他,對于喜歡的事物,袁家釗向來有足夠的耐心。

疫情期間,袁家釗花了一周完成的作品“齊心協力抗疫情”。馮佳倩 圖
在平凡的人生里追尋美
不同于其他匠人,袁家釗并不靠蛋雕謀生。蛋雕只是他用來抵抗孤獨、打發時間的一個業余愛好。
袁家釗的父親是一名賬房先生。“文革”時,因家庭成分不好,弄堂里的孩子總是排擠他。一次玩游戲,同伴拒絕將獎品給勝利的袁家釗,兩人爭吵著打了起來。對方父母來到袁家,不停地指責他。
為了少讓他在外面玩耍,父親要求他在家里練書法。年少的他靜不下心,總是趕在父親下班前隨便寫幾個字應付,也曾質問父親:“人家都不學,我學干嘛?”父親說:“任何時候,人都是要有文化的。”
學習書法后,他漸漸對繪畫、竹雕也產生了興趣。雕竹的刻刀是自制的。他撿來別人不要的鋼條,蹲在水泥地上磨,蹲累了,就站著在水泥墻上磨,烈日炎炎的一個又一個下午,他磨出了各種形狀的刻刀。
1999年,工作的服裝廠倒閉了。他想著憑手藝吃飯,開過裁縫鋪、理發店,還曾想過開飯店。但他似乎缺乏做生意的天賦,開的店都沒有存活多久就關門了。
五十多歲時,他還去應聘過理發店,對方說“這么大年紀還來干什么”。后來他干脆待在家里,照顧身體不好的母親,做起了家庭煮男,跟著電視學廚藝,每天想著怎么把菜做好吃、好看。
好看很重要,袁家釗是一個愛美的人。不管是做衣服、理發,還是玩蛋雕,他都追求一種有特色的、不落俗的美。他留長發,穿花襯衫,越時髦越好。同齡人說不敢這樣打扮,怕被人罵,他說,穿什么是我的自由,誰說老頭就沒人看?

袁家釗在淞南文化中心的工作室雕刻。馮佳倩 圖
2007年,臨近退休的妻子開始到虹口公園打太極,看他天天在家里雕蛋,便建議他去公園擺攤,“你既然這么喜歡,就把它推出去,讓人家看到,蛋殼可以雕刻。”
第二天一早,袁家釗帶上蛋殼和工具,去了公園。剛開始他有些怯場,一個人坐在長椅上,一動不動,“像偷東西一樣”。坐了一會,他才慢慢拿出刻刀和雞蛋,開始“表演”。他不敢看人,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在看他,也不敢去聽別人說話,怕刻壞了當眾出丑。半天過去,蛋沒刻成,出了一手的汗。
之后他每天都去,鍛煉了兩周,開始聽別人問話,諸如“這個蛋是熟的生的”之類的簡單問題。一個月后,可以邊刻邊回答,也開始有人買,每個20-50元。那時候,有一些熟人笑話他:“你這個東西拿出去,人家排隊搶的咯!”
時間長了,他漸漸被周圍人熟知。因為蛋雕在俄羅斯比較有名,附近外國語大學的俄語老師成了他的常客,定價50元,他們會給100元。這給袁家釗了信心,“我這個東西還能值一百?”
有位70多歲的老人看過他的蛋雕作品后,曾斷言他不出兩年就不會來這里了。袁家釗感覺像是遇到了伯樂,偷偷刻了一個兔子送給老人。
事情果真如老人所料。買的人越來越多,他來不及做,13個月后就不去了。
2008年,袁家釗搬到了淞南。他去居委會幫母親辦老年卡,看到門口的黑板上寫著要舉辦家庭手工大賽。他就問工作人員,蛋雕可以參加嗎?
“什么蛋雕?”對方不知道,也聽不懂解釋。他趕緊回家把“福娃”“鳥巢”“水立方”“熊貓”幾個作品拿過來。對方一看,忍不住驚呼:“天吶!這是真的假的?”最終居民全票通過,拿了一等獎。
之后,他參加了世博會民間工藝品選拔,交了15個作品上去,兩年后還給他11個,另外4個名為“上海風光”的作品入選了。
從事專業攝影的兒子替他高興:“你終于出頭了。”兒子從小看他刻蛋殼,從沒想過這是個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藝術品。
袁家釗驕傲極了,在QQ上跟朋友們大肆炫耀,覺得自己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光榮,“不是代表我自己,是代表上海。”
在世博會現場,袁家釗目不轉睛地看著自己的作品,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自己第一次看見貨郎雕蛋的樣子。

袁家釗在展覽會上向觀眾講解作品。受訪者供圖
傳承的困境
袁家釗說,他做蛋雕就是玩,玩了一輩子。沒想到玩出了名堂,成了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淞南蛋雕技藝”的傳承人。這項非遺技藝,目前上海僅有他一人。
談及此,袁家釗原本平和的語氣有些波動。他苦于至今仍未找到與他并肩作戰的傳承人。
早些年,他拒絕收徒。因為這門手藝很枯燥,他怕徒弟耐不住寂寞,學到一半就放棄。也有人來問他,“學蛋雕多長時間能賺錢?”他反感地回懟:“一想到錢,你就不要來學了!”
2012年,袁家釗開始在淞南文化中心普及蛋雕,免費授課,“不可能收費,收了就沒人來了。”
在他看來,學生和徒弟并不同。老師只能教學生入門的技巧,而徒弟要繼承師傅的衣缽。
袁家釗曾經被兩名徒弟傷過心。一位上海徒弟學了幾年后,為了自己獨立申請到非遺項目,離開袁家釗拜了外地師傅;另一位來自廣州,學了十年,因為廣州申請非遺需師從本地師傅,最后也不認他這個師傅了。

袁家釗正在教授學生。受訪者供圖
目前,國內不少省市都將蛋雕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也有許多人專職從事蛋雕藝術。袁家釗認為,蛋雕入門很簡單,但要制作出讓人欣賞的作品,則需要更漫長的磨練與忍耐。
“急功近利的人總比靜下心來的人多。”他無奈地搖了搖頭。
他現在只收了一名六年級的小徒弟,擔心隨著徒弟學業壓力增大,孩子會中途放棄,所有的努力又付之東流。他患有糖尿病,也擔心自己因為并發癥倒下,心愛的這門手藝將無人繼承。
他愿意將技術毫無保留地拿出來,但比起技術本身,他更重視賦予作品的文化內涵。
比如他耗時六個半月完成的“山河錦繡”,蛋殼上設計了四個屏風,有大江、云霧、高山,連接屏風的是象征長久的蝴蝶扣。如果將蛋殼自右向左轉動,可以看到太陽東升西落,永不停歇,寓意亙古不變的中國風光。

袁家釗作品“山河錦繡”。馮佳倩 圖
疫情期間,他還記錄下了淞南防疫的場景:防控員在路口測量體溫,志愿者在街道噴灑消毒水。蛋殼頂部是一面黨旗,將它放在轉盤上旋轉時,旗幟上的鐮刀就如旋風一般,象征著張文宏那句風靡全國的金句:“共產黨員先上”。
這些在一個又一個夜晚、費盡巧思孕育出來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
又一個夜幕降臨,袁家釗關掉工作室的燈光,輕輕合上門,和一個個精雕細琢的“孩子們”說了聲:“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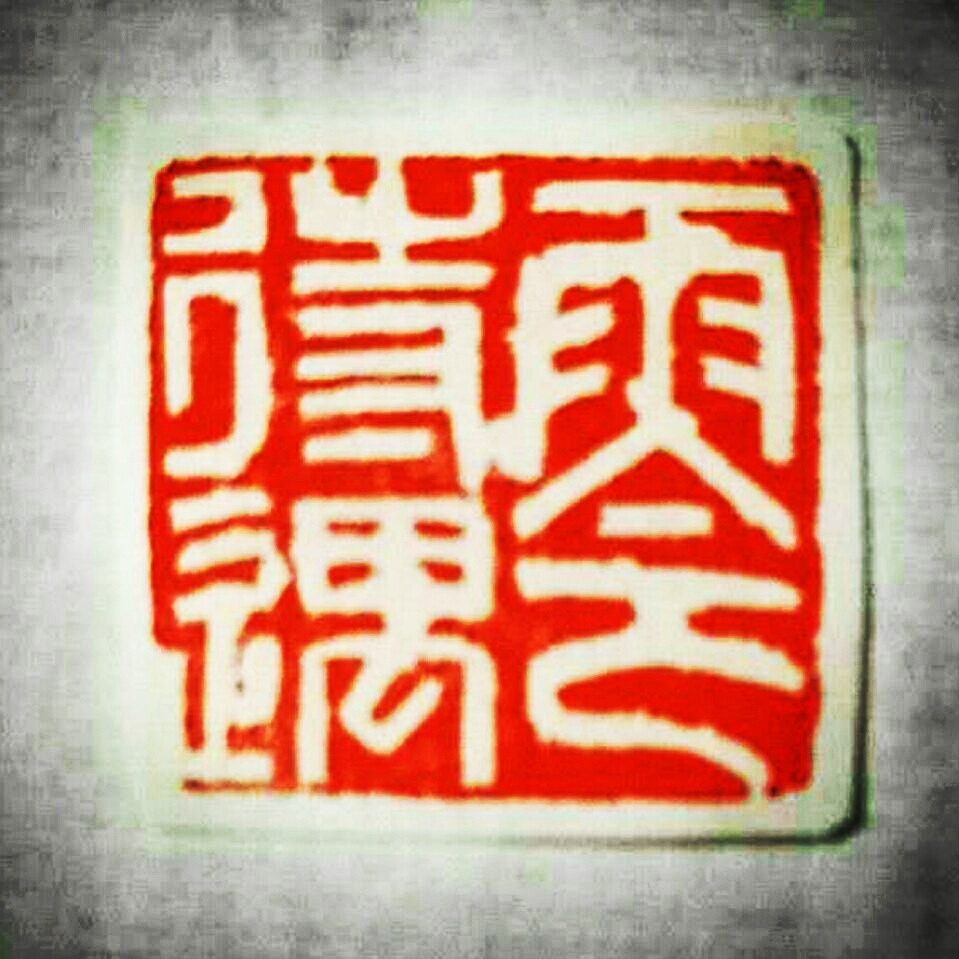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