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4
- +199
減稅與簡稅|增值稅減稅:謹防減收的風險
2019年是“減稅年”,與以往的歷次減稅相比,今年的減稅有兩個主要區別:一是“大規模”,甚至是“更大規模”,這說的是減稅一定會帶來減收的,往年的減收更多的是潛在收入下降,而實際的財稅收入依然是增長的,今年部分地區可能出現實際收入的下降;二是減稅重點集中在增值稅,增值稅是中國的第一大稅種,占全部稅收收入的40%,與其他稅種不同的是,增值稅的征收率一直很高,地方上很難通過強化征管的方式來對沖法定稅率的下調,這種減稅很容易落到實處。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為了配合這兩年的增值稅減稅,相關財稅部門頻繁下發了很多落實減稅的文件,例如2018年9月的《關于進一步落實好簡政減稅降負措施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2019年4月4日的《關于堅決查處第三方涉稅服務借減稅降費巧立名目亂收費行為的通知》,4月17日的《關于進一步做好減稅降費政策落實工作的通知》。需要通過文件的形式反復落實的,說明減稅也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輕松。
接下來,我們可以梳理一下減稅帶來的風險,從而更容易理解當下的政策,以及對風險有一個合理的預期和防范。
減了誰的收入
以2019年為例,全年的減稅降費規模為20000億,其中增值稅減稅8000億、個稅減稅4000億、小微企業減稅2000億、社保減費3000億、行政和涉企收費減少3000億,減稅占全部規模的70%,依然是減稅降費的重頭戲。這些數據是從企業層面計算的,并不能直接對應到哪一級政府的財政收入。
中國主要稅種的收入都是在政府間分成的,例如增值稅收入,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各50%,個稅的中央比重為60%,社保幾乎全是地方收入。按照現有的財政收入分成規則,20000億的減稅降費規模中,我們可以推算一下,其中屬于中央財政承擔的為8000億左右,屬于地方財政承擔的大約為12000億,即地方財政承擔了大約60%減稅降費任務。因此,地方政府對減稅降費政策的支持,是政策能否“落地”的關鍵。
另一方面,中國的稅收收入中的地區間分布是不平均的,這意味著減稅任務在地區間也存在巨大差異。以增值稅為例,廣東省的增值稅占全國的比重最高,達到13.7%,再加上其他5個東部省市(江蘇、浙江、上海、山東、北京),這6個地方的增值稅占全國的比重超過一半。考慮到這次增值稅稅率是分檔次下調,即制造業下調3個點、交通運輸、建筑業等下調1個點、服務業不變。因此,在同樣增值稅收入的地區,產業結構也會直接影響到收入減少的幅度。我們據此做了一個簡單的測算,廣東省的減稅占全國的比重為14.7%,實際上要高于其現有的增值稅收入占比,同樣的還有江蘇;不過,北京卻完全相反,其增值稅占比為6.2%,減稅占比僅有3.6%,這是因為北京的增值稅主要來自于服務業,服務業的基準稅率并沒有下調。
因此,減稅的政策效果,不僅僅取決于地方政府的支持,更取決于發達地方的支持。在以往年份,這些發達地區往往是對中央財政做“凈貢獻”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減收也可能影響到中央實際財力的盈余。
“落地”的風險
關于減稅的減收效應,財政學上有一個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定理。即減稅、控制債務風險、積極財政支出,這三個目標不能同時達到,當政策錨定在減稅和增加財政支出時,收支缺口就擴大了,需要通過發債來補缺口,此時的債務風險就加大了;當需要控制債務風險和減稅時,政府收入端就減少了,此時就無法增加財政支出;當控制了債務風險和增加財政支出時,就需要增加政府稅收收入,此時就無法減稅。
今年減稅政策的落地,實際上就是在這“三角”中做好平衡。現實中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國的地方財政長期采用彈性征收制度,在國地稅分設的時候,往往是地方政府先定當年的財政收入增速目標,然后把稅收目標作為任務下達給稅務部門,上級稅務部門再層層分解到基層征管部門,因此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包稅制”的現象非常常見。在“包稅制”的框架下,減稅的效應完全依賴于稅收任務的調整。今年的減稅政策是在全國“兩會”宣布的,但是地方的預算收入目標是在地方“兩會”確定的,后者是早于前者的,如果不調整地方預算收入目標,基層稅務部門將面臨非常尷尬的局面,但是調整地方預算目標又不是那么容易。
因此,第一個“落地”風險,是地方強化其他稅種的征管,來對沖增值稅的減收效應。與所有企業相關的稅種,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兩個大稅種,前者占全國稅收收入的40%,后者占22%,增值稅的征管彈性較小,企業所得稅的征管彈性非常大。稅務部門在核算企業的收入、成本和費用過程中,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權。從這些年的稅種收入占比也能看出這個特征,自2010年以來,企業所得稅的占比由17%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22%,而同期的三大流轉稅占比則從52.3%下降至48.8%。
第二個“落地”風險,是地方用“費”替代“稅”。最近幾年來,財政部門一直對財政收入的“質量”進行考核,實際上也就是稅收在一般預算收入中的占比,這個比重越高,說明地方對“非稅收入”的依賴度越小,企業的納稅環境更加透明、公正。但是對地方財政來說,費和稅都是地方財政收入的構成,一旦地方收入銳減,地方收支壓力加大,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過收費的形式把減收的部分彌補回來,在現有的框架下,這些收費同樣也是合法合規的。我們可以回顧一下2018年各月份的收入變化,會發現1-9月份稅收增速為正,此時的非稅增速為負,10-12月份的稅收增速為負,非稅增速就為正了,從趨勢來說,非稅收入對沖了稅收收入的變化。
減收的風險
解決了減稅政策的“落地”風險之后,也就意味著減稅能夠落到實處,從財政收入變化的角度,也就是會直接體現在財稅收入的減少。減收之后,同樣會產生一些風險,這些風險同樣需要提早預防。
第一個減收的風險,是部分地方財政收入的失速。減稅帶來的減收,如果只是收入增速的下降,而不是絕對規模的下降,所帶來的收支壓力還相對較小。從現有的減稅力度來看,全國層面的財政收入增速會放緩,不過加總層面的數據會掩蓋一些特殊地區的風險。以2016年為例,當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增速為4.5%,具體到各地區,則非常懸殊,其中上海的增速高達16%,陜西和青海則出現了-11%的大幅度減少。今年一季度的財政數據已經有所體現,以上海市為例,今年一季度的收入增速為3.3%,2018年同期增速為6.2%,這還主要是2018年1個點的增值稅減稅和個稅減稅,不包括4月份才開始的大規模增值稅減稅。此次的減稅對增值稅收入的沖擊較大,一些地區特別依賴于16%檔次稅率的增值稅,同時產業結構非常單一,其財政收入有可能出現失速,甚至是減收的風險。
第二個減收的風險,是地方的減支風險。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或者說收入規模下降,必然要求對支出規模進行壓縮,換句話說,財政支出的壓縮是減稅政策落到實處的基礎。相對于收入減少來說,支出壓縮的難度更大,原因在于我們非常清楚從哪里減少收入,卻無法判斷從哪里壓縮支出。財政學理論上經典的尼斯塔克模型,闡述的就是各領域支出規模的膨脹,其支出規模會遠遠超過合理的水平。減支的過程最忌“一刀切”的指標式壓縮,這會使得一些經費緊張的部門難以運轉,影響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因此,減支一定要配合支出結構的優化,這需要高水平的科學決策和管理藝術。
第三個減收的風險,是基層財政的壓力加大。中國現有的稅收分成,在中央財政和省財政之間有清晰、確定的規則,但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之間,則沒有統一的規則,并且經常調整。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往往可以利用其行政級別優勢,制定出有利于自身的財政分成規則。當地方財政收入增速下降,甚至是收入減少時,上級政府就會對財政分成規則重新調整,通過財政集中的方式擠壓基層財力。近十來年,中央財政一直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對基層財政進行“輸血”,但是地方政府分成規則的策略性調整,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央財政的作用。
綜上,一個大國的財政是非常復雜的,涉及不同層級政府、不同地區政府,而這些政府主體之間的差異又非常巨大,任何一個政策的調整,都會帶來一系列的衍生反應。減稅政策是提振實體經濟信心的重要舉措,為了最大程度發揮減稅政策的杠桿效應,就需要對潛在風險備足預案,確保減稅政策既能“落地”,又能“生根”。
(作者范子英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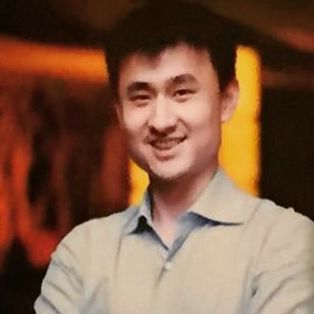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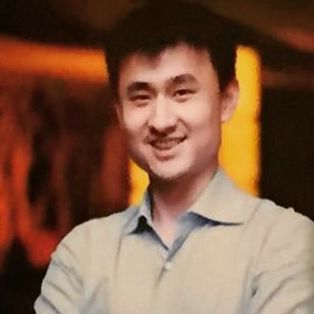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