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與教條化趨勢分流: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下)
【編者的話】
《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20年第5期刊發(fā)了一組重要的文章,包括《陳翰笙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以及兩篇譯文。《無錫的土地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前途》譯自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書記處研究員編選、翻譯的《農(nóng)村中國: 中國作者文獻選編》一書中第2章“上海附近無錫的土地集中”。《土地所有權(quán)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來源于由范世濤譯自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書記處研究員編選、翻譯的《農(nóng)村中國:中國作者文獻選編》第6章“土地所有權(quán)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
這是國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薛暮橋年譜》項目成果之一。作者范世濤曾為哈佛大學(xué)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xué)者,現(xiàn)任北京師范大學(xué)經(jīng)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lǐng)域在現(xiàn)代中國經(jīng)濟史、比較制度分析。
陳翰笙領(lǐng)導(dǎo)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始于1929年,終于1933年,在學(xué)界享有盛譽,但也歧說紛紜,撲朔迷離。作者綜合使用國立中央研究院官方出版物、哥倫比亞大學(xué)珍本圖書館特藏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檔案以及陳翰笙、王寅生未刊稿,對陳翰笙主持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過程、理論準(zhǔn)備和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報告。
文章提到,1935年紐約《太平洋事務(wù)》季刊發(fā)表伊羅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長篇論文,稱陳翰笙為“中國最有能力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者”。陳翰笙本人在評論關(guān)于中國和日本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時,坦率地指出俄語研究文獻在提供數(shù)據(jù)方面“毫無意義”。這是對蘇聯(lián)1930年代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經(jīng)濟經(jīng)驗研究(包括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衰落的權(quán)威評論,也是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研究教條化的一個側(cè)面。
“陳翰笙以理論結(jié)合實際的經(jīng)驗調(diào)查方法回應(yīng)重大問題,與同期莫斯科趨于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研究形成范式分流,進而導(dǎo)致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的中心從莫斯科轉(zhuǎn)移到上海。不僅如此,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等當(dāng)事人在參加陳翰笙主持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過程中建立起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能力,這種能力直到改革開放年代仍在發(fā)揮作用。”
原文近25000字,分五個部分,包括:“問題的提出”“從莫斯科辯論到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陳翰笙主持中研院無錫調(diào)查”“從馬季亞爾到列寧、考茨基:數(shù)據(jù)整理過程中的理論準(zhǔn)備”“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范式之建立:以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為基礎(chǔ)的成果”“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研究的范式分流和研究中心轉(zhuǎn)移”。
我們摘編在此,分享給朋友們,此為報告下篇,上篇詳見鏈接。
找到“無法找到的報告”
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和報告起草過程歷時甚久,研究報告也未盡及時發(fā)表。當(dāng)事人回憶調(diào)查成果時集中于當(dāng)時未發(fā)表、后來未找到的一份,以致學(xué)界普遍誤會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只完成一份報告,而這份報告也已經(jīng)無法找到。事實上,以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為基礎(chǔ)完成的報告并非只有一份,過去認(rèn)為無法找到的報告,借助考證技術(shù),也可以發(fā)現(xiàn)主要內(nèi)容已經(jīng)披露于英語文獻中。為全面認(rèn)識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有必要整理一下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系列成果。
秦柳方、錢俊瑞合寫《黃巷經(jīng)濟調(diào)查統(tǒng)計:本項調(diào)查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團調(diào)查材料之一部分》、廖凱聲《無錫農(nóng)村調(diào)查記略》和韋健雄《無錫三個村底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調(diào)查》,均為理解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必讀參考文獻。除這三篇文章之外,無錫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為如下五、六種作品:
(一)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社會學(xué)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1930)
此文最初刊于《國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總報告》,是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1929—1930年度報告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份工作報告中的社會學(xué)組部分不久單獨成冊,并冠以“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書名。
從《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看,1929年7月至1930年6月間陳翰笙主持的社會學(xué)組研究工作并不僅僅聚焦于農(nóng)村,都市也處于突出的研究位置,甚至一度較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更為優(yōu)先。在調(diào)查都市社會時,社會學(xué)組“首先從上海工人生活狀況之調(diào)查著手”。1929年9月至1930年2月,社會學(xué)組在上海楊樹浦區(qū)調(diào)查全部530家工廠中的474家,實際調(diào)查人員42人,調(diào)查規(guī)模和延續(xù)時間并不比1929年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遜色。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紗廠絲廠女工包身制度之盛行,實為現(xiàn)代勞動雇傭制度在中國特有之征象。”從收集的工人家書看,“雖喘息絞汗于工廠機器行間,精神上仍不免鄉(xiāng)間親屬之牽累”。目前尚不清楚此次楊樹浦調(diào)查與上海工人運動之間的關(guān)系,但對1925年爆發(fā)過五卅運動、1926—1927年曾發(fā)生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上海來說,楊樹浦調(diào)查在政治上高度敏感,引起了“反動派對我們的注意”“要調(diào)查我的背景”。在這種情況下,兼任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所長的蔡元培勸陳翰笙改變方向,多做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十九年度報告》“下年度研究計劃大綱”部分明確表示,“下年度本組專門從事于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之調(diào)查與研究”“本年度楊樹浦調(diào)查所得材料,則請本所經(jīng)濟學(xué)組計劃整理”。
因此,陳翰笙所領(lǐng)導(dǎo)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社會學(xué)組雖然最先開展的實地調(diào)查是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但主要聚焦于中國農(nóng)村研究是特殊政治局勢下接受蔡元培勸說的結(jié)果,而不是最初的研究設(shè)計。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原為覆蓋城鄉(xiāng)的經(jīng)濟調(diào)查有機組成部分,在客觀條件限制下才成為中國經(jīng)濟研究的首要重點。
為什么社會學(xué)組工作報告標(biāo)題為“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陳翰笙在報告中說,“構(gòu)成今日中國社會之經(jīng)濟的事實,大都屬于資本主義制度發(fā)達以前之種種關(guān)系。吾人所謂都市,其性質(zhì)不似City;吾人所謂鄉(xiāng)村,其性質(zhì)不似Country。即與歐洲前資本主義社會相較,都市之來歷非Polis及Compagna Communis 可比;鄉(xiāng)村之組織亦非Mir及Manor可比。”這可以看作“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的綱領(lǐng)性解釋和說明。其要點在于并不采用英美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學(xué)通行的以農(nóng)戶如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一樣行動的經(jīng)濟主體假設(shè),而是在社會經(jīng)濟史跨國比較的宏大綱領(lǐng)之下觀察和報告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吸收了馬季亞爾對中國政府統(tǒng)計的尖銳批評,也與馬季亞爾強調(diào)的分區(qū)域研究中國農(nóng)村思想一致,強調(diào)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勢必分區(qū)進行”。不過,報告認(rèn)為關(guān)于劃分區(qū)域的標(biāo)準(zhǔn)知識“現(xiàn)尚缺乏”“不得已只能先從農(nóng)村經(jīng)濟顯然特殊之地方著手調(diào)查”。報告列舉了無錫的特殊之處,并就實地調(diào)查所發(fā)現(xiàn)的復(fù)雜度量衡、田權(quán)關(guān)系加以介紹。
陳翰笙與薛暮橋、馮和法在20世紀(jì)八十年代合編的《解放前的中國農(nóng)村》第二輯專門收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會員作品,《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之發(fā)軔》置于全書之首,表明此文的綱領(lǐng)性地位。關(guān)于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指導(dǎo)思想和最初成果,提綱挈領(lǐng)的總體解釋和說明均包括在這一論著中。
(二)陳翰笙、王寅生、張輔良、廖凱聲、張稼夫、李澄、徐燮均著《畝的差異(無錫22村稻田的173種大小不同的畝)》(1929)
此書(以下簡稱《畝的差異》)被列為“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集刊第一號”。
《畝的差異》共計7位作者,除陳翰笙和王寅生外,另外5位均為1929年無錫調(diào)查后中研院正式聘任的調(diào)查員,張輔良還在1930年4月被改聘為助理員。這7位作者顯然是1929年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資料初期整理工作的主要人員。
陳翰笙晚年回憶,無錫和保定的調(diào)查資料,“由王寅生、錢俊瑞、廖凱聲和我以及其他三人整理”;秦柳方沿用此說,稱無錫調(diào)查告一段落后,“這些材料由陳翰笙、王寅生、錢俊瑞、廖凱聲等7人整理”。上述回憶并不準(zhǔn)確。原因是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資料整理工作歷時甚久,工作人員并不穩(wěn)定,有人中途退出,有人中途加入,前后參加調(diào)查資料整理的人員也就大大超過7人。在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間,《畝的差異》7位作者中的3位(張輔良、廖凱聲、李澄)先后去職;1930年9月至1931年2月,錢俊瑞、張錫昌、薛品軒、瞿明宙、石凱福陸續(xù)被聘任為調(diào)查員。陳翰笙在論文中還曾引用劉懷溥、劉端生整理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統(tǒng)計表格,可以確定他們參加了無錫調(diào)查資料整理工作。即使不考慮其他人員,僅上述調(diào)查資料整理者已有14人之多,比陳翰笙、秦柳方所回憶的資料整理人數(shù)整整多出一倍。
除了作者署名,《畝的差異》的主題和內(nèi)容同樣值得討論。“畝的差異”是馬季亞爾在《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第一章開篇所提出的問題,他說“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統(tǒng)計對于各種材料都不正確。關(guān)于耕地的面積,城市人口與鄉(xiāng)村人口的比例,收獲量的多少,每畝的面積有多少,這些材料都各自不同。”可以想見,1928年陳翰笙讀到《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征求意見稿時,這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因而“畝的差異”成為無錫調(diào)查的基本內(nèi)容,也是資料整理首先處理的問題。
《畝的差異》開創(chuàng)性地對22個調(diào)查村1204戶的農(nóng)田田塊逐塊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無錫所謂的畝大小不同至少有173種,同一個村畝的差異至少有5種。報告認(rèn)為,“工業(yè)資本主義沒有發(fā)展的中國本不能有統(tǒng)一的度量衡,并且積受了數(shù)千年分家、租佃、典押、買賣等習(xí)俗的影響,到現(xiàn)在差不多每一農(nóng)戶所謂畝也就都有兩三種的大小。”這“使浮征稅捐的種種弊端更加厲害,同時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由于畝的差異因素,無錫調(diào)查資料整理的第一步就是先折合各村戶調(diào)查表中的畝為統(tǒng)一的度量衡,這必然是繁重的計算工作。
《畝的差異》報告的事實扎實有力,至今仍可以提醒學(xué)者嚴(yán)肅對待數(shù)字的含義,用陳翰笙的話說,“茍所有地與使用地之實際面積不求真確,則與土地有聯(lián)帶關(guān)系之各項農(nóng)村經(jīng)濟統(tǒng)計,均將全部動搖矣!”
(三)余霖《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1932)
“余霖”是薛暮橋常用筆名之一。該文發(fā)表于蕭淑宇主編《新創(chuàng)造》第2卷第1、2期合刊“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專號”。
薛暮橋原為江蘇省立南京民眾教育館主編《民眾周報》的編輯員,1932年初應(yīng)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同學(xué)王寅生、錢俊瑞、張錫昌來信邀請,到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參加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資料整理工作。4月底,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遷往南京,編制縮小,薛暮橋作為辦公費支薪的編外人員被裁減,但仍與王寅生等一起到南京。為維持生活,“陳翰笙教我學(xué)寫文章”,回家鄉(xiāng)無錫禮社鎮(zhèn)調(diào)查后完成報告,陳翰笙加標(biāo)題“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后,送《新創(chuàng)造》雜志發(fā)表。因此,這是薛暮橋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不支薪的情況下由陳翰笙指導(dǎo)完成的作品。
薛暮橋自述回家鄉(xiāng)調(diào)查一個月,但陳洪進以含蓄方式談及此次調(diào)查時,稱調(diào)查時間只有“不到一個星期”,說薛暮橋“久離家鄉(xiāng),有次偶然重返故里,親戚好友,都少不得洗塵款待,登門拜訪,閑話麻桑,不到一星期的工夫,他已經(jīng)把這個村莊幾年來的變化,弄得清清楚楚,在一個刊物上發(fā)表一篇極詳細的文章,把這個中國農(nóng)村的細胞做了一次標(biāo)本式的考察,誰也看不出這會是利用一星期的時間有計劃的發(fā)問,有計劃的記錄的成績。”這樣看,薛暮橋的調(diào)查為時不長,是回鄉(xiāng)后有意識發(fā)問和記錄,然后整理成報告的。這與陳翰笙和王寅生1929年主持實施的無錫農(nóng)村調(diào)查方法明顯不同。
薛暮橋禮社調(diào)查正值麥?zhǔn)臁凹丛谀壳啊钡那帱S不接時間,江南農(nóng)村的貧困達于極點。據(jù)當(dāng)時報道,無錫桑田掘去十分之七,“這出產(chǎn)絲的地方從此后怕不能再有上絲的出產(chǎn)”“而現(xiàn)在將到割麥的時候,壯丁們都餓得在床上睡,眼看著麥蟲吃麥穗;稻田正等著車水,又有誰去做?”而政府仍在催收錢糧,結(jié)果出現(xiàn)了無錫搶米風(fēng)潮。在此背景下,禮社調(diào)查記述了鎮(zhèn)上地主挾其經(jīng)濟上及政治上的優(yōu)勢地位凌駕農(nóng)民之上的種種情形;認(rèn)為自足經(jīng)濟迅速破壞,都市工業(yè)品長驅(qū)直入,家庭手工業(yè)首當(dāng)其沖,都市高利貸資本假手鄉(xiāng)村地主侵入農(nóng)村;“農(nóng)村經(jīng)濟之恢復(fù),已非空言改良所能奏效也。茍非有絕大之決心,行徹底之轉(zhuǎn)變,決不能挽此厄運也。”報告篇幅不長,但涵蓋了人口、宗族、地主、農(nóng)民、租佃、行政、黨部、商團、農(nóng)會、教育、田賦、稅捐、家庭手工業(yè)、階級、革命等宏大主題在江南村莊的實際情況,是一份精要的中國經(jīng)濟史文獻,也反映了以陳翰笙為首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者對江南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基本看法,其中關(guān)于宗族的格外重視間接體現(xiàn)出陳翰笙與馬季亞爾共同的關(guān)切。
《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是薛暮橋完成的第一篇經(jīng)濟學(xué)專業(yè)作品。文章發(fā)表時,張錫昌以筆名“李作周”在同一期《新創(chuàng)造》雜志發(fā)表論文《中國底田賦與農(nóng)民》,其中談到“無錫西北鄉(xiāng)小小的一個禮社鎮(zhèn),三四年來積欠的田賦居然在3000元以上,積欠的原因也是地主‘抗不完糧’”。這顯然也來自薛暮橋禮社調(diào)查。《江南農(nóng)村經(jīng)濟衰落的一個縮影》發(fā)表后,馮和法將其收入《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一書,但刪除了標(biāo)題和末尾一段。這篇文章還被日本《改造》雜志譯載,薛暮橋在上海的內(nèi)山書店發(fā)現(xiàn)時“真是又驚又喜”。
《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吸收了陳翰笙、王寅生等人在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和資料整理時積累的經(jīng)驗,但調(diào)查方法更為靈活簡便,形成一種薛暮橋稱為“農(nóng)村通訊”的調(diào)查報告形式。“過去許多學(xué)術(shù)機關(guān)的調(diào)查,往往動員許多人馬,抱著一大堆的調(diào)查表格跑進農(nóng)村中去,調(diào)查完畢以后,還要帶回研究室來,慢慢整理,細細研究。這樣的調(diào)查縱然可以做得盡善盡美,但在我們鄉(xiāng)村工作青年,總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而薛暮橋的禮社調(diào)查和寫作方法較少限制,便于分散實施。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1933年12月正式立案成立后,農(nóng)村通訊即成為“編輯工作的一個主要的部分”,并在中華書局《新中華》第2卷第1期起設(shè)立“農(nóng)村通訊”欄目,專門發(fā)表會員農(nóng)村通訊作品,薛暮橋的筆名作品正是這一欄目開篇之作。薛暮橋主編研究會機關(guān)刊物《中國農(nóng)村》期間(1934—1938),農(nóng)村通訊是雜志的基本欄目。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還將農(nóng)村通訊的代表性作品單獨集合成冊出版,不僅希望這些作品成為社會經(jīng)濟學(xué)家參考資料,還希望因生動的筆調(diào)成為文學(xué)藝術(shù)研究者的讀物。清華大學(xué)物理系畢業(yè)生于光遠談及,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這些農(nóng)村通訊對自己的“思想進步起過頗為重要的影響”。從于光遠的案例看,這些農(nóng)村通訊所產(chǎn)生的影響甚至超出了預(yù)期。
總之,《江南農(nóng)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既是薛暮橋中研院期間在陳翰笙直接指導(dǎo)下完成的調(diào)查報告,是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也為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日后失去中研院這一官方學(xué)術(shù)機構(gòu)支持后,以不同于前的分散方式延續(xù)實地調(diào)查工作提供了新的經(jīng)驗范本,因此在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英文本《農(nóng)村中國》第2章(1932)和第6章(1933)
根據(jù)哥倫比亞大學(xué)珍本圖書館特藏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檔案,《農(nóng)村中國》是陳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1905-1984)1937—1938年在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資助下完成的研究項目。書中主要收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陳翰笙1933年7月離任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之前,主持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所完成的兩種未刊報告稿主要內(nèi)容。第一種未刊報告題為《無錫的土地分配與資本主義的前途》(“Wong Yin-seng,Chien Tsen-jui and others,Land Distribution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2”) ,英譯和編輯后列為《農(nóng)村中國》第2章“上海附近無錫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U,NEAR SHANGHAI”);第二種未刊報告稿題為《土地所有權(quán)的近代化》(“Wong yin-seng,Chang Hsi-chang and others,Modern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an unpublished MS. ,dated 1933”),英譯和編輯后列為《農(nóng)村中國》第6章“土地所有權(quán)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最近考證研究表明,的第一作者均為陳翰笙。

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會(1933-1951)機關(guān)刊物《中國農(nóng)村》(1934-1943)合訂本,薛小和藏書,無錫電視臺攝影
《農(nóng)村中國》中這兩章的核心內(nèi)容最早見于1932年夏季的《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二十年度報告》:“無錫田權(quán)正在近代化之過程中:田產(chǎn)買賣,日趨自由;租佃期限,逐漸縮短。因此田權(quán)更易集中。無錫農(nóng)民所有農(nóng)田,幾占全縣田畝之半數(shù)。地主多不自經(jīng)營,其所有農(nóng)田88%俱為出租;農(nóng)民耕地不足,多向地主零星租入。租地占農(nóng)田52%。”鑒于兩份報告罕見重要的文獻價值,對其形成過程有必要做更進一步討論。
“上海附近無錫的土地集中”章按照經(jīng)濟地位將村戶分為“地主”(landlord)、“富農(nóng)”(rich peasant)、“中農(nóng)”(middle peasant)、“貧農(nóng)”(poor peasant),另外還談到“農(nóng)業(yè)工人”(field worker),實際上隱含了“雇農(nóng)”概念。因此,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中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村戶分類框架,印證了學(xué)界此前指出的陳翰笙主持和實地調(diào)查時制訂的農(nóng)戶分類標(biāo)準(zhǔn)“發(fā)生在1933年以前”“陳翰笙教授的過人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學(xué)界之所以將1933年作為評論基準(zhǔn),是因為毛澤東1933年10月為中央工農(nóng)民主政府起草了《怎樣分析農(nóng)村階級》,提出了劃分農(nóng)村階級成分的標(biāo)準(zhǔn)。
錢俊瑞晚年表示,“在農(nóng)戶分類上,我們用的是富農(nóng)、中農(nóng)、貧農(nóng)、雇農(nóng),以所處經(jīng)濟地位來劃分。他們(指卜凱等人———引者注)卻是用自耕農(nóng)、佃農(nóng)、半佃農(nóng)等,以經(jīng)營形式來劃分。這兩種不同的分類方法決定了揭露還是掩蓋階級矛盾的根本問題。”這一回憶忽視了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資料整理的復(fù)雜過程,1929年開展無錫農(nóng)村實地調(diào)查時,這一可操作的分類框架尚不存在,但并不能說當(dāng)時就是“掩蓋階級矛盾的”。只是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資料整理和研究過程中,這一村戶分類框架才明確和確立下來。而這一框架的確立,也標(biāo)志著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取得長足進展,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農(nóng)村派研究范式的成熟。
“上海附近無錫的土地集中”章除了村戶分類框架引人注目外,報告還通過土地所有權(quán)的類型、移轉(zhuǎn)方式、土地分配、租金運用及土地利用分析,呈現(xiàn)出無錫農(nóng)村土地集中過程和租佃制度嵌含于廣泛的封建主義殘余的現(xiàn)實。這與馬季亞爾所謂帝國主義入侵后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殘余布滿中國的看法相對,既印證陳翰笙關(guān)于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肇因于和馬季亞爾莫斯科辯論的回憶,也可以看作是精心研究之后對馬季亞爾的正面回應(yīng)。
“土地所有權(quán)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章指出,只是在資本主義形式的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占主導(dǎo)地位時個人所有者才有權(quán)根據(jù)意志使用或毀滅財產(chǎn);在此之前,土地往往由整個家庭或家族所有,且這種所有權(quán)殘缺不全,其移轉(zhuǎn)受到形形色色的社會限制。隨后,該章分析了中國農(nóng)村永佃制正在瓦解,土地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及其交易變得越來越完整的局面。這實際上是中國農(nóng)村派此后各種農(nóng)村調(diào)查報告的土地產(chǎn)權(quán)基本分析框架,因此帶有中國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產(chǎn)權(quán)分析源報告的性質(zhì)。
(五)陳翰笙在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加拿大班夫雙年會上的論文(1933)
這篇英文論文共使用31張表格,其中10張表格使用了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其中,無錫土地分配表由劉懷溥、劉端生整理,江蘇374個大地主主要職業(yè)表由瞿明宙整理,江蘇4縣當(dāng)鋪表由石凱福整理,直接來自1929年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數(shù)據(jù)并不多,這印證了陳翰笙主持的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并非一次完成,而是一個復(fù)雜過程的判斷。
該文在國際上得到高度評價,“太平洋國際學(xué)會認(rèn)為這篇論文是關(guān)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權(quán)威著作”。雖然并未在學(xué)術(shù)期刊刊出,仍在學(xué)界引起關(guān)注。尤其是這篇論文指出,與大革命前法國舊制度下的地主大為不同,中國的地主常四位一體,同時是收租人、商人、高利貸者和行政官員。這既是一個宏大的分析框架,也指明了中國農(nóng)村制度與歐洲農(nóng)村的不同之處,給英語學(xué)界留下深刻印象。論文指出,中國的地主并未走上普魯士的經(jīng)營地主道路;而“中國的富農(nóng)也經(jīng)營高利貸和商業(yè),如同地主一樣”;俄國資本主義農(nóng)業(yè)向前發(fā)展時,貧農(nóng)將土地出租,富農(nóng)租進土地,而長江流域,貧農(nóng)多是佃農(nóng),富農(nóng)出租土地收取地租。這也就表明了世界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主要類型在中國前途黯淡,中國的地主和富農(nóng)致力于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法的持續(xù),貧農(nóng)、雇農(nóng)和中農(nóng)失去土地,地主和富農(nóng)集中土地,并不是為了改善生產(chǎn)而是使既有的生產(chǎn)方法加強。這篇論文引用馬季亞爾的地方不多,考茨基和列寧的名字均未提及,但關(guān)于土地財產(chǎn)長時段變化的討論受到馬季亞爾的深刻影響,收租人、商人、高利貸者和行政官員四位一體的看法在馬季亞爾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至于經(jīng)營地主和富農(nóng)的討論則反映了考茨基和列寧著作的影響。
這篇論文完成于1933年5月,此時陳翰笙還是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專任研究員;8月在班夫會議上正式報告時,他實際上已辭去專任研究員職務(wù),改任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通信研究員。因此,這篇論文實際上是陳翰笙任職國立中央研究院期間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是他領(lǐng)導(dǎo)社會科學(xué)研究所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工作的系統(tǒng)總結(jié),當(dāng)然也包括無錫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的總結(jié)。至此,一個肇因于1928年莫斯科辯論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范式,已經(jīng)以成熟的方式展示給國際學(xué)術(shù)界。
“中國最有能力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者”
雖然索訥指出,1880至1930年間俄國農(nóng)民經(jīng)濟研究最領(lǐng)先、記錄最完整,薛暮橋指出在莫斯科工作的匈牙利經(jīng)濟學(xué)家馬季亞爾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是關(guān)于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第一部完整著作”,莫斯科在農(nóng)村經(jīng)濟(包括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方面一度表現(xiàn)的開創(chuàng)性并未延續(xù)下去。這可以用陳翰笙1927—1928年客座訪問國際農(nóng)村研究所時的經(jīng)歷解釋。他晚年回憶:我覺得當(dāng)時莫斯科盛行一種學(xué)風(fēng):誰能背誦經(jīng)典著作辯論起來就占上風(fēng),不習(xí)慣實事求是。
陳翰笙1927—1928年在莫斯科所觀察到的情況在接下來的幾年愈演愈烈。馬季亞爾的著作在蘇聯(lián)引起巨大的爭論,1930年和1931年曾專門召開兩次研討會討論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問題,但與會者只是引經(jīng)據(jù)典援引有利于自己看法的語錄,對經(jīng)濟事實并未進行切實的深入研討。陳翰笙帶領(lǐng)的研究團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在同一時期深入無錫農(nóng)村,以經(jīng)驗和理論相結(jié)合的現(xiàn)代社會科學(xué)研究方式加以回應(yīng),與莫斯科形成一種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xué)派內(nèi)部的研究范式分流。
這種范式分流結(jié)果是莫斯科失去了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包括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傳統(tǒng)的領(lǐng)先地位,而陳翰笙主持的研究則成為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前沿。除了蘇聯(lián)方面,英語文獻也高度評價陳翰笙的研究工作。1935年紐約《太平洋事務(wù)》季刊發(fā)表伊羅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長篇論文,稱陳翰笙為“中國最有能力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者”。陳翰笙本人在評論關(guān)于中國和日本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時,坦率地指出俄語研究文獻在提供數(shù)據(jù)方面“毫無意義”。這是對蘇聯(lián)1930年代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經(jīng)濟經(jīng)驗研究(包括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研究)衰落的權(quán)威評論,也是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研究教條化的一個側(cè)面。
陳翰笙1935年再次訪問莫斯科。他回憶這次訪問“給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俄共(布)清黨的緊張氣氛”“我所認(rèn)識的一些蘇聯(lián)研究員,有的莫名奇妙地失蹤了,有的開槍自殺了。到后來,加拉罕和馬季亞爾也受到審查、被處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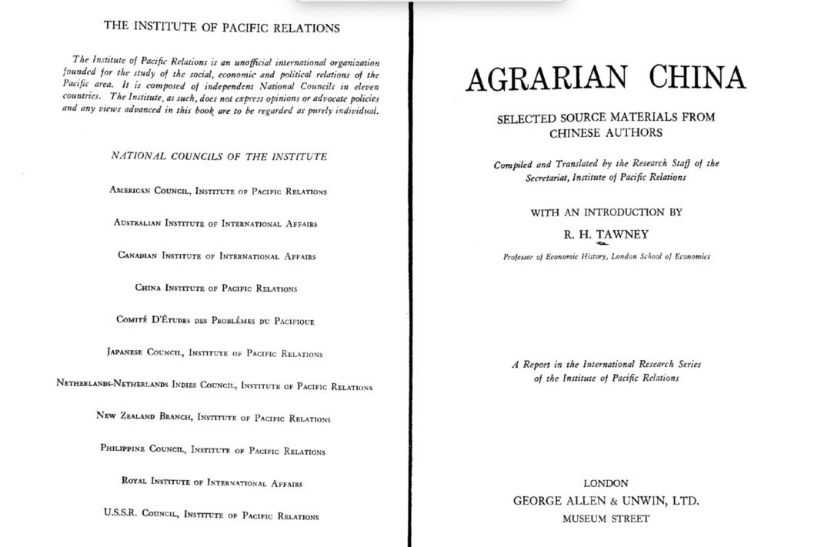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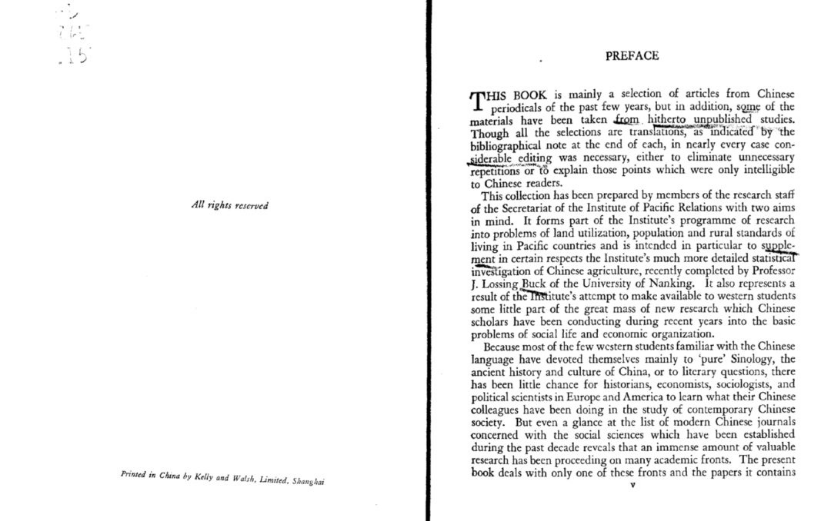
《農(nóng)村中國》,內(nèi)頁劃痕為費正清筆記。感謝作者提供圖片
原文及《無錫的土地分配和資本主義的前途》 《土地所有權(quán)的變革與永佃制的命運》見鏈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