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約翰·契弗:我一直對從未見過的國家充滿鄉愁
【編者按】
以短篇小說聞名于世的美國作家約翰·威廉·契弗(John William Cheever,1912年5月27日-1982年6月18日),被譽為“紐約城郊的契訶夫”。約翰·契弗在《紐約客》雜志上發表了121個故事,開啟了《紐約客》短篇創作黃金時代,影響了雷蒙德·卡佛等作家。近日,他的短篇小說自選集首次在中國國內引進譯介。本文為英國劇作家、編劇、電影制作人、小說家漢內夫·庫瑞什為該書所寫的導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標題為編者所擬。

約翰·契弗
如果你一邊讀這些小說,一邊參閱約翰·契弗的《日記》,同時獲知他是個什么樣的人以及他都寫了些什么,你會體會到一種陰郁的憂慮不安。契弗的《日記》本身就是最偉大的自白類作品之一,我會將其與盧梭和佩皮斯(編者注:Samuel Pepys,1633年2月23日-1703年5月26日,英國作家、政治家,著有《佩皮斯日記》)的作品并列為一種范例,它充分展示了一個無論對自己還是他人都從不滿意的復雜之人的內心斗爭。正如契弗本人所言:“我一直對我從未曾見過的國家充滿鄉愁,渴望去往我無法前往的地方。”
《日記》中所呈現的契弗生性孤僻,臉皮極薄,既愛男人又愛女人。這讓他備感困惑,跟他在一起有時候也會讓人感覺受不了,因為在他的年輕時代,遵照習俗按照慣例是該做個明確選擇的。不過對于一位作家而言,擁有范圍如此廣泛的同情心和感受力,反而只會成為一種優勢。
契弗寫的都是那些最重要的事情。說到他的短篇小說,你可能會想,你很難從他的創作中了解到更廣闊的美國社會,因為當中沒有黑人和拉美族裔的生活,他沒有反映后奴隸制的精神創傷,也沒有反映社會不平等、政治斗爭或是貧窮。但你確實感受到了電梯工、門房和正派的窮人那寒酸而又艱難的生活。
在《日記》中,契弗認為他的作品很有“局限”性,擔心他的題材過于逼仄狹窄。然而,他絕非對于四季常青、富裕體面的城郊之外的生活知之甚少的那種精英主義的中上層白人作家,眼中只有周六夜派對上的一片狼藉和馬提尼喝多了以后的絕望,男人都是通勤者而女人全都感覺浪費了自己的生命——與之后查爾斯·韋布(編者注:Charles Webb,1939年6月9日-2020年6月28日,美國作家,出生于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在《畢業生》中所諷刺的泳池世界不無相似之處——契弗的創作一直都正中世間萬物的中心。他的主題不是怪胎、廢柴或是各種的邊緣人,而是孩子們、工作以及西方文學的中心觀念——是契弗所謂的“婚姻那令人痛苦的秘密”,以及婚姻是如何使激情顯得荒謬可笑的——如果并沒有使得激情變得完全不可能的話。而且雖然他著迷于他有時候描述為“肉欲的無政府狀態”的那種現象,他卻有足夠的明智,知道推動我們前進的更多的是社會地位、自尊自重和工作,而非情欲和性欲:我們依靠金錢生活,又夢想著完美的愛情。
我猜想,你也許想把這些短篇小說描述為契訶夫式的,即使僅僅因為契訶夫的天賦就在于能夠以幽默的同情在日常生活中捕捉那些意味深長的時刻,并且毫無屈尊俯就的傲慢態度;因為契弗有能力寫出令人屏息驚嘆的挽歌式的那結尾的最后一段,既包容涵蓋了整個故事同時又是一種超越和提升,就仿佛所有的一切最后被以一種酒神慶典式的方式整個兒拋向了空中。你也許還想說,相對于卡佛而言契弗沒那么陰郁荒涼,相對于海明威而言他更加廣闊、反諷,而且活潑俏皮。但歸根結底,契弗一直都是完完全全的他自己,反反復復地斟酌、推敲和平衡,直到每個句子都恰如其分,而且經常還不止于此,能上升到使日常生活的火車通暢地奔馳在更寬闊的政治的鐵軌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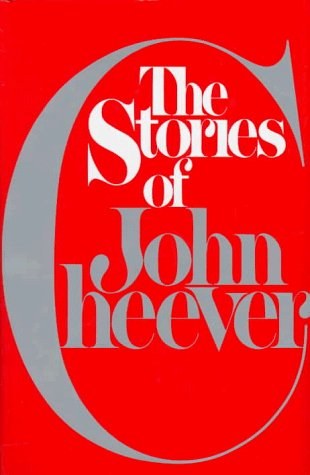
《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英文初版書影
契弗說起一種社會,在其中人們“聯合在心照不宣的宣言當中:沒有過去,沒有戰爭——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危險或是不幸”。那個時候的美國是何其廣闊而又重要,他筆下的人物都共享著美國戰后的那個對于繁榮與和平的普遍希望,而與此同時那個希望又總是因害怕它實在太新、怕它可能被收回而遭到損害。而說到政治局勢,你在閱讀這些小說時幾乎不可能意識不到隨之而來的到底是什么:這些淺薄的、逼仄的生活將被“六十年代”徹底粉碎——那改變了一切的興奮、固執和反叛的風起云涌。契弗使我們看到了它的到來:他那些內心分裂的人物渴望得到安逸與安全,但他們也渴望愛情和解放;他們為一種非常迫切的欲望所吸引,而它會打破對心滿意足的大部分嘗試,經常還會導向災難性的后果。
因此,你預期在這些城郊地區只能找到最干凈和乏味的誠實和正直;這大概也正是人們選擇住在那里的原因之所在。但在進一步的審視之下,你會發現那里也有非同尋常的人類激情和弱點,會發現一種可怕的喧囂不寧。它以最穩健、最有節制的樣態出現,這是合乎情理的。“為了能看到任何東西——一片樹葉或是一枚草葉——我想你必須懂得愛的強烈。”
話說回來了,對任何人的愛又何曾簡單容易過?正如《蘋果世界》中那位睿智的詩人巴斯科姆所肯定的那樣,在很多情況下,“猥褻——下流猥褻——似乎成了生活中唯一具有色彩、值得歡慶的因素”。
進一步推究下去,欲望會變成一種具有毀滅性的激情,甚至會成為一種變態,永遠無法得到滿足。這在《鄉居丈夫》——契弗最優秀的,也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短篇小說之一——當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一個男人差一點在一次飛機迫降事故中喪命,回到家卻發現他的妻子和孩子們非但對于他的死里逃生漠不關心,甚至對他的整個存在都毫不在意。他瘋狂地在年輕的保姆身上尋找慰藉,最后只能求助于心理醫生。一九五〇年代的很多美國人都是這么做的,在非常明確地向醫生坦白“我戀愛了,赫爾措格醫生”以后,他能找到的只有更多的失望,醫生的推薦療法也只是建議他干些木工活兒。如此說來,一個深受痛苦折磨的人如果不去酗酒的話,又能求助于什么呢?
契弗本人性格上的復雜性——今天會被描述為“掙扎于酒精與性愛之中”——使他能夠看清,他筆下那些人物的不幸更多地應歸因于他們自身的軟弱和他們的過去,而非歸咎于社會的因素或者他人的歹毒。人們為什么會做出不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事情?為什么會有一種本能的欲望,將對他們而言最為珍貴的東西棄之不顧呢?這個永恒的謎題使得契弗深深地著迷于人類那些最嚴重的自毀行徑。
一個同性戀連續三次把腦袋伸進煤氣爐里,只是為了能被一個怒不可遏的恐同的電梯工把他救下來,有時這是顯得很好笑。而在《重聚》這個只有兩三頁篇幅的優秀短篇當中,那個父親卻只能反復不斷地破壞他跟自己久已疏遠的兒子那難得的聚會,使父子倆全都無法得到他們最希望能夠建立起來的一點點親情的聯系和真正的交流。

約翰·契弗
約翰·契弗一九一二年生于馬薩諸塞。參軍服役之后,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成為一位全職的作家。一九四八年他曾寫道:“我們仍舊跟以前一樣窮。我一個禮拜能寫一個短篇,也許能寫得更多。”他成功了,他既寫短篇又寫長篇,直到他一九八二年去世。他曾在羅馬住過,寫過很多以意大利為背景的優秀短篇。在那個商業世界里工作,主要為《紐約客》供稿,契弗做到了用寫作來養家糊口。身為一半藝術家、一半娛樂者,他跟莫泊桑、弗蘭納里·奧康納(編者注:Mary Flannery O'Connor ,1925年3月25日–1964年8月3日,美國小說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好人難尋》、《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以及兩部長篇)及其他偉大的美國作家一起,其作品居于最頂端的位置;他的作品絲毫不因襲陳腐,而是充滿了實驗性——最有趣的意味上的實驗性。
在他的《日記》中,極少有對他實際寫作過程的記述。當他實際上并沒有正在做的時候,契弗很不愿意跟自己談論他在做的事。也沒有人強迫他這么做:他還不需要像現在的作家那樣要去進行漫長的新書宣傳、面對眾多讀者朗讀自己的作品再繼以簽名售書,并要不斷地接受采訪,直到他們都要被自己的聲音給嚇到為止。不過,他也確實給過我們重要的提示,那是在《巴黎評論》上:“小說就是個實驗的過程;當它不再是實驗了,它也就不再成其為小說了。一個句子,直到你感覺在此之前從來就沒有以這樣的方式寫下來過,這個句子才算是可以完成了。”
不過對于短篇小說家而言,特別是出版小說合集的時候,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其多樣性,尤其是如果讀者希望一口氣把這些小說讀完的話;那就像是狼吞虎咽地吞下太多的牡蠣,而非以理想的方式間隔開來,一個一個地細細品味。但這部小說集卻有著極為廣闊的范圍和無限的多樣性:這是一個作家一生的創作成就,而且那又是充滿了好奇與革新的一生。
奇怪的是,契弗從未創造過一個像他本人那樣有天分、有智慧或者有文化的角色;他的角色全都是比他本人更為渺小的人物,但他們也都是他的一部分。角色的創造,對長篇小說家而言那最重要的工作,并非他的首要關切點,他的短篇都是一次性創造成型的。如他所言:“我關注的不是情節。我關注的是直覺,是穎悟,是夢想,是觀念。情節只關乎故事和一大堆廢話。”
他洞察和描述的能力是驚人的,在一閃而過的一節臥鋪車廂里,有“一位美得出奇的女人,沒有穿衣服,正在梳理自己的金發”;一個鄰居正在彈奏《月光奏鳴曲》:“他全然不顧節拍,以自由速度從頭彈到尾,全然是在宣泄那種眼淚汪汪的任性、孤寂和自怨自艾——凡是貝多芬的偉大所不曾包括的,無所不有。”
能夠寫下這么多其他人在五十年后仍讀得興味盎然的短篇小說,能夠寫下這么多充滿智慧、引人共鳴、富有詩意而又不可言喻的語句,他的人生可算得絕沒有虛度;而我們之閱讀它們,一遍又一遍地反復閱讀,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并且向契弗表達他當之無愧的尊敬和仰慕之情。
漢內夫·庫瑞什
二〇〇九年

《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美】約翰·契弗/著 馮濤、張坤/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