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系統論法學的中國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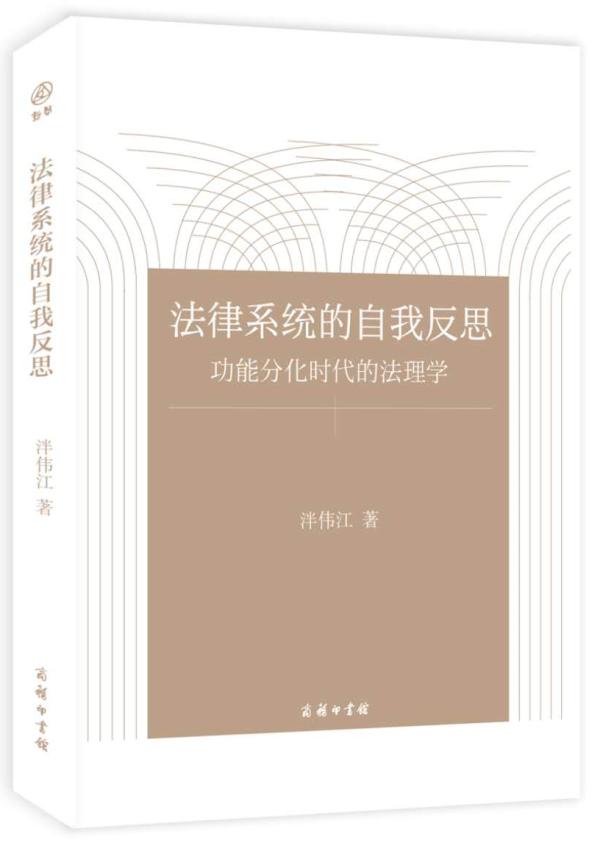
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傳世的社會系統論,讓我和泮偉江成了朋友。盧曼理論因晦澀難懂而聞名學界,但堅持讀上數年,也容易上癮,甚至淪落為“盧曼迷”。我和偉江學術興趣一致,在盧曼這個“理論大王”的王國里巡游多年,算得上是盧曼鐵桿粉絲,雖然這并不妨礙我們對盧曼理論有所保留并提出自己的質疑。
2006年,我誤打誤撞,當然,也可以換種說法,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必然性牽引,終于完成了以盧曼法律社會學為主題的博士畢業論文。回顧畢業論文,即便沒有遺恨,也有諸多遺憾吧。這是手忙腳亂研讀盧曼兩三年后匆匆結出的小果子,難免味道青澀。論文答辯完畢數日之后,接到清華大學高鴻鈞老師聚餐邀請。久聞高老師盛名,但素未謀面。聚餐是在清華校門的“醉愛”餐館,在座的還有高老師門下攻讀碩士學位的沈明。高老師和我們慢慢說話,慢慢喝酒,美食蒸騰,美酒飄香,十分愜意。高老師對我說過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盧曼很重要,希望你能把盧曼理論研究繼續下去。在當時國內研究盧曼冷啟動的條件下,在孤獨堅持了數年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直抵內心的溫暖和認可。那次聚會之后,我漸次了解到,其實高老師早已落子布局了社會理論與法學的對接工程。
近十幾年來,高老師對哈貝馬斯和盧曼等重要社會理學大家的思想展開了系統深入的解讀,并在清華開設講壇,令學界矚目,領我國當代研究社會理論法學風氣之先。名師出高徒,高老師的學生也雨后春筍般登上社會理論法學舞臺。魯楠、陸宇峰、泮偉江、馬劍銀、余盛峰、張文龍、楊靜哲等青年才俊,個個身手不凡,圈內一時異彩紛呈。其中,泮偉江專精盧曼理論,對盧曼的系統論法學用功最勤,感情最深,切入最透徹。
我幾乎不與人私下聊學術,聊得更多的是學術八卦。但與偉江的交往是個例外。相隔京滬之遠,除了開會,我與偉江見面并不多。每每抓住機會,就會向他刺探學術情報。我有所問,他必爽快答。有一回他講,正在翻譯盧曼的《社會的社會》和《社會的政治》,并談到了翻譯進度,也坦承遇到的麻煩,等等。他說得溫和平靜,我心里卻已翻江倒海。我曾與師弟趙春燕合譯過盧曼早期著作《法社會學》,體驗過被盧曼折騰得蛻皮的焦慮。偉江要從德文原版翻譯這兩本盧曼中、后期的重量級著述,加起來估計上千頁,而且這還遠不是數量的事,翻譯盧曼不知難倒了多少江湖好手。這得下多大的決心,熬多少個日夜,又是多大的功德啊。至于偉江翻譯盧曼的功力,我最不擔心。偉江研讀盧曼十年,英文德文俱佳,對西方社會理論的知識譜系做過細致梳理,研習過政治哲學,熟悉現象學,精通系統論,法學科班出身,對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法文化傳統也頗有造詣。國內學者中,罕有人比他更具備翻譯盧曼大作的知識條件了。
有時,我與偉江也交流研讀盧曼的心得和困惑。翻看和偉江往日微信的記錄,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對話。我問偉江,你的學術使命是什么,他的原話是:把盧曼讀好,翻譯好,讀準確,翻譯準確,講清楚,能做到這一點,已經很滿足了。我說:你這么年青,訓練扎實,抱負肯定不止于解讀盧曼。他謙虛地回復:我對自己的定位,還是努力把盧曼學懂搞透,如果有一點自己的創造的話,就是和中國的一些具體問題相結合,在具體問題的分析中展現盧曼理論的魅力。
讀者諸君手頭捧著的這本《法律系統的自我反思——功能分化時代的法理學》,就是偉江兌現自己 “把盧曼讀懂搞透,在具體問題中展現盧曼理論魅力”這一承諾的階段性成果。此書分為三個編章:“上編:功能分化時代的法理學”,“中編:法理學與中國社會的功能分化”,“下編:系統論法學的理論譜系”。僅從標題看,似乎下編的任務是“把盧曼讀懂搞透”,上編和中編的任務是“在具體問題中展盧曼理論魅力”。但是,我的體會是,各編的任務并非涇渭分明,上篇和中篇中有大量對盧曼理論的精細解析與融貫理解,下篇中的純理論考察也時時用余光瞄向中國具體問題。這本書應該是偉江之前若干論文經過再創造后的一個文集。幾乎在每一篇論文中,都能感受到偉江既要把盧曼搞透,也要以盧曼理論回應中國法律運作的實踐和理論問題的雙重努力。可以說,在偉江的整個工作邏輯中,“把盧曼讀懂搞透”和“在具體問題中展現盧曼理論魅力”這兩項目標,是相互交織的,是他每一篇論文或明或暗的背景意識。
先說“把盧曼讀懂搞透”。所謂大師,就是能夠突破時代的觀念圍墻,為人們貢獻另一套看待世界的顛覆性視角,重新激活已經例行化和僵化的社會生活,并在新的層次上讓社會世界獲得再合理化的蝶變;所謂大學者,就是能夠擺脫舊的概念之網的地心引力,抽象出新的概念之網,令熟悉的經驗再陌生化,讓我們領悟到更深刻更寬廣的意義世界。盧曼就是這樣一位當之無愧的大師和大學者,在學術廣角和社會穿透力上,能與他相比的,可能只有一百年前的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盧曼提煉的每一個關鍵概念,都是在與舊歐洲傳統較勁,這些概念之間阡陌交錯,循環指涉,編織成極為復雜的意義網絡,對社會世界給出了包羅萬象又精致細膩的嶄新詮釋。然而盧曼理論是堅硬的,不太照顧讀者的閱讀體驗,他幾乎是以最為晦澀的方式展示了最為清晰的社會理論圖景。讀者如果貿然闖入,遭遇的只有晦澀,而無法領悟到清晰;收獲的不是看待世界的嶄新意義網絡,而是陷入挫折自尊心的概念迷宮。所以,把盧曼“讀懂搞透”,絕非易事。如果沒有打怪過關的果敢,沒有武裝到牙齒的知識準備,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看過太多的誤讀。甚至國內某位專攻社會理論的學者,在翻譯一篇盧曼論文后的譯后感言中,也暴露出因其對盧曼后期理論的隔膜而產生的偏見。通讀了偉江這本文集數遍后,我親測之下的體驗是,他對盧曼的理解既準確又全面,更難得的是,還貼心地奉上了明晰易懂的增值服務,為讀者提供了一幅探索盧曼理論秘境的路線圖。我和偉江曾在聊天中達成過一項共識:摸索著盧曼著作的注腳,追讀盧曼讀過的書,這就是學問的捷徑。偉江在社會理論上“冰凍三尺”的功力,可以在《輝煌的失敗:哈貝馬斯民主法治國理論的方法論批判》這篇文章中得到直觀的驗證。他之前的一切準備,似乎都是為了最終能夠庖丁解牛般進入到盧曼理論世界的無人之境。偉江這本文集,應該說在盧曼的核心概念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雙重偶聯性”“觀察”“復雜性”“結構耦合”“意義”“二值邏輯”“象征性一般媒介”“區分”“悖論”等等,甚至以盧曼本人都不曾有過的顆粒度和飽滿度,清晰準確地再現了這些關鍵概念的內涵,并且補足了這些概念附著其上的思想史背景。盧曼通常隱藏或者壓縮了這些背景,預設他的讀者都是通家大識,因而極大增加了讀者的心理壓力和理解成本——即便這些讀者已經是社會理論領域的專家。可以說,偉江對這些思想史背景的澄清,大大縮短了我國年輕學人迅速進入盧曼語境的路徑。
再說“在具體問題中展現盧曼理論魅力”。偉江所謂的具體問題,不只是中國本土的學術問題,也包括為中國學者所關注的西方學術史上的大案要案。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大陸法學圈,踏著改革開放大合唱的節奏,一波又一波法學理論走馬燈似的登臺亮相。哈特與德沃金之爭曾是我國一批優秀博士論文和重要專著的靈感來源,自然法學與法律實證主義之間的相互辯難注定是法哲學領域的永恒話題,在法學方法論熱過又降溫以后,社科法學對于法教義學的挑戰成為重頭戲,學界倚重的韋伯法社會學以及官方意識形態加持的馬克思主義法學也以非凡的分量左右著我國社會理論法學的再生產。比較起來,系統論法學在當下中國法學圈顯得相當小眾,然而其異軍突起的姿態,還是給法學界留下了無法忽視的硬漢形象。這本論文集中,偉江攜系統論法學之威力,與國內中青年法學翹楚們就當代中國法理學、法教義學、憲法學、司法裁判理論、社科法學等領域中的重大學術話題展開對話,在教義學和社科法學爭論的理論戰場之外,開辟了另外一個身份超然的話語空間,同時又精彩地診斷并治療了教義學和社科法學的盲點。與社科法學相比,系統論法學不是社科法學意義上的“精確科學”,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嚴格科學”,是對法律系統這個“意義世界”的觀察,因此,偉江特別強調了不能以社科法學的“因果關系”掏空教義學上的“因果關系”;與法教義學相比,系統論法學既能進入到法教義學的“內部觀察”,又能以社會科學的立場對法教義學加以“外部描述”,這種雙重視角的優越性,用偉江充滿系統論味道的話來說,就是可以把教義學內部的“必然性”還原為外部視角中的“偶連性”,這對于我們重新理解法律系統基于“社會事件”的運作邏輯而言,無疑可以掀起一場理論上自我革命的頭腦風暴。
這本文集中,最讓我驚訝的兩篇論文是《通過法律認識社會:一種描述性法理學的嘗試》和《論社會學對法學的貢獻:一個古老遺產繼承案引發的法哲學反思》。在《通過法律認識社會》這篇文章中,偉江創造性地運用系統論方法重讀哈特法哲學,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哈特基于“社會學描述”回答“法律是什么”問題上所暴露的社會學上的營養不足。偉江熟練掌握了后期盧曼基于斯賓斯-布朗的“形式規則(laws of form)”所發展起來的區分理論,發掘出支撐哈特理論的一系列區分,比如,“存在/不存在”“義務性/非義務性”“強制性/非強制性”“法律/道德”等等,正是這些區分的使用,讓哈特落入了“存在論進路之描述法理學”的困境。這種運用系統論新工具揭示哈特法哲學存在論困境的巧妙發力,與德里達運用解構理論揭示隱藏于黑格爾經典文本中的本體論世界觀相比,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進一步證成了系統論法學手術刀的鋒利。就我個人的閱讀體驗而言,這篇論文經過進一步打磨,完全可以放在世界法學舞臺上與斯科特·夏皮羅(Scott Shapiro)、布萊恩·比克斯(Brian Bix)等分析法學代表人物展開對話。《論社會學對法學的貢獻》這篇文章,圍繞著“第十二只駱駝”的貝都因人故事,吹出了許多奇思妙想的泡泡,讀起來妙趣橫生。偉江寫這篇論文時,一定是在盧曼能量的灌注下,爆發了自己的小宇宙。關于貝都因法官在判案中出借“第十二只駱駝”的軼事,盧曼本人已經借題發揮過,德國系統論法學代表人物托伊布納也有佳作奉獻。偉江承接了盧曼關于法律“內部視角”和社會學“外部視角”的啟示,進一步挖掘了“第十二只駱駝”的社會功能,認為這是一只“執行公務的駱駝”,也是一只“程序性的駱駝”,并結合中國經驗,揭示了法律上的“擬制”如何在克服了法律自身的悖論同時又實現了對于社會的饋贈——這其實也有機融入了托伊布納的“法與社會”的視角。這篇文章清新可人,巧思靈動,對于正在向系統論法學靠近的新人而言,是一份很好的見面禮,對于研習系統論法學的老法師,也提供了一次躬身自問的參照系。
在閱讀偉江的這本文集的過程中,我與偉江在盧曼詮釋上有大量的、基礎性的重疊共識,然而,差異也在所難免。就像盧曼所言,共識只能產生套套邏輯,只能導致系統的空洞的自我指涉,這意味著乏味的自我重復。如果沒有差異所帶來的驚訝值,溝通就會終結,社會就會瓦解。“差異的差異”就是信息(葛瑞利·貝特森語),社會系統基于差異不斷制造“信息/冗余”的區分。正是這個區分所形成的動力機制,不斷破壞既定的共識,又在新的條件下促成暫時的共識,然后又不斷自我破壞——這就是社會溝通得以延續的動態演化過程。學術系統反對抄襲,強調創新,道理不過如此。為了給學術系統的正常運轉出份力,我必須勉強自己去找出與偉江的差異,哪怕是雞蛋里面挑骨頭。
偉江之前出過一本著作《當代中國法治的分析與建構》(2017年修訂版),其中《論指導性案例的效力》一文,已經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力。文中,偉江與張騏、雷磊、陳景輝等學者關于“同案同判”展開了對話,他認為,法教義學的功能定位是“對判決之間的一致性檢驗”,并且強調“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同情況不同對待”這項現代法律之“偶聯性公式”的正義原則。就這些論點而言,偉江無疑貫徹了盧曼系統論法學的精髓,我本人也深以為然。然而,我想指出的是,在偉江的論證中,還沒有完全釋放盧曼“區分”理論的潛力,導致他對“同案同判”機制的理解上沒能走得更遠——雖然偉江也是深諳盧曼區分理論的要害。
盧曼后期越來越重視斯賓塞-布朗的“形式”或“區分”理論,甚至成為他晚期學術的標簽。德克·貝克爾(Dirk Baecker)是當代公認最為重要的盧曼弟子,他的工作重心是繼續拓展“區分”理論在社會學上的運用空間。鑒于盧曼社會理論的強勢,甚至有這樣的說法,德國每個擁有社會學系的大學,都想聘任一位研究斯賓塞-布朗的形式理論的專家。“相同/不同”、“平等/不平等”、“涵括/排除”等等區分,都具有自我指涉的悖論性質:區分的兩邊同時存在,但在運用這些區分觀察的時候,我們只能看到區分的一邊。對于社會觀察來說,最為重要的是,這個區分會“再入(re-entry)”到區分的一邊。在司法裁判中,有許多區分會引導這個社會溝通過程,比如“合法/非法”、“信息/冗余”、“系統/環境”、“類推/區別”、“平等/不平等”、“相同/不同”等等,其中“相同/不同”這個區分有其特殊功能。對案件做出相同還是不相同的判斷,并非本質主義上的比對,而是社會建構的過程。所謂的相同,不過是在既有判準下所認定的“相同”,被“視為”相同。所謂“視為”,是法律上的擬制,是法律系統的內部建構。每次肯定“相同”的時候,其實已經把“不同”考察了一番,“相同”和“不同”同時出現在司法溝通的過程中。司法裁判不僅僅關注“事實”與“規范”是否能夠“等置”(阿圖·考夫滿語),更為重要的是尋找這個等置的標準,也就是相同還是不同的判準。以前“視為”相同的案件,現在為什么“視為”不同?是因為法律系統之外的社會環境發生變化,誘發了法律系統內部的原則、規則或概念之間的關系重新排列組合,由此導致了判準的變化。因而,以前視為相同的案件,現在可以被看成不同。比起“相同情況相同對待”,法教義學尤其關注“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帶來的激擾。在盧曼關于社會系統的演化理論中,包含了“變異-選擇-穩定化”三個循環往復的階段。對于法律系統而言,正是“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帶來的激擾,引發了系統在運作上的變異和結構上的變遷,而教義學則是穩定結構變遷的機制。僅就偉江這篇論文而言,似乎還沒有突出系統論這一面的深刻性。
更為重要的是,“相同/不同”這個區分會“再入”到區分內部。當我們說某個手邊案件與先例不同的時候,也就是運用了“類推/區別”這個區分中的“區別”這一面。當運用區別技術時,并不是只關注“不同”,而是在尋找這種“不同”的標準時,同時考慮了“相同”的判準。更為重要的,也通常被忽視的是,在做出“不同”的選裁決時,系統必須在更高層次上識別自身同一性的標準,或者說在更為抽象的層次上建構“相同”,這尤其體現在法教義學所具有的“對判決之間的一致性檢驗”的功能上。此時,“相同/不同”的區分,已經再次進入(內插)到這個區分的“相同”這一面。盧曼有言:“平等對待是其自身的理由,但是不平等對待需要一個裁判。一個形式(平等/不平等)的兩邊的對稱性,通過針對規則的‘規則/例外’這個圖式,轉換為不對稱性。”在我看來,這是偉江在論文中闡述得比較弱的地方。偉江和他的論戰對手們相似的地方在于,他們都更為關注“相同 /不同”這個區分中的“相同”這一面,沒有揭示“再入”機制在司法裁判中的獨特作用。我認為,在“同案同判”的爭論中引入“相同/不相同”區分的“再入”機制,可以給司法裁判理論帶來全新的研究視角。
法律人肯定都熟悉“有規則就有例外”這個格言。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有規則就有例外”本身就是一個規則,因而,這里其實運用了一個“規則/例外”的區分。那么,“有規則就有例外”這個規則的例外是什么?思考片刻,我們驚訝的發現,答案居然是“有規則就有例外”這個規則本身。這只是“再入”機制所導致的自我指涉的邏輯魔術的一個簡單演示。在現代社會的法律系統中,這種邏輯魔術無處不在。比如,反歧視法中平等/不平等、涵括/排除這些區分,就具有這種魔術性質,是研究“平等對待”與“不同對待”的歷史譜系學的邏輯工具。正如盧曼所說:“平等/不平等這個區分無所不包,甚至包含了其自身,因為,平等原則本身就需要被平等地適用到每一個案件之中。”我想,系統論法學的工作重心之一,就是揭開掩蓋在這些魔術效果后面的秘密手法,讓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法律系統的運作模式。
最近,在德國開設社會學的72所大學中,搞了一個“社會理論課程大綱”的統計,講授盧曼的課程穩居第一,布迪厄和韋伯交替排在第二,哈貝馬斯則要排到第八位之后。“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經濟上富起來的當代中國,正在培育自己的學術自主性,我們有自信不再照抄西方的作業,當然也更不需要照搬盧曼。但是,如果能夠把盧曼的社會理論變成一種刺激,以增加我國社會科學溝通系統的復雜性,那將是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要演化契機。對于我國的法學溝通而言,偉江和其他中國系統論法學學者們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為是對盧曼系統論法學的中國表述,無疑,這在近年來我國法教義學和社科法學之爭的僵局之外,綻放出了一個別開生面的溝通空間。
泮偉江所著《法律系統的自我反思——功能分化時代的法理學》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文為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賓凱博士所撰的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