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人嗑瓜子簡史
原創 風物菌 地道風物

-風物君語-
誰才是頭號國民零食?
瓜子!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吃瓜”變成了看熱鬧的同義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專心看熱鬧的時候,到底為什么要吃容易弄臟衣服、吃幾口就撐得不行、吃完還要洗手的瓜?
優秀的零食,應該只填嘴、不填胃,便攜、易清潔,有一定食用樂趣,又不讓人為了吃而分心……不禁讓人懷疑“吃瓜群眾”其實應該是“吃瓜子群眾”。畢竟,論零食的自我修養,瓜子可比瓜高多了。

為了嗑瓜子,人們培養出了“種子選手”
顧名思義,瓜子當然是“瓜的孩子”,而常見的“產子”的瓜——西瓜、吊瓜、南瓜,全是葫蘆科的成員。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人們從這些葫蘆籽里摳出一點點能量,既是對食物的珍視,也是為豐富食譜而做出的努力。

小時候吃西瓜,總會好奇地把西瓜籽放在上下牙之間嗑一下,得到一片柔嫩的米白色瓜子仁。隨著無籽西瓜的普及,現在在超市、水果店已經很難買到種子發育茁壯的西瓜了,許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零食區售賣的大板瓜子真的是西瓜籽。
雖然現在葵花籽當道,大有搶走“瓜子”之名的架勢,但西瓜籽仁才是傳統中式點心里的“瓜仁本仁”。《紅樓夢》里令人肅然起敬的“內造瓜仁油松瓤月餅”(宮廷限定聯名款五仁月餅),用的就是西瓜籽。

作為著名的非洲土產、“大象犀牛的最愛”,西瓜傳入中國的時間至今沒有定論,但唐代之后,西瓜和瓜子的“中土之旅”時間線便逐漸清晰了起來:
成書于公元953年的《陷虜記》中記載,“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作為契丹特產,“西瓜”一詞首次以文字形式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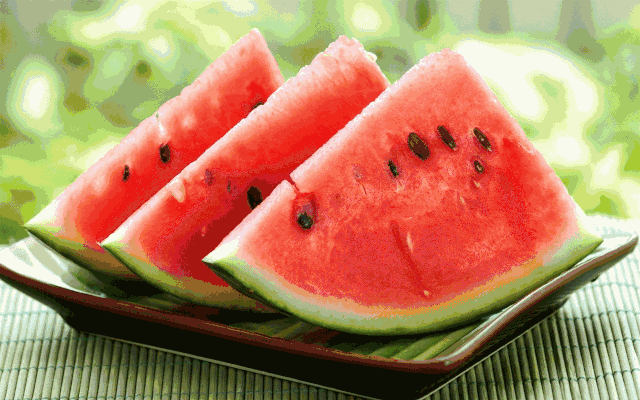
北宋初年,《太平寰宇記》中第一次出現了幽州土產“瓜子”;
元代的《王禎農書》記載道,“(西瓜)其子爆干取仁,用薦茶易得”;
到了晚明,嗑瓜子登上大雅之堂,成了皇家活動,明神宗“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清代初年,瓜子的街頭地位已經堪比今天的奶茶,孔尚任的《節序同風錄》中就有“炒西瓜子裝衣袖,隨路取嚼曰嗑牙兒”。19世紀中葉來華的法國傳教士古伯察甚至在《中華帝國紀行》中說,“你就是到了最荒涼的地區,也不用擔心買不到西瓜子。”

至于葵花籽大量取代西瓜籽,就是民國之后的事了。
問題來了。現在的西瓜要么“小籽”、要么無籽,那么大板瓜子又是從何而來?這還要歸功于農業育種。為了獲得更大更飽滿的瓜子,在農人的引導下,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一些愈發爽脆甘甜,另一些則始終綿軟寡淡,瓜瓤被種子搶盡風頭,連名字也從“西瓜”變成了“籽瓜”。
清朝光緒年間,籽瓜頻繁出現在全國各地的鄉土志中,得到的描述也大同小異,“味淡”、“瓤不堪食”、“子大而多”、“專取其子”……由于一切為種子服務,籽瓜瓤的口感和味道完全無法與水果店里的嫡親們相比,但綿軟清淡的特性也讓它成為了另一種風景:

到了收獲季,瓜農將籽瓜堆在路旁,供口渴的路人隨意取食。肉質松軟的籽瓜可以被徒手打開,免去了切瓜的麻煩;更為便利的是,由于糖度僅有西瓜的20%,人們還可以把打開的籽瓜分為兩半用:取一小半的瓤擦洗雙手,再用洗干凈的手挖食另一大半。
補充完水分,“吃瓜路人”把抖落的瓜子留給瓜農,雙方皆大歡喜。別的不說,光是“洗手”這一項神奇技能,就令西瓜望塵莫及。

在甘肅靖遠,七八月的田野是天地間最壯觀的“大珠小珠落玉盤”。作為籽瓜最重要的產區之一,豐收時節的靖遠往往給人一種錯位的荒誕感:最生硬的砂石里長出了最可愛的圓滾滾,最蒼涼的高原懷抱著最飽滿的果實。
幾個月后,這些果實的“果實”——大板黑瓜子,將會出現在遙遠城市的某戶人家,躺在茶幾上的干果盒里,參與全中國規模最大的社交活動——拜年。半生不熟的親戚之間話題用盡、陷入沉默時,幸好還有嗑瓜子的聲音,可以填滿冷場的空隙。
葵花籽:你們都說我瓜,其實我一點都不瓜
中國人嗑了幾百年的西瓜籽,在民國時期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對手——葵花籽。

明代,隨著地理大發現的推進、西方商團來華,向日葵作為觀賞植物登上了中國大陸。到了晚清,葵花籽的食用價值仍未被國人發掘,只是偶爾有“子生花中……可炒食”的記錄。直到民國初年,《呼蘭縣志》中才出現了“葵花,子可食,有論畝種之者”。新中國成立后,食用向日葵(食葵)和油用向日葵(油葵)在中國北方全面開花。
現在,說起“瓜子”,大部分人腦海中浮現出的形象,恐怕已經是瘦瘦長長、黑白條紋的葵花籽,而不是扁平黝黑的西瓜籽了。

比起真正的瓜子,葵花籽幾乎是個全方位作弊的選手。論口味,葵花籽的母親——食葵,可是世界五大油料作物之一的油葵的親姐妹,豐富的油脂時刻發出“真香警告”;論形狀,中間膨起、外殼帶有縱向棱柱的葵花籽比西瓜籽更好嗑、更不易斷;論采收難度,跟包藏種子的“葫蘆兄弟”比起來,頂著巨型花盤、將種子全部暴露在外的向日葵顯得極為慷慨。

像“吃魚吐刺”一樣,長久以來,嗑瓜子似乎是中國人的獨家秘技,但其實這項技能已經在“世界大同”的道路上走出很遠了。從西歐到北美,你都能在球場邊看到滿地瓜子皮,狼藉背后,是球迷和運動員們無處安放的焦慮。
“小眾”瓜子:古風、田園風、夏天的風
向日葵固然強勢,但“葫蘆兄弟”以量取勝。除了西瓜,吊瓜、南瓜也是貢獻卓著的“種子選手”。
西瓜已經在中國生活了至少一千年,然而最中國、最本土的瓜子,還要數吊瓜子,或“栝(guā)樓籽”,或“瓜簍籽”,或“果臝(lǔo)籽”……后三者顯然是同一個詞的發音變體,其中,“栝樓”成了學界認可的通用名。一個物種的名稱能頑強地流傳數千年,幾經迭代卻仍可溯源,可見栝樓在中國的根基之深。

故事還要從先秦時代說起。早在《詩經·豳風·東山》中,栝樓就以野草的形象出現了:“果臝之實,亦施于宇”,說的是一個遠征多年的戰士回到家,發現屋頂已經爬滿了栝樓。西漢的《禮記·月令》中提到,“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東漢的高誘為它添了一筆注釋,“王瓜,栝樓也”。
帶著“荒頹”和“繁盛”兩種看似矛盾的屬性,栝樓年年生、年年熟,讓我們嗑上了祖先嗑過的瓜子。
雖然吊瓜子名氣不大,主產區也只在浙江、安徽一帶,但在愛好者眼中,它是絲毫不遜色于西瓜籽、葵花籽的私心珍藏。吊瓜子的形狀比西瓜籽更立體,嗑的時候不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瓜子和兩排牙齒垂直;瓜仁雖小,勝在飽滿圓潤,比西瓜籽多一些油性,又比葵花籽少幾分燥氣。

“葫蘆兄弟”中,數南瓜與中國的交情最淺。南瓜的“訪華之路”與向日葵十分相似,明代嘉靖中葉開始,南瓜在中國史料中的存在感激增,《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了935種明代方志,其中118種提到了南瓜;而江蘇、安徽、山東、河北的南瓜記錄尤為豐富,讓人有理由相信,京杭大運河就是南瓜在中國的第一條“綠色通道”。
或許是有栝樓籽、西瓜籽的良好示范,中國人欣然接受了南瓜籽。清末,張之洞的父親——張锳主持纂修《興義府志》,其中就提到“郡人收其(南瓜)子炒食,以代西瓜子”,同一時期,上海、浙江一帶的方志也出現了南瓜籽“香美可食”的記述。到了民國,南瓜籽的人氣一路走高,到了“終年市于茶坊酒肆,人競買食之”的程度。

即使一直被視作西瓜籽的替代品,南瓜籽也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與“肉不堪食”的籽瓜、“籽不堪食”的西瓜不同,在南瓜籽的世界里,不僅有黑龍江寶清“大白板”這樣的專業產子選手,大部分蔬食南瓜也能做到“長肉結籽兩不誤”。
每一個從菜市場抱回整個南瓜的人,心底都藏著對南瓜籽的期待——畢竟,誰會拒絕“隨瓜贈送”的一大包零食呢?即使在離田園最遠的水泥城市,你也能找到無數個鋪著南瓜籽的廚房窗臺。
淘洗、晾干、熱鍋烘炒,自制瓜子的過程并不復雜,卻給人以一種莫名的收獲感。出鍋的瓜子雖然皺的皺、焦的焦,但齒縫間傳來一聲輕脆的“喀啦”、瓜仁香氣鉆進鼻孔的一瞬間,城市人還是滿意地發出了“我真是中華小當家”的感嘆。

海水之中,還藏著最特殊的“瓜子”。錐螺、尋氏肌蛤、虹光亮櫻蛤……在海鮮大排檔的菜單上,這些物種共享同一個名字:海瓜子。它們小巧、易食、平價,清水煮出鮮美,辣炒賦予風味,配上啤酒和晚風,就是一場親切踏實的夏天。

熱搜榜上的瓜一個接一個,吃得人心浮氣躁。與其讓時間在劃水摸魚中消磨殆盡,不如在陽臺上種一棵栝樓,用半年的光陰仔細感受“果臝在宇”的古老風情,或者栽一盆向日葵,讓自己獲得“抱著花盤吃瓜子”的有趣體驗。
- END -
文丨密林
封圖丨攝影/Dave Reede 圖/視覺中國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新人文浪潮計劃
簽約賬號【地道風物】原創內容
未經賬號授權,禁止隨意轉載
原標題:《中國人嗑瓜子簡史》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