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雙陽︱“文學叛徒”與“叛徒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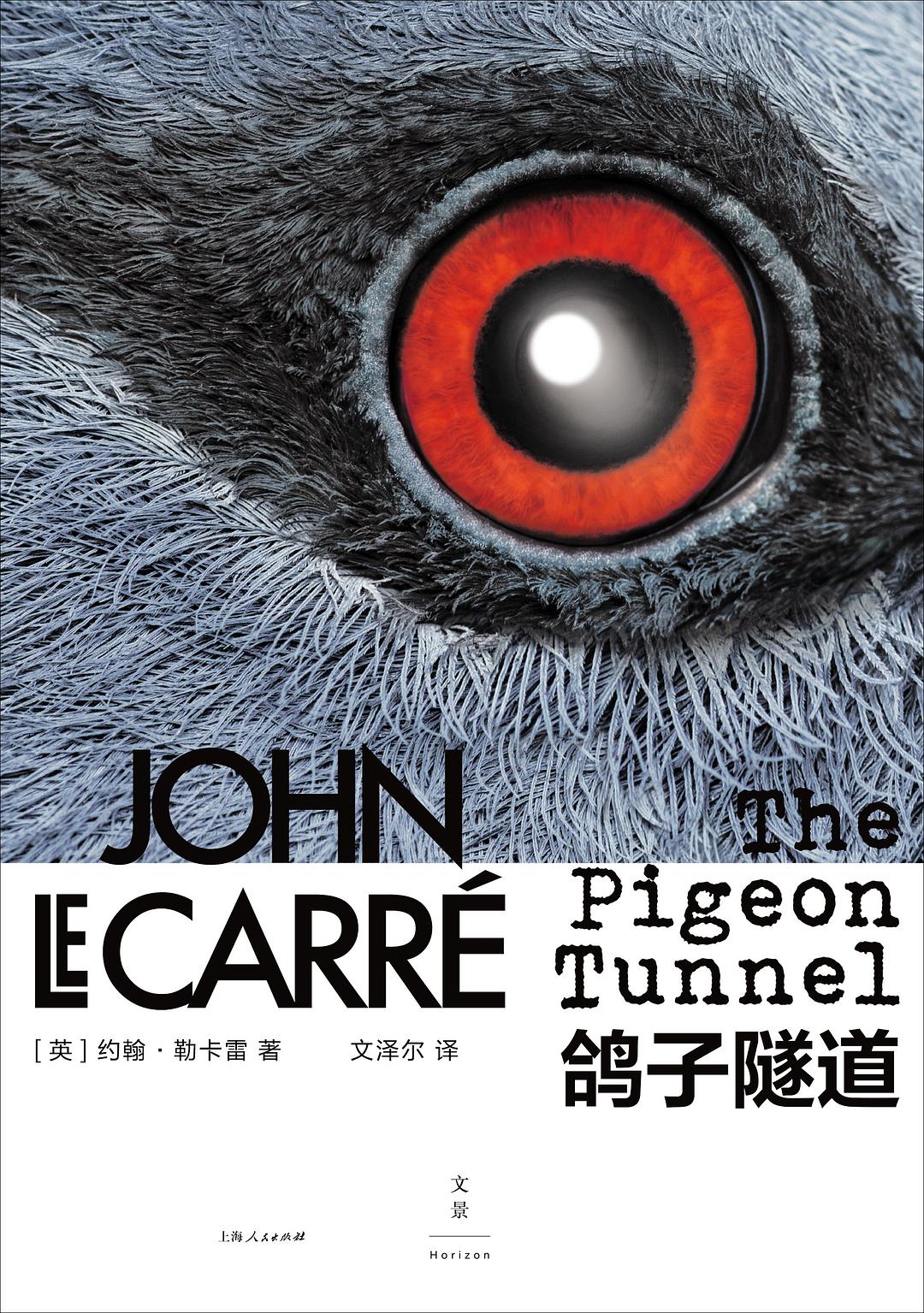
《鴿子隧道》,[英]約翰·勒卡雷著,文澤爾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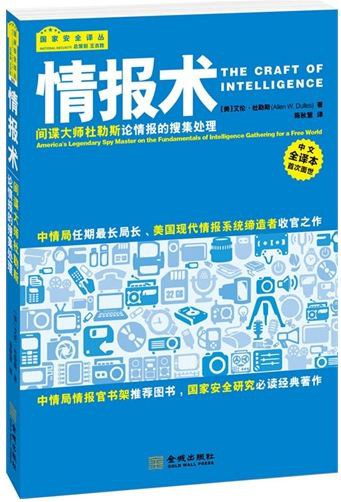
《情報術(shù):間諜大師杜勒斯論情報的搜集處理》,[美]艾倫·杜勒斯著,陳秋慧譯,金城出版社2014年1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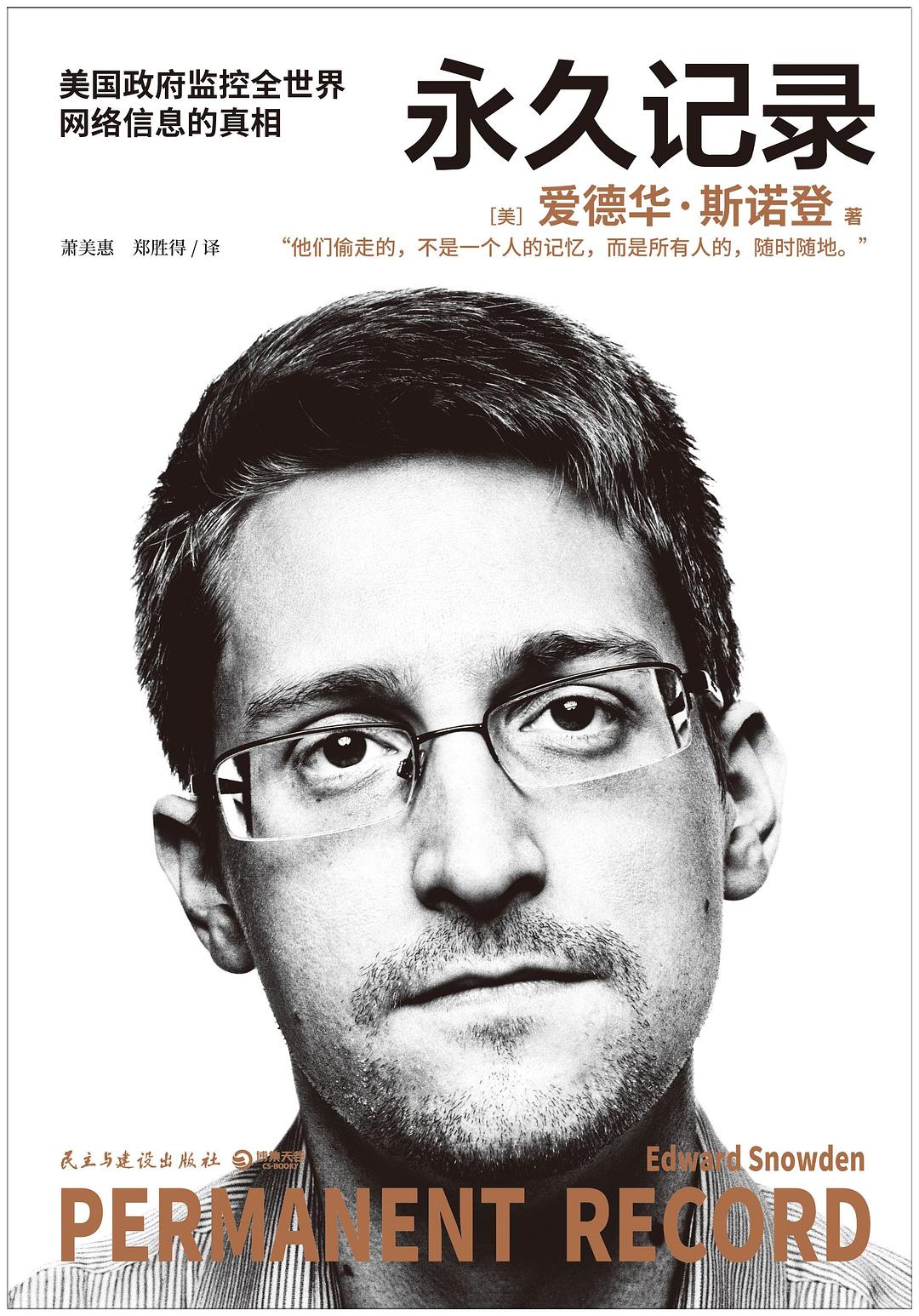
《永久記錄》,[美]愛德華·斯諾登著,蕭美慧、鄭勝得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能把自傳寫得像小說一樣精彩,即使對小說家來說也不是一件易事。英國間諜小說大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的自傳《鴿子隧道》(Pigeon Tunnel)算是不錯的樣板。他有一個名副其實的詐騙犯父親,在牛津大學研究過日耳曼文學,在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也即秘密情報局)都從事過貨真價實的情報工作,能夠轉(zhuǎn)型成為最成功的間諜小說作家,無疑是合乎“想象”的。
內(nèi)行寫內(nèi)行,有什么問題?在自傳的第一章,勒卡雷便記述了圍繞著自己的“叛徒”爭議——直至他的第三部作品也即成名作《柏林諜影》(1963)出版之時,他還是正式在編的英國情報官員,這一吸引讀者的身份,卻讓舊同事詬病不已。情報官員必須“守口如瓶”,不僅是工作要求,也是職業(yè)倫理。一部風格悲凄的富有“真實性”的暢銷書,哪怕是小說,也能讓無數(shù)讀者一窺聲名顯赫的情報機構(gòu)神秘厚重帷幕后的種種沉悶無聊和無情無恥,讓自己的“老東家”顏面盡失。因此,前國防部長憤斥勒卡雷為“共產(chǎn)黨間諜”,情報局官員稱他為“玷污了情報局榮譽”的“十足的混蛋”,前局長則嚴肅地指出他寫小說的“個人喜好”“使得情報局在招募合適官員和獲取資源上都變得更加困難了。他們讀他那些書,然后就打消了念頭。真是再合理不過的事”。勒卡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自嘲為從情報界轉(zhuǎn)向文學界的“叛徒”,但“與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風血雨的方式相比,寫作簡直像小孩玩積木一樣人畜無害。有多少處境困難的間諜希望愛德華·斯諾登當初選擇去寫小說啊”。這一定位,耐人尋味。
間諜與作家
勒卡雷不忘順便征引幾位經(jīng)歷近似的前輩——薩默塞特·毛姆,一戰(zhàn)期間作為知名作家被英國秘密情報部門招募為間諜,以個人切身經(jīng)歷為基礎寫成《英國特工》(又名《阿申登故事集》),被《泰晤士報》譽為“頭一部由親身經(jīng)歷并親力親為者創(chuàng)作的間諜小說”,結(jié)果被丘吉爾控訴他違反了《國家機密保護法》,導致毛姆燒毀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說,《英國特工》也成為毛姆一生當中創(chuàng)作的唯一一部間諜小說。小說家兼?zhèn)饔涀骷铱灯疹D·麥肯齊(Compton Mackenzie),曾在軍情六處擔任派駐希臘的情報主管,“他發(fā)現(xiàn)派給他的指令,還有他的上級經(jīng)常都很荒謬,作為一名作家,他理所當然地把這些都拿來作為取笑的素材”。1932年,他出版了帶有自傳性質(zhì)的《希臘回憶錄》,因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遭到起訴,最終只被罰款一百英鎊。書中“最糟糕之處在于……麥肯齊揭露了情報局通訊專用的一些符號,有些目前仍在使用”。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被勒卡雷稱為“軍情六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叛徒”,其《哈瓦那特派員》(又譯《我們在哈瓦那的人》)不少借鑒了他自身作為“弗里敦(塞拉利昂首都)特派員”的經(jīng)歷,據(jù)稱“利用戰(zhàn)時在軍情六處工作得來的工作經(jīng)驗,精準描繪了英國大使館情報主管與外勤特工之間的關系”。在《哈瓦那特派員》和《人性的因素》前言中,格林都得例行聲明自己“沒有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
英國情報部門人才鼎盛,簡直比名校文學系還多。經(jīng)常被拿來與勒卡雷作比的伊恩·弗萊明,也曾在軍情六處工作,實際主持過諜戰(zhàn)行動,并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007”的形象。007與史邁利的區(qū)別,既是弗萊明與勒卡雷的作品風格的區(qū)別,也是他們在情報工作中職位——“外勤特工”(operater)與“分析員”(analyst)的區(qū)別。當然,科幻式的孤膽英雄007離現(xiàn)實更遠,按照原美國中情局長艾倫·杜勒斯所言,“現(xiàn)在的情報紀律都要求其必須是不顯眼的那種人,摒棄奢華的生活,與可疑女性的緋聞以及其他這類轉(zhuǎn)移注意力的行為”。有一句毒評便是:詹姆斯·邦德不過是個英國政府的公務員。但弗萊明還是明智地讓自己遠離了“叛徒”的質(zhì)疑。此外,以《豺狼的日子》成名的弗雷德里克·福賽斯則在七十高齡才自己披露曾經(jīng)在軍情六處工作過二十多年,每一本小說出版前都經(jīng)過“審查”。
英國在現(xiàn)代小說史上無疑有著特別的地位,在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乃至政治驚悚小說上更是有開山之功,給世人帶來了許多樂趣。麥肯齊最后獲封爵位,格林被頒發(fā)了“大英功績勛章”,勒卡雷也被稱為“國寶級”的作家。其他渠道成長起來的間諜小說家中,沒有人能取得他們這般的成就。這無疑是一種值得研究的現(xiàn)象。
趣味與真實
在各種似是而非的“諜戰(zhàn)大片”和“大戲”密集轟炸之前,間諜小說是公認難寫的,其難點在于把握小說的趣味性和真實性,一般作者固然因其云遮霧罩而不得其門而入,行內(nèi)人也受到工作性質(zhì)、保密要求等種種限制。《英國特工》的譯者高健在譯后記中稱:
困難的原因就在于,寫這種作品所需要的生活與體驗一般無處去尋,除非作者本人便曾是此道中人,但即使是如此,并有過其切身實際的經(jīng)驗,這種經(jīng)驗也未必便一定能提供他多大便利,這又是因為諜報工作本身便常常是機械單調(diào)枯燥乏味的,不是材料來源的豐富供應場所。……情報工作的性質(zhì)本身便天然產(chǎn)生出它的許多特點:保密性大、透明度低、隔離性強、聯(lián)系方式的有限與單調(diào)以及分工上的過窄過細等。正因這樣,一名參加者由于其上下左右周圍己方與敵方的過多過繁的重重限制,其個人的了解內(nèi)容與范圍便常少得可憐,對不少情況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這段,而不知道那上段、中段、下段,更不必說那全過程。孤陋寡聞正是情報人員的一大本質(zhì)特點。處在這種情況下,情報小說好寫嗎?更不必說能寫好。別的不說,只趣味性一項便無法解決。這類小說的故事性與趣味性只可能是極弱的,沒有多大讀頭與寫頭……即使說(趣味性)這個問題已解決了,那真實感會是如何,可信性又將怎樣,也都不是好處理的,原因是這幾者之間常常是不一致的,彼此排斥,互相矛盾。
《英國特工》只是一本短篇故事集,不算太成功,譯者的論調(diào)也由此較為悲觀。毛姆自己的定位也左右搖擺,在再版前言中既稱“本書的依據(jù)是上次大戰(zhàn)期間我在情報部門時的經(jīng)歷見聞,后作了改編,以供人當小說看”,又夫子自道“總的來說一名諜報人員的工作乃是特別單調(diào)乏味的。其中絕大部分東西毫無用處,可供小說取材者更屬寥寥,即或偶爾有之,也是支離破碎,意義不大。如何使之具有連貫性、戲劇性或可信性,那就全憑其作者的一寫了”。從格林和勒卡雷的實踐看,他們顯然更好地解決了這一難題。格林《哈瓦那特派員》的主題——靠胡編亂造情報材料騙取錢財,便源自格林負責葡萄牙方面情報時的經(jīng)歷。勒卡雷的名作《鍋匠、裁縫、士兵、間諜》靈感則來自原秘密情報局級別最高的“鼴鼠”金·菲爾比叛逃的事件。雖然勒卡雷說過“蒼天在上,我所知道的秘密情報,少到根本沒辦法拿出來泄露的地步……我希望我的故事不要讀起來像是某個文學叛徒被揭露之后的偽裝,而是我自身想象力的產(chǎn)物,僅僅只是增加了一些用于渲染故事的真實而已”。如果認為他們依靠更多的是想象力而非職業(yè)生涯中的靈感的話,那也未免過于輕信了。
無疑,間諜工作是一座“富礦”,其中有多少黑幕與陰謀,多少謊言與欺騙,幾乎任何一場震驚世界的歷史政治事件,背后都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情報較量,也給后人留下了可以無限挖掘的空間。誠如杜勒斯所言,“雖然反情報活動的日常工作大多數(shù)比較辛苦且枯燥,但它那些復雜和微妙的行動卻很像是將全世界作為棋盤,進行著一場規(guī)模宏大的對弈”。沉浸其中的人難以自拔,不甘滿足的人別有懷抱,讀者則借此探奇消乏,不亦宜乎!
間諜工作對創(chuàng)作的一項意料之外的刺激是其中還包含著寫作訓練的內(nèi)容。情報官的產(chǎn)品多數(shù)是書面報告,從各種紛紜復雜的表象中梳理出有價值的情報線索、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甚至精準預測出未來的走向,最經(jīng)典者莫過于作為美國外交官的喬治·凱南一封改變了歐洲局勢的“長電報”——盡管后來的杜魯門政府根本沒有聽從凱南的意見。有個性的情報官員會在報告中加上有特色的個人評論。菲爾比在《我的無聲戰(zhàn)爭》中說,“(格林)在寄來的信件(報告)中發(fā)表的尖刻的評論,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復”。更令人莞爾的是,勒卡雷稱,“我受過最嚴謹?shù)膶懽饔柧殻⒎莵碜匀魏沃袑W老師或者大學教授,更不是從寫作專業(yè)學校那里學來;它來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區(qū),來自軍情五處總部頂樓那些受過古典式教育的高級官員。他們一副幸災樂禍的老學究模樣,抓起我的報告,對我那些炫耀式的從句和毫無必要的副詞表達了極力的藐視。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頁邊空白處打上分數(shù),以及諸如‘行文累贅——注意省略——論證缺失——結(jié)論草率——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之類的評論。我遇到過的編輯們都沒他們這般嚴苛,或者說沒他們這般正確”。杜勒斯則指出,雖然情報人員都宣誓不向任何未授權(quán)的人包括妻子或友人透露任期內(nèi)的工作內(nèi)容,這份工作也有一些優(yōu)勢,“某種程度上它促使人們表現(xiàn)出一定的創(chuàng)造力,幫助他們培育業(yè)余興趣愛好,提醒他們關心工作以外的事物。我回想起有位杰出的情報人員就有栽培蘭花的愛好,也有人寫小說和神話故事,還有些在業(yè)余時間熱衷于音樂和美術(shù)”。正是在杜勒斯任內(nèi),中情局資助了奧威爾的小說《動物農(nóng)莊》拍攝成電影,還資助了《日瓦戈醫(yī)生》的出版。彼得·芬恩與彼得拉·庫維合著的《日瓦戈事件:克里姆林宮、中央情報局和為一本禁書展開的戰(zhàn)斗》中說,“冷戰(zhàn)期間,中情局喜愛文學——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喬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納博科夫。書就是武器,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在蘇聯(lián)或東歐不可得或被禁了,就能用作宣傳,以挑戰(zhàn)蘇聯(lián)所宣傳的現(xiàn)實”。
“泄密”與“解密”
如果把非虛構(gòu)作品也算入的話,情報部門的“作家”就更數(shù)不勝數(shù)了。雖然標準格式應該是“本書不含機密信息,不揭露秘密,不暴露丑聞”(帕特·霍爾特《秘密情報與公共政策》),但曾經(jīng)宣誓一輩子要“守口如瓶”的人,往往也有在機遇或是危機出現(xiàn)時“找個樹洞”或“藏諸名山”的沖動。典型者如荷蘭“納粹克星”奧萊斯特·平托的《我的反間諜生涯》,被菲爾比稱為“最能干、最富有洞察力的情報官員”的斯威特·埃斯科特的《貝克街特工隊》、因在澳大利亞出書被英國政府告上外國法庭的彼得·賴特《抓間諜者》,非典型者如曾被中國抓捕過的美國間諜李克和李又安夫婦的《解放的囚徒》(中譯更名為《兩個美國間諜的自述》);被美國抓捕受審的蘇聯(lián)“千面特工”魯?shù)婪颉ぐ⒇悹柋粌蓢粨Q釋放后,其辯護律師唐納文根據(jù)這段奇特經(jīng)歷,出版了一本名為《橋上的陌生人》的回憶錄,成為電影《間諜之橋》的原型。
出身普林斯頓大學文學碩士的杜勒斯本人雖然推崇保密,但也不禁技癢,出版了《情報術(shù)》(The Craft of Intelligence)等半是“自述”半是“專業(yè)教材”的書籍,考證華盛頓總統(tǒng)手下的兩名情報人員布迪諾特(Boudinot)和塔爾米奇(Tallmage)都寫過回憶錄(可能是最早的情報人員回憶錄了),揭秘“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的丹尼爾·笛福原來曾經(jīng)擔任“一個有組織的英國情報系統(tǒng)的首任主管……這在他去世多年后廣為人知”——
毫無疑問的是,笛福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也是因為根深蒂固的保密意識,他在書中謹慎地避開寫到任何自己所知道的現(xiàn)實中的間諜活動……作為一個小說家,笛福超越了與情報術(shù)不相符的創(chuàng)作。
杜勒斯將間諜按意識形態(tài)、陰謀、唯利是圖、上當受騙等動機分為幾類,而將“小說中的間諜”作為單獨一類。即便如此,他還是覺得弗萊明的《女王密使》“讓我讀得相當過癮”,而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最為引人入勝——都是描寫間諜、線人以及叛徒心理動機的故事”,批評格林的小說《文靜的美國人》加深了國內(nèi)外對美國特工的偏見——“其中之一便是:美國官員有點像不實際的社會改良家,也有點像傳教士,堅持用自己的方式來插手他并不是很了解的事情。”杜勒斯還認為,大多數(shù)人是從未窺見內(nèi)幕的作家寫成的所謂內(nèi)幕故事當中獲取信息的,不必把本是常識或者對友人、對手都不言自明的事情弄得神秘兮兮。他舉例道,原來中央情報局門口掛的是“政府印刷局”的牌子,但華盛頓的觀光車向?qū)看味紩陂T口停車,喋喋不休地向游客介紹“華盛頓最秘密、隱藏得最好的地方,美國間諜組織的總部”,當他改掛了“中央情報局”的牌子后,觀光車就再也不來了。
也許是受惠于這一政策,加上美國日益成為“世界陰謀的中心”,美國情報“作家群”終于接棒英國后來居上。典型者如因參與“水門事件”而臭名昭著的中情局特工霍華德·亨特,黯然離職后筆耕不輟,一生居然共出版了八十多部間諜小說(似乎從未引進國內(nèi)),成為曾任中情局長的理查德·赫爾姆斯最愛的小說家,離世后還有回憶錄《美國間諜:我在中情局、水門大廈和其他地方的秘密歷史》出版。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副局長馬克·費爾特退休后出版了影響不大的《在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金字塔里》,直到九十高齡才承認自己就是當年“水門事件”中的“深喉”,又出版了《特工人生——“深喉”回憶錄》。他的“競爭對手”、另一副局長威廉·沙利文則口述出版了《我在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三十年》。記者托馬斯·鮑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曾任中情局長的理查德·赫爾姆斯為主角采寫了《守口如瓶的人》,他通過采訪了四十多位前官員,吃驚地發(fā)現(xiàn):
中央情報局的人非常愿意介紹自己的經(jīng)歷,這部分原因是其中有很多人已自1973年起陸續(xù)退休,聳人聽聞的通欄新聞,公眾的批評以及長時間的深思,使他們變得談鋒極健,而主要原因是,中央情報局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對公眾的誤解深感痛心。他們一方面慣于保守機密,另一方面則又急欲作出解釋,兩方面相持不下,后者似乎終于占了上風。
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蘇聯(lián)和東歐“檔案解密”成為熱潮,原來的“禁區(qū)”隨之解體,眾多特工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一大批“有故事的人”則撰寫了一批“紀實”作品,一時蔚為大觀,如原蘇聯(lián)國家情報局副局長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的《情報機關與克里姆林宮》、瓦季姆·巴卡京《擺脫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憶錄》、博布科夫《克格勃與政權(quán)——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回憶錄》、原克格勃對外反間諜局局長的卡盧金的《克格勃第一總局》、克留奇科夫《個人檔案:蘇聯(lián)克格勃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獄中自述》、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情報總局局長馬庫斯·沃爾夫的《隱面人》等等,作者立場各異,文筆參差,勝在“親歷”(當然也難免藏頭露尾、道聽途說),總體基調(diào)是“我和我的部門做得很好,垮臺都是別人搞砸的”。“911”事件之后,反恐情報失敗成為共識,2005年一篇《美國前特工掀起出書熱》的報道中一氣列出了六本回憶錄性質(zhì)作品,共同基調(diào)則是“描繪中情局內(nèi)領導失敗,各部門內(nèi)紛爭不斷,不愿在政治上承擔更大風險”,可謂風水輪轉(zhuǎn),各擅勝場,都是亂世一景。有意味的是,這么多“內(nèi)部人”的頻頻“揭秘”,撒落“一地雞毛”的多,揭出驚天動地的真相或丑聞卻幾乎沒有,讀者寄望其揭發(fā)“黑幕”,作者本人則執(zhí)著于為自己樹碑立傳、涂脂抹粉,這倒是從另一方面證明了高健“孤陋寡聞正是情報人員的一大本質(zhì)特點”的妙論了。“靠想象力”的小說家仍然不乏生存空間,勒卡雷、福賽斯、陸伯倫、克蘭西等作家以及好萊塢等都及時從冷戰(zhàn)轉(zhuǎn)型到反恐題材,收獲累累碩果。
當然,在間諜世界里,“真實”與“造假”本身就界線模糊的,沒有比他們更明白“懺悔錄”的雙關性的了,“泄密”有風險,盡信“解密”則幼稚。法國小說家莫爾迪諾在其小說《夜巡》中臆造了一本《叛徒文選:從阿爾西比亞德到德雷福斯》,存心置讀者于虛實之間。毛姆當年就發(fā)現(xiàn)“(《英國特工》)此書僅是一部虛構(gòu)之作,雖說據(jù)我看來,其虛構(gòu)程度也未必便更甚于目前號稱為實錄的若干同類作品,這些近年來坊間確曾出過不少”。勒卡雷更指責,許多前情報官員“獲得批準”的回憶錄實際上都是為了給情報局披上一張羊皮,以此換取他們希望獲得的贊許;而所謂“官方發(fā)行的正史”,其實是給那些十惡不赦的罪行罩上懇求寬恕的面紗。讀“口述歷史”者,不可不鑒之。
背叛與效忠
與“文學叛徒”相比,最有爭議的作品還屬真正的“叛徒”的作品,更是間諜戰(zhàn)中的“另類武器”。最典型者莫過于菲爾比叛逃蘇聯(lián)后出版了《我的無聲戰(zhàn)爭》(1967,在中國曾以《諜海余生記:菲爾比自述》為名出版)。菲爾比在前言中強調(diào)了自己三十多年不變的信仰,并引用了格林小說《密使》中的一段話表達自己“一旦選中一方就絕不改變”的心理。此書后在英國順利出版,格林在英國版序言中投桃報李地說“他(菲爾比)背叛了自己的祖國——是的,他可能是背叛了,但是,在你我諸君之中,有哪位不曾對比國家更為重要的事或人有過背叛行為呢?在菲爾比本人看來,他投身的是要改變現(xiàn)狀以利祖國的事業(yè)。”菲爾比還曾想邀請勒卡雷寫作續(xù)集。對此,英美無疑深受打擊,好在“叛逃”總是相互的,1970年,美國便拋出了“王炸”——《赫魯曉夫回憶錄》,其分量令一切間諜都啞然失色,其后還有原克格勃特工處上尉阿列克謝·米亞科夫《克格勃內(nèi)幕》、原蘇聯(lián)高級外交官、聯(lián)合國副秘書長舍甫琴科的《與莫斯科決裂》等等,形成了壓制性優(yōu)勢。勒卡雷在《鴿子隧道》里意味深長地提到:
由克格勃控制的《蘇聯(lián)文學報》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掌控的《文匯》這兩大戰(zhàn)壕,各盡職責地互相扔炸彈,心里明明清楚,在枯燥無味的文字邏輯戰(zhàn)里唇槍舌劍,根本不可能有哪一方最終獲勝。
在中國,“叛徒文學”也自有其龐大體系和復雜源流。“中共最危險的叛徒”顧順章投敵之后,一連寫了數(shù)本密切結(jié)合自身經(jīng)歷實踐的特工教材,成為國民黨中的“培訓專家”。抗戰(zhàn)中的“大漢奸”陳公博、周佛海,都曾留下《苦笑錄》《往矣集》之類作品,卻巧妙地將人生記錄截止“七七事變”之前,試圖來日為自己“留史”“洗刷”。新中國成立之后,周恩來組織大量“戰(zhàn)犯”撰寫自述材料,要求必須遵守“三親原則”(親歷,親見,親聞)并力求事實相對客觀,留下了著名的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叢書》。原軍統(tǒng)特務沈醉,一躍成為名作家,卻被臺灣方面痛斥。另一邊廂的中共“叛徒”如張國燾、“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等也以回憶錄形式為“革命”留下了反面案例材料。臺灣方面的“軍統(tǒng)老人”陳恭澍、李世杰等,寫下《英雄無名》《調(diào)查局研究》等紀實作品,以求解決自己的“變節(jié)”“匪諜”嫌疑。“文革”中,圍繞“黨內(nèi)叛徒問題”,帶出李秀成自述、瞿秋白自述等歷史資料問題,成為政治熱點,大量“被審查者”也紛紛寫下自述材料,被要求“不準丑表功、不準攀領導、不準埋釘子”(見《李一氓回憶錄》),恢復名譽后成為自身回憶錄的“雛形”,可謂五味雜陳。還有一類作品,往往作于塵埃落定之時,雖然自我吹噓美化、歪曲事實、詆毀對手甚至思想“放毒”都在所難免,但勇于披露私密,揭舉矛盾,也由此把握了另一種“真實”,堪與“正史”相發(fā)明。
從孫武提出“五間”理論至今,間諜世界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國家安全局外包公司分析員”斯諾登橫空出世后,他的回憶錄《永久記錄》也已出版,書中稱“我這一代不只是重新設計情報工作,我們?nèi)嬷匦露x情報。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秘密會晤或暗中交換消息,而是數(shù)據(jù)”。但不管世界如何變化,人心人性總是不變的,在權(quán)力與欲望的陰影籠罩下,“背叛”與“效忠”的戲碼總在不斷上映,此處的叛徒,也許就是彼處的英雄,今天的鮮花,也許就是明天的懸劍,還是以勒卡雷的話作結(jié)吧:“間諜生涯和小說寫作其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兩者都要隨時準備好去窺視人類的罪過,以及通往背叛的種種途徑。”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