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趙園談學術與寫作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到明清之際,再折回當代史,趙園回顧自己的學術歷程,可以說在每個方向上無不全力以赴。雖成績不同,評價有別,每當投入一個陌生的領域,都有動機、動力,研究過程中有熱情與興奮,每次選擇都不曾違拗個人意愿,有非如此選擇不可的理由。
稍有重量的論著都有故事,都有“文本內外”。在這篇訪談中,趙園將與我們分享她游走于文史之間的學術甘苦,及溢出學術之外的現實關切。知人論世,對她而言是無限期的功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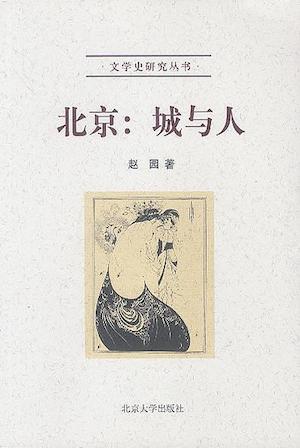
學術起點中往往包蘊著一個學者畢生與之糾纏不清的一些基本問題,不論他以后如何偏離原有的學術軌跡,仍會忍不住折返回來重新作答。在您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是否也埋藏著一些貫穿始終的問題線索,您是如何摸索出適合自己的研究路徑?
趙園: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還不大有學術自覺。當時的情況是,我周圍涉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知識分子的“道路與命運”作為研究課題——自然與剛剛結束的“文革”相關。既清理歷史,也是自我梳理,只不過路徑互有不同而已。我是將這一方向的考察貫穿始終的一個。至于問題意識,仍然不出“道路”“命運”之類是吧,盡管這種說法比較老舊。碩士論文最初的選題,就是現代文學中的知識分子。碩士論文格局狹小,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這樣龐大的主題無從展開。倉促間改寫老舍,為一些年后的《北京:城與人》作了準備,卻是當年不曾想到的。由此看,你的選題是否有所謂的“生長點”,還要看機緣。
畢業后一邊鋪開了寫《艱難的選擇》,一邊寫小說家論(《艱難》中也有個案即作品分析)。此后的路徑于此形成:由文集入手,綜論與個案分析并行,無論《城與人》《地之子》,還是關于明清之際的五部學術作品,直至關于當代史的考察。這種路徑似乎也未經設計,大約與“由文集入手”有關。當時我的同學,有的是謹遵王瑤先生的指導,先翻閱舊期刊的。大歷史中的個人,始終對我有強大的吸引力。
您曾說“沒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研究,沒有自我反省可能的研究,其最佳命運,是作為思想及語言化石擺放在學術陳列館中”。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一直在急遽變化中。我們回過頭去讀上世紀八十年代公認的學術經典,在語氣、語調上已覺得有些隔膜,很難進入。八十年代共通的問題意識與表述方式,是否也在您早期的學術著作中多少留下了一些痕跡?您是如何從八十年代的氛圍與腔調中掙脫出來,不讓自己的語言、思想過早定型、僵化?
趙園:八十年代曾經共享的一套概念系統、表述方式、分析工具等等的被廢棄,讀自己的舊作就不難發現。我讀《艱難的選擇》就有隔世之感。由一個角度,那一套概念系統、表述方式、分析工具也是歷史的印跡。最先忘掉的,是你曾經怎樣書寫與言說,往往要賴文學藝術的提醒。你曾經怎樣書寫與言說,是否也有可能作為分析材料?其實那本書并不屬于“典型的”八十年代作品,不大適合以“年代”歸類。走出八十年代的學術氛圍,與此后選擇的研究對象、也與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學術轉型有關。我們或許還會談到。

把歷史集中在人那里,是您擅長的學術路徑。如今強調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導向,作家論似被視為過時的文章體式。事實上,作家論極考驗研究者對歷史中人的整體把握。要把作家論寫活了,絕非易事。近三十年來“重寫文學史”的潮流打亂了現代作家的座次表。在現代作家與文學流派中,您應該也有個人偏好,哪些人的文字、品性更跟您“投緣”?我注意到魯迅在您個人閱讀史中的特殊位置,他是否構成了您思想底色的一部分?
趙園:由“后‘文革’時期”起步進入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代,似乎有對“左翼”的偏好。我選的“小說十家”,七家為左翼作家。事后看來,對張愛玲、沈從文以至凌叔華,持論均不免于苛。寫張愛玲的一篇,題目就未出左翼視野。當年的我曾經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不能容忍對于魯迅的任何非議,態度之偏激,幾十年后回想,會覺得不可思議。圍繞“兩個口號”(“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爭,我的傾向之明確,像是沒有脫出“文革”中派仗的情境,選邊站隊。但偏執中何嘗沒有年輕人的熱情!偏激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就我而言,在漸趨平和之后,那種偏激,偏執,“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確是曾經年輕過的一份證明。
確如你所說,對魯迅的閱讀,構成了我“思想底色”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如此。只不過認知仍有變化罷了。八十年代初讀研,夏濟安的魯迅論,張灝的“幽黯意識”,要費一點力氣才能適應。人性的幽黯處,原先的那種二分的視野中,是沒有位置的。尤其關于魯迅。讀夏志清小說史的論張愛玲、沈從文,有觸動,卻也說不上震動。我更相信自己的閱讀感受。盡管“感覺”“印象”在那個西潮(其時的“新學”)滾滾而來的年代,已是“舊派”“老派”的標記。“趨新”(亦“趨時”)從來超出了我的能力。對陌生的學術資源、理論,卻非但不排斥,而且始終保有了吸納的愿望。盡管依我的天資,對有些理論,的確難以理解那奧義。
“文革”期間讀魯迅之后,初入中國現代文學專業,最先吸引了我的,是有舊式文人氣息的郁達夫。深厚的舊學修養而能出之以暢達的白話,氣質像極了活在現代的古人,卻又有與時代的親密關系:由左翼到抗戰。見人見事之明,則如對周氏兄弟,對“廣州事情”。睿智犀利,奇思妙解。種種似矛盾不相容的東西,在一個人那里攪拌在一處。至于文字,郁達夫的瀟灑,既關性情,更緣學養。許子東的早期著作之后,對郁達夫其人其文,似乎沒有見到更精彩的分析;是否也因為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專業人士,古典文學的修養普遍較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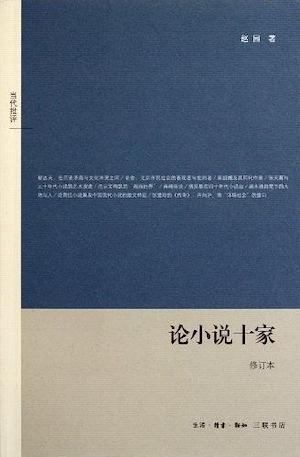
《北京:城與人》是您社會影響面較大的一本書。您對城市的觀察與省思,不限于學術研究層面,還曾以學者身份參與到城市建設與改造的社會討論中。能否談談您在城市這個公共話題上“溢出”學術研究的那部分工作,如何把北京變為“自己的城市”。
趙園:《北京:城與人》完竣是1988年,因故于1991年才面世——對于這本書,或許時機剛剛好。九十年代開始,“老北京熱”“胡同熱”升溫,這本溫和平淡的書意外走紅。這本書作為分析材料的八十年代最初幾年發表的“京味小說”,重又引起關注。此后京味話劇、京味影視大熱,迄今熱度未減。寫《城與人》,不曾下過文獻工夫,不免單薄,只是較為單純地討論小說、借小說略及老北京文化的書,卻受邀出席了北京市政當局主持的關于北京城市建設、改造的會議。書的命運,書的故事,有非作者所能預料者,這也是一例。這本書之后,自以為負有對城市建設/改造批評、建言的責任,發表了系列文章在《中華讀書報》上(后收入隨筆集《世事蒼茫》)。當然,人微言輕,不過自說自話而已。但我得說,即使有上述的以及后續的“緣”,也不以為北京是“自己的城市”,盡管在這里居住時間最久。這是另一個話題,不便在這里展開。
《地之子》的寫作,似緣于某種鄉土情結。這種斬不斷的鄉土情結,及對“三農”問題的關切,日益淡出知識青年的視野。即便出身鄉土或來自小城鎮的年輕學子,所焦慮的是如何抹去自己身上的土氣,盡快在城市扎根。在《城與人》與《地之子》中,無疑融入您對城鄉關系的觀察與思考,能否談談您壓在紙背的關懷?
趙園:寫《地之子》,選題的確更出于個人情懷。著手時,我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已然乏力。該書幾乎沒有引起反響,也因盡管“文革”后每年高層的一號文件照例關于農業,公眾對于農村、農業、農民的關注度已經大不如前。我成長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會關心氣象對農作物的影響,農業收成的豐歉,尤其在三年自然災害之后。時下的年輕人何嘗有這份閑心。
《城與人》《地之子》,有一代人文化記憶、歷史記憶中的城市與鄉村。1949年之前城市發展雖然并不充分,卻有上海這樣的國際性大都會。1949年以來有城市的鄉村化(城鄉的某種同構),“文革”后又有城市的“再城市化”。“改革開放”之初,老派北京人曾有過對市場化的柔性抵抗。我看到鬧市區有商業價值的沿街房舍遲遲不變身商鋪。由汪曾祺那里聽到一種老北京人的說法,“窮忍著,富耐著,睡不著瞇著”。于今看來,這種態度自有可貴的一面。
對鄉村的關注,除了是一種文化感情,也因無論對“革命”還是“現代化”,鄉村都犧牲太大,且是一再地被犧牲。這種社會不公令人不能無視。這也是難以在這里展開的話題。

1938年內遷至成都的卞之琳寫了一篇短文,題為《地圖在動》。他說中國人向來安土重遷,對地圖不感興趣,但戰事一起,沉睡的中國地圖逐漸動起來。抗戰造成的社會流動,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也改變了邊地的文化面貌。您向來關注“流動中的人事”,是否源于某種個人經驗?
趙園:回答一位年輕同行的訪談,我提到了三四十年代由戰爭引起的社會流動。曾經與陸建德聊到他家當時隨浙大的遷徙,他說自己兄長的名字多取自貴州的地名。我說我家也一樣,只不過他們是向西南,我們則向西北。令我不解的是,明清之際永歷小朝廷向西南的流動,留下的痕跡,如陳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寫到的,何以抗戰之后,無論西南還是西北,都長期延續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
2009年,與幾位友人有西北之行,當地的朋友安排看了蘭園——蘭州的青少年宮。后來又由天水師院的教師陪同去了父親在該地國立第十中學任教的清水縣。校址還在,校內有國立十中老校友立的紀念碑。國立第十中學是面向河南的流亡學生的。當時的大后方,無論西南還是西北,除西南聯大、浙大等等高校外,還應當有相當多類似的流亡中學。近年來被較多談論的,有文物的大規模南遷,更有西南聯大。國民政府在戰亂中對教育、文化的重視,豈不令人感動?
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后,北大、清華相繼南遷,燕京、輔仁等教會大學成為淪陷區中的“孤島”。淪陷區并非鐵板一塊、密不透風,其與大后方、解放區之間仍有信息、人員的流動。您如何看待燕京大學這樣的教會大學在戰時發揮的作用?
趙園:在《中華讀書報》2017年11月1日第十七版讀到侯仁之的哲嗣記述北京淪陷后,在燕京大學得司徒雷登校長與美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支持,送學生赴大后方與解放區的往事。西南聯大、西北聯大、浙大外,燕京大學有同樣可歌可泣的故事。至于燕京大學在戰時發揮的作用,我不曾專題考察,應當是如你這樣的年輕學者可以選擇的題目。
去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新京報·書評周刊》及上海《文匯學人》發表了系列紀念文章,聚焦于這一歷史瞬間,以人物志的方式,呈現出五四時代新舊之間更復雜的思想光譜。除了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此前關注不夠的老輩學人甚至舊派人物都被喚回“五四”的歷史舞臺。您認為百年后我們應該如何紀念五四,書寫五四,才能充分釋放出這一歷史瞬間的思想活力?
趙園:2019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媒體的言述策略,就包括了敘述處在該時間點的人物。我接觸的有數的幾種報紙,《新京報·書評周刊》的人物志與紀念特刊,發表了系列人物記述計十八篇。系列文章涉及的,既有運動中的風云人物,也有與運動無涉的人物,或關系不甚直接、較為邊緣的人物,如張元濟;以至舊派人物,包括前清遺老如那桐。逐一考察處在某一“歷史瞬間”的人物,以日記、書信等等為基礎性材料,以年(1919)或以日(5月4日)為單位。這種考察方式,應當有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影響。某篇的寫法,多少有點像我的《那一個歷史瞬間》(《想象與敘述》)。
人物志作為史學方式,有廣泛的適用性。1919年——或不限于該年的新文化運動中——的梁漱溟、陳寅恪、陳垣、熊十力、馬一浮、錢基博等等,五四人物志都不應當遺漏。上述文化人、知識人,似乎不宜于僅僅在新文化/舊文化的坐標上定位。將2019年報刊所載五四人物記述輯為一編,想必可觀,可補陳平原、夏曉虹主編的《觸摸五四: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所未及,或多或少改變、豐富對于1919、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想象與認知(五四運動中的小學生、伶界、青樓、幫會、囚犯等,參看陳占彪《五四細節》,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不惟1919、五四,中國現當代史宜于像上面所講的那樣打開的,還有其他“歷史瞬間”。1930年的“中國之一日”征文活動,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文革”,就屬于類似架構。由這點看,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僅僅就結構、敘述方式看,難言“創發”,只不過使用類似的方式,所成就者互有不同罷了。
中國傳統史學原本有紀傳一體。正史的紀傳以《史》《漢》為摹本,往往介于文史之間(尤其承《史記》一脈者)。一段歷史,由眾多人物傳記構成(傳統史學的體例不限于紀傳,尚有志、表等,補紀傳所未及)。這種散點式的敘事結構,自然有其利弊。“通史”一體興起,其線性敘事另有利弊。平衡點、線、面,似乎還缺少佳構。我們的視野被已有的學術研究限定,也像是一種宿命。打破這種宿命,我還不敢寄希望于年輕學人。
考察五四,有些點,非確實下過工夫,不會注意到。即如陳平原所說的,大學階段的政治激情與社會活動,影響了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們的一生(《新京報·書評周刊》,2019年5月4日B9版)。由此看,五四運動不僅為共產黨準備了“干部條件”,影響于文化史學術史,也不可小視。此外學運的“后遺癥”,也應當作為五四考察的一部分。蔡元培當時就想到,北大“今后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西潮與新潮》,引自《新京報·書評周刊》,2019年4月27日B9版)。民國時期學潮頻起,與五四運動的示范效應當不無關系。
難以復原“五四”時代的全景,其實受制于學科邊界及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現代文學研究者與他的研究對象之間,多少存在著學養上的不對等。現代中國的文史之學,可以說是“不古不今、非東非西”之學。面對從舊學中掙脫出來,又從西學中汲取養分的五四人物,我們通過專業訓練積累的知識庫存嚴重不足,平日的閱讀儲備無論中學還是西學都難以與“五四”一代打成平手。如何才能跟我們的研究對象建立一種相對平等的對話關系?
趙園:大陸治中國現當代文學者,大多甚至讀不懂淺近的文言,更無論重要典籍。以這樣的知識基礎研究五四,研究前五四,限制太大。1949年后語文教育的積弊,到了“信息時代”更難以補救。專業圈內似乎也少有人意圖補救。小有成就者固然不屑于這種不急之務,年輕學人忙于立項,爭取學術資源,心思更用于揣摩,但求速化,何嘗肯下一點笨功夫。一仍舊貫,陳陳相因,不難做出中規中矩的所謂“論文”,也就不會有危機感,感受到壓力。這也可以歸為時下所說的“舒適圈”的吧。
較之《新京報》上較為“文藝范兒”的文字,上海《文匯學人》關于張元濟的敘述更有分量(見該刊2019年4月19日第5至7版)。五四時期新舊交接、纏繞,有些議題、人物,非兼通古今者則不能應對。一個時間跨度僅三十年的專業,從業者據說有數千人,不能應對的議題如此之多,確實有點可悲。且不必侈談“跨界”,先將這一界與其前其后(尤其其前)打通,如何?
“五四”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基石。長期以來這塊奠基石過于穩固,以致我們仿佛忽略了它的存在。當“五四”的價值與歷史定位受到各方質疑,逐漸松動時,既給現代文學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而在危機當中或也蘊涵著自我更新的生機。您如何看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正在面臨的,以及將來面臨的挑戰,尤其是來自近代史研究的挑戰?
趙園: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沖擊不止由“傳統文化”的方面,也來自史學考察的深入,即如關于北洋政府、“二十一條”的新的發現與闡釋(其中有臺灣學者唐啟華的相關研究)。致使這一學科的專業基礎被撼動的,還有來自近代史專家關于革命史的再發現與再敘述。倘若相關史料進一步披露,勢必對中國現代文學專業造成沖擊。以我的觀察,這個專業并不具備應對沖擊的能力,即如重新審視專業的諸種預設,重構學科框架。“文革”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研究者趨“冷”(冷門議題、邊緣作家等),與剛剛成為過去的那段歷史自然相關。“去政治”“告別革命”成為時尚;回頭看,不免淺薄且一廂情愿。
就學科建制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夾在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僅有三十年的跨度,給研究者的施展空間相對有限。從研究對象中得到的回饋與給養,也不及業已經典化的古代文學。從您這一輩開始,已有“走出”現代文學的趨向,各有各的出口,有的進入當代,有的上溯晚清,有的走向學術思想史、教育史,當然您更決絕,走得更遠。您認為現代文學出身的年輕學人,如果不當“逃兵”,一走了之的話,該如何在立足現代、立足文學的同時,打開自己的研究視野與發展空間?
趙園:由于“溯源”合法性論證的需要,中國現代文學盡管時間起止僅有三十余年(1917-1949),不但不能與古代文學,且不能與尚在延伸中的當代文學相比,作為學科,體制內的定位卻并不在古代文學、當代文學之下,同屬作為一級學科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即使如此,你仍然不能不感到來自古代文學的壓力(時長、人才狀況、遠為深厚的學術積累,等等)。在社科院文學所,現代室與古代、當代、理論諸室同屬大室,至少沒有顯性的學科歧視。這也應當與學科曾經擁有的實力有關。八十年代以降,中國現代文學風光不再,漸漸失去對于人才的吸引力。學科趨于封閉,學術成果“內部循環”,難以對學術界、讀書界發揮影響力。
制度化的文學史(以及一般歷史)的分期,本不應當成為選題時的考量。近代、現代、當代的分期尤其如此。近代史專家早已進入“當代”,且深度進入,如楊奎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忍不住的關懷》《“邊緣人”紀事》,沈志華關于朝鮮戰爭,關于中蘇交惡,關于反右的研究。惟文學研究者才能提供的當代考察,賴有當代題材的文學作品。這一部分“史料”,史學家還不曾利用。值得開發的,就有文學文本內外的當代史。我注意到的確有年輕人在做這種開發,只是認為他們應當留心洪子誠先生的如下提醒:“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在挖掘‘十七年’文學經驗上成為熱點”;十七年文學“在它行進的當時,就不斷有從內部進行反思、檢討的情況發生。回到‘十七年文學’展開的歷史情境,設若回避、剝離這些已經一再被反思、檢討的問題,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做法”(《內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問題》,《讀書》雜志2019年十二期)。近期受訪的時候,黃子平對部分年輕人取向的批評有更直接的針對性(參看2020年第二期《文藝爭鳴》李浴洋對黃的訪談)。不知道上面那些批評對于立場(亦預設)在前的研究者有沒有一點點觸動。
至于我自己,無論考察中國現代、當代文學,還是當代史,無不在補個人經驗之不足。對于寄身的這個世界,較之非虛構類的文字,虛構類如小說未必不真實。問題在你如何理解真實。看小說,看影視,也是看別人的生活。轉向當代史,更想到了文學作品作為“史料”的可能性,與運用中的工作倫理。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包括影視)對于“存史”,貢獻堪稱巨大。
從現當代文學到明清之際,近三四百年的“跳躍”,一般學人不敢輕易嘗試。是怎樣的歷史機緣促成了這一“跳躍”,從哪些人物或文字上您窺見了轉向明清之際的入口?明人譚元春《詩歸序》云:“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遠矚人”,您在閱讀明清之際士人文集時,是否有這樣與古人“對視”的時刻。
趙園:從事學術工作后的低谷,發生在完成《北京:城與人》之后,嘗試進入明清之際之前。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學術轉型,于我是機遇。一些年后回首,會發覺我與有些同代人之間的區分,也在“轉型”與否,是否憑借這一機遇走出八十年代。走出并不就是告別,更不是永別。背景仍然在。盡管八十年代引起了持久的懷念,大陸學術仍然在后一個十年臻于成熟。不少學人有代表性的學術作品是在九十年代完成的。如實地說,九十年代趨于沉靜的學術環境,有利于學術的整體水準的提升。資源更為豐盈,更有對于打破狹隘專業眼界的鼓勵。當時有一本書,題為《開放社會科學》。社會并沒有更開放,不如說在逐漸收緊,卻無妨于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開放邊界,開放視野。我的學術工作起步較晚,來不及定型,有愿望求變,對其他專業始終有濃厚的興趣。轉向明清之際,于是順理成章。在我所屬的世代,這或許是不可錯失的機會。
學術自述中,我談到過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讀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后來讀到趙儷生說自己由文學轉向史學,受該集的感動;馮天瑜則提到王夫之《讀通鑒論》對他的影響。由此得知我自己對兩書的傾心,確非偶然;至少閱讀體驗與前輩學者有“暗合”。無論讀《鮚埼亭集》還是《讀通鑒論》,確實都是一種美好的經歷。但你說的那種“與古人‘對視’的時刻”,搜索一下記憶,似乎不大有。沒有任何一個明人或清人,能如魯迅那樣打動我。由結果看,闖入一個陌生領域,得遠大于失。一個朝代從此與我相關,一批人物從此與我相關。你只能對當初的決定冒險心懷感激。
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將他的研究工作視為“沒有地圖的旅程”,仿佛孤獨的行旅者在未知領域的游蕩、摸索。從現代文學上溯至明清之際,您的研究路徑多少帶有一點偶然性,因而是很難復制的。在文學與史學之間獨來獨往,您收獲了怎樣特殊的風景?
趙園:我寫過一篇學術自述,《尋找入口》。“尋找入口”同時也是“尋找出口”:由專業走出,嘗試別種方向、學術方式以至表述方式。進入明清之際,最初即使閱讀也有阻力,如讀線裝書時的斷句,所幸這一階段較快地走過。我下面還會談到,較之此前的讀中國現代文學,此后的讀當代史史料,那二十幾年的讀古籍,更美好,值得懷念。你不會認為自己錯生了時代。你知道正因為你在斯世,有前此的閱歷,才有這時的沉湎,感懷。
關于明清之際,因文學研究的這一種背景,我的長項或許更在對于人性、人的生存境遇的敏感,短板則在制度層面的討論。這時的我,已經更加遠離“文革”文化。其表現之一,即不在東林/非東林之間選邊;盡管情感上親近的,是當年公論中的正人、清流。不再像年輕時的偏激,也就對“明人習氣”有了一種批評態度。不在所涉足的那段歷史中扮演一個角色,或許要拜史學之賜。
近年來,青年學者愈發意識到壁壘森嚴的學科體制對自我學術發展的桎梏,開始到鄰近學科尋求可以對話的學術伙伴。我個人與本專業的學術交流,反不及與近代史、社會學的青年學者對話頻繁。當“跨學科”成為一種潮流以后,如何看待它對人文學的沖擊與影響?
趙園:關于“跨學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為,若不將“跨”僅僅理解為“在……之間”,就需要應對“系統地調和兩門或者更多學科的基本框架和工具這一困難的任務”,“這一方法要求精通每一學科,并需要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可以將每門學科納入其間的超級框架。唯有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能做好這一工作”(《椰殼碗外的人生》中譯本,頁16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這種“跨”對我而言自然可望而不可即。我也從來不曾設這樣的目標,只是不在既有學科分類中為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而已。由別人看來,像是游走在文化史、思想史與一般歷史間的模糊地帶,非此非此,亦此亦彼。
八九十年代之交,學術研究/評價的體系還有彈性,也使你有可能在較大的空間選擇。即使在“跨學科”成為時尚之前,學科分界也不那樣嚴格。即如我們最初從事的,就應當歸入以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為材料的準思想史研究(《論小說十家》除外)。《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引起關注,也應當由于難以用已有的史學規范界定,我也就順勢將自己的研究模模糊糊地定位在“思想史研究的邊緣”上。
據說有所謂的“T型人才”,兩翼伸展,跨學科,跨知識領域。這種人才,哪里是我輩所能做得到的。只要不以學科的既有邊界自限,充分開發與議題有關的資源,打開盡可能廣闊的思考空間,將那個題目做到極致,也就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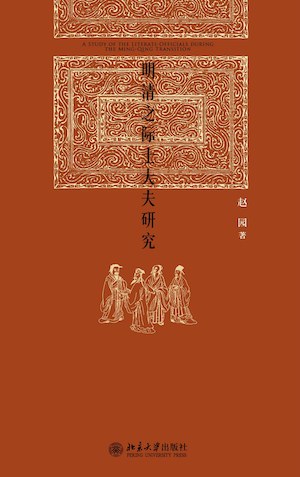
您在《治學雜談》中,除了思想、材料、文體之外,還格外看重視野、境界等務虛的追求,對以學術為志業者的重要性。令我印象頗深的一句話是:“學人在學術中是難以隱身的”,個人的修為、品性乃至私心雜念都會不經意暴露在戴上面具的學術文字中。您何時形成對學術“境界”的自覺追求?能否回顧一下您學術經歷中的“高光時刻”?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出版,有媒體說這是趙園第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大意):雖有對于文學研究的偏見,卻不難接受。至此我才有了對“境界”的追求,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完成了一本書,得到圈子里的好評。
2000年“長江讀書獎”的風波,與我獲獎的學術作品無關。輿論風暴中似乎不大有對《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獲獎的爭議。至于2010年《想象與敘述》獲“魯獎”,多少算得不虞之譽,不大能受之泰然。即使如此,也應當說,在學術文化界生態惡化的今天,沒有所謂人脈而獲此獎,仍然讓我心生感激。評獎活動往往成為丑陋的集中展示。倘若沒有可以用于交換的利益,少一點出諸私誼或私怨的吹捧或打壓,在我們這里已經屬于難得。
我的學術經歷中沒有過所謂的“高光時刻”,即使獲獎。記得“魯獎”頒發當晚的“走紅毯”,儀式現場一派冷清,證明了這種仿娛樂明星的“走秀”的失敗。對于無論“嚴肅文學”文學評論還是文學研究,這都是最正常的情境。

“人的隱去”,特別是具體的、單個的人的隱去,是現代西方史學的一大趨勢,也影響到中國近代史研究。近來有思想史家呼喚“人的回歸”,以對抗剔除人名的新史學。歷史中人的處境,幾乎是您每部學術著作都會涉及的話題。是否有一些特別的歷史人物,對您觸動更深,承載了您更復雜幽微的歷史思考,也代表了您所向往某種歷史心性。
趙園:寫明清之際,因所選議題更因積久形成的工作方式,涉及了為其他明末清初的考察不曾或難以觸到的人物、言論。這種寫作或多或少為相關論域至少在材料的方面擴容。在嘗試打開面、延展線的同時,隨時聚焦于人物,既與文學研究的專業背景有關,也更是一種個人取向。如已經說過的,具體的人在大歷史中,始終對我有強大的吸引力。由結構看,將綜論不能容納(或因綜論而有可能同質化)的部分另作處理,確也可以聊補綜論所未及。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續編論唐順之,較之正編的選擇傅山,出于更復雜的考量。唐順之是近人、今人眼中的古文家,文學史將其歸為文人無疑。當其世的唐順之,道德上的潔癖,耽于苦修,更類似理學之士,交游也多儒家之徒。卻為了他自己領受的使命也為了自我完成,不惜有所“玷污”,甘冒觸發物議的風險挺身而出,承擔或非他宜于承擔的軍事重任。我素來不喜歡理學家,卻被唐順之吸引;由他同時代人對其正負兩面的評價,試圖探入并理解其人;經由這一具體人物,討論經世、任事的代價。即使處在唐順之的境遇中,我也不會作同樣的選擇,卻無妨我對唐懷了敬意,將他作為考察“政治中的人性”的案例。明末人士仰慕的嘉隆人物的精神魅力或許也在此。即使經歷了“文革”,我沒有以政治為骯臟的偏見,不將政治人物視為異類。唐順之的“知不可而為”,基于強大的人格力量。黃宗羲《明儒學案》評論泰州學派的一段文字,令人血脈賁張。那種“赤身擔當”,屬于英雄時代。泰州學派正不乏有青蠅之玷的人物。寫唐順之,我或許不自覺地面對了自己心性的強與弱,擔當與逃逸間的矛盾糾結。盡管我從來不曾面對真正嚴峻的情境,有的不過“天下本無事”時的庸人自擾。

跟《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續編》相比,《易堂尋蹤》這本小書似乎意在探尋另一種學術表達的可能性,把您的兩套筆墨糅合在一起,借實地踏訪,給那些業已褪色的,或被遺忘的歷史人物,提供了鮮活的時空背景,甚至暈染上山水林木的氣息。能否談談您寫作這本小書的機緣,以及如何看待危機時刻的友情?
趙園:《易堂尋蹤》體量較小,不知道能不能歸入“微觀歷史”。由這個“點”本可以進一步鋪展——有很多點都可以鋪展。收到過明代文學專家嚴迪昌教授的信。來信說對《易堂尋蹤》中“東南人士的文字,與叔子有關的卻難得一見”“略感費解”,“不知所指為何種‘文字’。不然如冷士嵋《江泠閣集》中贈與或祭哀叔子之詩與文似不下數十篇,魏氏病故前尚與冷秋江聚首于京口。冷氏之集雖小而不算僻見,博識如閣下或亦曾目覽”。其實嚴先生哪里知道,我于明代文學始終在門外,竟不知冷氏其人,更無論“目覽”其文字。不曾博覽而遽下斷語,輕率可知。寫那本小書,更像是偶爾的逸出。材料主要為九子的文集。我做到的,大約只是不將這一關于友情的故事理想化:詩意與不那么詩意,美好瞬間與生存窘境,聚合與終不免的離散,尤其因思想根底不同的離散——呈現的是看似完美的故事的諸種裂紋。我或許生性多疑,更相信直覺,容易讀出被艷稱的事物的破綻。
寫這本小書也如寫《北京:城與人》,是一種不無愉悅的經歷。其實“實地考察”只是為敘述提供線索,所得甚少。考察仍然更是紙上的。

作為文學研究者,卻對文字“無感”,或不能從文字中獲得愉悅與滿足,就像廚師失去味覺,未免有些可悲。跟目下流行的概念工具、學術黑話相比,“文字感覺”說起來過于虛玄,近乎個人的天分,師徒間亦無法授受。文學研究者對“文學”不自信,很多時候是對自己的文字感覺不自信,不能嗅出文字的好壞,即便有辨別力,也難以把自己模糊的感覺訴諸文字。“文字感覺”未必是天賦,或可通過日后的點滴積累,通過與特定對象的朝夕相處而習得。近些年不少學生喜歡蕭紅、沈從文、張愛玲,紛紛以三人為畢業論文選題,我都會推薦她們先讀您的《論小說十家》,提醒她們此類作家研究似易實難,難就難在如何捕捉各人的文字感覺。您能否談談“文字”這一介質之于您的特殊意義。
趙園:審美,文字感覺,不但是作家,也應當是文學研究者的強項。向其他學科學習并不意味著有必要棄長用短。職業性專業性的閱讀中,我的愉悅主要來自文字,不止于一流文人被公認的美文,更有我自己發現的堪稱奇崛的文字。可惜的是閱讀的當時未曾著意裒集。倘若能輯為一編,或許能多少影響對明人文字的印象吧。文字這一介質對于我過于重要。最初曾嫌王夫之文字的村夫子氣;翻到《讀通鑒論》中觸目皆有的警策,精神就頓時為之一振。這樣的閱讀經歷,何嘗不是枯燥的學術工作的最好補償。
寫蕭紅、傅山,更因為文字感覺。蕭紅式的稚拙,未嘗不是有意的文字策略,略如魯迅《秋夜》的寫棗樹。傅山的文章在明清文壇上獨標一格,適于用上面說到的“奇崛”形容。不同于同時代的文人,傅山的筆墨雜糅了民間風味以至鄉氣。小箋的方言土語,尤其難得見于江南的風雅之士。對文字有感或無感,有時是我選擇某一作家、人物做專論的主要理由。有感、無感無關乎好惡。寫蕭紅,并非出于喜愛。不寫魯迅,倒是因過于喜愛,怕力有未逮。無論張愛玲、蕭紅還是傅山,都不是我私心向慕的人物。所以寫那些篇,無非因自信能捕捉閱讀中的文字感覺。當文字感覺鈍化,這一種寫作也就難以為繼。
一位朋友說過,我的學術研究賴有“觸發”,文風也如此。因對象的轉換而變換筆墨,是一種不自覺的模仿過程。說研究工作豐富了自己,也包括這一層面。進入明清之際,表述方式易于為對象誘導的脾性發揮了作用。集中閱讀明清文獻,筆調的變化也就不待有意追求。文言使我有如對故土、故人的親切感,盡管我那點有限的古代文學閱讀撂荒已久。文言歷千錘百煉而有的高度凝練的表意功能,讓我重新有了書寫的快感。這種快感在寫《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過程中有痛快淋漓的表達。這種快感在我的學術/寫作生涯中并不常有,偶或一現而已。
在您關于明清之際的系列論著中,《想象與敘述》這本書或許是可讀性最強的,更能引起非專業讀者的興味。其中收錄的兩篇《治學雜談》,我會反復重溫,也多次推薦給剛入門的研究生。《那一個歷史瞬間》一篇寫得實在漂亮,在組織歷史敘事上尤有啟發性。我曾依葫蘆畫瓢,模仿此文的寫法,試著呈現1937年北平淪陷的瞬間。能否談談您這本書的寫作狀態及收到的讀者反饋?
趙園:《想象與敘述》可以作為在一個方向上因選題而使視野得以擴展的例子。將除了正史外的私家史學著述、“野史稗乘”明清人的筆記、近人、海外學人的明史著作留到這個時候才讀,與通常的入手處確有不同。自己也吃驚于進入明清之際這么久,才讀這些被認為基本的書。倘若有老師指導,一定不會這樣吧。
這本書寫得較《續編》順暢。或許證明了強項確實在“敘述”。劉錚的書評稱許的,也是文字。文字或許的確如劉錚所說,但寫作狀態仍然與最初不同。干凈是干凈了,卻沒有了最初那種蕪雜中的蓬勃生機。如果不因為“在職”,或許寫到這一本也就罷手了。寫《家人父子》,多少也出于不得已。盡管那個題目值得寫,尤其值得延伸到現代、當代。
寫《想象與敘述》一書諸題,再次證明了“生長”的可能賴有發現。《那一個歷史瞬間》一篇,觸發的契機,似乎是延安《解放日報》紀念“甲申三百年”所選的日子,竟然是公歷3月19日(1644年的農歷3月19日乃公歷的4月25日)。時間點的選擇往往出于“操作”。由3月19日被定為明亡的時間點也可以推及其他,即如“文革”的始點與終點。
由一篇關于《想象與敘述》的書評意外地讀到了“快樂”兩個字。那篇似乎是寫在海外的書評,一再使用“快樂”的字樣:“她的‘讀出萬分激情’的體驗,傳達著她的快樂:閱讀的快樂、想象的快樂、思想的快樂以及文字的快樂。她的快樂,在字與字的空隙處流出,我被她的語言感染,也快樂起來。”(張昭卿《書本的生命力——讀趙園〈想象與敘述〉》,《書屋》2018年第十期)我從來沒有想到也不敢期待別人對我的書有這樣的閱讀體驗。看來“接受”的確有因人之異。知道自己的文字使別人快樂,令我感到安慰。回頭想,寫作這本書的確有快樂,尤其第一篇。不惟這一篇,學術性寫作何嘗沒有“快樂”。只是這種快樂更是私人的,與所寫是不是有價值無關。快樂地做學術,一定有人這樣。但快樂必有條件,即未必快樂的知識準備與學術訓練,艱苦的材料積累與思路梳理。這本書之前之后,我都有快樂的時刻。快感之來,多半因了苦思冥想后的豁然,或表述時的筆能應心。
讀您的著作,我往往會跳過正文,先讀余論,從中了解您的選題緣起與現實關懷。《家人父子》一書雖處理的是明清之際的人倫日用,若放到更長的歷史脈絡中考量,則自會聯想到近百年來中國倫理秩序的全面崩塌,尤其是鄉村社會在戰爭與革命的損蝕沖洗下形成的道德真空。我們該如何在二十世紀的革命語境中續寫“家人父子”的悲喜劇?
趙園:多少也因為前面提到的不得已,寫《家人父子》較為匆促,未能充分利用明清兩代編纂的大量家譜、家集。那部分材料應當有發掘的價值。這本書附錄兩篇討論的問題,確有現實的針對性。關于宗族的部分尤其有與當下的對話關系,包括未加甄別地試圖“修復”傳統,而后又承認有所謂的“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由書評類媒體讀到關于已故美國漢學家易勞逸(L. E. Eastman)的著作《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的評介。該書系近年來引進(中譯本由重慶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我寫《家人父子》的時候沒有讀到。相比之下,我的那本視野之狹,格局之窄,與該書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我明白自己關于明清之際的著述中,《家人父子》最可能有續篇:二十世紀至今革命與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家人父子。這是個需要長期投入的題目。我自己最佳的寫作狀態已過,不想糟蹋了這么重要的題目;問題過于敏感,也不敢鼓勵年輕人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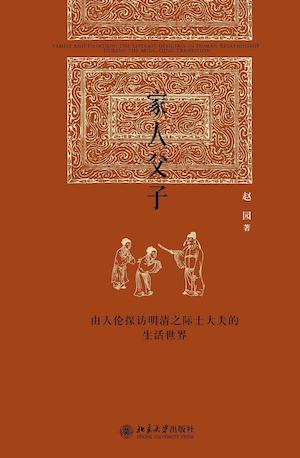
無論面對現代文學,還是轉向明清之際,您的工作狀態、研究路徑、核心話題及所倚重的材料類型都有內在的一貫性。如何進入不同的歷史脈絡,傾聽各色人物的心聲,日本思想史家溝口雄三曾有一個簡要的回答,就是:“空著雙手進入歷史”。用“忘我”的狀態面對歷史,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則要求盡可能地擴大原始材料的蒐討范圍,從頭到尾地閱讀,不帶成見地閱讀。您的工作狀態接近于溝口所謂的“空著雙手進入歷史”,能否就此分享一下您蒐討文獻、闡發材料的經驗。
趙園:我已經說到過,無論進入中國現代文學還是明清之際,都“空著雙手”。關于明清之際,沒有人為我開列書單。除明清人重要的歷史著述與個人文集外,至少部分閱讀是隨機的。這也是“空著雙手”的好處。隨機的閱讀有可能一無所獲,也會有意外的驚喜:一扇門開啟。開啟了這扇門未必就有創獲。但一扇扇門的打開,豐富了你關于這段歷史的認知與想象。只不過對此也不便想象過度——似乎無所謂“預設”。事實是,你所有的儲備都參與了你當下的選擇,只是你對此不自知罷了。
形成論題后,自然會有定向的閱讀。即使“定向”,所得也有因人之異。一望可知的材料與出諸獨見的材料,后者才是需要你發掘的——黃侃所說發見/發明的“發見”。其所以是材料,有待“燭照”。它只是因了你的視野、敏感與分辨能力,才成其為“材料”。有時一條或幾條材料可以作為骨架,支撐起一篇論文。設若沒有這一條或幾條,也就流于平庸。與這樣的材料相遇自然需要準備。有一句濫調,機會是為有準備的人……“材料”也如此。你的識見未到,那些材料也就如過眼云煙。
有人說研究宋代,材料不多不少:比之于宋之前,也應當較之于宋之后。明代由于印刷業的進一步規模化,書籍的流通量增大,個人文集的面世有了更多機會,傳播也更快更廣。研究明清,材料就不能說不多不少。數字化方便了借諸關鍵詞的搜羅,卻有“碎片化”的危險。材料在由文本中抽取的時候,割裂剝撦在所難免。對科研的量化評估,不利于“慢閱讀”,更遑論非功利的閱讀。“上天入地找材料”已像是前現代的手工作業,便捷的是利用科技手段。我確如你所說,往往“從頭到尾地閱讀”,卻不敢說“不帶成見”。即使這樣,也自知已經不合時宜,不敢向年輕人傳授經驗;同時也體貼他們的處境,知道陳義過高,只能自說自話,流于空談。
學術研究特別人文學,本質上是通過對象“迂回”地理解自己。您早年關注現代文學中的知識人形象,進入明清之際又著眼于士大夫研究,無不有“持鏡寫真”的意味——以歷史人物為鏡,對照自己所屬的時代。您標舉的士大夫精神,對當下普遍缺乏歷史感的知識界是否是對癥之藥呢?士大夫亦有不同的理想型,如名士、文人、儒者,您更親近哪一類?
趙園:由中國現代文學到明清之際,一以貫之的,是對中國知識人的關注。這種研究的一部分動力,的確在面對自身。至于題目背后的現實關懷,寫作當時未見得自覺,也就是說并不都出于預先的設計。事后看來,不但如“戾氣”,而且“流品”“井田”等等選題,均非出自“純粹的”學術興趣。這些或許是可據以辨識“代”的面目的東西。經由對象面對、發現自我,經由對象思考你身處的世界,如果介質有足夠的深度,這份努力(以至掙扎)就是值得的。
我的興趣始終更在有思想力或有行動力的士大夫。為人艷稱的江南名士,自始就不曾吸引我——或許也由于對江南的隔。對江南文化、名士風流,既少經驗,也缺乏向往。更像是精神家園的,是出生地的西北,那里的沙磧、枯河。也因此讀傅山的文字,有特殊的親切感。
在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肯定有自覺暢快淋漓的得意之筆,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失敗之作。前者或是機緣湊泊的產物,或跟某一段特殊的生命狀態相呼應。后者則觸及個人知識結構的缺陷,甚至是一代人文學者的宿命。能否回顧一下您學術生涯中那些不可多得的機遇良緣,及歧路徘徊的時刻。
趙園:我的學術生涯中確有那種時刻,你相信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了題目;這樣的經歷極其稀有,不可重復。關于蕭紅、傅山的作家、人物論外,寫收入《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說“戾氣”(該書的第一章第一節),寫《想象與敘述》的第一篇《那一個歷史瞬間》,屬于這樣的時刻。未必因為醞釀既久,或許更是你挾已有的準備(包括經歷,經驗)與對象相遇,時機、狀態都剛剛好。隨筆的寫作,快感時有。但那種透徹、無遺憾,卻只能在如上的學術寫作中感受到。那種你與對象間的默契,甚至難以解釋,緣于諸種條件的湊泊,不無偶然。借用郭沫若“做出來”“寫出來”的說法,有些文字是“寫出來”的,猶之自然流出。這無關乎價值判斷。“寫出來”的未必較“做出來”的更有學術價值。那更關系個人體驗而非學術尺度的裁斷。也有不堪重讀的舊作,證明的毋寧說是風氣中人的“膽氣”。漸少敗筆、爛文,也因有了不茍做的自覺。
迄今為止,我的稍具規模的學術考察,最初都只有大致的方向——關于當代史也如此——然后將閱讀所得與可能的“材料”錄以備用。積累到相當的字數,初步分類。此后一次次重新分類,排列組合,既是大致的方向生成,又是新的思路、方向不斷衍生的過程。有了初步的提綱后,仍然一再調整。調整貫穿始終。最終的架構是不計其數地調整的結果。初稿一再增刪。一旦定稿,交付出版、發表,也就不再修訂——“硬傷”除外。稍有重量的學術作品,程序無不這樣繁復。至于每有“硬傷”,甚至低級錯誤,不是由于粗心,而是訓練缺失。有時會想,“文革”十年,何不將《新華字典》帶在身上,隨手翻翻?這只能是“事后聰明”,當時何嘗會想到這些。得知“文革”后期上海就有地下、半地下的外語學習班,只有羨慕的份兒。
先河后海,盈科而后進,屬于正常的過程。可惜我們經歷的,是“橫空出世”。一旦崩塌,就會是“斷崖式”的。因而不敢狂傲。低調不是故作姿態,而是確確實實知道自己的斤兩。一代人文的缺陷,只有少數天才能幸免,而我是常人。
學界中的代際更迭本是自然現象,但當遭遇政治動蕩與歷史斷層時,就會形成不同代的疊壓并存。有的世代被夾在中間,還沒來得及登場,便已臨近謝幕。有的世代則一直處于聚光燈下,不斷告別,不斷返場。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并非同一年齡層的學者就被歸為一個世代,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參與了某一歷史進程,經由反復地自我論述,確實留下了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學術作品,才能構成一個有生命力的學術時代。您既是上一個學術時代的見證者,又是一個新的學術時代的開創者,能否談談您對代際問題的看法。
趙園:文學所關于樊駿的紀念文集,題作“告別一個學術時代”。那一代之后,似乎在不斷“告別”。正常的學術環境,本不應當如此。學術不是時尚品牌,經常在更新中。每一次告別都有必要追問:有何種學術遺產,其中是否包含了特定世代的“學術精神”,甚至有沒有所謂的“學術精神”。我們早已到了被“告別”的時候。至于我,的確是一個學術時代的親歷者;“開創者”愧不敢當。何況你所說的“新的學術時代”尚待展開,走向未明。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