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云研討︱古代國家治理能力與救災經驗
5月8日,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傳承與融合研討班”主辦的第五次網絡研討會召開。此次會議主題為“古代國家治理能力與救災經驗”。本次討論會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烏云高娃、王申、吳四伍主持。會議采取報告人主講、與談人點評的討論形式,共有8位研究人員一起做了深入討論,奉獻了一場難得的學術盛宴。
目前,全球正遭遇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疫,中國抗疫實踐體現了獨特的救災路徑,且取得了明顯成效,其中優秀傳統文化與歷史救災經驗的作用不容忽視。審時度勢,在學理上系統探討古代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救災機制,總結全人類,尤其是中國在無數次救災實踐留下的寶貴經驗,是學術界的責任與擔當。歷史是一條奔騰的大河。宋元明清各朝代開創、繼承和發展的諸如倉儲、水利、賑災、地方治理等救災制度,在中國歷史發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鑒于此,此次學術討論聚焦兩大問題:一是宋元明清的救災經驗,二是救災所反映的國家治理能力。
宋代救災的大平臺與國家治理新理念
唐宋以后,傳統社會中諸多治理制度開始日漸成熟,影響深遠,在救災領域表現尤為突出。通過制度化救災,實現救災儲備的合理布局與能力提升,是宋元以降的重要經驗。因而,此次討論的重點是國家利用物資儲備調控物價、災害治理的常平體系。
盡管囿于網絡問題,略有插曲,來自首都師范大學俞菁慧做了非常精彩的主題演講。俞菁慧多年來從事王安石變法研究,對于北宋常平體系的建設,有自己的全新觀察。她獨辟蹊徑分析北宋推行常平體系的國家治理理念,檢討國家參與商業競爭的困境與得失,分析王安石變法中,推行常平大救災平臺的歷史經驗、制度創新、內在邏輯。在有關常平體系的經營方式、物資儲備、資金流動、機構協同、斂散機制、基層信息、人事梯隊、立法修正等方面,俞菁慧提出了諸多極富創新意義的思索,以及“雙軌制”“物資池”等簡易明白的概念。關于宋代常平賑濟的多元賑濟模式和多機構協作的治理機制,她又給出了十分詳細的專業論述,通過精確的圖表給予形象展示。

來自華東師范大學黃純艷老師,認為俞菁慧老師多年來在王安石變法研究中,有自己的獨創性,特別重視制度闡釋與制度實踐的關系,重視王安石對《周禮》的運用。指出,此次在常平體系的新研究中,俞老師一是敏銳指出了常平新法的經營方式;二是揭示了常平倉作為救災平臺的統攝作用,常平體系成為一個調動各種物資的平臺;三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重新評價了常平新法的變法效果。特別是國家的治理能力得到大大提升,不僅財力增加、手段增多,而且制度體系更加豐富。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國家救災能力得到大大加強,財權越來越集中,地方財政越來越弱。這在宋史學界得到一定的認同。對于常平新法,黃純艷老師提出,一是要重視常平司的研究,二是要注意朝廷財政和國家財政的區別,朝廷財政更多的是儲備財政;三是要注意新常平新體系的持續性問題。圍繞傳統社會的國家治理,黃老師還補充了南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應對災害能力特點的闡述。認為南宋地方治理呈現出機制十分完備,救災制度建設十分顯著,民間力量參與顯著增加,救災手段日趨多元化、嘗試開拓財源等特點。
來自福建師范大學朱義群認為俞菁慧老師主要講常平新法中蘊育的救濟理念和常平賑濟中新法和舊法的質變和量變的超越性。其文章強調常平新法的重點并非賑濟,而是建構一種國家治理新模式。俞菁慧主要是以王安石變法中常平倉建構為主題,沒有糾纏于新法的利弊得失、是非定論的傳統研究模式,也非集中于史料考證,且超越探討新法個案的方法,強調常平倉的新經營理念,將其置身國家治理的視野中考察,打通各項新法之間的樞要,體現王安石變法中的創新性因素,成為中國傳統社會財政改革的非常特殊的存在,并與近代國家社會主義思潮遙相呼應。文章視野開闊,內容豐富,有很好的縱深感。朱老師簡略回顧了近百年有關王安石變法的分歧,即梁啟超、鄧廣銘、漆俠、日本京都學派等推崇肯定派和蒙文通、王曾瑜、梁庚堯等批判否定派。并進而提問:俞老師提出常平新法的關鍵創新在于其經營方式與財政體量的“質”的變化,王安石追求不止是賑災救民,更是如何將之“做大做強”,在財賦規模上獲得質的提升,這一觀點是否間接映證了梁庚堯等指責王安石財政之策高于社會之策的觀點呢?第二點是常平新法實施的連續性是否值得檢討,在熙豐年間和元豐年間,兩者是否是一脈相承?三是新法的延續性問題,蔡京的變法放棄了王安石的改革理念,是否可以證明這一點,即王安石的新法并沒有取得理想的社會效果?
俞菁慧老師在回應環節指出,第一,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爭論的火藥味非常濃,近現代以來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國家派和自由派的激烈交鋒。避開這場歷史紛爭的關鍵在于回答:王安石新法本身的運作性質與運作邏輯。青苗借貸“二分之息”的設定從根本上改變的了舊常平的“保本福利”模式,走向自運營為主的“保本盈利”模式,實現常平功能的“質變”,由原來的“賑濟常平”逐步轉向“經營常平”。與此同步的“量變”則來自于新常平規模與體量的全面提升,既包含全渠道的本金與物資投入,也包括由基層借貸與轉移支付所形成的流通效應。第二,人們以往習慣于從二分取息法去強調常平的斂財屬性,而事實上,和均輸、市易不同,常平青苗斂散的盈利效果并不明顯,甚至都難以保證一定處于盈利狀態。常平儲備規模的大幅度膨脹,并不主要來源于“取息獲利”,而是持續的財政撥入和各路物資源源不斷的歸集。既包括龐大的基礎運營本金(1500貫級別),也包括三司-轉運司、內藏系統的調入,還有新法財政的平行調入。總之,它的“做大做強”背后有著一套明確的財政歸集路線,恐非傳統“剝削聚斂”、“國富民窮”等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所能涵蓋。第三,新常平體系的有保本盈利的運營初衷,但從根本上還是對接各種形態的農業政策:小農借貸、農田水利基建與大規模災傷賑濟等等,并從理論到實踐搭建起一種新的“開闔斂散”機制,依托中央到地方各級資源、機構、渠道、信息、價格、倉儲等要素,形成強大的平臺效應,推動了神宗朝財政結構與組織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第四,關于改革的延續性,俞老師以為王安石變法被推翻后,即使是其后繼者也并未延續其運作邏輯與整體模式,雖然很多具體新法是被重新“撿”起來了,但是如同撿起一堆散狀螺絲,背后的“機器”(系統)卻始終沒有搭建起來。
元代救災的大場域與新史料
元代國家治理能力和救災特點跟宋明等朝明顯不同,是學術界研究的薄弱之處。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烏云高娃老師注意從長時代和大視野出發,重點闡述元代救災的特殊性與階段性。第一,從學術積累方面深入淺出總結百余年來元代救災研究的重要發展歷程與特點,特別是提到國內甚少關注的一些尚未出版的專門研究,如崔允精2003年完成博士論文《元代賑恤制度研究》,對元代賑恤制度的專門研究,如《救荒活民類要》以及常平倉的研究等,展示了元代救荒研究的諸多新趨勢。第二,從元朝的特殊朝代實踐出發,歸納元代救災和賑恤的廣大場域,包括對高麗等地的糧食轉運,其賑災規模和手段都跟內地賑濟明顯不同。賑災的對象和賑災物資也有自身的特點,這是我們比較邊地賑濟和內地賑濟不同的重要內容。第三,從《元史》《元典章》《高麗史》等史料中,細心梳理和論證元代災害發生軌跡和救災實踐的特點,以此論證元代救災在大規模賑災中展示出來的新的賑濟特點,顯示國家賑濟手段和運輸工具的新發展,借此展示國家治理能力發展的新高度。此外,新史料展示元代救災政策、救災范圍、救濟對象,也存在不少誤解之處,值得學界重新討論。
同樣,北京師范大學王培華教授認為救災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她指出,白壽彝先生所著《中國通史》導言講到,救災賑恤是國家的重要社會職能之一。歷代正史中,有十六部史書有《五行志》。《五行志》記載了水旱蝗霜雪冰雹等災荒,體現了國家的救濟職能。我國歷史悠久,文獻豐富,對研究全球變化,可發揮積極作用。我國救濟災荒,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災荒與救災史研究,自上世紀三十年就開始了,并且取得成就,相比來說,漢唐和明清災荒與救濟研究較多,元代賑濟研究較少。她個人重點研究元代北方的水、旱、蝗、霜雪、冰雹、桑蠶病害蟲等災害與救濟,研究各種災害的時空特點,及國家救災制度與措施,指出特大蝗災有11、60年左右的周期規律及其與太陽黑子活動的關系。從研究方法來說,她注重使用元人的文集,采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災荒與救濟問題。
明代救荒的政策設計與地方施行
關于明代救荒研究和最新思考,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解揚主講,他重點檢討明代地方政府在面對救荒問題上面臨的困境和采取的措施。首先總結了當下明代救荒研究的諸多最新研究,如經濟史方面,我們可以參閱張兆裕老師研究明代國家實施的以工代賑,檢討國家在救災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政策實施的靈活性;在政治史方面,可以參照最新法國歷史學家魏丕信即將出版的《歷代官箴公牘研究》,該書經過近30年的收集和整理,系統地收錄了中國歷史上官箴書籍1165種,其中有30部左右是宋代書籍,其余大多數是明清部分,其中救荒書籍也得到分門別類的列舉,值得我們認真關注。從歷史救荒文獻的積累來看,明代有關專門救災個案的書籍較少,大多數有關救荒經驗集中在官箴書等政務類書籍中。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代救荒性書籍中處理危機時刻的應急經驗較少,而處理日常政務中有關災荒管理的書籍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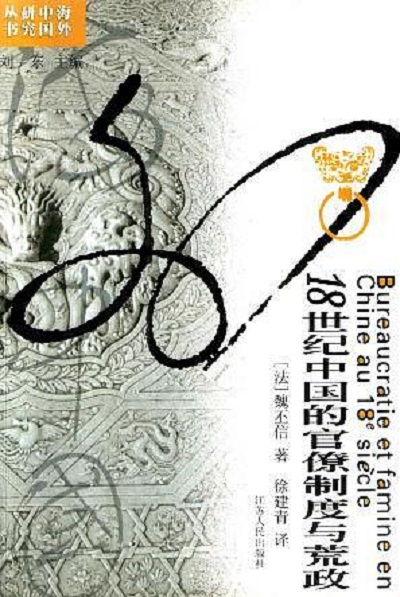
對于明代地方政府救災中,最為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之一就是有關“有治人無治法”的提法。此類提法在明代的地方政書中十分普遍,乃至成為“口頭禪”。對于“治人”和“治法”的分開解讀,可以理解救災中有能干的官員,但是缺乏有效的辦法。然而從官箴書的內容來看,僅從目錄就可以看出,有大量內容涉及救災的具體方法,以吳尊、呂坤的書可以得到印證。在大量的官箴書中,往往同時涉及“治人”和“治法”兩個方法,但是比較而言,涉及“治法”方面的內容往往要豐富得多。在某種意義上,官箴書等文獻呈現的“治人”“治法”跟明代地方實際行政中人們感知的“治人”“治法”問題有著很大的距離。如何理解兩者的差異呢?如果以明代的倉儲為例,無論是社倉還是常平倉等,明代救荒文獻中都有非常豐富的討論內容和經驗記載。呂坤的《實政錄》不僅有施粥的具體條例,也有曬谷的具體方法。這不僅讓人困惑,究竟時人缺乏的是什么“治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人們都將蠲免當做救災的重要政策來呼吁,甚至是救荒的唯一良策來對待。這種建議也在諸多救荒書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文獻中諸種建議往往來自著者親身的地方行政經驗,對朝廷實施蠲免,成為地方官員的真誠希望。這種建議還在不同地區得到實踐,特別是江南重賦地區。如果針對某些特別個案,如周孔教的救災方案,我們還可以發現救災重心的下移趨勢,對民間力量的重視,讓老百姓自治自究,建立鄉黨議事的地方秩序等新趨勢。以吃大戶為例,就是要求地方政府調控,保護富戶利益,又照顧地方利益。
概言之,地方士紳希望國家能夠實施蠲免等政策,以國家力量拯救地方,這是他們的首選之策;在此失望之后,他們往往轉向謀求地方自治救災的理想,他們希望建立跟地方政府二元并行的救災模式,這種理想是整個明代中后期自治風氣的一種具體體現,跟明代中后期國家治理方式一脈相承。以此觀察明代地方實政中的“治人”“治法”實質反映地方士紳的某種自我努力。如果聯系魏丕信等人對于清代十八世紀有關救災的“行為轉向”,從長時段觀察明清地方救災跟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顯然仍是學術界值得重視的關鍵問題。
清代國家救災中倉儲規模與治河理念
清代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全國維持了3000萬石至4800萬石的巨大糧食儲備規模,如何看待這種倉儲規模跟國家治理能力、救災能力的關系,是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吳四伍指出,清代倉儲政策的實施有其特定性,在工具價值的層面考慮,其興建有其必然性。但是,倉儲巨大規模和高強效率仍是值得分析的問題。他比較贊成和衛國等對清代倉儲數據的部分質疑,但是也強調巨大規模的客觀性和難以推倒性。在他看來,清代倉儲經營的高效與低能,才能最終決定倉儲巨大規模的存在和救災效率的高下,通過具體的救災案例可以看出,清代救災效率跟倉儲規模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聯系,清代倉儲是否能夠反映國家的強大救災能力,仍是值得學界重新探索的重要問題。
黃河治理是清代救災的重要內容。山東大學賈國靜多年來潛心研究清代黃河治理問題,尤其側重探討晚清銅瓦廂決口等重大問題。此次她從清初黃河水患入手,在分析明清易代之際黃河水患極為深重的原因的同時,重點闡述了康熙治河的成功經驗,并回應了學界有關治水與國家建設的討論。在她看來,盡管魏特夫“水利社會”等理論值得檢討,但是黃河跟國家之間的關系卻不能忽視。當下有關水利社會的研究,側重探討水與區域社會的關系,在這里,國家更像是一種隱形的存在;關于“治水政治”的研究,比較注意國家力量在治水中的重要作用,但多表現為單向度的關系。在她看來,“水之政治”中的治水不止是國家治理的工具,以及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更是國家政治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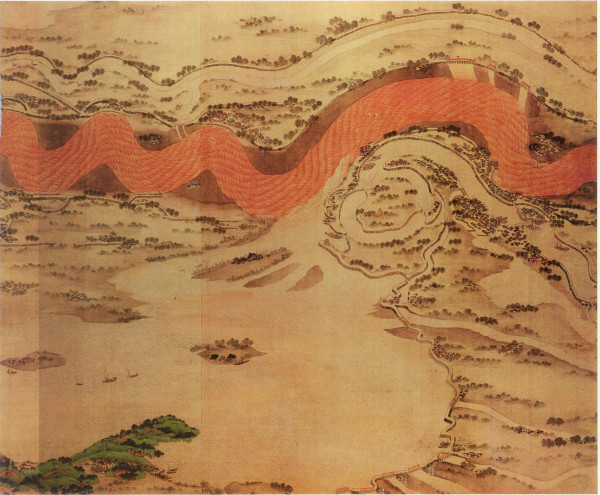
跨朝代視野下的國家治理能力與救災經驗
一朝為斷,蜻蜓點水,成為當下歷史學“碎片化”的重要特征,無論是救災中作為物資儲備的倉儲,還是救災中黃河家園,縱觀宋元明清,乃至先秦漢唐,都是一脈相承,緊密相連。唯有跨朝代、多鏈條,以長時段的視角,重新審視傳統社會的國家能力和救災經驗,才能深刻揭示中華文明成長的寶貴經驗。此次來自宋元明清的綜合討論,對于我們了解古代國家治理能力和救災經驗,形成三點基本判斷:一是制度化救災成為中華民族頑強對抗自然災害,不斷前行的重要歷史經驗。不管是糧食的儲備,還是河患的治理,都是在國家和地方的良性互動中,形成了專門的救災制度,同時依賴救荒書籍等得以流傳,成為今日救災的重要歷史遺產。二是由國家主導的救災實踐,成為中國救災的重要特色。事實上,自宋代王安石變法以后,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救災等民生工程進行強有力的干預,此種潛流在清代終為巨浪,儼然成勢。清代倉儲的超大規模,清代河政的巨額開支,都是一種歷史的延續,不能簡單看做某個朝代的臨時政策。三是官民互動的救災機制,不管是治人還是治法,在國家治理的漫長演進過程中,來自地方經驗的積累,和國家力量的推廣,往往在救災經驗的傳播和實踐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以復雜的倉儲體系為例,官方代表的常平倉和地方社會代表的社倉、義倉,他們一起在歷代救災實踐中產生的巨大合力,成為傳統社會官民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取得抗災勝利的重要法寶。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