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作為(男性)資本的性:羅志祥事件與男性共同體
曾經作為塑造著男性個體的性/別意識、氣質和作為與其他男性以及整個共同體形成的互動與聯系的性資本,如今雖然依舊承擔著這樣的舊職,鞏固著傳統性別制度,區隔著兩性在其中的等級和差別對待。
伴隨著周揚青微博的爆料所引起的全網吃瓜和輿論,我們看到許多人的關注焦點大都是她的微博文中所提到的幾個關鍵詞,無論是“看伴侶手機”是否合適,情侶間的出軌、還是對“多人運動”這一婉約說法的揶揄、惡搞和討論。在其背后實則依舊隱藏著許多存在于此類相似的、尤其是涉及男女兩性問題中(例如如今再次發酵的屈楚蕭的特殊性偏好,和其對女友PUA或是傷害的新聞)的線索,而根據它我們也能再次發掘出那些彌漫在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中的性別制度的運作,以及其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力量與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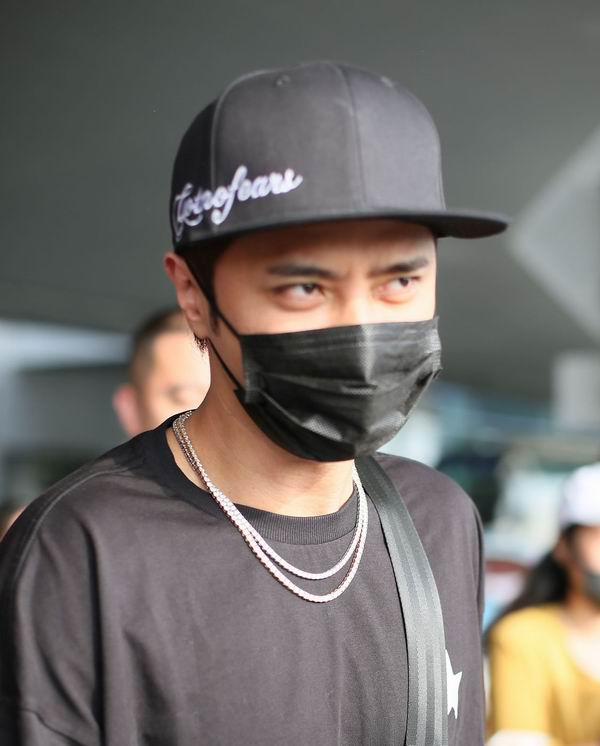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此次事件中存在的諸多特殊性都應該指出來。首先,爆料的是明星的女友,并且在其爆料中涉及許多私人——尤其是性生活——問題;另外就是被爆料者是男明星。而也正是這些看似平常的狀況背后所隱藏的某些問題,才會導致當下我們所看到的輿論趨向。
明星的私生活一直以來都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如果這一話題還涉及性,則必然炸鍋。然而按照往日的趨勢,我們也會發現,這樣的爆料不僅可能導致被爆料明星由此聲名掃地,遭到輿論強烈地排斥和批評【最典型的便是明星因為(婚內或婚外)出軌問題】;也可能產生此次我們在關于羅志祥的輿論中所看到的狀況,即大部分的輿論并未出現過分上綱上線的批評,或是由此產生群情抵制。其中主要偏重的,是諸多網友根據周揚青微博中爆料的幾點內容進行了幾乎可以說是“十分善意”地揶揄、惡搞和打趣,其中以對“多人運動”的輿論最為典型。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或許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因為此次事件涉及明星私人的性生活,而且因為這一性的“非主流”特色(雖然日常生活中我們聽聞、所知或是實踐著形形色色的性體驗,但在公共以及主流討論中,它往往隱而不現,或是以某種暗號般的形式進行旁敲側擊的言說)引起了人們窺探欲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種幾乎是心照不宣的共識。而就如網上許多評論所指出的,對于“多人運動”津津樂道的大都是男性網友。而根據他們的評論中所表現出的傾向和在一系列揶揄背后所暗藏的(潛)意識,展現出的其實就是十分典型的男性共同體的聯系網絡。
這一“男性共同體”在傳統性別制度中,一方面有著堅定的生物學基礎,即建基在“男性”(male)這一生理性別意義上;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想象性。尤其在網絡世界中,屏幕的存在使得原本區隔人與人的其他諸如階級、社會地位、種族甚至國家的范疇被暫時的懸置,最后把他們連接在一起的也就只有“男性”這一看似本質的標簽。
根據朱迪斯·巴特勒在法國社會學家列維-施特勞斯和女性主義人類學家蓋爾·魯賓觀點的基礎上所討論的人類原初禁忌的思想,為了使得部落能夠發展和形成聯系,除了外婚制與亂倫禁忌之外,巴特勒認為還存在著更為原始的同性情欲禁忌。即男性之間的情欲與性因為無法進行人類繁衍,而遭到壓制,由此才使得外婚制和亂倫禁忌出現。這一被壓抑的同性情欲便成為異性戀情欲與其結構中無法被抹除的陰影和存在,一直延續至今。
在伊芙·塞吉維克的《男人之間》,她通過研究英國十八十九世紀文學中展現出的性別意識形態,指出男人之間存在著一種被她稱為“同性社會性”(homosocial)的結構。而在其中便產生了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代指沒有性愛關系的男性之間的紐帶(這一關系福柯在其《性經驗史》以及其后的采訪中也曾稍有涉及,并把它稱作“友誼”。在福柯看來,正是因為西方傳統友誼的消失,才導致“同性戀”(homosexual)的誕生)。因此,同性之性在此不僅被隔絕且禁止,而且與此同時——巴特勒指出異性戀結構本身是憂郁的,而其原因便是因其無法徹底哀悼被禁止的同性情欲,因此內化成為它自身的一部分——卻又是無法被徹底割除。
正是為了維持男性之間的“純潔”以及杜絕同性情欲的出現,女性的在場便由此變得十分重要。這一現象在我們熟悉的各種三角戀故事中最為常見。兩男一女的感情糾葛,看似中心人物是女性,但就如塞吉維克的研究所發現的,實則最終被主要關注與講述的是兩個“異性戀”男性之間的各種沖突、角逐、斗爭以及連接。也正是在這里,列維-施特勞斯在其《親屬關系的基本結構》一書中所發現的原始社會對于女性的使用本質上是工具性的,即女性和貝殼(充當錢幣)、土地等物質一樣,是可以作為不同(男性)部落之間進行溝通和交流的貨物的。也正因此,我們才會在東西方歷史中的各種戰爭中看到,被掠奪的除了金錢和土地之外,女性始終也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而這一結構不僅存在于男性共同體內部,也存在于個體的男性之間。
因此當我們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看此次關于羅志祥事件的諸多評論和爭議時,便會發現其中同樣存在著一道隱秘的連結、交換以及對共同體的共享與共建。這一點不僅體現在人們對周揚青所爆料的出軌和“多人運動”的津津樂道上,還體現在輿論中出現的對周揚青的各種批評、謾罵、羞辱和污名。
人們對出軌以及“多人運動”的關注焦點大都在其所暗示的性能力上,并且也由此展現著一個異性戀男性所能擁有的性魅力,以及對女性的駕馭。在其背后是一個看似古老但卻又十分近代的迷思,即在某種程度上,男性的性能力的高低被塑造成一種霸權性男性氣質中的重要元素。一個男性的性表現力越高,他的男性氣質便“越高”,而其由此所收獲的性別紅利、在男性群體內部所得到的贊譽,以及因此所能擁有的地位也便隨之升高。這一過程本身看似只在男性群體內部運作,但我們不要忘了,異性戀男性“多人運動”的對象都是女性。正是通過對她們以及她們的性的掌握和擁有,才讓男性獲得在其共同體內的榮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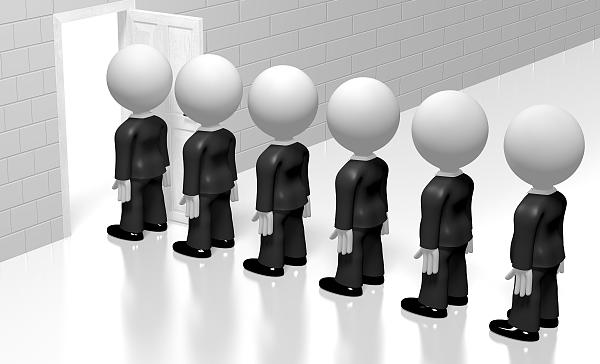
因為女性及其性被用作男性以及其群體之間流通和交換的物品,而為了維護這一壟斷地位,性別制度必須擁有對性的掌控權,因此解釋性成為它的特權。作為客體的女性,她們時常因其在現實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由此被粗略地分為“蕩婦”和“圣母”兩種形象。這一來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男性生活的經驗,通過這一二元對立的劃分,不僅一方面鞏固了傳統的性別制度中的兩性等級,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內部出現裂痕,從而出現了布爾迪厄在其《男性統治》一書中所發現的問題,即一些女性同樣積極地參與和保衛傳統性別制度的鞏固與完整,成為共謀者。
近幾年發生在韓國的諸多女明星的自殺事件,當我們觀察其生平所受到的諸多批評時便會發現,圍繞著性的污名和羞辱占據其中很大一部分。而當這一點與東亞許多國家對傳統中女性“清純”形象的想象和建構合流后,像崔雪莉與具荷拉這些展現著自己性魅力的女明星必然會遭到主流充滿了男權意識的性別制度的圍剿。而與之形成對比的便是當我們看到男明星展現其性魅力或是性能力(許多網友根據此次事件,制作出各種各樣惡搞的時間作息表,其大都圍繞著如何能有足夠的精力開展自己的性生活)時,輿論則往往一邊倒地對其進行贊美、羨慕和鼓勵。
導致這樣雙重標準的不正是性別制度本身的等級化和不平等嗎?在許多男性那里,性越多似乎就暗示著他們能夠擁有更多無論是物質的還是象征的資本;而在許多女性那里,性則往往是她們被污名和羞辱的最典型手段。而為了抵抗這一強勢的傳統污名,我們也看到無論是在性騷擾性侵事件中,還是在日常的生活層面,女性們為了奪回這一自主權利而不斷強調其背后的強制力以及雙重標準中的等級化。而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西方女權運動在上世紀中后期在對淫穢色情品的態度中才會產生出堅決抵制的一派。
在與凱瑟琳·麥金農一道發起反對淫穢出版物的安德蕾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看來,一直以來主要面對男性的淫穢色情品是對女性基本權益的侵犯。在其《色情文學:男性對女性的占有》一書中,她批評傳統此類色情中所暗含的強烈男性宰制力和權威便是通過性在發揮作用。而由此喚醒了男性內心深處的本能,將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穢出版物本身并沒有直接描寫暴力,但其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識形態,仍然是男性世界觀念的暴力表述。德沃金把它稱為“男性真理”。
然而,在這樣的雙重標準,以及人們對男性的性表現和性能力所流露出的某種“過分”的熱情和討論背后,我們或許也能窺探到某種更隱秘的焦慮。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王德威通過對晚清狎邪小說中那些在煙花柳巷內混的如魚得水的男性之性的討論,發現存在其背后的是當時整個男性群體對性的焦慮和不安。在這背后不僅牽連著整個社會轉型期所產生的各種震蕩,還與男性本身在新的、未知的未來社會中的角色和位置等的不安緊密相連。在一個混沌且充滿種種意外、無常和迷惘的社會中,男性通過對性的反復言說和討論,以及對其幾乎是癡狂的解構、揶揄、嘲諷與再建,一方面來掩蓋自身的性焦慮和不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過這一古老的傳統來穩定自身的舊日地位和利益。
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布呂克內在其《愛的悖論》中指出,伴隨著20世紀性解放所帶來的是一系列的無所禁忌。性成為人們享受生活、完成自我以及與他人建立親密關系的重要手段。而伴隨著性話語、言論和表現的層出不窮,在這看似蓬勃的表象背后卻是性的枯竭。并且,當這一龐雜且漸漸占據主流地位的關于性的神話的誕生,許多人——尤其是男性——開始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即一旦自己未能達到那一完美標準的性表現或能力,則可能會迅速遭到其他人的嘲笑,甚至由此可能遭到在男性共同體內部的排斥與打壓。最終,不再是人們控制性,而是性反過來規訓和鞭策著每個個體,就如福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性話語爆炸中所發現的現象。
對性的過分推崇最后使得人們對性的焦慮遍生。在此次那些關于羅志祥性能力的贊嘆、揶揄和各種吃瓜中,也從側面反映出參與者們自身對于性的神話的了解與臣服,而在那些諸多教授人們——或許主要面對男性——如何合理分配時間、保障自己精力的惡搞海報中,我們也能發現許多男性對此的焦慮與不安。
曾經作為塑造著男性個體的性/別意識、氣質和作為與其他男性以及整個共同體形成的互動與聯系的性資本,如今雖然依舊承擔著這樣的舊職,鞏固著傳統性別制度,區隔著兩性在其中的等級和差別對待;但同時卻也在成為新的“大他者”(The Other),掌控著每一個擁有它的個體,讓他們為此奔波不斷,最終成為其奴隸,而徹底失去了原初性解放所具有的關于個體、人性以及自由、性快樂、開放和多元的生活的期望。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