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個值得警惕的事實:這些藥物可能改變你的性格
原創 簡單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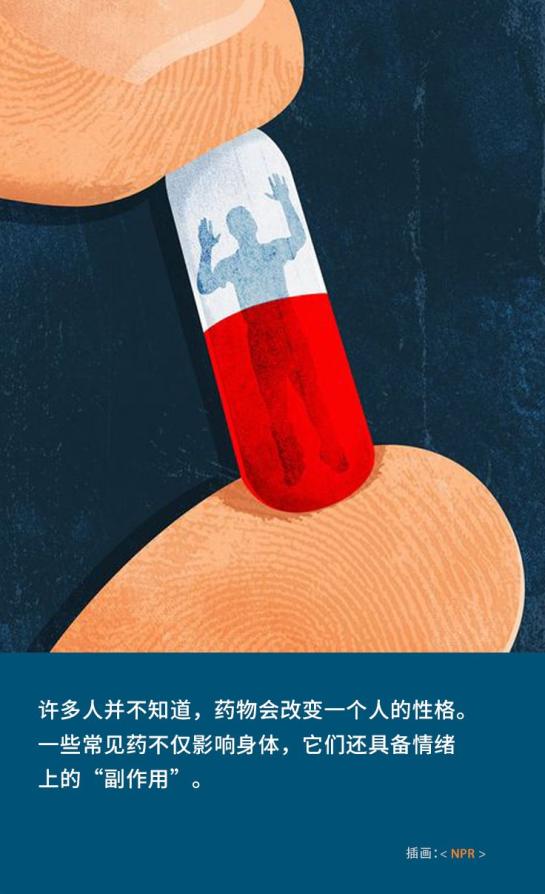
江湖邊 ? 編輯
“吃完這藥,你就會從一個通情達理的好人,變成一個性格暴躁的人,會對家人摔杯子、砸電視”。
——聽完這句話,你是不是覺得這是什么管制毒品?
不,新的研究告訴你,它可能是撲熱息痛,是抗組胺藥、他汀類藥物,是哮喘藥物和抗抑郁藥。
這些看起來普通的藥物,不僅影響身體,還影響大腦。它們可能會讓人產生沖動、憤怒或不安的情緒,削弱共情能力,甚至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性格。
藥物帶來的變化極其微妙,卻可能具有災難性后果。
2011年,一名法國男子起訴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他說,自己吃的帕金森藥,讓他變成了一個賭徒和同性戀性癮者,還讓他犯下了強奸罪;
2015年,一名在網上尋找色情交易的男子辯稱,是抗肥胖藥物杜羅明“讓”他這么做的。他說,這個藥降低了他控制沖動的能力。
除此之外,還有些殺人犯,會把他們的罪行歸咎于鎮靜劑或抗抑郁藥。
如果這些說法是真的,那這些如此常見的藥物,可能正在影響數百萬人的性格和命運。
吃完他汀類藥物后,他被“完全顛覆”的性格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研究者Beatrice Golomb一直在收集美國各地患者服藥后的報告,并見證了無數被藥物改變的不幸的人生。
她發現,患者的性格問題往往都始于服用他汀類藥物,而在停藥后迅速恢復正常。
“五號病人”50歲,患有糖尿病。
在報名參加一項他汀類藥物(一種可以降低膽固醇的藥物)臨床研究后,這個曾經的好脾氣老實人突然變得暴躁易激惹,表現出路怒癥的行為,甚至還曾威脅要將家人送進醫院。
幸運的是,他和家人很快意識到了問題,他不顧研究者的反對堅決停藥,并在兩周后恢復到原先的性格。
但是,像“五號病人”這樣好運的人并不多。更多人的結局,往往是家暴、婚姻破裂、職業生涯被毀甚至失去生命。
Golomb表示,大多數患者其實是很難意識到自己產生了行為變化的,更不可能聯想到變化與藥物之間的關系。可是,行為變化帶來的后果卻在不斷困擾著他們的人生,在對真相毫無知覺的情況下,一些患者甚至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二十年前,Golomb是最先懷疑他汀類藥物與人格改變相關的科學家之一。
她試圖在醫學文獻中尋找線索,發現藏在蛛絲馬跡之中的證據比她想象要多得多。比如,已有研究證明,如果讓靈長類動物吃低膽固醇飲食,它們會變得更具攻擊性。
這跟藥有什么關系?
一個可能的機制是,低膽固醇會影響血清素水平。血清素是一種重要的大腦化學物質,被認為參與調節動物的情緒和社交行為,研究表明它與暴力、沖動、自殺和謀殺有關。如果他汀類藥物影響人們的大腦,可能就是因為它降低了低膽固醇,進而干擾了血清素水平。
隨后,更多證據涌現了出來。
比如,Golomb在1000人樣本中進行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發現,降低膽固醇的藥物增加了絕經后婦女的攻擊性,但對男性沒有影響。
比如,2018年,科學家們曾給尼羅羅非魚服用他汀類藥物,發現這使它們更具攻擊性,甚至改變了它們大腦中5-羥色胺的水平,這表明膽固醇和暴力之間的聯系是一個可以用百萬年為單位考量的古老生理-心理聯結。
再比如,Golomb在瑞典進行的一項研究,比較了25萬人的膽固醇水平與當地犯罪記錄,發現膽固醇水平較低的人,更可能因暴力犯罪而被捕。
這一切證據都指向一個結論——他汀類藥物可以引起人們的行為改變,而這種影響的強度因人而異。

如果他汀類藥物還不夠常見,那么,我們來說說撲熱息痛
在美國,人們每年消耗的對撲熱息痛(也被稱為“對乙酰氨基酚”)超過4.9萬噸,相當于每人298片。
比起“迷幻藥”這類幾乎在全球都被嚴格管制的藥物,它足夠常見和易得,甚至不需要醫生的處方。
但俄亥俄大學的疼痛研究員Dominik Mischkowski在自己的研究中,發現撲熱息痛一個可怕的副作用——降低人們的共情能力。
很長一段時間來,科學家們都知道,撲熱息痛可以通過削弱某些腦區活動來止痛,例如抑制在我們的情緒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島葉皮層。這些腦區通常與社會痛苦有關——有趣的是,在我們在經歷社會拒絕或排斥后,撲熱息痛可以讓人感覺更好。
最近的研究顯示,同一個腦區的功能比想象的更加復雜多樣,大腦中感知疼痛的中樞與共情也有關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顯示,當我們“積極共情”時,腦區會變得活躍,就好像我們正在經歷痛苦一樣。
為了證明二者的關系,Mischkowski與同事招募了一些學生,一組服用標準劑量的1000毫克撲熱息痛,另一組服用安慰劑。然后,讓他們讀一些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振奮人心的故事。
結果顯示,撲熱息痛顯著降低了他們感受積極移情的能力。
這一結果對藥物如何影響數百萬人的社會關系具有強烈的啟示意義。盡管這項實驗沒有考慮到消極共情,即感受他人的消極情緒,但Mischkowski懷疑,消極共情同樣會受到抑制。他還表示,考慮到撲熱息痛的受眾之廣,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令人擔憂的研究。

“當你給某人一種藥物時,你不僅僅是給他藥,你還給了他一個新的社會系統。”他說。
共情能力不僅僅決定你是否是個“好”人,或決定你是否會被電影感動流淚。好的共情能力還意味著更穩定的浪漫關系、適應能力更強的孩子和更成功的事業。一些科學家甚至認為,共情是人類之所以能夠超過其他動物的本質,我們不能小看降低一個人的共情能力所帶來的后果。
但是,嚴格來說,撲熱息痛并沒有改變我們的性格,因為它的作用只持續幾個小時,而且很少有人持續服用。
但Mischkowski強調,了解它對我們的影響依然非常重要。比如,在服用撲熱息痛后,最好不要把自己置于一個需要有情感反應的環境中。
抗抑郁藥的副作用:讓一個人“人格改變”
另一個研究,則更直接地揭露了藥物與人格的關系。
2009年,美國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開始探究抗抑郁藥是否會影響我們的性格,尤其是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人格,一種表現為恐懼、嫉妒、嫉妒和內疚等焦慮情緒的人格。
研究者招募了中重度抑郁癥的成年人,將其分為三組,分別給予抗抑郁藥帕羅西汀(一種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安慰劑和談話療法。然后,跟蹤他們在隨后的16周內的情緒和性格變化。
結果是,藥物讓患者的神經質人格分數降低了。其中一名參與者Robert DeRubeis還表示:“藥物才是根本原因,安慰劑(或談話治療)根本不起作用。”
更令人意外的是,藥物對神經質人格的減少程度,甚至高于對抑郁的減緩程度。它對神經質人格和抑郁上的影響是完全獨立的。除了神經質人格外,服用抗抑郁藥的患者也開始在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人格上得分更高。
這個研究尚在初步階段,其結論并非絕對可靠,但其觀點依然是啟發性的。一種解釋是,SSRI改變了大腦內5-羥色胺的含量,而這種化學物質與神經質人格有關。

或許有人覺得降低神經質聽起來是個好事情——確實,過高的神經質與早逝有關,但神經質也是有好處的,它可以幫助人們規避風險。
“美國精神病學家Peter Kramer曾警告大家,抗抑郁藥物可能會讓患者變得冷漠。如果我的朋友需要服用抗抑郁藥,我肯定希望他知道這一點”,DeRubeis說。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研究結果并不是讓人們停止服藥。
抗抑郁藥物已被證明有助于防止自殺,降低膽固醇的藥物每年挽救了數萬人的生命,撲熱息痛因其緩解疼痛的能力而被列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藥物名單。
只是在治療主要疾病的同時,我們希望人們都有權了解藥物在心理上的副作用。
比藥物影響更糟糕的,是學術研究的空白——因為性格的改變不易測量
有時,藥物對性格的影響可能突發且極其強烈,這就比較可怕了。
比如,左旋多巴(用于治療帕金森的藥物)增加了沖動控制障礙(ICD)的風險,它會讓抵抗誘惑與沖動變得更加困難。
2009年,一名帕金森氏癥患者犯下了6萬美元的詐騙罪,他把自己的行為歸咎于藥物治療,聲稱藥物改變了他的個性。
他說的話并非沒道理。帕金森氏癥會逐漸破壞大腦里產生多巴胺的部分,而左旋多巴本質上就是為大腦提供額外的多巴胺。但它可能導致患者突然開始進行高風險行為、沉迷賭博、過度購物甚至產生性癮。
時至今日,左旋多巴依然是治療帕金森氏癥最有效的藥物。因此,盡管藥物的副作用能列出長長的一籮筐,每年依然有數千人服用左旋多巴。

但是,比藥物影響更糟的,是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忽視。
Golomb發現,研究者更關心易于測量的事情。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他汀類藥物副作用的研究都集中在肌肉和肝臟上,因為它可以通過標準的血液檢測來追蹤。
“藥物對人格和行為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存在巨大空白,”Mischkowski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我們對這些藥物的生理作用了解很多,卻不明白它們是如何影響人類行為的。”
盡管已經有許多研究,揭露了不同藥物對心理的副作用,但DeRubeis、Golomb和Mischkowski都認為,他們正在研究的藥物仍會繼續被廣泛使用。
“作為人類,我們經常嘗試一些可能有害的東西“,Mischkowski說,“比如我就常常用酒精來止痛,。只要你在正確的環境中使用它,就不會有太嚴重的后果。”
為了盡量減少不良影響,讓藥物的價值最大化,他強調我們依然需要知道更多。
因為,如今關于藥物如何影響個人乃至整個社會行為的研究,可以說依然還處在“一團迷霧”之中。
本文編譯自
BBC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