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康復后的幽靈
窗外天蒙蒙亮,丁宇輝躺在床上,渾渾噩噩的,好像聽到貼在墻上的對講機發出沙沙的噪音,“量下體溫哦”,是護士的聲音。
丁宇輝條件反射般醒來,抓到手機,清晨6點半。
床頭看不到溫度計,手指頭也沒了血氧夾,這是家里臥室,不是醫院的病房。他轉過身,兩個孩子還在熟睡,口水的痕跡蜿蜒著留在下巴上。
他們對這個剛治愈新冠肺炎的33歲男人的心思一無所知——總揣摩著身體還帶著毒,怕傳染,他一度習慣背對孩子睡。出院半個月,妻子仍在隔離點接受醫學觀察,他瘋長的焦慮無處可訴。
丁宇輝屏著呼吸,小心翼翼幫孩子補上踢掉的被子,勒令自己再次睡去,起床后,他還要面對鄰居、同事的冷眼。
截至3月26日24時,全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1340人,死亡3292人,治愈出院74588人。
他們出院了,從疑似患者、確診患者到治愈者,邁過一道道坎,卻發現自己成了“感染過病毒的人”。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200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非典痊愈出院病人在3個月內抑郁狀態和焦慮狀態的檢出率分別是16.4%和10.1%,這種心理損傷可能是慢性的。北京安定醫院的心理醫生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期也發現,約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認為自己很倒霉,愈后不被社會正常接納;而那些把病傳染給別人的人又感到愧疚。
治愈者另一版本的故事,是傳染病留下的長久余響。
流言
從醫院走出來那一幕太令人熟悉了。握手、獻花、拍照,醫生戴著口罩道賀,“恭喜你啊,你治愈了,克服了困難,又一例出院了”,兩人都滿臉喜色。“官方而暖心”,丁宇輝回憶說。
他曾是汕頭確診病例的25分之一。2月12日出院,“自由的氣息”,丁宇輝在朋友圈寫道。
業主群里,他馬上發了一條信息報告出院。群里一派歡欣,有歡迎他回家的,有叮囑多休息的,緩和了他不安的神經。臨近出院,他反復問醫生回去后可不可以出門,醫生說只要戴口罩,基本上沒什么事了;他擔心病毒在自己車里留存,“在沒載體的環境下存活不了多久”,這點他也特地和疾控中心的人確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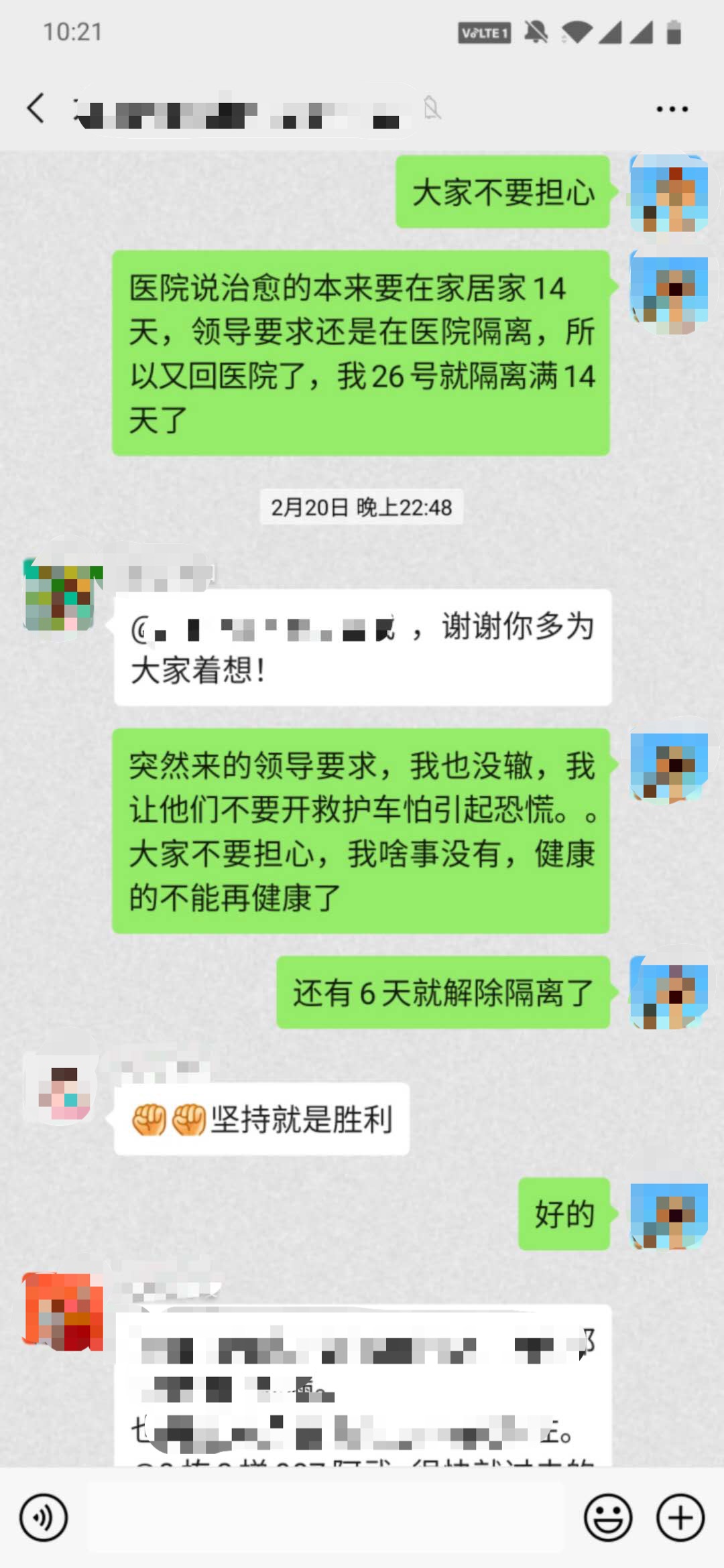
丁宇輝出院后被送往隔離點,擔心救護車進小區會引起恐慌,在群里安撫業主。受訪者供圖
刺耳的言論還是冒了出來,是某個業主的方言語音,“你生病了回來干嘛呀,到時候傳播給大家。”丁宇輝默默聽著,沒有回復。
一些康復者因此“不想回家”,身處湖北黃石的田靜向開車來接她的社區書記倒苦水——田靜48歲,1月底確診住院后,密切接觸者隔離政策還未頒布,愛人和女兒經鄰居投訴被送至隔離點。因此,田靜尤其在意鄰居的反應。
社區書記安慰道,“誰也不愿意碰到這個事情……”田靜心不在焉,精神緊張,和他有意隔著一段距離,用酒精把衣服噴得深一塊淺一塊。
回到小區卡點,鄰居在門口指指點點,怎么回家了?他們家有幾個人感染了?經過她們家要帶幾層口罩?……
田靜一句句聽得真切,皺著眉快步往家走。
冬夜寂寥,回家第一晚,田靜坐在臥室床上,睡不著覺,“我該不該回來?”她想不到還有什么退路。
之后沒幾天,鄰居的流言蜚語又竄了出來。
田靜家住2樓,房間窗戶外是一塊空地,廚房的排氣口正對空地,天氣好時鄰居們會在這里曬太陽、聊天。他們的議論聲也從窗口傳來,“誒呦,他這個氣傳出來有毒的,你們離他家遠一點。”
田靜不理不睬。“你能怎么樣?你只能聽別人說,是不是?”她向記者傾訴。
某天早晨,沖突差點升級。窗外,她看到對門鄰居藏在一棵樹后面盯著她的房間。“像被關在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田靜形容。
她忍不住多日的憤怒,拿起手機拍照,沒想到那人摘下口罩,對窗戶吐了一口痰,她止不住害怕。
憂思集中在小小的房間里。早上醒來,晚上睡前,想到現在的處境,田靜的眼淚流進口罩。
鄰居的健康是她的頭等大事。田靜每天問愛人,附近的鄰居是不是沒事?聽到肯定的回答,心才落下來,“如果有什么事,人家肯定會放到你頭上來”。
流言從小區蔓延到城市和網絡。田靜擔憂的事,在荊州首例治愈的危重癥患者李振東身上成了真。
李振東1月31日出院后,曾在2月16日因為左心室下有點疼,去醫院做了復查,再次住院。李振東知道這不是復發,他做了三次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出院記錄寫有“經新冠肺炎專家組討論,排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2月19日,他的手機突然涌入大量信息,朋友們轉來一張微信聊天截圖——“因為之前那個出院的李振東又住進去了,他又復發了,現在小區成重災區了。”
新增了確診和疑似病例,小區強制隔離,每家每戶封門,李振東猜測,業主們“有了想法”,認為他是傳染源。
實際上,最初確診后,李振東就住進父母的社區,沒有接觸過原來小區的住戶。
截圖在各個群流傳,罵聲一片。不認識的微信好友也給他發私信,打電話。
4天后,區防控指揮部將小區所有病例行動軌跡公布,李振東才感覺獲得“清白”。
難聽的話還是鉆進了他和家人的耳朵里。一次視頻聊天中,家人無意中說出,剛開始那幾天,他們不敢出門,怕見到人被指著鼻子罵,覺得尷尬。
郁悶、氣憤,那幾日,他總是不由自主會想到這些事。后來,他不再回想,“調整心態,身體是自己的”,電話那頭,37歲的李振東憨憨地笑。
這不是他第一次被“全網轉發”。1月確診后,荊州市辦公室信息綜合室一份關于荊州市新增1例危重癥疑似病例的報告在網絡上泄露,李振東的姓名、工作單位、家庭住址被曝光。
那時,他正病重,不知能否熬過生死關頭,電話都轉到家人手機,很多客戶打到公司詢問他的病情,擔心自己被感染。
這是他事后知道的,還有后來才知道的事情是,愛人到政府辦公室找人詢問,最終獲得道歉,但仍不清楚在哪一個環節發生了泄露。
他被冠上“毒王”的名號,網絡上,恐慌還在傾瀉,“有說我把我公司的人都感染了,后來變成只要我去的地方,所有人都感染了”,而李振東的同事家人實則沒有一人感染。
“有時候,覺得病毒都沒什么,真正傷害大的就是這種謠言”,說到這里,李振東的聲音低了下去。
驅逐與隔離
有家難回。武漢姑娘倪晶73歲的外婆居住在孝感鎮上的老小區,3月11日隔離后回家,街道書記擔心引起抵觸,特意將時間安排在晚上。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到了封閉小區的門口,幾十人堵著不讓老人進門。
這場鬧劇最終以撥打“110”收場。警察勸誡無效,只得護送倪晶外婆到家門口。
倪晶說,老太太怕給鄰居添麻煩,之后在家不愿開窗開門。洗好的衣服要曬,只敢晾在衛生間,怕掛在陽臺上水滴到樓下。
身為在外地的湖北租客,徐盛的回家路更漫長一些。
父母早年來廣東打工,在村里租的房子中住了十幾年。1月27日徐盛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下午,救護車拉著警報開到家門口,房東下了最后通牒:一個星期之內搬走。
父母四處打電話找房子,因為家有感染者和湖北人的身份,找了十幾家無果。
“你們住在那我們就不敢回來”,房東催得緊,“你們必須走,永遠離開這里。”2月11日徐盛出院,住處仍沒有下落。
徐盛得知,村委會同所有房東規定,不接納湖北人,違反者罰款。他后來找到村委會,工作人員告訴他,只要房東愿意租房子,可以破例并提供他的健康證明。
眼看搬家期限將至,2月16日,徐盛在網上發出求助信,信中說,“我們戰勝了‘病毒’,卻被像‘病毒’一樣排擠、隔離,無處可去”。
當天下午,鎮長聯系徐盛,安排了酒店住處。鎮政府跟房東協商,為房東提供兩個月住宿,2月25日,徐盛一家終于回到自己房中。
回到了家,出門也不那么容易。3月14日,一位湖北黃石康復者的房門被社區貼了封條和告示,社區稱要打個洞穿鏈子把門上鎖,他無法接受,“我們又不是犯人,何況家里還有無感染的人要生活”。
大多數時候,那是無意之舉。武漢的治愈者邵勝強有天發現,家門口的貓眼上多了一張粉色的紙,一個愛心圈著一行字“肺炎防治關愛家庭”,他總覺得有些不是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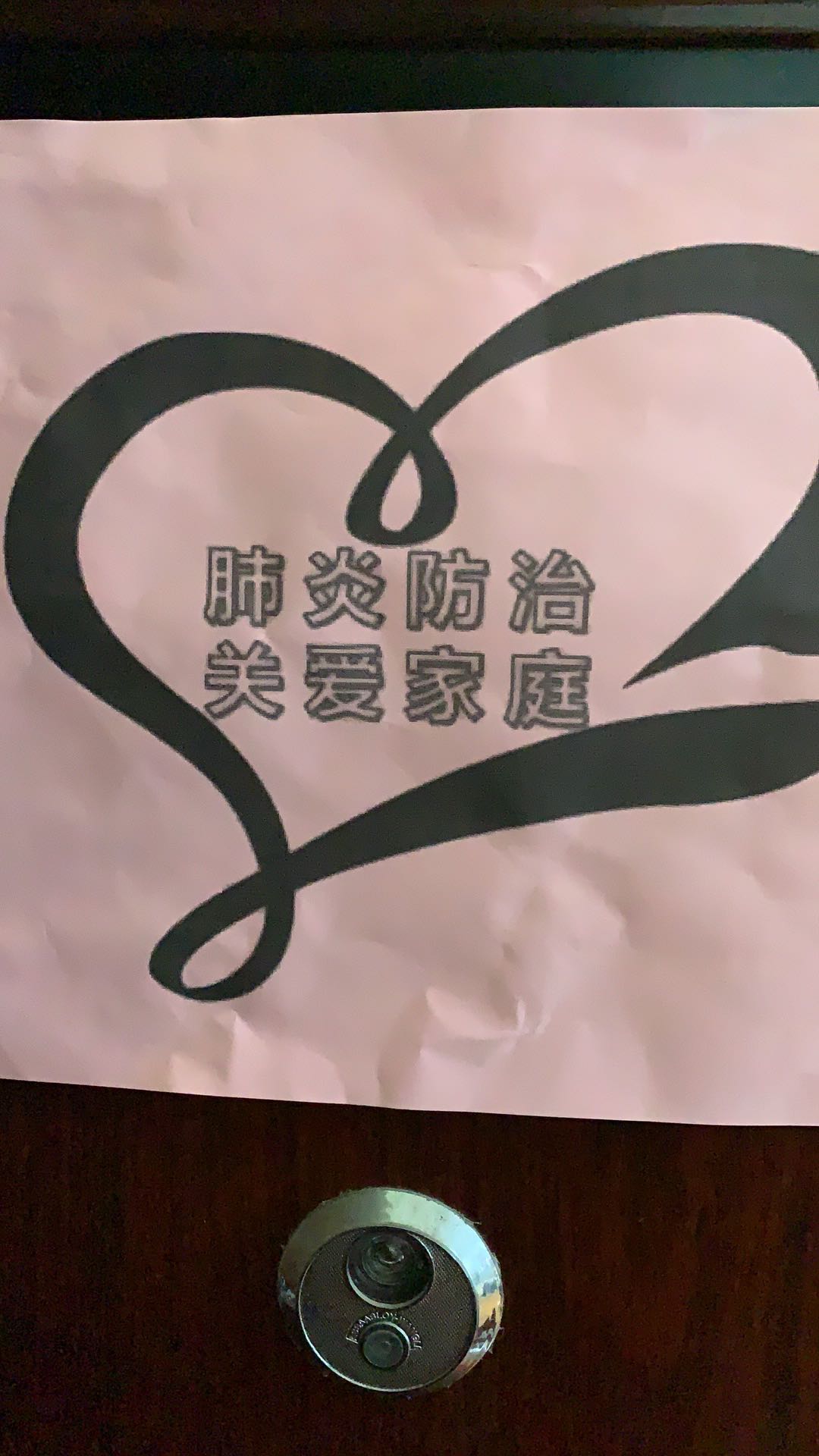
康復者房門上貼有“肺炎防治關愛家庭”的字樣。受訪者供圖
“一個標準的工作流程,本身并沒有任何的錯,可是它帶來的這種感受是需要平復的。”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常務秘書長、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杜洺君曾在心理熱線的電話那頭聽到過隨之而來的“恥感”。
“恥感是在大型公共事件中,社會后來加之于個體的感受”, 杜洺君漸漸明白,康復者所面臨的不僅是心理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回歸社會之困
徐盛母親10年的工作差點丟了。最初,是老板遲遲不讓報到,清理了所有私人物品。報到后,要求選擇其他職位,老板透露出辭退的意思,質問,“你知道多少人在投訴你嗎?你知不知道你現在都是個名人了? ”
“她當場就哭了,回到家傷心了很久”,徐盛只有不斷勸母親,內疚不已。閑時說起,一家人坐在一起落淚,互相安慰。3月10日,徐盛告訴記者,經鎮政府協商,母親獲得了另一崗位,只是工時加了一倍多。
徐盛說,身邊治愈的病友也在經歷類似的困境,“他過了兩三個隔離期了,公司還是不讓他去,他覺得是變相的開除。”
如何真正回到人群中,成為康復者與家人共同的擔憂。
2月18日,《浙江工人日報》報道了一位在杭州食品公司打工的湖北籍員工因為被確診過新冠肺炎,公司決定解除勞動合同。
來自湖北的康復者周鵬還在線上辦公,但已經做好今后線下工作的打算。早會時,他會堅持戴口罩,到天氣熱了為止;他準備待在獨立辦公室,用麥克風跟員工交流;每天上班最早去,下班最晚走;訂了臭氧殺菌機,“盡可能在環境上給大家更多安全感”。
湖北外地區復工早,出院又再隔離14天后,丁宇輝去公司上班。剛進辦公室,同事神色驚訝,“你怎么回來啦。”“你不在家里休息兩天嗎”,有同事語氣委婉。也有人心直口快,“回家補一下身體啊,過兩天再來。你千萬不能有事啊,你有事大家都有事。”有人往后縮了縮,“我現在特別怕,壓力特別大”。
丁宇輝理解,“都是正常的情緒。”他拿出醫生的說法,詳細解釋了情況。
話說多了,又戴口罩,心情和氣息浮動,丁宇輝咳了一下。同事們看他一眼,他感覺整個空氣“凝固了”。隔著口罩,丁宇輝看不清他們的表情。
這天中午,以前一起去食堂的同事和他誰也沒叫誰。有人經過他座位,會繞道走,路上碰到會讓他先過。
丁宇輝性格大大咧咧,平時和同事間也愛開玩笑。這次,他固定在座位上不想再離開,“沒法哭,會被人說跟小孩子一樣。”其他人有說有笑,他對著電腦文檔,變換著打字。
丁宇輝甚至想過去山里生活,“最好一個人待一個月。”
疫情暫時得到控制,但曾彌漫的恐懼與羞恥不會立時消散。紀錄片《非典十年·被遺忘的時光》記載,“我們采訪了3個(非典患者)家庭,每個主人都會戰戰兢兢問: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們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當時的采訪時間,是2013年3月。
湖北省中醫院神志病科主任李莉對一位方艙醫院的康復者印象深刻。后者在隔離時接到朋友電話,說好等出來以后一起喝咖啡。她不斷跟李莉揣測對方會有的心路歷程,“(朋友)她其實是照顧我的情緒,其實她肯定還是怕我的。”
這個康復者還說,今年一年就不出去了,不跟外界聯系。
“慢慢來”,李莉告訴她。
李莉給她分析了新冠的傳播性、傳播途徑,讓她消除疑慮。“然后我們鼓勵他們,不一定非要去跟別人去相處,這段時間先學會跟自己相處。從封閉的環境到上班的環境,中間一定要有過渡,再慢慢擴大,去適應”,李莉說。
杜洺君在接聽熱線時,會引導治愈者把個人和集體、社群的反應分開,“我們邀請他把焦點調到自己身上。”隨后,把新冠病毒和他這個人分開,“這只是生命當中的一個經歷,不能因為這個經歷去否定和抹殺了自己的全部。”
在電話的最后,杜洺君會和來訪者一起討論一個行動方案,先在認知和情緒上進行調整,再強調生理上的營養、運動、睡眠的恢復,“這也是另外一種調焦,把他從情緒的點擴大到身心全部。”
慶幸和感恩,是治愈者常提起的兩個詞,“他們也說,通過我自己的力量,把現在的時光當第二次來活”。
這反而讓杜洺君意識到,他們的心理狀態恰恰是嬰兒的狀態,“從我們社會支持系統來講,我們能做點什么?”杜洺君對記者感嘆,“他們是因為這場疫情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人,我們要予以他們尊敬和感謝,而不是排斥和疏遠。”
治愈者的自我懷疑
走出醫院的時候,山東濱州的康復者趙冉冉看到了太陽,有種“囚禁了很久解放的感覺”。在隔離病房時,窗戶不能打開,她住在陰面,偶爾陽光斜射進來,更多的時候,只能望見連綿的雨雪。
真正出院之后卻沒那么舒心。趙冉冉向記者描述那種“不確定感”:“就想聽到一個權威的說法,說你徹底康復了,你跟正常人一樣了。特別想。那樣的話,哪怕有什么風吹草動,我也不用擔心了。”
出院隔離到第10天,她的精神還一直處于緊繃狀態,“一直走在鋼絲繩上小心翼翼,就想趕快跑、奔跑”。
丁宇輝出院時,網上剛好出現康復者復陽的消息,他翻來覆去看新聞,安慰自己,出院做了咽拭子、肛拭子等六項核酸檢測,結果全部是陰性,但身邊人的躲閃讓他更加動搖。
姐姐告訴丁宇輝,你不在這段時間,嫂子這個人啊,看到你們家小孩就跟看到鬼一樣,跑得特別快。“小孩都檢測過,很健康”,丁宇輝懶得再解釋。
他開始懷念起在醫院的日子,想要躺在病床上的安全感。
出院隔離觀察結束后,丁宇輝再次和醫生確認,“我是不是真正的出院?”
醫生說,電梯在前面,你可以自己下去了,我們不用送你,你回去可以叫滴滴,上班,去食堂,你前后做了八次核酸全部通過。
但上了班,自己是個“帶毒的人”的想法又扎到心里。他耳朵變得靈敏,聽別人咳嗽,想到萬一“傳染”給同事,公司整個廠區就要隔離,承擔不了,壓力越來越大。
一有空,丁宇輝就去門房測體溫,“你看!我才36度5”,他對門房說。連花清瘟,每天吃三次,“其實沒什么問題,也想吃。”
湖北省榮軍醫院老年病科主任張晉在新冠疫情中管理醫院的發熱三區,在對出院病人進行電話回訪時,她發現“死”仍然是高頻詞,“但凡出現一點點不舒服,比如食欲差一點,拉肚子,呼吸不順暢,胸悶,就會聯想到原來的病”。
張晉做出解答后,有患者會說,“醫生你別騙我,我會不會死?”“我這樣搞會不會半天就不行了?”一位在隔離點的出院病人拉肚子,渾身無力,吃止瀉藥也不見好,“早知道我就不出院了呀,我好想住回來,想打針”。
不少康復者依靠安眠藥度過焦慮的長夜。多數求助,想要的就是醫生簡單一句“沒事的”,“在最痛苦的時候,病人是跟我們一起朝夕相處的,所以在信任度、依從性上會好一點”,張晉說。
“沒有得過這個病,就沒有辦法去說,別人是不是矯情”,張晉感受很深,她的同事也感染了,“他們對這個病的認識肯定比一般人更清楚,但他們也會和病人一樣,無比焦慮,無比害怕每一個指標。”
一個醫生每天問張晉,“我的背每天到幾點鐘的時候就開始微微發熱,我一量我也不燒”,張晉不知道怎么安慰好,她能隱隱感覺到,“這個病會改變人很多”。
疫情還沒結束,張晉回不了家,有時候晚上躺在酒店的房間,她也在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還是健康。
后來,張晉建了“康復之家”微信群,對自己科室經手出院的20多個病人“負責到底”,跟進后續用藥和身心的康復。
一些康復者會解讀每一版指南里更新的診療措施;有患者一直核酸檢測陰性,只能診斷為疑似病例,內心焦慮,“他說我這個病得了一場,我還不是這個病,心里很不甘”;有人出院后想到一些問題,會給管床醫生、張晉和群里都發一遍,希望得到各方的認定。
張晉能想象咨詢的病人在手機那頭焦急等待的樣子。有時她一回復,對方馬上就發來一條“謝謝”。一天清晨7點,一位一家6口感染的30多歲女患者往群里轉了一張新聞截圖,是從方艙出院回家的病人4天后突發身亡的事件。女患者提出想再做抗體的檢查,張晉覺得,她可能掙扎了一晚,等到早上才發出消息。
醫生張晉與患者溝通病情。受訪者供圖
“你想TA在隔離點或在家,一個人在房間,捧個手機,也沒有什么娛樂,眼巴巴等著你回一下,而且現在有小毛病也沒法去附近醫院看,醫院都在治新冠。”
康復群給了出院病人一種歸屬感,張晉說,那是像定心丸或者后盾一樣的東西。出院患者互相打氣和安慰,說的話特別管用。
3月5日,首個新冠肺炎康復門診在湖北省中醫院開診,主要對出院并隔離后的患者進行恢復期的復查和心理評估。湖北省中醫院感染科副主任醫師肖明中告訴記者,他接待了很多焦慮的康復者,一個明顯的特征是,有些人來,戴著帽子,穿著襖子,圍著圍巾,“捂得嚴實”。
除了在指標上給出專業的判斷,肖明中也會告訴他們:你已經是個健康人或正常人了,只不過有時候有一些小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跟你以前一樣,但是這不影響什么。
負罪感
張晉的手機像樹洞一樣,從早到晚接收著出院病人的情緒。問的最多的,除了是否完全康復,有沒有后遺癥,就是,什么時候能夠正常接觸到家人?“很多人感覺自己像個定時炸彈。”
最初,丁宇輝在家面對兩個孩子,一般仰著臉,戴著口罩。1歲半的老二伸手要拿口罩,丁宇輝只好一直往后躲。
“小孩上完廁所,我就看他的便便,稀的,中了新冠肺炎了?喝水嗆了咳嗽兩聲,我也覺得完了,你又被我感染了,怎么辦呢。”
即使在家,田靜的口罩也沒有摘下來過,不戴反而覺得空空的。回家第一件事,是把衣服丟在門外垃圾袋,然后沖到衛生間洗澡,愛人沒來得及和她說上幾句話。
洗完澡,她把浸濕的口罩換了,換下來的衣服拿開水和84一起泡,隨后馬上鉆進自己房間。
不得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讓她痛苦。晚飯時,愛人原打算慶祝一番,田靜出來端上碗就走,“你們離我遠一點。”田靜說,愛人神經大條,“哎你別搞那么緊張!”他勸,田靜不聽。
仿佛在病房一樣,房間里外,田靜分出屬于家的污染區和清潔區,并囑咐家人也戴口罩做好防護。
上廁所是唯一出房門的時刻,這讓田靜感到頭疼。出來必須經過客廳,她會等到家人離開,不對著任何人說話;有時水喝多了,家人還在,她就憋著不出來。上完廁所,消毒也是必須的,看著馬桶里泡沫螺旋往下沖,田靜覺得安心。
日常吃飯變成一場精細的作戰。家人將盛有飯菜的一次性的碗筷放在房門口,微信傳達,“飯放在那里了。”門開一條縫,田靜伸出一只手,用酒精噴一圈,再拿進來吃。
透過這條門縫,她能看到客廳的樣子。過去,一家三口會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其樂融融,“肯定會想到以前的生活,人誰都渴望自由,你說是不是?”
感到憋屈,丁宇輝給病毒研究所、主治醫生、疾控中心挨個打電話,“你們能不能幫我再檢測下?”“要不給我小孩檢測下吧?”
“我覺得很辛苦”,他談到那種自責的感受。
主治醫生安慰他,“你現在需要一個心理醫生,也有很多病人要我重新給他們檢測,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治愈的病人很多有負罪感,這種心理對你們來說是正常的。”
周鵬在重癥時,執意在身旁護理他的父母也被感染了。好在他們都是輕癥,最終治愈出院。
等到父母病情穩定,周鵬終于提起,“兒子對不起你,讓你受苦了!只有等你們康復回來了,兒子好好照顧你。”
75歲的母親聽了沒說什么,只說一句:“知不知道你有多危險,我們都以為你回不來了”,眼淚瞬間往下掉。
周鵬才知道,在病情最嚴重時,自己的血氧一度到了82%,再往下低就要切氣管了。
從ICU出來沒幾天,周鵬聽說有護士感染了,“雖然不一定跟自己有關,但總會覺得有愧疚”。
他說,等疫情完全結束,一定要回一趟醫院。穿著防護服的護士們看不到臉,不知道名字, “真的要去謝謝他們”。
長久的創傷記憶
2月中旬開始,湖北省心理咨詢師協會的熱線中,康復者的求助來電逐漸增多。
杜洺君告訴記者,很多人把感受封存起來,還沒有要進行梳理,但是在他們內心,感受都是翻騰和裹挾的,有一點點外界的觸動,馬上會被提取出來。
64歲的武漢康復者沈芳青來不及想太多,她的丈夫在ICU已經超過50天,仍在嘗試脫呼吸機。醫生說,病毒、大白肺、持續高燒,引起腦梗,若能活下來已是奇跡,后期的恢復是漫長的。
在隔離點,沈芳青每天心揪著痛,吃飯有一頓沒一頓,她看小說分散些注意力,疲倦了睡覺,醒來就在與先生的微信私聊中自說自話,把焦慮、擔心用語音存進去,希望他醒來后能聽到。
這是他們結婚42年中最久的一次分離。沈芳青常常責怪自己,為什么沒有早早發現先生的不適。
隔壁房間三個康復病友的老伴都離世了,沈芳青看她們回憶當初的場景,眼淚都流干了。那是武漢最艱難的時期,十多天沒地方查病,“最后好不容易坐在大廳里,在椅子上一邊輸液,針還在手上,人就去世了”。
康復者,這個名字意味著他們也是災難的幸存者。讓不少心理專家更為關注的是,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上,康復者可能會出現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汶川地震以后PTSD的發病率比正常人群高了10%左右。SARS時,我們調查的一個數據顯示是13%左右。玉樹(地震)也一樣,一直到過后三年,PTSD的發生率仍然居高不下”,溫州康寧醫院集團精神心理科主任醫師、浙江省第三批援鄂醫療隊心理醫生唐偉告訴記者,他曾參與過汶川地震、溫州“723”動車事故、麗水里東山體滑坡等災害的心理援助。
唐偉介紹,現在一些患者和醫護人員存在急性應激障礙,而“PTSD”會在事件發生后三個月開始出現,有幾個癥狀——閃回,清醒時,腦子里會想起以前痛苦的畫面;躲避,不敢到相似的環境和場景;警覺性增高,比如睡不著,聽到稍微一點小動作,心驚肉跳;再嚴重者甚至會自殘、自殺。
熬過病危的30歲康復者邵勝強記得重癥病房里的安靜。一天,透過病房門上的玻璃窗,他看到幾個醫護人員拖走一張床,床上是包得很嚴實的白布,醫護人員正對著白布消毒。
他感到害怕,和一種說不上來的情緒,“有多少人都在經歷著這樣的磨難?”
病房里,大家都見證著,沒有人說話。
身邊人逝去,病友間會以故作輕松的方式提起,“旁邊房間今天又打包了一個”,“昨天不是看著還好好的”。
回到家,偶爾,邵勝強會夢到病房的場景,醫護人員還在奔跑,正在查看各個病人的生命體征。
在隔離病房,護士們站在防護鉛板后,觀察胸片拍攝情況。澎湃新聞記者 鄭朝淵 圖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心理科主任醫師王健向記者提到,因為“PTSD”,一些康復者還會出現抑郁的心理狀態。
王健曾在2003年對非典患者心理干預,后續長期支持,也曾參與汶川地震的救援和2014年馬航墜機事件的危機干預。
非典疫情后期,他在心理科門診坐診,陸陸續續有一些患者來看病,他們有非典的病史,已經出院一兩個月,抑郁,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很自卑,“覺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這輩子怎么就攤上這事兒了呢”。
一位護士留下了“PTSD”,將近一年來找王健看診。她在一次運輸中近距離接觸患者,感染了病毒,“好長時間老去想,當時怎么得的病,不能釋懷”。
也有人在冷眼中產生自卑。不過,王健指出,不是所有自卑都會發展成心理問題,災難后,隨著時間推移,開始新的生活,人們就會淡忘恐慌,患者也能慢慢走出來。
“如果需要,也可以尋找精神科或心理醫生,評估心理狀態是否達到抑郁或者創傷后應激障礙,再進行吃藥、認知重建、情緒疏導等等專業的治療”,王健說。
目前,讓唐偉、王健憂心的一個問題是,當各地心理干預隊伍撤退后,后續的心理支持誰來做?能否形成長期機制?
唐偉提出,是否可能延續一省援助一市的機制,回去之后,由各省的心理醫生、精神科醫生繼續與湖北各市對接,然后以當地的心理咨詢機構為主,形成組織,“長期1年-5年繼續做,我們后方提供技術和信息方面的支持”。
王健已經在患者中排查了一些高危人群,同他們建立了聯系。“之后同行的門診還能繼續做心理輔導”,王健在北京通過網絡、電話做心理康復。
治愈后,邵勝強變得樂觀、豁達。他開始覺得,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很多事情要做,就盡快去做,不要等了”。
整個武漢按下了暫停鍵,邵勝強的創業項目也是,資金鏈斷裂,一個月有幾十萬的缺口,員工要還車貸房貸,一度讓他焦頭爛額,但他也不怕了,“大不了從頭再來”。
過去,他一天工作18小時,現在久違地早睡早起,鍛煉,看書,學習。他開始看孩子的手工視頻,列好了和妻子未來旅游的時間表。
回家后,邵勝強在手機上做志愿咨詢,為不了解新冠肺炎的人科普解答,凌晨他會接到人們慌亂的信息。“他們看到我一個重癥患者恢復過來,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也給了他使命感,讓他更好地重返生活。
許多康復者提起捐獻血漿的場景。丁宇輝也捐了血,“彌補一下自己給國家添麻煩的過錯。”看到血從靜脈中被抽出來,丁宇輝心里“感覺好多了”。
周鵬變得感性,血站反饋他血液合規,抗體也達標,兩名患者用上了,在第2天已經情況好轉,“我聽了特開心”。
田靜所在的地區還未解封。在家待著,田靜格外想看窗外,外面的世界現在只有一排排房子,所幸,陪伴她的還有一株桂花樹和家人的支持。
“春天來了,好多樹葉都發芽了。”她期待真正走出家門的那一天。
(丁宇輝、田靜、倪晶、徐盛、周鵬、沈芳青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王蓮張對本文亦有貢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