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梅劍華讀《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從羅素到克里普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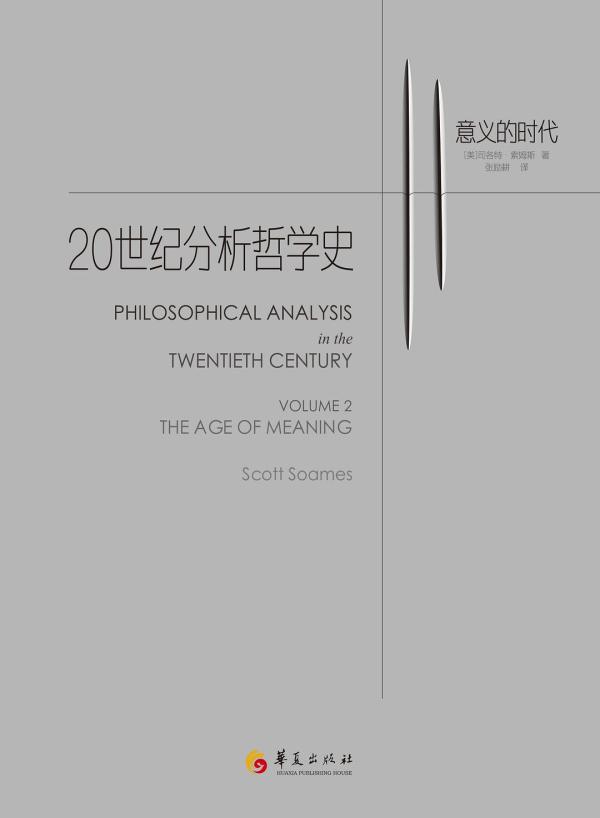
對西方哲學史有所涉獵的讀者大概知道哲學史家溫德爾班的名著《哲學史教程》乃是以康德為中心敘述的哲學史。溫德爾班是一個典型的康德主義者,在他眼里西方哲學史分為三個階段:康德之前的哲學、康德哲學和康德之后的哲學。以此類比,當代美國語言哲學家斯各特·索莫斯(Scott Soames)的兩大卷《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可稱得上是以克里普克為中心敘述的哲學史。在索莫斯眼中,二十世紀前七十年的分析哲學歷史不妨可以劃分為:克里普克以前的哲學和克里普克哲學兩個階段。雖然從目錄上看不到這個區(qū)分,你讀到的是摩爾(倫理學、認識論和哲學分析)、羅素(邏輯和語言分析)、早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邏輯實證主義(包括情感主義和倫理學)、晚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日常語言哲學派(賴爾、斯特勞森、奧斯汀、格萊斯等)、奎因(哲學自然主義)、戴維森(真理與意義)、克里普克(《命名與必然性》)。稍加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索莫斯的敘述乃是以克里普克的語言哲學(主要是《命名與必然性》的立場)為線索,重構(gòu)了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1900-1975)的版圖。
七種武器
2004年秋,我到北大外哲所老化學樓227旁聽葉闖老師的研究生課程“分析哲學原著選讀”,葉老師指定的讀物就是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當問到如何學習分析哲學時,葉老師的建議是在兩三年時間內(nèi)把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奎因、戴維森、克里普克的基本著作系統(tǒng)讀一遍。我把他的要求概括為分析哲學必備的七種武器,這包括:弗雷格的《算術(shù)基礎(chǔ)》《概念文字》(部分),麥克·比尼編輯的《弗雷格讀本》,羅素的《哲學問題》《我們關(guān)于外在世界的知識》《邏輯與知識》《數(shù)理哲學導論》《我的哲學發(fā)展》,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哲學研究》,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gòu)造》《語言的邏輯句法》《意義與必然》,奎因的《從邏輯的觀點看》《語詞與對象》,戴維森《行動和事件論文集》《對真理和解釋的探究論文集》,克里普克《命名與必然性》《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與私有語言》。實際上,能把這些哲學家的代表著作系統(tǒng)讀下來是相當困難的。
葉老師相當重視克里普克,多次開課講讀《命名與必然性》,對該書每個注釋所涉及的問題如數(shù)家珍。葉老師開設(shè)的其他課程也多和克里普克哲學密切相關(guān)。印象中我讀過卡爾納普的《意義與必然性》、薩蒙的《弗雷格之謎》、索莫斯的《超越嚴格性》、賽恩斯伯里的《沒有指稱物的指稱》等。2010年,葉闖教授出版《語言·意義·指稱:自主的意義與實在》,提出語言的發(fā)生學圖像和語義學圖像的區(qū)分,進一步區(qū)分形而上學指稱和語義學指稱,系統(tǒng)回應(yīng)以克里普克為代表的直接指稱論。有人或許以為葉闖追隨克里普克,步克氏思想之后塵。實際上,盡管他很喜歡克里普克風格的哲學,但從具體論證到整體圖景,葉老師都反對克里普克的指稱論,站在了弗雷格一邊。
言必稱羅素
克里普克何以值得索莫斯大書特書,以之為其哲學史撰寫的中心?暫且按下克氏不表,先說一說人盡皆知的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這對早期分析哲學的師徒。羅素堪稱民國時期分析哲學在中國的代表人物。張申府先生乃當時學界公認的羅素專家,羅素這個中文譯名即出自其手。據(jù)羅素書信,曾有一個法國青年想研究羅素哲學寫信求助,羅素回信說有一個人比他自己還了解他的哲學,那就是中國的張申府。申府先生引導其弟中國哲學大家張岱年先生閱讀羅素哲學,張岱年先生在羅素哲學的影響下,于1936年提出了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孔子、馬克思和羅素三結(jié)合。邏輯學的鼻祖金岳霖先生靠著羅素三大卷本《數(shù)學原理》開啟了中國的數(shù)理邏輯學派,沈有鼎、王憲鈞、殷海光這些大學者都出自金先生門下。十多年前我曾從清華圖書館借出過這三大卷《數(shù)學原理》復印,貼在卷首的借閱單上依稀可見數(shù)位邏輯前輩的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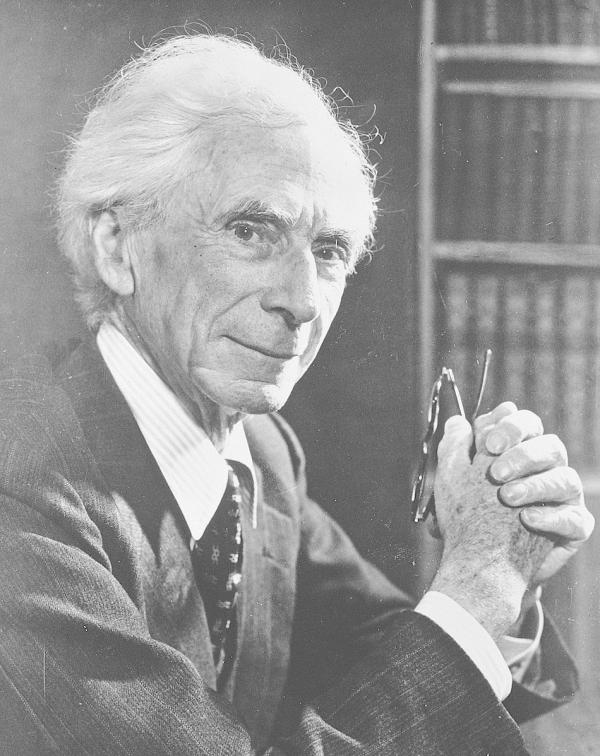
話說1920年9月羅素到中國,除了演講“中國問題”,還講了“心的分析”先后結(jié)集出版。這些觀點并未過時,《心的分析》所提出的中立一元論甚至成為近期心靈哲學的熱點。1927年張申府先生翻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譯為《名理論》),這是《邏輯哲學論》第一個外文譯本。在老輩學人看來,分析哲學在中國基本上等同于羅素在中國,《名理論》不就是羅素邏輯原子主義的擴展版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柏泉之學,浩如煙海”(“柏泉”即羅素名“Bertrand”的舊音譯)。遙想當年,“柏泉吾友”和“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簡直成了學界的通行證。在這種學界風潮下,牟宗三先生早年也苦學邏輯,閱讀羅素的《意義和真理的探究》并寫下長達兩萬余字的書評,還撰寫《邏輯典范》一書。殷海光先生從金岳霖先生學習羅素,撰寫《邏輯新引》帶動研習羅素之風。二十世紀上半葉,羅素在國朝學界就等同于分析哲學甚或等同于哲學。為學無論中西,似乎都重視分析哲學,都重視從數(shù)理邏輯的觀點看,據(jù)說這是咱們天朝文化最欠缺的。
柏泉之學雖一時風云,終有過氣去勢之日。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始,學界風氣為之一變。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先后逐漸進入華語學界視野。牟宗三開始閱讀《存在與時間》和《哲學研究》,很快他發(fā)現(xiàn)自己讀不通海式之作,參不透維氏的《哲學研究》,遂重拾康德三大批判哲學,依據(jù)康德的形而上學建立了新儒家哲學思想體系。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界才接通海德格爾與中國天道。
維派、概幫、自然門:分析哲學的三國演義
遲至二十世紀末,維特根斯坦哲學方在國內(nèi)獲得應(yīng)有之地位。在陳嘉映、韓林合、江怡等學者的推介帶動之下,維特根斯坦巍成顯學。在我求學的年代,陳嘉映翻譯的《哲學研究》、韓林合的《維特根斯坦哲學之路》和江怡的《維特根斯坦:一種后哲學文化》是了解維特根斯坦的必讀之作。陳嘉映老師曾在北大外哲學所帶領(lǐng)學生逐字逐句研讀《哲學研究》,開創(chuàng)了國內(nèi)研習《哲學研究》的風氣。2004年我到北大外哲學所老化學樓227旁聽韓林合老師開設(shè)的兩門維特根斯坦哲學課:一門《邏輯哲學論》研讀課,一門《哲學研究》研讀課。其間韓老師還約請陳老師在課堂上展開一次指稱論的討論。這兩門對應(yīng)于韓老師在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兩本大部頭著作《〈邏輯哲學論〉研究》和《〈哲學研究〉解讀》。江怡老師的《維特根斯坦哲學—一種后哲學文化》出版較早,在本科階段就讀到了。彼時在我看來,分析哲學不就等同于維特根斯坦哲學嗎?早期維特根斯坦代表了早期分析分析哲學的大成,后期維特根斯坦代表了“晚期”分析哲學的大成,這是早年間我對分析哲學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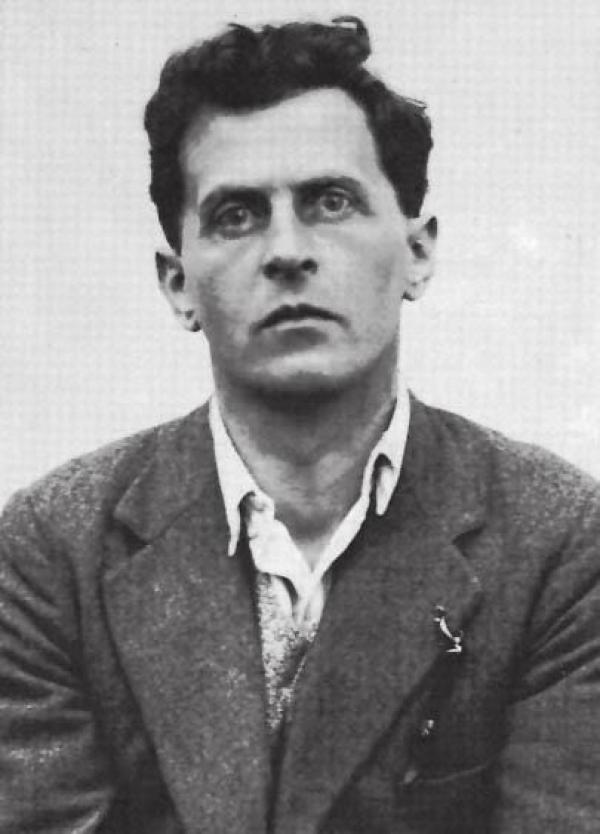
一次翻看《走我自己的路》,李澤厚先生特意提到維特根斯坦和主流分析哲學的區(qū)別。李先生有此言論,想必受其好友王浩先生的影響。1954年王浩曾在牛津大學主持洛克講座,討論過維特根斯坦的《數(shù)學基礎(chǔ)》。王浩反對他導師奎因的自然主義哲學,親近弗雷格、哥德爾的柏拉圖主義哲學。這可算分做析哲學中的自然門與概之爭吧。維特根斯坦獨樹一幟,既和弗雷格、哥德爾概幫路線不同;也和奎因、丹尼特自然主義路線不同。私心以為分析哲學的格局大抵可以看作是維派、概幫和自然門的三國演義。頗有意味的是研究邏輯的王浩是柏拉圖主義者,典型的概幫長老;同為研究邏輯的葉峰卻是一個自然主義者,樸實的自然門大俠。雖然他們二位都同意維特根斯坦與主流分析哲學不同。如何看待哥德爾、維特根斯坦這樣的哲學家在分析哲學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出各自不同的哲學立場。這種立場,經(jīng)常被李澤厚總結(jié)成幾句口頭禪式名言:要康德不要黑格爾、多來點波普爾少來點海德格爾,甚至多來點神經(jīng)科學少來點存在主義(在《中國哲學登場》這個訪談錄里,他曾提出運用神經(jīng)科學證據(jù)研究陽明的龍場悟道)。李澤厚喜休謨似更親分析哲學,無論如何,李澤厚把維特根斯坦和分析哲學拉開距離,還是啟人深思的。
分析哲學當然既不止于羅素也不止于維特根斯坦。公允而論,羅素和維特根斯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概而言之,羅素是大眾的哲學,維特根斯坦是貴族的哲學(可參維氏傳記《天才之為責任》),雖然兩位都算出自貴族門第。選擇羅素和維特根斯坦實際上是選擇了精神氣質(zhì)極為不同的兩種哲學。要羅素還是要維特根斯坦?似乎是每一個分析哲學研究者面對的問題。百年中國學界的趨勢是從羅素哲學逐漸轉(zhuǎn)向維特根斯坦哲學。
分析哲學的典范之作
客觀來說,奎因以來的分析哲學界并不太重視維特根斯坦。克里普克是個例外,他1981年根據(jù)演講稿整理出版的《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和私有語言》只手攪動了英美學界,形成了一個研究維特根斯坦的熱潮,不過這是一個關(guān)于克里普克所理解的維特根斯坦的研究熱潮。克里普克把對《哲學研究》中遵循規(guī)則部分的解讀和傳統(tǒng)懷疑論(休謨對因果關(guān)系的懷疑、古德曼的歸納悖論)結(jié)合在一起,引起了英美哲學界的極大興趣。我最早讀到的這方面中文文獻,乃是發(fā)表在趙汀陽先生1998年主編的《論證》第一期上陳嘉映和程煉二位先生關(guān)于私有語言和遵循規(guī)則的文章。這些文章現(xiàn)在讀來,仍頗受教益。自克里普克論著發(fā)表以來,就招致了很多批評,著名者如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彼得·哈克等。批評者盡可以指責克里普克錯解了維特根斯坦,不過克里普克本人早就說過,他關(guān)注的是打動了克里普克的維特根斯坦論證,而非維特根斯坦本人的論證。他不是做文本解讀重構(gòu),而是以維氏思想為起點提出了自己的論證。
這種論證思路也體現(xiàn)在《命名與必然性》一書上,克里普克提出了一種新的指稱論:名字的意義就是指稱,名字通過命名儀式和因果歷史鏈條獲得指稱。從而反對了弗雷格-羅素-塞爾所主張的描述論:名字的意義就是描述,意義確定指稱。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克里普克并不是要反對哲學史上的弗雷格觀點、羅素觀點和塞爾觀點,而是要反對一般意義上的描述論。他在演講中所刻畫的描述論立場要比哲學史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的描述論更為全面系統(tǒng)。一旦他反駁了自己所刻畫的描述論,那些歷史上曾經(jīng)有的各種描述論版本就不攻自破了。所以他不在乎歷史上有誰對描述論說了什么,而是在乎描述論可能是什么,并進一步反駁之。
這個思路和圖靈的名作《計算機與人工智能》的策略類似。圖靈在提出通過圖靈測試的計算機就表示它具有思考能力之后,就系統(tǒng)列舉了九種可能的反駁,一一加以回應(yīng)。2004年秋季,我在程煉老師于北大外哲所開設(shè)的研究生課程“心靈哲學”課上讀到此文,程老師將此文定位為分析哲學的典范之作。我想,分析哲學不在乎歷史文本細節(jié),而在乎論證和反駁,這是分析哲學的基本精神。在這種精神氣質(zhì)熏陶下,你可能因為個人偏好喜歡某個分析哲學家,但不大可能崇拜某個分析哲學家,因為這違反了分析哲學的基本精神。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分析哲學家不重視文本細讀,實際上這是分析哲學家重構(gòu)論證的起點——正是因為細讀,才得以發(fā)現(xiàn)思想具有多重構(gòu)造的可能性。
“真正的哲學家”要懂數(shù)學
羅素的中國之行、數(shù)次婚姻、幾度入獄和獲得諾獎等不凡經(jīng)歷,給他增添了奪目的光彩。維特根斯坦更為學人所津津樂道:羅素一讀到他的文字即驚為天才;他放棄自己的巨額遺產(chǎn),在認為解決了所有的哲學問題之后改行去做小學老師……這些都為他的哲學增添了無比的魅力。與羅素、維特根斯坦相比,克里普克的生平乏善可陳,他不過是個學院里的哲學家。1940年出生的他,既不能像維特根斯坦趕上一戰(zhàn)被俘,在戰(zhàn)俘營里研究哲學,也沒有趕上二戰(zhàn)像奎因一樣去海軍服役獲得上校軍銜。但據(jù)說他六歲就能閱讀《圣經(jīng)》,九歲讀完《莎士比亞全集》。小學四年級就獨自發(fā)明了數(shù)學,開始思考笛卡爾的懷疑論問題。高中時,他已經(jīng)寫了幾篇模態(tài)邏輯的文章并先后發(fā)表,在審稿人看來,他早已是一個成熟的邏輯學家而非乳臭未干的高中生。當他把文章寄送給普林斯頓大學數(shù)學系時,對方以為他是在找工作,給了他一個職位。克里普克回信說,我媽媽告訴我,我應(yīng)該先讀大學才能教大學。羅素、維特根斯坦和克里普克都在早期就表現(xiàn)出卓越的數(shù)理天賦,這是他們的共同之處,讓人不禁想起柏拉圖學院門口的訓示:不懂幾何者切勿入內(nèi)。以賽亞·伯林也是因為不懂數(shù)理,被哈佛邏輯學家謝弗勸誡不要做真正的哲學,轉(zhuǎn)行做了思想史。

后來克里普克到哈佛大學讀數(shù)學本科,同時給麻省理工的研究生教數(shù)理邏輯。1960年左右的哈佛哲學系應(yīng)該是奎因哲學主導的。據(jù)說有一次奎因?qū)懥似獤|西想請克里普克看一看。第一次約在奎因的辦公室討論,結(jié)果克里普克爽約了。奎因又約了第二次,見面結(jié)束后奎因送克里普克到門口,有人在走道聽到奎因目送克里普克遠去時的喃喃自語:“難道我錯了嗎?難道我錯了嗎?”大學畢業(yè)后的克里普克沒有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而是留校任教了。畢竟,哈佛還有誰能教克里普克呢?1968年轉(zhuǎn)到洛克菲勒大學,是王浩請的他。
新范式之爭:《命名與必然性》
真正讓克里普克聲名鵲起的是他1970年到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做的三次公開演講,當時克里普克剛剛年屆三十。這三個演講錄音稿是吉爾伯特·哈曼(1938年生) 和托馬斯·內(nèi)格爾(1937年生)整理的。哈曼和內(nèi)格爾正當盛年,見證了一個新哲學范式的誕生。克里普克在《命名與必然性》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塑造了1970年以來美國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他的指稱論不僅僅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和形而上學上有重要價值,在元倫理學、美學上也有應(yīng)用,甚至齊澤克在《崇高精神的客體》中也專辟一節(jié)討論描述論與反描述論之爭、嚴格指示詞的哲學蘊含。大哲學家為我們的思考提供基本框架。克里普克最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后天必然命題,他指出,像“晨星是暮星”“水是H?O”等是可以通過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的,但又是必然為真的。這就打破了邏輯經(jīng)驗主義者所秉持的分析命題就是必然命題就是先天命題,綜合命題就是偶然命題就是后天命題的二元概念框架區(qū)分,為人類知識給出了新的解說。在這個意義上,克里普克對后天必然命題的闡釋呼應(yīng)了康德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
《命名與必然性》一書對英美分析哲學界影響巨大,茲舉兩例。第一例是,2002年由蘇珊·哈克教授和陳波教授聯(lián)合發(fā)起的過去五十年來最重要的西方哲學著作投票中,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得了六票,位列第五。在此書之前的是《哲學研究》和《正義論》九票,《個體》八票,《事實、虛構(gòu)和預測》七票。客觀來講,《個體》和《事實、虛構(gòu)與預測》兩書的影響是不敵《命名與必然性》的。第二例是,在非常有名的“3:AM哲學家訪談系列”中,每一個訪談?wù)叨急灰笸扑]五本哲學著作,在問到當世邏輯名家、美國人文藝術(shù)科學院院士范恩(Kit Fine)時候,他只推薦了一本書,那就是《命名與必然性》,這本書被視作語言哲學和形而上學領(lǐng)域的必讀之作。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恢復了政治哲學研究的合法性,那么克里普克的《命名與必然性》恢復了形而上學研究的合法性。學界莫不認為《命名與必然性》建立了語言哲學的新范式,這個范式概念來自庫恩。有一個關(guān)于克里普克和庫恩的段子,兩位哲學家都任教于普林斯頓,其哲學思想有沖突之處。庫恩的范式概念講不同時期的思想和對象是不可通約的,而克里普克的指稱論恰恰強調(diào)的是個體和對象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同一性。概而言之,庫恩強調(diào)世界、思想的斷裂和變遷,而克里普克強調(diào)世界、思想的連續(xù)和統(tǒng)一。
據(jù)說庫恩畏懼克里普克的名聲蓋過自己,不允許他的學生、后來成為電影和紀錄片導演的埃洛·莫里斯去聽克里普克的課。有一次哲學爭論,庫恩忍不住把煙灰缸砸向了莫里斯。心懷芥蒂的莫里斯后來也沒能學成哲學,轉(zhuǎn)行搞了電影。從事電影行業(yè)的莫里斯不忘初心,搞副業(yè)出版了《庫恩的煙灰缸》,敘述當年恩怨,該書和《維特根斯坦的撥火棍》相映成趣。這本書并不限于八卦,莫里斯試圖回歸哲學,從克里普克-普特南(本質(zhì)主義、實在論)的立場出發(fā),批評庫恩的相對論和觀念論,提出了他所謂的探索的實在論立場:雖然沒有所謂絕對真理,但我們可以通過理性、觀察、探索、思考和科學研究來獲得真理。在莫里斯看來,這可視作克里普克理論的應(yīng)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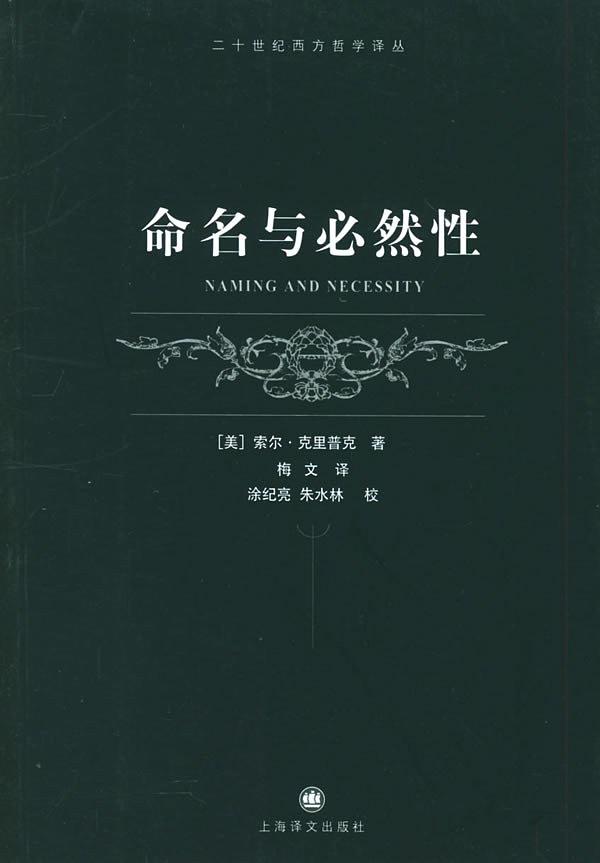
克里普克的希臘工作方式
克里普克是一個典型現(xiàn)代學術(shù)體制下的學院哲學家,但他的工作方式卻是希臘的,他很少為了發(fā)表而撰寫哲學論文和著作。所有的文章和專著實際上都是根據(jù)現(xiàn)場演講錄音稿整理而成,讀來有明顯的口語化風格。他只出版了三部專著:《命名與必然性》是演講稿,《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和私有語言》是演講稿,《指稱與存在》是洛克講座演講稿。據(jù)紐約城市大學克里普克中心透露,克里普克還有大量的演講錄音材料沒有整理出來。
克里普克的研究作風相當傳統(tǒng),迄今為止他的論述主題仍然集中在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哥德爾這些哲學家上。除了罕見在《科林伍德與英國觀念論研究》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歷史與觀念論:柯林伍德的理論》(2017),那實際上是他在哈佛上學期間的本科論文,1960年寫就的。在他當時的老師Richard T.Vann教授和一些科林伍德研究領(lǐng)域的學者催促之下,才在半個世紀后發(fā)表此文。他的《指稱與存在》是1973年洛克講座的演講稿,多年來一直存放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沒有正式發(fā)表,我曾輾轉(zhuǎn)多人獲得一份復印件(此稿2013年正式在牛津出版)。與他本人大量原創(chuàng)的思想相比,他發(fā)表的作品極少。當然也有人指出,也許是因為他晚年身體不好的緣故。
他的研究重點是早期分析哲學史上的人物所關(guān)注的話題。2005年,羅素《論指稱》發(fā)表一百周年之際,他在分析哲學雜志《心智》(Mind)上發(fā)表了長篇論文《羅素的范圍概念》,2008年他發(fā)表了研究弗雷格的論文《意義與指稱:沒有完成的筆記》,他還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中心(CUNY)開設(shè)了一系列分析哲學課程:2012秋季:跨時間同一性;2013年春季:后期維特根斯坦;2013年秋季:維特根斯坦、羅素和我們的自然數(shù)概念;2014年春季:路易斯卡羅爾與邏輯認識論I;2015年春季:羅素哲學;2015年秋季:邏輯認識論II;2016年春季:《命名與必然性》專題再討論;2017年春季:弗雷格;2018年春季:真理論;2018年秋季:偶然先天與數(shù)字的識別性;2019年春季:跨時間物質(zhì)對象的同一性;2019秋季與菲爾德、普拉斯特合開“真與說謊者悖論”討論課。這些問題都是他經(jīng)年累月思考的主題。他在1981年發(fā)表的《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和私有語言》序言中已經(jīng)說過,大概從1965年左右,他就在思考這個問題,直到十幾年后成熟才加以發(fā)表。
克里普克的寫作風格重視直覺,重視思想實驗,重視概念區(qū)分。從分析哲學的三派來看,他當屬概幫。他的指稱理論極大地依賴于他訴諸的大眾的普遍直覺:我們都直覺到尼克松可以不是1972年的美國總統(tǒng),但尼克松不能不是尼克松本人;哥德爾可以不是真正發(fā)現(xiàn)算數(shù)不完全性定理的那個人,但哥德爾不能不是哥德爾本人。在舉這些例子時,尼克松正任美國總統(tǒng),哥德爾就在他講座的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他的例子取自生活。克里普克認為這種關(guān)于名字的直覺是人類所普遍具有的,支持了名字的意義就是指稱這個論斷。克里普克關(guān)于直覺的看法激起了實驗哲學研究,新一代哲學家通過設(shè)計思想實驗,調(diào)查大眾關(guān)于名字的直覺,克里普克的哥德爾案例成為實驗語言哲學引用最廣的思想實驗,這些都是克里普克沒有料想到的。在獲悉實驗哲學的結(jié)果,西方人具有因果歷史直覺,東方人具有描述直覺。據(jù)說克里普克有個頗不友善的回應(yīng):難怪東方人沒有哲學(大意)。他對描述論的批評不僅僅帶著論證,還帶著偏見。
1970年初期發(fā)表了直接指稱論觀點后,他意識到自己理論的漏洞。1973年洛克講座《指稱與存在》試圖解決空名的指稱問題 。1979年發(fā)表的長文《信念之謎》解決名字在內(nèi)涵語境下的可替換問題。
從分析哲學到分析哲學史
1970年以來,克里普克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在他的理論框架下推進分析哲學研究。其中,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哲學系教授內(nèi)森·薩蒙和克氏在普林斯頓的前同事、現(xiàn)任南加州大學哲學系教授司各特·索莫斯堪稱克里普克哲學兩大擁躉。薩蒙1980年出版的系統(tǒng)解釋克里普克哲學的專著《指稱與本質(zhì)》、1986年出版的《弗雷格之謎》可以看做是對克里普克《信念之謎》的推進。索姆斯的著作《超越嚴格性》一書的副標題即為“命名與必然性:未完成的事業(yè)”,他的語言哲學核心工作是修改、擴充、完善克里普克哲學。
除了繼承發(fā)揚克里普克哲學,索莫斯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分析哲學史,他自覺把克里普克放在分析哲學歷史的中心,從克里普克的視角去重構(gòu)分析哲學史。2012年,根據(jù)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所開研究生課程講稿,索莫斯寫成兩大卷《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此書的英文名是《二十世紀哲學分析》,這實際上是一個更具野心的題目,表明除了分析哲學方法再無其他哲學分析方法)。我在本文開頭提到,葉闖老師建議閱讀七名分析哲學家的著作。在意識到存在實際操作困難之后,葉老師給了一個更為實際可行的建議,初學者主要閱讀由馬蒂尼奇教授編輯、牟博教授主持編譯的《語言哲學》論文選即可,因為這個文獻涵蓋了語言哲學和早期分析哲學領(lǐng)域的基本文獻。即便如此,該文選里的一些論文如塔爾斯基的“形式語言中的真概念”對初學者仍然是非常困難的。
最近一些年,葉老師的建議就是初學者可以閱讀索姆斯的兩大卷《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這套書有其獨特價值,索莫斯在序言中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分析哲學史的兩項主要成就:
在我看來,這段時期內(nèi)的分析傳統(tǒng)所造就的兩項最重要的成就是(i)認識到哲學思辨必須扎根于前-哲學的思想,(ii)在理解如下這些基本的方法論概念并將它們彼此區(qū)分開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邏輯后承、邏輯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就前一項成就而言,一條在該時代最好的分析哲學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的主題便是:人們認識到,無論一個哲學理論抽象地而言有多么吸引人,與產(chǎn)生自常識、科學和其他研究領(lǐng)域——該理論有涉及這些領(lǐng)域的推論——的大部分日常的、前-哲學的信條相比,它都不會得到更多可靠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哲學理論都面臨上述這些信條的檢驗和約束,沒有一種切實可行的理論可以大規(guī)模地推翻它們。當然,不只是分析哲學家們認識到了這一點;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他們也并不總是可以抗拒創(chuàng)立一種不受約束的、有時非常反直覺的理論的誘惑。不過,這種傳統(tǒng)已經(jīng)擁有了一種修正上述偏差并回歸可靠基礎(chǔ)的方法。就(ii)而言,與在區(qū)分邏輯后承、邏輯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以及理解其中每一項的獨特特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二十世紀沒有任何一項哲學進步比之更重要、影響更深遠且注定會更持久。導致了這種成功的斗爭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其中有很多彎路。但是,當我們站在一種他們幫助我們達到的立場上來回顧自己二十世紀諸位偉大的前輩時,便會發(fā)現(xiàn),上述斗爭的最終結(jié)果,以一種現(xiàn)在才顯得明顯的方式改變了哲學的圖景。(《分析哲學史·序言》)
《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的特點
索莫斯刻畫的兩個成就揭示了分析哲學的兩個重要特征:重視直覺常識,重視概念分析。這不是一本完全“公正”的哲學史著作,但卻是一本真正的哲學著作。黑格爾稱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索莫斯所建構(gòu)的哲學史就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的展開,而且是一個有立場(克里普克視角)的展開。因此這個哲學史難度要高于一般的本科教材,但要比文選和專著難度略低。有些教材是以問題為中心進行敘述,例如萊肯《當代語言哲學導論》,但對于中文讀者來說從歷史脈絡(luò)來進行敘述更容易進入語境。不過與純粹以歷史為線索的教材相比,索莫斯的書更重視論證的重構(gòu)和批評回應(yīng)。站在今人的視角上更容易看到早期分析哲學家的“功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此書出版之后,即有學者批評指出索莫斯的視野過于克里普克了,以至于掩蓋了其他重要的歷史事實。不過我們已經(jīng)說過這本書并不是要提供一個全面系統(tǒng)的哲學史敘述,而是一個基于特定視角的哲學史論證重構(gòu)。我們已經(jīng)提到了克里普克的策略,在《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和私有語言》一書中,克里普克為自己的論證做了辯護:我不是關(guān)注維特根斯坦到底說了什么,我關(guān)注的是打動了克里普克的維特根斯坦論證。索莫斯也可以做一個類似的辯護:我不是關(guān)注哲學史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我關(guān)注的是打動了索莫斯的分析哲學史。如果你的興趣是了解分析哲學史,那么這本書可能會錯失一些東西。但如果你的興趣是了解和學習分析哲學,閱讀這本書不會讓你錯失掉什么。因為通過索莫斯的論證和批評,一方面了解分析傳統(tǒng)中的哲學論證和批評,可以看到以索莫斯為代表的分析哲學家如何做哲學;另一方面可以嘗試建立自己的論證和批評,真正學會如何做哲學,而不僅僅談?wù)撊绾巫稣軐W。
除了上述兩大特點,此書以摩爾開篇,有深意存焉。索莫斯重點分析了摩爾捍衛(wèi)常識反駁懷疑論的論證和他在倫理學上提出的開放問題論證。作者把知識論和倫理學作為分析哲學史的起點對讀者是相當友善的。人類如何認識世界和人應(yīng)該如何生活這兩個基本的哲學問題是初入門者最容易理解也最直接感受的哲學問題,雖然他的處理較為繁瑣細節(jié),但并非不可以完全掌握。在第二卷日常語言學派的論述中,他又不斷回到知識論和倫理學這兩大主題。這是他和一般分析哲學教材的不同之處。
索莫斯在撰寫兩卷本分析哲學史之后,開啟了更大的計劃,撰寫了五卷本《分析哲學史》,目前已經(jīng)撰寫了兩卷《奠基的巨人:弗雷格、摩爾、羅素》(卷一)、《哲學中的分析傳統(tǒng):一個新的視角》(卷二),他還撰寫了一卷《分析哲學在美國以及歷史和當代哲學論文集》專門討論美國的分析哲學。普特南曾言:“我們從康德那里學到很多,而無須稱自己為康德學派;我們從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學到很多,而無須稱自己為實用主義者;我們還可以學習維特根斯坦,而無須稱自己為維特根斯坦學派。同樣,我也可以從弗雷格、羅素、卡爾納普、奎因及戴維森那里學到很多,而無須稱自己為‘分析哲學家’。”(普特南,《親歷美國哲學五十年》,載《世界哲學》,2001年第二期)在這個意義上,分析哲學本身也進入了哲學史,成為哲學史研究的一個部分。作為一種思潮的分析哲學和現(xiàn)象學業(yè)已退出了歷史的中心舞臺。但分析哲學的歷史發(fā)展卻留下了方法、問題、目標和規(guī)范為后續(xù)哲學發(fā)展奠定了更為穩(wěn)固的基礎(chǔ)。分析哲學史研究逐漸成為分析哲學和哲學史研究領(lǐng)域的一個熱點。
展望:中國的分析哲學史研究
涂紀亮先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分析哲學及其在美國的發(fā)展》是分析哲學史領(lǐng)域的濫觴之作,陳波教授主持編輯的《分析哲學:回顧與反省》(第二版與江怡教授合編)是分析哲學史的重要研究文獻。江怡教授主持翻譯的由麥克? 比尼教授主編的《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即將出版,這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的分析哲學史研究。這個《哲學史手冊》中譯本屬于江怡教授2012年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分析哲學運動與當代哲學的發(fā)展研究”的部分結(jié)項成果。比尼教授是《英國哲學史》刊物的主編,研究弗雷格、羅素、維特根斯坦早期分析哲學,乃分析哲學史領(lǐng)域的一員老將,他還擔任中英美暑期學院的英方主席推動中西哲學交流。比尼教授將于今秋到清華大學哲學系開設(shè)早期分析哲學課程,這也是諸君閱讀索莫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的一個契機。今夏索莫斯大著出版前后,江怡教授獲批“分析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國家重點項目運用分析方法對西方哲學史進行重新解釋,并擔任了國際分析哲學史學會執(zhí)行理事。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分析哲學史和基于分析方法的哲學史研究獲得了國內(nèi)外學界的高度重視。
八十年代以來,在幾代學人的努力下,關(guān)于分析哲學的翻譯、教學和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撰寫教材方面,大陸學界趙敦華教授撰寫了《當代英美哲學舉要》, 陳嘉映教授撰寫了《語言哲學教程》并修訂撰寫了《語言哲學簡明教程》,江怡教授撰寫了《分析哲學教程》,陳波教授撰寫了《邏輯哲學教程》,韓林合教授撰寫了《分析的形而上學》,黃敏教授撰寫了《分析哲學教程》,大陸學者還組織在人大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原典哲學教材譯叢,復旦大學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了《知識論》《形而上學》等分析哲學教材,復旦的徐英瑾教授翻譯了塞爾的《心靈導論》 等等;港臺學界有王文方教授撰寫了《形而上學》《語言哲學》,彭孟堯教授撰寫了《知識論》。凡此種種,流布后世,嘉惠學林。此次索莫斯教授《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的出版進一步推動了分析哲學的教學、研究和傳播。《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史》的主題內(nèi)容和敘述方式介于教材、專著、史論之間,學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有不同意見。該書當年在美國出版即引起相當熱烈的爭論/爭議,此次中譯本出版希望能引起讀者諸君更多批評討論,反思、質(zhì)疑、批判,追求真理而非盲目跟隨崇拜,千百年來哲學即是如此。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