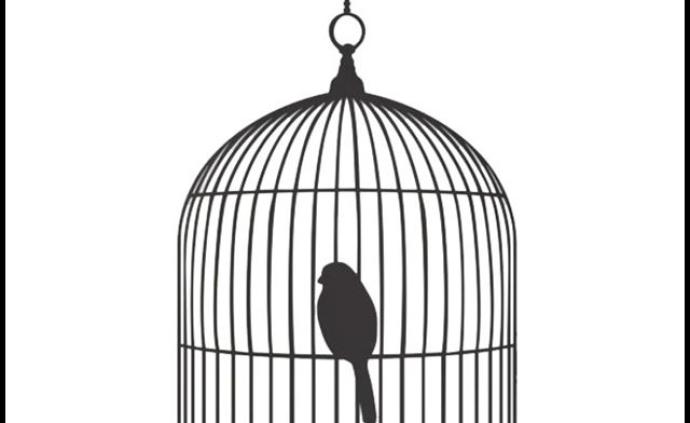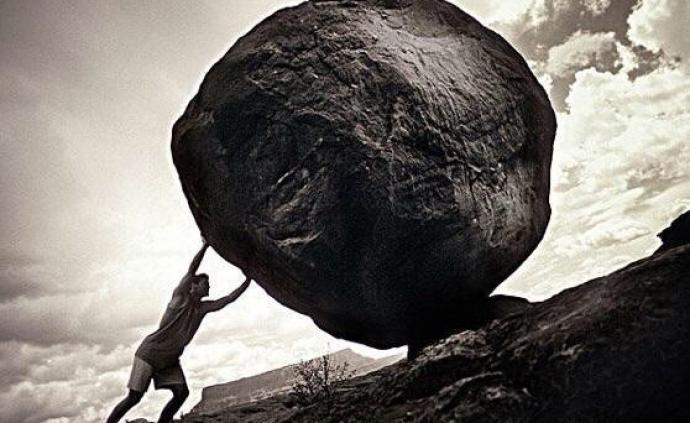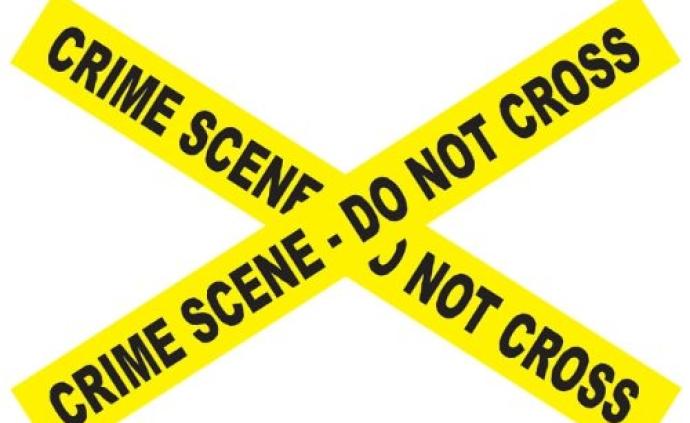- +1408
法治的細節︱沉默權的沉默
聽說今年清華法學院研究生考試的綜合卷里有一道大題:論述認罪認罰制度與沉默權的關系。我十分同情考生,因為中國的認罪認罰制度里面問題不少,而沉默權也處在曖昧難辨的狀態,所以這道題要回答好還真頗費思量。
上周我的同事羅翔老師也問道:“中國真的有沉默權么?”我很肯定地回答:“有的,請參考刑事訴訟法第52條: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他馬上追加了一個問題:“那律師能夠建議當事人保持沉默么?”對這個問題,我心領神會地沉默了,原因請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20條: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
這兩個規定出現在同一部法律里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假設一只貓,偷吃了魚,在你訊問它的時候,它是否可能同時處于兩種狀態:既可以沉默不語,又必須有問必答?那它可能真的是薛定諤的貓……
以上只是個玩笑。我國訴訟法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既然把“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寫進刑事訴訟法,就標志著我國接受了在當今世界具有普適價值的“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刑事訴訟規則,也就是確認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雖然法律也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但上述規定的合理解釋應當是: 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可以選擇回答,也可以選擇沉默,但如果選擇回答,那就要如實陳述。
所以,“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是對司法人員行使權力的要求,“應當如實回答”是公民權利的問題,正是區分了這兩個角度,才能讓兩個看似矛盾的條文存在于同一部法典當中。
上述觀點可以援引2012年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郎勝先生的答記者問,他說:“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是我們刑事訴訟法一貫堅持的精神,因為現在的刑事訴訟法里就有嚴禁刑訊逼供這樣的規定。至于規定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是從另外一個層面,從另外一個角度規定的。就是說,我們的刑法規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了問題,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可以得到從寬處理。刑事訴訟法作為一部程序法,要落實這樣一個規定,它要求犯罪嫌疑人如果你要回答問題的話,你就應當如實回答,如果你如實回答,就會得到從寬處理。這是從兩個角度來規定的,并不矛盾。”
這樣的沉默權似乎和我們耳熟能詳的美國式沉默權的表現形式不太一樣。所以直到今天,學界和實務界仍然有觀點認為中國沒有沉默權。我的理解是,中國確實沒有美國式的沉默權,也大可不必追求同款沉默權。
在美國,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都會熟練的念上一段:“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能成為不利于你的呈堂證供。你有權聘請律師。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我們可以給你免費提供律師。”這段著名的“米蘭達告知”,借助美國影視作品的影響力,傳播到世界各地,使人們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權在面對警察訊問時保持沉默。
毫無疑問,美國的米蘭達告知對于沉默權制度的傳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其實,美國人的沉默權不是米蘭達規則賦予的,而是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的。1791年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有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由此確立了美國刑事沉默權的憲法地位。
這一思想源自英國,它的核心內容“反對自我歸罪”可追溯到英國的古老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究其根源,在13世紀,英國宗教法庭在刑事訴訟中強迫被告人進行“職權宣誓”,否則將被處罰。后來,為了對抗這種不人道的審訊方法,被告人經常以“不必自我歸罪”作為辯護理由。經過發展,“不必自我歸罪”逐漸演變成一項重要的司法制度,沉默權即源于此。
在米蘭達案以前,美國憲法早就規定了“任何人有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可在很長一段時期,警察在訊問中經常使用野蠻刑訊和三級審訊來獲取嫌疑人的口供。直到20世紀中期,這種狀況仍未得到明顯的改善。經過1966年的米蘭達案,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精神才深入人心,眾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警察的“提醒”下、在律師的指導下,紛紛沉默是金,不乏成功脫罪的例子。所以有人指責,在美國,行兇者的人權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權更重要,保護壞人好像比保護好人還要優先,針對警方的清規戒律好像比打擊犯罪的法律法規還要多。
根據美國學者的解釋,這個著名的沉默權包含三項基本內容: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義務向控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陳述或其他證據,控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損人格尊嚴的方法強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實作出供述或提供證據。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拒絕回答追訴官員的提問,有權在訊問中始終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檢察官、法官應及時告知其享有這一權利,并不得因其行使這一權利而作出對其不利的推論。
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就案件事實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陳述,但這種陳述必須是在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后果的情況下作出的出于真實意愿的陳述,法庭不得將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強制或壓力所作出的陳述作為定案的根據。
顯而易見,1966年的米蘭達案,并不是賦予了美國人沉默權,因為沉默權早就存在于憲法里,然而它并不盡人皆知。以沃倫大法官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確立這一規則,“完全不是基于保護無罪人的考慮”,他們認為,“富有的、受過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從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權;反之,貧窮的、未受過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則不知道這種特權。因此,一切被羈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剝奪自由的人,必須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米蘭達規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例如在沃倫法院時期,由于美國當時的審訊制度是三級審訊,警察在一定程度上過度依賴口供,刑訊現象普遍存在并且難以禁止。由于犯罪率不斷上升,法院也默許刑訊逼供所得供述作為定罪證據,從側面縱容了警察的非法審訊。這些都導致了社會以及司法界對于限制警察刑訊逼供的呼聲越來大。當時最高法院的掌門人沃倫大法官是典型的自由派代表人,他做出的一系列判決都表明了當時最高法院自由主義的態度走向。到伯格法院時期,風氣為之一改。總統尼克松認為沃倫法院“過分放縱”犯罪而導致犯罪懲罰力度下降,因此提名保守傾向明顯的伯格作為最高法院掌舵人。同時大法官的派系變化也使得最高法院內部對于米蘭達規則的態度逐步走向保守,例外之門因此不斷打開。
值得一提的是羅伯茨法院時期,美國發生了令人震驚的“9?11事件”,政府加大反恐力度,公眾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部分自由,有學者甚至建議加大米蘭達規則“公共安全例外”的適用范圍。米蘭達規則再次走向保守。但無論如何,直至今日,即便是最保守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還維持著米蘭達規則的崇高地位。
簡單說,1966年前美國的警察不必大費周章的念上這么一段,但那之后,美國的沉默權不再沉默,它以被以充分告知的方式得以體現和保障。漸漸地,有人就在米蘭達告知規則和沉默權制度之間畫上了等號。但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我們可以把美國的沉默權叫做“明示沉默權”,明示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要求司法和執法人員必須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沉默權。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一些國家也采用了明示的沉默權制度,如英國、法國和加拿大。
更多國家采取的是“默示沉默權”。例如,德國、日本并沒有采用“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美國式表述,而是規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享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另外,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款規定,凡受刑事指控的人,不得被強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強迫承認犯罪。
不管是明示還是默示,沉默權之根本目的就是保障人權。它不僅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給予其在偵查程序中對抗的機會,同時也加重了控方的舉證責任。所以,不管在什么歷史時期和國家,沉默權制度都會遇到了不可回避的挑戰:沉默權將會影響刑事司法制度的最初目的,即預防和懲罰犯罪。
也正是這樣的理由,我國刑事訴訟法才會出現貌似薛定諤的條款。既要保障人權,也要懲罰犯罪,沒有哪一個價值取向更不重要。
回到文首那個問題:律師能否建議當事人保持沉默?早年間,確實有律師在會見時對貓說:“給我頂住!”結果貓果然問啥都不知道,最后做了證據不足不起訴。然而這句話并不符合法律精神。基于對現行法律的尊重,我會這樣指點貓的處境:“按照法律規定,你要實事求是。如果認為不構成犯罪的,你要如實向辦案機關說明。你不想說的,沒有人強迫你說。”
沒有人強迫你,這就夠了。
-----
作者陳碧,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