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建陽出版興衰史:閩北山區何以成為中華帝國的出版中心?
【編者按】
中國的書籍文化很早就進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盡管東亞印刷在世界上開啟先河,卻沒有像西方書籍文化那樣被深究細探 。究其原委,一是恰因中國的印刷起源很早,約在公元7世紀后期,當年的資料無論是印本還是寫本,現存實物都很少 。二是有數百年歷史的中國傳統版本學對文字記錄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研究,重點不在刻本和寫本如何影響學習、信息如何傳播、如何借助閱讀獲取知識、書籍如何定價之類現代學者所關注的課題上 。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賈晉珠(Lucille Chia)的代表作《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是一部研究中國書籍文化的作品,圍繞福建建陽的出版業展開,勾勒了一個地處偏遠的中華帝國出版中心的興衰面貌。本文節選自《謀利而印》(賈晉珠著,邱葵、鄒秀英、柳穎、劉倩譯,李國慶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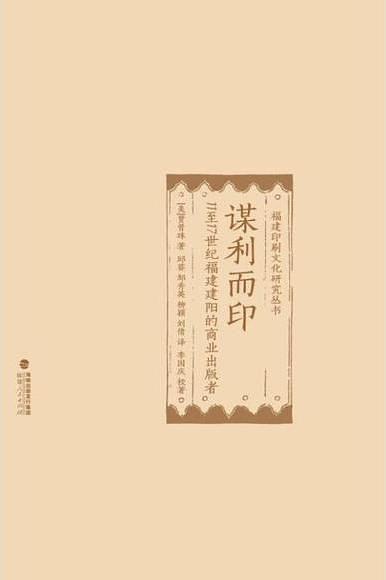
宋初雍熙年間(984—987),唐代數學家、天文學家李淳風所作預言書《推背圖》的印本在開封書市上非常暢銷。但是,出于政權安全的考慮,天文歷法之書必須經朝廷批準才能上市,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因此龍顏大怒,下令印制了一百部含有明顯錯誤預言的印本并投入坊間。劣幣驅逐良幣的格勒善定律在書籍市場中也起了作用,使得買家對包括坊刻本在內的所有刻本都失去了興趣。可見,到了公元10世紀末,雕版印刷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技術,被用來達到各種目的。中國社會中,不只是出版商和讀者,國家的最高統治階級也深諳如何巧妙應用雕版印刷的力量和影響,有些人更是完全出于私利才從事大規模的編撰和出版活動。
建陽出版業長達六個世紀的歷史并非開始于中國雕版印刷發明之初,其在清初的消亡又比雕版印刷的整體衰落提早了至少兩個世紀。但建陽本的故事的確與中國雕版印刷的光輝時代(或世紀)相契合。因此,《謀利而印》揭示了如何通過聚焦于某個地區所刻印的圖書來獲得中國書籍社會史方面的信息,以及如何通過多樣的渠道提取這些信息。由此,我們能夠更準確地界定主導這一研究領域的一系列問題:印刷對于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該影響已在印刷文本和圖像的諸多用途中有所體現;商業出版者對讀者需求的反應;贏利性的印本在外表和內容上隨著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化;雕版印刷主導的文化與歐洲活字印刷在最初幾個世紀里所塑造的文化之間的差異。盡管這些問題讓研究中國的學者長久著迷,大家卻已有一個共識:僅從文獻中找不到可以充分解答以上任一問題所需的信息。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這個共識恐怕過于悲觀。
當然,如果以建陽這樣的歷史悠久、范圍廣闊的出版業為對象,中華帝國書籍文化的諸多方面都沒有辦法細究。但是,如本研究中各章所示,我們仍可發現很多東西。其一是延續性。比如,從公元8世紀雕版技藝的濫觴到19—20世紀被其他印刷方式取代,雕版技術上大的改進寥寥無幾;盡管折葉和裝訂的方式有所進步,中國雕版印本書葉的格局卻幾乎一成不變;幾類書籍,如“四書五經”、小學書、史書、醫方合集及名家詩文集,近千年來一直暢銷(直至今日)。評判印本質量的標準仍然是視其與精美寫本的相似度,即紙墨精良、書法精妙。不管是私刻還是坊刻,大多數出版商所表達的印書目的,都是將一部作品不加變動地刻印出來,使讀者可以讀到珍稀或精善的版本。其二是中國印本在使用上的變化。例如,各個社會群體開始將印刷納為己用的時間順序顯示,要確定一項技術形成的確切時間以及服務對象是很困難的,除非是事后推算。雕版印刷品起初用于宗教傳播,如佛經和道教符箓。到了公元8世紀晚期,有證據顯示,四川和長江下游地區刻印了粗糙的日歷、蒙學課本和小學書。因為當地用于印書的自然資源充足,加速了出版業的發展。直到宋代,朝廷和文化精英們才開始大規模地采用雕版印刷。
宋代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狀況,促使中央和地方的官府及知識階層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采用雕版印刷。這也推動了一些地區出版業的發展,如建陽。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們探討了建陽為何會成為一個如此重要的出版中心的原因。與四川和長江下游地區一樣,閩北擁有雕版印刷所需的豐富資源。宋代商業的整體蓬勃發展也同樣重要,致使那些原非顯赫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區,有可能憑借其適當的自然資源和地理位置,在經濟上占據重要地位。閩北諸鎮是連接福建和江南地區多條內陸商貿路線的貨物集散地。因而通往建陽本的重要市場的商業途徑是暢通的。宋代另一個促使出版業擴張的重要原因,是士人精英階層的發展及與之相應的圖書文化的興起,這種文化也因官府積極地組織編纂、校勘和刊行學術著作而得到推廣,也因科舉制度而成為必然。當然,也有學者認為,科舉制度限制了圖書文化的深度和廣度。上述因素導致了建陽出版業在宋代的迅速崛起,僅看出版商家族和相關蒙學私塾取得的名望就可得知。自宋以降,對學術的尊崇,加上科舉制度,產生出相當一大批深諳儒家士人文化知識并推崇其價值的人,他們中能在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力上達到較高層次的則寥寥無幾。大多數人,盡管身份低微,卻成為這種精英文化的傳播者和弘揚者。以坊刻商為例,他們累積的影響力與儒家思想、價值體系的代表者們可謂不相上下。
在建陽,這些出版商們刊行了自宋以來現存的儒家經典中一些最好的印本,與早已廣為人知的此地盛產低劣印本的名聲完全不符。而且,其他證據顯示,建陽坊刻業在南宋已經相當發達,那頗招非議的“麻沙本”,不論是儒家經典的節略本,還是科舉程文或文集,早已廣泛流通于全國的大多數市場。建陽的坊刻商們生產所有可售的內容,他們的書不僅行銷中國,還遠銷日本和朝鮮。
建陽出版業顯著的商業特點使之到了元代仍然相當活躍。除了學術論著,日常和娛樂所用書籍成為元代建陽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趨勢到了明代更是勢不可擋。事實上,諸如醫書、日用類書、插圖小說之類的書在元代已經存在,并可能在南宋晚期就已出現,從而使人質疑“通俗用書是明代才有的新發展”這一看法。太多不確定因素,以及早期此類作品少有留存至今的情況,使這種看法難以得到證實。
而且,在明前期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全國的官刻、私刻和坊刻活動全面衰落,可作為對中國的書籍刻印在數量和種類上隨著時間單向持續增長這一假設的質疑。特別是建陽,其明刻本只有10%生產于明代前半期(1500年之前),而閩北圖書貿易的全面繁榮更是等到16世紀已過去四分之三時才形成。實際上,因為建陽的圖書貿易,尤其是明代的,像鏡子般反映出中國印刷史的一些總趨勢,我們可以通過1600余種明代刻本所含的信息,推測華南中心地區尤其是江南和福建沿海等文化、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與文化狀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所述,明代建陽本更多地揭示了更廣大的區域的情況,而不局限于建陽本地。
最后,建陽出版業在17世紀中期的徹底消亡仍然是個沒有完全解開的謎。明清易代時閩北地區遭受的混亂和破壞并不能提供充足的解釋。更不能令人信服的說法是,非城市地區的出版中心面對來自大城市同行的壓倒式競爭只能衰落。對此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情況恰恰相反。答案也許在于,至少自明初起一直蔓延于閩北地區的經濟停滯,途經閩北的區域間貿易越來越少,使情況雪上加霜。沒有了這種貿易,建陽出版業失去了與江南和福建沿海那些大都市的圖書中心競爭的優勢。
在一些重要層面上,建陽出版業是獨特的。首先,盡管普遍認為廉價、中檔和低劣的印本多來自中華帝國偏遠的圖書中心,建陽出版商們的產品卻既有刊刻精工的善本,也有廉價低質的劣品,包括了各個層次的書籍。同樣獨特的是建陽出版商們的巨大產量,在他們最活躍的幾個世紀,其產量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偏遠的出版中心,從而成功地與屬于全國最大城市的出版中心進行競爭。因此,關注建陽出版業長期成功的一些因素,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雕版印刷的總體發展情況。那么在中華帝國,是什么造就了一個成功的出版中心呢?首先,由于長期以來運輸費用較高,出版中心應位于有充足的刻書所需自然資源的地方,這是至關重要的。第二,因為當地缺乏大型圖書市場,出版中心的位置必須在重要的商路沿線,以便抵達維持圖書貿易所必需的市場。以上兩個條件都不需要出版中心在都市中心或位于有重要文化、政治意義的地方。 在早期,建陽出版業無疑受到知識階層活動的刺激,使閩北在宋代成為科舉考試最為成功的地區之一,并成為道學的大本營。但在元代和明代,當該地區的文化衰落后,支撐圖書貿易的是上述地理和經濟因素。對圖書出版中心來說,只需要將圖書作為商品,能夠生產、銷售并獲得利潤即已成功,并不需要在當地消費掉。這與中華帝國晚期出現的廉價中檔刻本的成功有所不同。
對未來研究的一些建議
以下建議無法涵蓋中國書籍史研究的所有課題,僅是筆者在做此研究中產生的想法。既是對某些問題的進一步拓延,也是在研究早期中國雕版印刷時,由于有些論題幾無相關信息,因而想到的替代方法。
一些論題僅與建陽出版業相關。首先,對于有足夠多樣本的那類書,個別著作能讓我們做詳細分析。比如,對于宋元時期在建陽刻印的各種儒家著作,我們能否更精確地了解其刊刻模式呢?宋元時期的建陽地區是朱熹及其追隨者提倡的道學的大本營,而明代的建陽沒有和任何哲學流派發生過明顯的關系。這樣一來,這兩個時期建陽所刊刻的儒家著作有何不同?第二,另一類不同的書,如以上圖下文版式刊刻的小說,也值得更詳細地研究。這類書中的歷史演義和公案小說,學界已就其文學風格、內容和面向的讀者群做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析。針對晚明時建陽刊刻的類書,可以做同樣的研究。
諸多當地文人、官員參與了建陽的書籍編纂和刊刻,所以我們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該地區的文化生活,以及為什么在中央和地方官府對于編修和刊刻大部頭作品已經不太積極的明代中期,他們卻開始資助建陽的刻書工程。我們可以搜集來自地方志、族譜和印本的信息來完成這項研究。印本中的序言極有可能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因為序言通常會談論該作品的成書歷史,包括早期的各個版本。有時序言中還會提到刻印該書的原因、參與編纂和發起刻印的人。
不僅如此,如果能夠將現存印本的序跋與那些已亡佚作品的序跋相比較的話,會很有意義。這是可行的,因為現存的序跋遠多過書,在個人文集、地方志的藝文部分或同一作品現存的其他版本中都可能找到。考察序跋既能夠拓展對于抄本和印本歷史的了解,又能驗證從現存印本上所得推測的可靠性。比如,我們能更充分地了解不同歷史時期的文人在使用印本上的不同態度。一個典型例子是科舉制藝集的序。在晚明,編纂和刊行這類書的行業高速發展。這類序跋往往突出所收科舉制藝的優美文辭和博學多聞,即使作者自己從未成功通過任何一科科舉考試。這類序跋在默默無聞或鮮受推崇的學者文集中也并不少見,說明當時的文人并不像后世學者那樣輕視所有這類作品。
關于建陽圖書貿易的另一方面,我們也有所了解,即閩北出版商和江南地區的大城市、特別是南京出版商之間的聯系。建陽本中有證據證明,閩北人在江南從事編校、雕版和刷印的工作。所以,從江南著手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其整體面貌。例如,目前還沒有關于著名的周氏出版家族和同樣出名的唐氏出版家族的研究,而兩者在南京都擁有多家書坊。我們可能由此更好地了解劉孔敦和周氏出版商的關系。在第五章,我們談到過劉孔敦及其父劉龍田與周氏合作的事。如果我們能對世德堂的其他印本了解更多的話,也許能揭示唐氏世德堂《西游記》被建陽熊云濱翻刻再版的細節。就當時南京刻坊的數量和晚明印本的數量,可以做一次系統的研究,并包括所有現存印本的書目,這對于研究該時期的書籍史是至關重要的。還可以就江南其他出版中心,如蘇州和杭州,做類似的研究。
另一些問題主要緣于建陽出版業信息的缺失。其中一系列重要問題都關系書籍貿易的經濟層面。我們對于一部坊刻本的印數、成本及人工,都知之甚少,尤其是清代以前的。此類信息缺失不僅限建陽出版業,全國出版業也是如此。一些零碎的信息雖然看似有用,在沒有背景的情況下難以用來做推論。比如1611年劉氏安正堂刻印的一部類書值一兩銀子,如果不知道當時其他書和貨物的價值,這一信息就沒有什么用處。在各版《大藏經》中可能找到相關信息,因為其中每卷末會記錄捐資者所出的銀錢數,有時還會出現生產成本和人工費用。如果將這項信息與相應時期的一般物價數據對應起來,就有可能了解刻印一部大型宗教作品的資金運轉情況,從而推演出同時期諸多小規模、贏利性刻坊的經濟狀況。
對私塾、書院的刊刻活動還可以開展更多研究,目前所做的研究側重于其印本的文獻目錄整理。盡管建陽地區的一些書院在宋代和元代已在刊印經史類書籍,但這些書院的歷史及其刊刻活動卻從未被深入研究過。而且,其他地區知名書院的歷史細節已為人所知,比如元代杭州的西湖書院和明代的崇正書院(一在無錫,一在廣東)。將其歷史細節與刊刻活動聯系起來研究會很有價值。
在中華帝國末期,也曾存在一些地處大城市以外的出版中心。如前所述,就所出印本的數量、書籍貿易持續時間的長度和影響地域的廣度而言,它們中沒有一個可以與建陽比肩。但安徽徽州的出版開始興盛,在某些方面與建陽很相似。首先那也是個山區,擁有足夠的刻書所需自然資源。自宋以降,該地以出產優質的宣紙、煙墨和硯石而聞名。第二,無論在文化上還是經濟上,中華帝國晚期的大部分時間里,徽州都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在明中期,此地的私家和官辦書院都因其培養的學者而聞名全國。徽商積極參與其寄居地的鄉間事務。同時,這些商人與其故鄉家族的緊密聯系也反映在徽州嚴密而悠久的宗族組織上,可參見諸多族譜的記錄。在明代,徽州以其優質的印本聞名,其中包括套色墨譜。徽州還因其刻工的出色技藝和徽派木雕版畫而聲名遠揚。尤其是黃氏刻工,在晚明非常活躍,我們對于其家族成員和作品都已有一定了解。有了這些資料,加上大量當地方志,對徽州尤其是明代的刻書歷史開展細密的研究,不僅可行,更將成果豐碩。
除了徽州和江南,中華帝國晚期多數處于非城市地區的出版中心在規模上要小得多,往往只生產滿足當地和臨近市場需求的印刷品。這些當地的出版中心也值得研究,因為它們代表了中華帝國雕版印刷文化的核心部分:通過它們,在鄉野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人群與印刷品發生了最為直接的聯系。除了那些簡單粗陋的印本,諸如蒙學課本、勸善書、簡明指南(用于家族禮儀、風水、契約或尺牘),出版商還生產廉價的日歷、冥幣、宗教經文和畫像,以及其他日用印刷品。事實上,許舒關于香港新界一個現代小鎮的發現反映出中華帝國晚期社會的一些狀況,上述各種作一時之用的印刷品,對于大多數目不識丁的民眾而言,必然比書重要得多。不幸的是,這意味著此類資料即使出自最晚的清代,現在留存下來的也極少。很難確定究竟曾有多少個這樣的出版中心存在過,因為幾乎所有的出版中心都已消亡,并且沒有留下什么記載或印本。幸運的是,個別出版中心留下了足夠的痕跡,使得歷史學者可以研究其部分細節。其中之一是位于閩南內陸的長汀四堡。此地曾是這一地區商路上的一處樞紐,當地出產的一些印本及最重要的兩個出版商家族的族譜也留存了下來。包筠雅在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這些小型的出版中心,它們很可能曾遍布整個中國。另一處值得研究的地方是湖南邵陽的周邊地帶(清代的寶慶府),清代和民國時期那里據說曾有近四十家刻印鋪。由于缺乏中國北方的資料,長期以來被認為難以進行研究。但是對山東省的初步調查顯示,追溯清代和民國時期小城鎮(除了主要城市)的刻書活動是可行的。
研究這些小型又偏遠的出版中心的另一更迫切的原因,是它們似乎于晚明或清初開始,數量不斷增長并越來越重要,代表了一種與之前完全不同的謀利性刻書模式。之前的模式是由幾個相對少數的大型圖書中心來掌控的,而后一種模式貫穿整個清代和民國初期,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仍繼續通過雕版印刷而傳播,然而是以一種更廣闊的方式。當然,研究這些出版中心的方法與研究早期出版中心的方法也大不相同。比如,可能有更多的實物證據留存下來,如書版、印本甚至是刻印鋪及其經營記錄。在那些民國時期仍然參與書籍刻印和銷售的地方,甚至有可能采訪到知情人。另一方面,這些地方的印本存世比例非常低。由于圖書館和藏書家一直輕視,不會努力去搜集這些“破爛東西”,這些印本對于研究中國書籍史的重要性也沒有被認識到。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雕版印刷的末期狀況,我們仍需盡可能多地研究這些出版中心及其印本。實際上,在今天中國的舊貨市場仍可以買到部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印本。即使對于這些地方做不了充分研究,嘗試估計它們的數量、位置、活動時期和有時遠得驚人的分銷網絡,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在研究中國印本的歷史時,一個更為人忽視的領域是雕版插畫的發展。它們總稱為“圖”,特別是圖像、地圖、示意圖以及圖表、表格,用以體現或補充文字中所要表達的信息。通過細審六百余年間建陽本中的“圖”,可以發現插圖使用的延續性和逐漸提高的普及性。大致而言,這可以從雕版印刷的本質特點來解釋:雕版印刷的方式便于復寫式雕刻,或根據與原書、原圖幾乎一樣的臨摹本來雕刻。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這些印刷圖像有多古老,傳播有多廣?它們是首先出現在印本中,還是從其他媒介轉換而來,比如宗教繪畫、雕塑或青銅器皿?這些圖像是否也出現在年歷或神仙、民間英雄題材的日用年畫或其他版畫上?如果是的話,我們能否推測出不同表現形式中有系統性的差別?我們能否追溯某一幅圖像的刻印歷史?在中華帝國大部分歷史時期內,文字和圖像始終都是鐫刻在木版上的,不像西方書籍那樣存在工藝上的差異,精品用蝕刻或雕刻的金屬版插畫,廉價的通俗讀物用木刻插畫。中國的差異,存在于愈加趨同、簡化、喪失藝術情趣的“圖”與審美上倍受推崇的、相對獨立于文字外的“畫”之間。換言之,中華帝國的各個階層在將印刷術納為己用的過程中,雖然不得不受限于共同的媒介,卻各自以不同方法滿足了各自不同的需要。長達一千兩百多年的雕版印刷史證明,上述策略是可行的,但一些顯著的共同特征,如重復出現的圖像,也同樣貫穿了整個雕版印刷史。隨著更多關于中國書籍史的著作出現,我們對一件雕版印刷品所蘊含的內容,將了解得更深刻,更不吝贊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