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傳奇到世情:文學中對上海的新想象
在文藝作品里,從來就不缺少與上海有關的刻板印象。比方說,只要在影視劇中有上海男人登場,則八成是個妻管嚴加膽小怕事的形象。要是有上海丈母娘登場,則大概率呈現出的是拜金加挑剔的嘴臉。
這當然不只是一個“地域炮”的問題,毋寧說,這一現象和文藝領域,尤其是文學中的上海想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什么是上海?毋庸置疑,它可能是茅盾筆下的商業,可能是張愛玲筆下的人性,也可能是王安憶筆下的欲望。似乎,受眾心目中的上海形象,不過是在以上幾種模型之間來回切換。
就在今年11月,澤東電影公司官方微博曬出來一張《繁花》的概念海報。雖然退到了監制的位置上,但王家衛和金宇澄的強強聯手,仍然值得期待。而我最為關注的是,《繁花》能不能改變一下上海這座城市自帶的刻板印象?

如果說茅盾書寫的是上海的“史詩”,那么張愛玲與王安憶描寫的則是上海的“傳奇”。她們作品中的奇女子代替了革命的斗爭,占據了文學舞臺的C位,也幾乎成為了文學上海的代名詞。只是,弄堂、旗袍、石庫門……這些“傳奇”里的必備品,卻漸漸淪為一種新的文學套路。然而,橫空出世的《繁花》,試圖用一個個鮮活的故事,寫出真正鮮活的“世情”,對抗固化在讀者腦海中的上海“傳奇”。
在 《繁花》尾程,一次酒宴歡場,“夜東京”的女老板玲子,從那一桌來這一桌搬救兵,要叫上她的小姐妹小琴去跟陸總喝酒,小琴的現任相好陶陶不讓去。此時,玲子說,“陶陶認得小琴,也就是這種胡天野地場面嘛,不要忘記,是我擺的場子,現在一本正經,像真的一樣。”另一邊,陶陶“不響”。
如果說,張愛玲與王安憶筆下的女子尚有對純真情感的渴望,只是因為人性的扭曲或世俗的誤會而未能如愿,那么這場飯局,無疑徹底擊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一本正經”“像真的一樣”,但畢竟不是真的。從小說的情節來看,陶陶、小琴之間的感情果然如玲子所言,建立在海市蜃樓之中。
但更重要的是,這兩人從來就是以自身為目的,以他者為手段。即便是陶陶的“當真”,終究也只是一種錯覺。換言之,就連張愛玲小說主人公求而不得的目標,也是不存在的。去除浪漫、回歸生活,這正是金宇澄的“世情”與張愛玲的“傳奇”最根本的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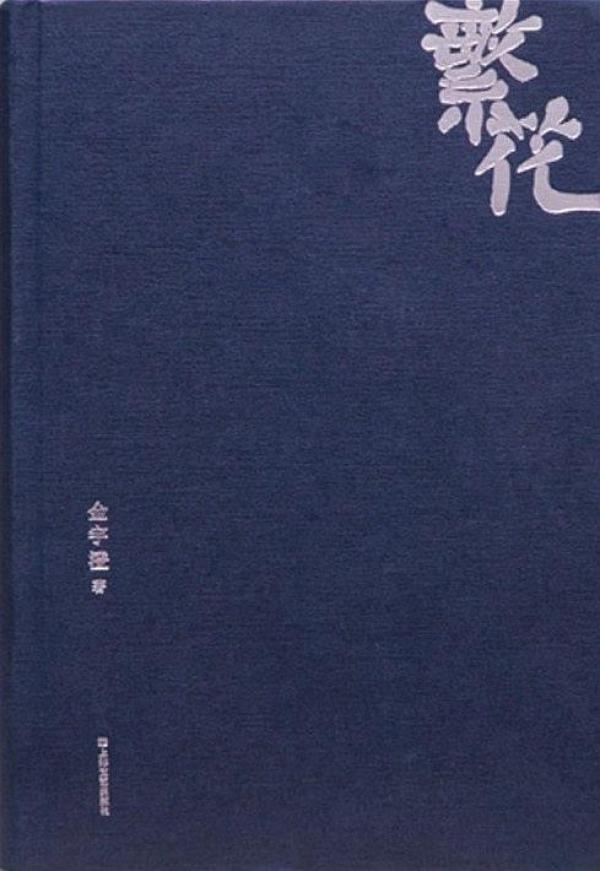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這一有關上海的文學創作轉向,不僅僅出現在了金宇澄的作品里。吳亮的《朝霞》,是一部反敘事、反主題、反人物的“反小說”。或許正因為作者太熟悉小說創作,所以更要在創作中率先進行自我“批評”,自行排除一切“套路”。但在這部看似紛繁復雜的作品里,我們仍然可以發現“世情”而非“傳奇”的存在。
《朝霞》中,生活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阿諾以及他的朋友、同學常常談論政治,然而“這種不再讀書陽光燦爛的日子,在他們看來簡直糟透了,他們疏離政治,他們論政治不是為了好奇,而是政治影響他們的命運和未來,倒不是對這個國家有多少關心”。這實在是一種悖論——他們關心政治,可又主動疏離于政治。
這不能不讓我們聯想到19世紀俄羅斯小說中常常出現的“多余人”。只是,“多余人”并不缺乏高昂的理想主義,他們的受挫或失敗往往來自于社會的重壓。然而,《朝霞》中的年輕人們時常“請病假消極怠工,抽煙并且過早地談情說愛,不務正業且 ‘游手好閑’”。換言之,他們從來沒有挑戰社會、挑戰世界的想法,更不用說行動了。
在閱讀過程中思考、懷疑甚至踩踏思想的禁區,卻無意挑戰或反抗,這正是《朝霞》“反傳奇”的最生動體現。這群年輕人不是令人惋惜的悲劇英雄,也不是毫無頭腦的市井無賴,他們只是他們自己,他們代表的就是“世情”,是一個活生生的特殊時代的上海。
張怡微對上海“世情”的探索,同樣不該被遺忘。在她的《細民盛宴》里,描寫了主人公“我”與小茂的一段短暫、倉促的婚姻。在這樁婚姻里,父親執意要“我”相信,沒有給嫁妝并不是不愛女兒;“我”與小茂父母初見的宴會上,小茂父母便直接、赤裸地評估“我”以及“我”的家庭收入到底是否能承受得了雙方的愛情。
對張愛玲來說,“算計”是現代大都市中的人性之惡,是摧殘愛情、善良的根源。但張怡微給予了這種“算計”更多同情和理解。因為在她看來,生活在上海,面對著局促、逼仄的現實,人們或許只能依靠精確的數字來獲取一絲岌岌可危的安全感。和跌宕起伏的“傳奇”相比,這才是當代上海的“世情”。
正如張怡微所言,“只要說到上海,人們想起的都是旗袍、背頭、老洋房、石庫門,但這些意象我都很不熟悉,我也是看來的”。因此,怎樣把“傳奇”之外的上海生活納入文學,也許是更多寫作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周嘉寧正是這么做的。她的《密林中》,敘述了戀愛、成長、迷茫這些經常出現在青春文學中的要素,卻也不缺少一位年輕寫作者的文學的自我意識和野心。小說主人公陽陽在歷經滄桑后,既沒有獲得寫作事業上的真正突破,也沒有放棄探索和努力。或許,這才是生活的常態,而不是“傳奇”的面貌。
在她的筆下,上海成為了“密林”。陽陽看到的,是生活方式的空洞、無趣,是生活背面的疲憊、空白。陽陽“靈魂的作坊”受困于“密林中”,而“密林中”的困境經驗不是別的,正是無窮無盡的“世情”。
另一位年輕寫作者走到了她的對立面,那就是郭敬明。在他的作品中,上海異化為“資本”和“時尚”的代名詞。可盡管如此,“小時代”仍然精準地命名了某種真實存在的“世情”,那就是一部分年輕人無所顧忌地向金錢、向權力獻媚的姿態。
有車有房、名校名企、英俊愛人、充滿“時尚”的中產階層生活,或許都是“世情”的一部分,但注定是傾斜、偏頗的。因此,郭敬明努力描寫的大都會“傳奇”必然與歷史脫鉤,帶來的則是讀者心理上的懸空之感。何況,與張愛玲、王安憶對人性的洞察相比,他筆下的人物近乎抽象符號。
因此,克服郭敬明式虛偽觀察的關鍵,仍然在如何準確地把握、書寫上海的“世情”。就此而言,任曉雯的《陽臺上》無疑是個值得關注的例子。小說以張英雄的復仇為主線,描寫的是上海底層社會空間的時代變遷。
在2019年,被改編成電影的《陽臺上》里,出現了一段原作中沒有的情節——當主人公張英雄為慶祝自己的生日第一次許愿說“我希望國家富強、世界和平”時,被父親摑了一巴掌說 :“為自己!”這一幕體現出的是張英雄自我認知、自我認同的困境,卻也是上海普通家庭所身處的“世情”的真實寫照。張愛玲的“傳奇”遠離了茅盾筆下的宏大說辭,但絕不缺乏“意義”“主題”“理想”。可在張英雄看來,生活就是“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有孩子,沒事可以咪咪老酒。”既不偉大,也不虛無,對上海的文學描寫,就這樣落到了實實在在的“世情”里。
在《繁花》結尾,有意來拍攝電影的法國青年滿腦子上海傳奇,阿寶們卻不斷提醒其蘇州河畔并無法國廠。法國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裝滿棉花的駁船里做愛,阿寶卻說當時的棉花船上都養著狗,避過惡狗耳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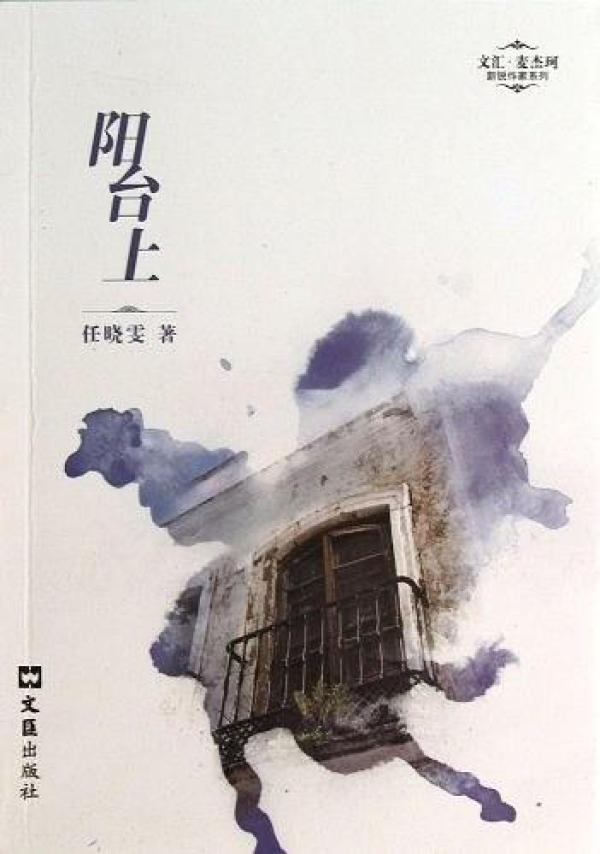
這段情節隱喻的顯然是對上海的認識。“傳奇”對上海的描摹,就和法國青年的浪漫幻想一樣,很誘人,很動人,卻和真實的上海相距甚遠,充滿隔膜。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在書寫上海時,正在努力突破“傳奇”的束縛和套路,這絕不是偶然現象。
只是,到底什么是真實的上海?誰有資格制定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評判標準?這些問題,注定不會得到一個百分百正確的答案。但寫作者的嘗試,絕非沒有意義。歸根到底,從“傳奇”到“世情”,對上海的文學想象模式正在潛移默化中被顛覆。它的新生,值得期待。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