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圓桌|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青年學(xué)者漫談:學(xué)術(shù)共同體與工作倫理
近日,來自海內(nèi)外高校和科研機(jī)構(gòu)的二十余位學(xué)者共聚長沙,舉辦了一場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青年學(xué)者漫談會。與會學(xué)者圍繞“經(jīng)典作家、中國革命、世界視野”、“史料與理論”、“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范式”、“中國經(jīng)驗(yàn)”和“學(xué)術(shù)共同體”等主題展開熱烈討論。以下是此次漫談會記錄稿的第三部分。

嚴(yán)靖(武漢大學(xué)):今天的青年學(xué)者漫談會很不一樣,因?yàn)槲覀兌夹闹敲鳎芏鄷h都是很多帶有官場性質(zhì)的排資論輩罷了,如今無論是研究范式、研究思路,還是學(xué)者之間的關(guān)系都有點(diǎn)隔閡,這樣的漫談會很有意義。我最近幾年在做的主要是1940年代文學(xué)轉(zhuǎn)折、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形態(tài)之間的關(guān)系。如果承認(rèn)我們現(xiàn)在中國經(jīng)驗(yàn)的提出主要還是因?yàn)?990年以來中國經(jīng)濟(jì)的崛起,從中汲取相關(guān)的思想、第三世界或者說后殖民的思想反過來考察、衡量、評判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如果用居身于現(xiàn)在的中國經(jīng)驗(yàn)來研究1949年以前的東西,這如何可能?這是我比較困惑的。我的研究感觸可以用八個(gè)字歸納:事大于人(革命視野大于作家),人推動事(人的主動性)。當(dāng)我們用一種強(qiáng)勢的或者說時(shí)髦的、先鋒的前沿理論,來思考不同時(shí)代的文學(xué)研究,這是否是一種仗勢欺人?第二個(gè)我想說的是,我們對現(xiàn)在普遍存在的知識性研究過甚的情況是不滿的,于此召喚人文性、思想性,還是要回到知人論世的。然后想談一談現(xiàn)代主義的地理屬性的問題,現(xiàn)代主義的空間,可以延伸到很多思想的問題。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主義可以說是西化的思想,意義不在于糾結(jié)它是外來的還是內(nèi)在的,我覺得有意義的是這本身就是屬于中國經(jīng)驗(yàn)的一部分,把理念融入歷史和現(xiàn)實(shí)。
楊姿(重慶師范大學(xué)):剛剛幾位老師都提到了“回到生活”,乍一聽,這個(gè)訴求很切合時(shí)代命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之后,學(xué)術(shù)的內(nèi)部繁殖導(dǎo)致研究日漸顯出“知識與道德的分離”的傾向,所以“回到生活”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知識分子的研究行為,是生活的組成部分,不過是一種職業(yè)而已;另一方面,將研究視為一項(xiàng)職業(yè),必然會認(rèn)同研究內(nèi)容的科學(xué)化、實(shí)驗(yàn)室化,更直接地講,就是人文學(xué)科的智力游戲化。雖然我可以理解,這是自文學(xué)告別八十年代理想主義之后的正常反應(yīng),但是,我仍然感到這樣的看法與我們從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選擇存在著必須正視的距離。
第一,現(xiàn)代革命與封建起義的差異之一,便在于走向革命的先輩并非由于生活所迫,而是基于生活需求以上的理由選擇革命道路,同樣,文學(xué)革命先驅(qū)也是如此。作為研究對象,他們不單單留給我們關(guān)于革命的知識與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們以文學(xué)事業(yè)投身革命運(yùn)動的理念,以及這個(gè)革命觀所包含的種種矛盾與沖突,那才是我們需要獲得的經(jīng)驗(yàn)。比如,關(guān)于魯迅與托洛茨基這個(gè)話題,我的想法是一步步形成的,最初的念頭是想要對魯迅的“革命”進(jìn)行去魅,找到他無產(chǎn)階級革命觀的由來與構(gòu)成,于是發(fā)現(xiàn)了托洛茨基和他的《文學(xué)與革命》,進(jìn)而認(rèn)識到托洛茨基對于魯迅的意義,恰恰在于他為魯迅提供了對“文學(xué)革命”進(jìn)行“再革命”的理由和方向。說到底,就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革命時(shí)期對個(gè)人的文學(xué)行為的調(diào)整,它不是一個(gè)外在的階級理論訓(xùn)誡,而是內(nèi)在的思想進(jìn)化,客觀上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因此,我的研究以對革命“去魅”為開始,最后以對革命“賦魅”為結(jié)束,所謂“賦魅”指重新提出革命的延續(xù)性,革命從來不是一個(gè)實(shí)體的存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觀在二十年代對現(xiàn)代作家的吸引力也不純粹是史學(xué)方法的優(yōu)越性,最具感召性的是契合了現(xiàn)代作家的心理需要。知識分子最本質(zhì)的傳遞性,就在于能夠?qū)r(shí)代變動作出及時(shí)判斷并賦予超越式的預(yù)構(gòu),文學(xué)自然也不會僵化,而應(yīng)具有對本體修正甚至否定的功能,即不斷革命的必要性。當(dāng)今世界秩序正在進(jìn)入一個(gè)重建時(shí)期,并不是一個(gè)“非政治”的時(shí)代,研究文學(xué)的人與研究對象保持最基本的關(guān)聯(lián)性,也只能是對革命經(jīng)驗(yàn)的繼承。
第二,中國革命的話題一直被處理成區(qū)域問題,這是由種族-文化傳統(tǒng)塑造的,實(shí)際上,中國革命的問題包含了時(shí)間和空間兩個(gè)向度。從空間來看,現(xiàn)代中國的反殖民運(yùn)動與全球殖民化浪潮是一致的,無論多么民族化的訴求,其實(shí)都是在一個(gè)殖民鏈條的背景中呈現(xiàn)出來,當(dāng)然,這種一時(shí)一地的變革也造成了全球范圍內(nèi)的影響,總而言之是共生系統(tǒng)的反應(yīng)。目前研究要解決的問題,是重新整理出這種革命經(jīng)驗(yàn)對于世界進(jìn)程的作用,反過來,也是構(gòu)建新的全球格局的一種途徑,今天的世界格局便是這一延長線的產(chǎn)物。從時(shí)間來看,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動蕩與傳統(tǒng)中國朝代更迭的狀態(tài)極其相似,每逢民族精神渙散,總有思想家對舊文化舊思想進(jìn)行再闡釋,比如晚明、清代的一些學(xué)者反復(fù)解讀儒學(xué)經(jīng)典,他們?yōu)槭裁匆跁r(shí)間中逆流而上尋找意義,并不是要回到過去,回到“三代”,除了緩解大眾恐懼革新的心理,尋求“傳統(tǒng)中的變革”作為依據(jù),更重要的是提煉和重組適合當(dāng)下的經(jīng)驗(yàn)。德里克說過,拒絕革命,就拒絕了理想,對未來就沒有了期望。對將來的預(yù)期,是歷史意識的一個(gè)部分,沒有了這種預(yù)期,就沒有辦法對過去賦予意義。在這個(gè)意義上,中國革命在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永恒關(guān)系中,它是歷史的,也是現(xiàn)實(shí)的,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實(shí)踐。
邢程(浙江大學(xué)):我曾經(jīng)幻想過一個(g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存在,但事實(shí)后來證明,一個(gè)純?nèi)坏拿裰魃鐣呛茈y真正有效或者成功的。所以特別感謝寶林,給了我們這樣一個(gè)機(jī)會。我想我們也不是來就具體的學(xué)術(shù)問題進(jìn)行交流的,只是真誠地,分享一下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和體會。
題目中的三個(gè)關(guān)鍵詞,經(jīng)典作家,我算是沾邊,畢竟做魯迅(研究)出道,現(xiàn)在仍然在出道的過程中。但是我現(xiàn)在也不大說自己做魯迅了,上半年找工作的時(shí)候,有些單位會說,你的領(lǐng)域太窄了。所以這個(gè)教訓(xùn),也順便分享給在座即將面臨這個(gè)問題的同儕。中國革命,非常慚愧,這四個(gè)字組合在一起,似乎尚未在我的任何學(xué)術(shù)文章中出現(xiàn)過,所以暫且不表吧。世界視野,本來我對此也覺得無甚可談,但是剛才熊權(quán)老師講到的那個(gè)孫犁研究的例子讓我想到一個(gè)事情:有些東西,到底是古今的問題,還是中西的問題,如果我們把它認(rèn)定為前者,是不是可以剝?nèi)ヒ恍┝龇矫娴膱?zhí)念?
熊權(quán)老師以后就是邱老師的宏論。邱老師的宏論讓我很害怕,因?yàn)樗v的事情我從來沒有在自己的研究中思考過,所謂“學(xué)科重置”、“中國經(jīng)驗(yàn)”等等。我比較認(rèn)同接下來李國華師兄講的,我們往往是找一個(gè)能滿足智性挑戰(zhàn)的快樂的東西去做,覺得有趣,有快感,而已。這一點(diǎn)是讓我能在這個(gè)行當(dāng)里做下去的,最長久的因素。
我自己沒有學(xué)科的整體性焦慮,但是我剛才發(fā)現(xiàn)似乎許多同仁有,大家想要“方法論”的更新。但我自己的經(jīng)驗(yàn)是,你面對材料、文本、理論,你與之肉搏,然后有問題有新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所謂“方法”,是從“對象”里來的,是實(shí)踐來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否則空談“方法”,“方法”就只是一個(gè)口號,這個(gè)樣子下去,做什么都是硬做。
但同時(shí)我也覺得自己很“悖論”。我其實(shí)對整個(gè)時(shí)勢是很焦慮的。我非常——如果不是最——關(guān)心時(shí)事,經(jīng)濟(jì)的金融的政治的……我甚至?xí)ァ白詫W(xué)”相關(guān)方面的東西。但是這些關(guān)切和焦慮會被我自然地排除在我的學(xué)術(shù)研究之外。
關(guān)于我的研究對象魯迅,我比較反對在他那里找一個(gè)系統(tǒng)性的東西。系統(tǒng)性恰恰是他沒有的。魯迅的根柢是什么呢,我自己覺得是一種美學(xué)上的東西。
這又讓我想到另一個(gè)問題——既然是漫談。作為“青椒”我現(xiàn)在也面臨上課的問題,那么我教學(xué)生什么?想來想去,其實(shí)無非三件事:知識、方法、審美。三點(diǎn)要并重,但最后一點(diǎn)我覺得現(xiàn)在的情況就是災(zāi)難。文學(xué)專業(yè)要告訴學(xué)生,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真正的文學(xué)。但我們領(lǐng)域里可能很多人都不具備文學(xué)感受力。
我最近看了一些當(dāng)代的東西,我覺得當(dāng)代文學(xué)寫得確實(shí)比現(xiàn)代好啊,整體來看。盡管我們好像一直有一個(gè)秘而不宣的學(xué)科鄙視鏈,好像現(xiàn)代就比當(dāng)代高。然后最近王安憶被弄成“駐校作家”,在浙大開系列講座,我就夾在許多學(xué)生中間一次次聽下來,覺得挺受益。這個(gè)意義上我也是想要“回到歷史現(xiàn)場”,什么歷史現(xiàn)場呢,就是一個(gè)真正搞創(chuàng)作的人,Ta怎么閱讀,怎么寫作,真正投入寫作的時(shí)候,那個(gè)微觀的狀態(tài)是怎樣的,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仲濟(jì)強(qiáng)(北京師范大學(xué)):我一直都很虛無,始終有一種無意義感。其實(shí)也沒什么可講的,就隨便說兩句。國華師兄提到國族認(rèn)同與世界性的問題,認(rèn)為在窯洞里生產(chǎn)出的恰恰是世界性的。我很有同感。一方面,認(rèn)同首先源于吃飽飯,另一方面,世界性的東西往往產(chǎn)生于地方性之中,甚至往往產(chǎn)生于我們每個(gè)人最切身的經(jīng)驗(yàn)之中。正是解決了窯洞里的農(nóng)民的吃飯問題后,陜甘寧邊區(qū)政權(quán)才促生了農(nóng)民的認(rèn)同,進(jìn)而生產(chǎn)出了世界性的中國經(jīng)驗(yàn)。中國一直在發(fā)展,發(fā)展中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我們現(xiàn)在,由于物質(zhì)資本和知識資本擁有量的差異,不同階層之間似乎分化越來越明顯,平時(shí)感覺不到,當(dāng)面臨一些公共事件的時(shí)候,原本安靜的朋友圈往往就紛紛站隊(duì),分屬于不同類的人,似乎已經(jīng)很難相互溝通了,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卻往往缺乏一種共同感。這種感慨有點(diǎn)大而無當(dāng),暫且打住。說一下我個(gè)人的學(xué)習(xí)經(jīng)驗(yàn)。我剛轉(zhuǎn)行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時(shí)候很無知,那種無知是意識不到自己無知的無知,后來慢慢意識到自己無知了,又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邊界,很難掙脫,到現(xiàn)在也還很無知,一天到晚總在焦慮自己的知識結(jié)構(gòu)問題。就寫論文而言,有很嚴(yán)重的路徑依賴,很難在寫法上有突破。在我就讀的學(xué)校里,同一專業(yè)的人大都單干,也沒有多少有效的交流機(jī)會。后來,去聽了哲學(xué)系、社會學(xué)系的一些課程,才突然像打開了一扇窗似的。由此,我就很有感觸。我們一直把自己封閉在鐵屋子里面做魯迅研究,單干久了,往往缺少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而且和一個(gè)對象呆在一起太久,視角也會固化,自然無法做到視域融合。我研究的是關(guān)于周氏兄弟書寫方式的現(xiàn)代變革問題,涉及到語言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歷史問題,很復(fù)雜,需要有一個(gè)打破現(xiàn)有學(xué)科體制的大的人文學(xué)的視野去處理。我寫博士論文的時(shí)候,還沒太想明白,只是一味用概念來推動問題,論述過程有嚴(yán)重的去語境化的傾向。也就是說,魯迅說的某句話本來是針對某個(gè)現(xiàn)實(shí)問題說的,但是被我截取出來,用哲學(xué)概念一分析,納入到重新組織的話語體系之中,似乎把魯迅納入到世界思想史的坐標(biāo)中去定位了,但卻容易遠(yuǎn)離這句話在原初語境中的意涵。后來,我進(jìn)一步讀了一些其他學(xué)科的書,也受到在座一些朋友的啟發(fā),慢慢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我現(xiàn)在覺得,要把思想問題談明白,還是要重構(gòu)書寫時(shí)刻的場域,重建書寫者置身其中的論辯光譜,在這個(gè)基礎(chǔ)上,來談魯迅給予我們的中國經(jīng)驗(yàn),來與世界其他場域中的地方經(jīng)驗(yàn)共振,以達(dá)成視域融合。這個(gè)漫談會關(guān)鍵詞是中國經(jīng)驗(yàn)、中國革命、世界視野,我覺得這三個(gè)維度對周氏兄弟都很重要。周氏兄弟一直反感別人稱他們?yōu)槲氖浚簿褪钦f,周氏兄弟書寫實(shí)踐的初心并不是為了達(dá)至一種純文學(xué)性的目標(biāo),而是有很自覺的社會關(guān)切,跟我們現(xiàn)在時(shí)代人的關(guān)切不太相同,我們大都關(guān)切自己買不買得起房子的問題,對于周氏兄弟而言,這都不是事,周氏兄弟在北京有兩套四合院。中國問題、革命問題都是他們思考的重心所在,甚至形塑了他們書寫實(shí)踐的表達(dá)形式。在中國經(jīng)驗(yàn)、中國革命的視域下思考周氏兄弟的散文書寫,可能比用后設(shè)的純文學(xué)理念從周氏兄弟的作品中強(qiáng)行提純文學(xué)性要靠譜得多。至于世界視野,我想,周氏兄弟的世界視野可能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大得多,甚至都不需要研究,大致翻一下周氏兄弟的購書記錄就能明白,他們當(dāng)時(shí)讀的外國書有多少,我記得某一年日本剛出了托爾斯泰全集,周氏兄弟當(dāng)年就買了一套,這種接受速度是相當(dāng)驚人的。至少我自己覺得,周氏兄弟所讀的外國書,我連二十分之一都沒有讀過,為此,我就很惶恐,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怎么研究周氏兄弟呢?在閱讀量遠(yuǎn)遠(yuǎn)低于周氏兄弟的情況下,怎么重建周氏兄弟的世界視野呢?反正我覺得,挺愁人。我就先說這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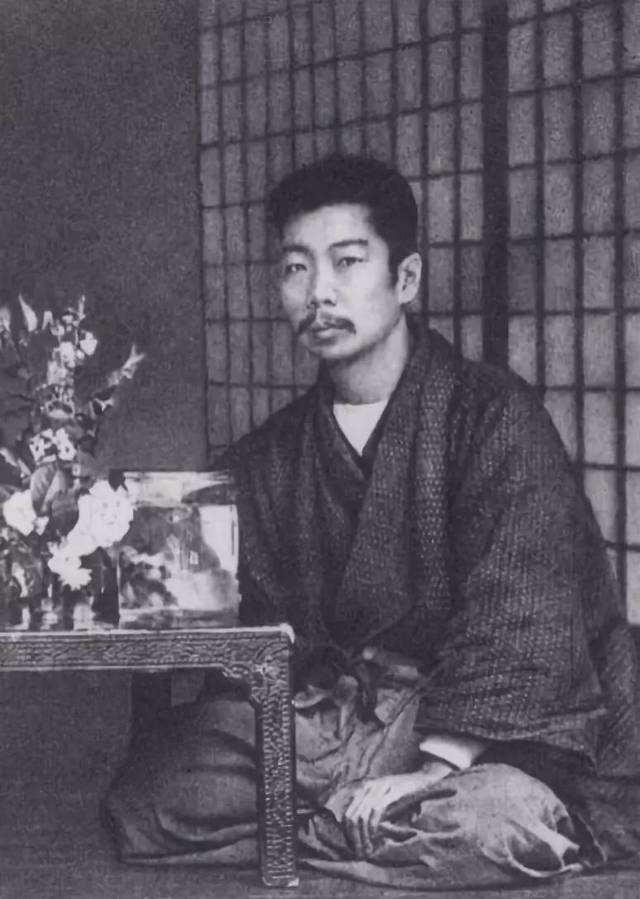
自由討論
邱煥星(江蘇師范大學(xué)):因?yàn)閯偛糯蠹覍ξ业陌l(fā)言反應(yīng)激烈,提出的問題都主要指向了我,所以我先回應(yīng)一下大家的看法,主要有兩個(gè)方面。
首先是剛才有人質(zhì)疑我說的學(xué)科重置,是不是陷入了宏大敘事的一元霸權(quán),因而就取消了個(gè)人興趣和其他研究的問題。我覺得這只怕是對我的誤讀,實(shí)際上后現(xiàn)代主義對我影響很大,我本人是一個(gè)多元主義者,支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我覺得這其實(shí)是兩個(gè)層面的問題,作為個(gè)體,你盡可以選擇自己喜好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式,但作為一個(gè)學(xué)科,如果整體沒有方向感,缺乏反思,尤其是漠視當(dāng)代中國四十年巨大變遷和世界體系變動的話,那只怕是非常成問題的。剛才有的朋友用言語擠兌我,我覺得研究不是辯論術(shù),你即使駁倒了對方,但問題還在那里,等著你去回答。我覺得最悖論的,就是當(dāng)前有些研究者倡導(dǎo)歷史還原,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求真和知識化,但他們試圖還原的那些人,像魯迅、胡適、陳獨(dú)秀恰恰當(dāng)時(shí)在搞革命、參與現(xiàn)實(shí)實(shí)踐,我想這是我們必須反思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質(zhì),如果丟掉了這個(gè)本質(zhì),我們就不是在研究現(xiàn)代文學(xué)了。
其次,剛才做史料的朋友特別強(qiáng)調(diào)史學(xué)求真的意義,這個(gè)乍一聽非常合理,但我想特別說明的是,這恰恰是有問題的。整個(gè)八九十年代倡導(dǎo)的歷史求真,是以“文革”意識形態(tài)是虛假為前提的,因而“史學(xué)”具有先天的合法性、正確性,但是如果我們引入中國古代的“經(jīng)學(xué)”思維的話,會發(fā)現(xiàn)這兩者不過是兩種認(rèn)知方式。正如康德區(qū)分真善美,人類的訴求不僅有真,還有善和美,而這恰恰是意識形態(tài)和經(jīng)學(xué)的核心功能,甚至意識形態(tài)能制造出“逼真”。其實(shí),科學(xué)又何嘗不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五四時(shí)就有人提出“科學(xué)主義”的問題,即便我們今天最信奉的科學(xué)實(shí)證歷史研究的鼻祖蘭克,他當(dāng)年倡導(dǎo)科學(xué)的背后,實(shí)際也有民族主義和基督教的背景。因而史料研究者實(shí)際一上來就認(rèn)為科學(xué)是對的,而經(jīng)學(xué)是錯(cuò)的,從理論層面來看,這兩種方式之間不存在高下之分,只存在實(shí)踐差別,我們正是因?yàn)椤拔母铩睂?shí)踐的后果,才認(rèn)為意識形態(tài)經(jīng)學(xué)建構(gòu)是錯(cuò)的。這點(diǎn)是我特別想說明的。
李哲(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在今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對史料的意義和價(jià)值再怎么強(qiáng)調(diào)都不為過。但是,由近代史學(xué)科生發(fā)的諸多史料處理方法及其相關(guān)的歷史觀則需要在充分消化的前提下予以反思,尤其是對其背后的諸多預(yù)設(shè)性前提有充分自覺。在一次會議上,有歷史專業(yè)的老師認(rèn)為楊天石先生在1988年發(fā)表的《“中山艦事件”之謎》這篇文章對當(dāng)下史學(xué)研究整體思路具有深遠(yuǎn)的影響。我自己在隨后的閱讀中也為作者扎實(shí)的史料功底、縝密的論證以及充滿細(xì)節(jié)的生動敘述所折服。但即使這篇具有典范意義的研究性文章,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諸多進(jìn)一步思考的地方,這些地方并不是作者得出的結(jié)論,而是其內(nèi)在的方法和歷史觀念。這里僅舉一個(gè)小例子。首先,題目中所提的“事件”一詞頗值得重視。我們知道中國近代史的敘述非常倚重“事件”,如胡繩所寫的《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yùn)動》即是用一系列“事件”串聯(lián)起從1840年到1919年的歷史進(jìn)程,每一個(gè)“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咬合在因果關(guān)系的鏈條之中,昭示著歷史發(fā)展的深層規(guī)律。這背后的歷史觀和敘述方式頗值得深入思考。由此來看,楊先生以“事件”為單位劃定研究對象的范圍實(shí)際上對既往的歷史敘述方式有承續(xù)性,而區(qū)別則在于,傳統(tǒng)的近代史研究更注重“事件”發(fā)生的原因,及其產(chǎn)生的歷史影響,即它們是在一個(gè)“歷史運(yùn)動”的進(jìn)程中去審視“事件”,將“事件”視為一個(gè)大脈絡(luò)的節(jié)點(diǎn);而后者實(shí)際上把“事件”從歷史進(jìn)程中拎出來,作為一個(gè)內(nèi)部包蘊(yùn)著復(fù)雜信息的“歷史現(xiàn)場”來處理。正是基于此,作者調(diào)用了大量日記、書信這些私人性的材料去勾勒其中的種種糾葛、沖突和來龍去脈,“偶然性”從“必然性”中不斷衍生出來。這既是歷史研究方法的變化,但其實(shí)也意味著歷史研究者對“歷史真實(shí)”的認(rèn)識發(fā)生了變化。在前者看來,“事件”僅僅是表象,而由此揭示的歷史規(guī)律才是具有“本質(zhì)”意義的“真實(shí)”。而后者則相反,他們會認(rèn)為歷史規(guī)律和進(jìn)程都是抽象和敘述的結(jié)果,而那些錯(cuò)綜復(fù)雜的、與歷史當(dāng)事人個(gè)人相關(guān)的、充滿細(xì)節(jié)的信息才是“真實(shí)”。從這個(gè)意義上說,今天的我們在審視歷史的時(shí)候,不僅要對前輩學(xué)者運(yùn)用史料的功夫予以體會和把握,更要對他們賴以立論、敘事的歷史觀有充分的自覺。這需要我們小心地區(qū)分“歷史材料”和“歷史經(jīng)驗(yàn)”之間的界限,具體來說,既要意識到“史料”的不透明性乃至敘述性,也要意識到抽象、敘述這些非實(shí)體的因素在歷史中所起的“真實(shí)”作用。

再回應(yīng)一下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世界視野”這個(gè)概念“太空、太大”的問題。為什么我們會把“世界視野”僅僅視為成一個(gè)宏大高遠(yuǎn)的層面呢?在人們的意識里,確實(shí)存在著一個(gè)空間想象的等級,如“地方-中國-世界”,“地方”在“中國”之中,“中國”在“世界”之中——在很多學(xué)術(shù)研究中,“中國”甚至被視為“世界”的一個(gè)“地方性”空間。正是在這種想象空間的方式之中,我們才會下意識地認(rèn)為,“地方”小于“中國”,而“中國”也小于“世界”,而“世界”之于“地方”乃至地方社會內(nèi)部的“人”會顯得過于“宏大”。但在我看來,今天談?wù)撌澜缫曇安⒉粌H僅是引入一個(gè)更宏大的坐標(biāo),而恰恰是要打破“地方-中國-世界”這類充滿等級的空間想象方式。在今天這樣一個(gè)全球化的時(shí)代,空間實(shí)際上處于復(fù)雜的交錯(cuò)之中,我們當(dāng)然可以說中國在世界之中,但也會發(fā)現(xiàn)世界在中國之中,甚至在地方社會內(nèi)部。或者說,中國乃至一個(gè)微小的地方社會本身都可能包含著“世界性”的因素。基于這樣一種體認(rèn),我們可能需要調(diào)整自己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認(rèn)識。比如我們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諸多青年學(xué)者討論的“中國經(jīng)驗(yàn)”,并不必然意味著是一種在世界大坐標(biāo)中的“特殊經(jīng)驗(yàn)”。相反,中國20世紀(jì)革命進(jìn)程中的種種復(fù)雜經(jīng)驗(yàn)是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當(dāng)然,這種“世界性”或者“普遍性”不是就一種抽象的原理層面而言,它其實(shí)意味著某種可溝通性、可理解性。“特殊的經(jīng)驗(yàn)”可以通過文明比較彰顯,但蘊(yùn)含著可溝通性、可理解性的“普遍性”卻需要對歷史予以更為深入、細(xì)致和小心的把握。
漫談會最后在自由討論與提問中結(jié)束,與會學(xué)者皆意猶未盡。即便是同時(shí)代人,走的或許也是異路。每個(gè)學(xué)者關(guān)心的問題,探求的歷史縱深和精神廣度各有千秋、各有差異。但是,同聲處異而相應(yīng)、意合未見而相親,青年學(xué)者俱游良會,圍坐圓桌而漫談,會后各走異路,前輩學(xué)者謂之神仙會是也。
(本記錄稿由中南大學(xué)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2016級本科生何蕊、鄒詩雨整理,業(yè)已經(jīng)與會者審閱。)





- 報(bào)料熱線: 021-962866
- 報(bào)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bào)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