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們為何要“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
文 | 曾于里
編輯 | 俞詩逸

城市里的盲道經常遇到“斷頭路”,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7月9日晚,微博網友爆料稱,北京截癱者之家創辦人文軍,在大理考察無障礙路線時不幸殞命。
該網友在微博上寫到,“7月7日晚,他回酒店路上,因無障礙路口被私家車占用,他不得不另尋他路,但不幸開著輪椅車頭掉進了停車場的坑里,當時停車場沒有任何的警戒標識。直到他被保安發現,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
隨后,多家媒體證實了文軍不幸遇難的消息。一個始終為殘疾人權益奔走的公益人士,卻以這樣的意外走向生命的終點,這令人傷心,也令我們汗顏。
筆者在國內的幾個城市有過多年的生活經歷,回想起來,無障礙通道(包括盲道)被占用的情況實在是太普遍了,甚至有的無障礙通道的設計也非常不合理,比如走著走著迎面就是一堵圍墻,或者盲道磚的鋪設不是直線的而是彎彎繞繞……這折射的是,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老百姓,并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無障礙通道的重要性。文軍的不幸發生后,微博上不少評論留言道:他們這才頭一回聽說無障礙通道,頭一回聽說盲道磚。
中國有數量龐大的殘障人士,有數據顯示有8000多萬。但回想一下,我們在生活中碰到他們的概率實在是太低了,30余年來筆者從未遇到有盲人在盲道上行走。事實上,中國并非缺失無障礙設施,只是我們的許多無障礙設施的利用率實在太低,形同虛設。我們欠缺的是真正地為殘障人士考慮的那顆心——用不久前全網熱傳的葉敬忠教授在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2019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談到的,我們沒有“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我們沒有形成一個穩定且善良的“弱者觀”。
誰是弱者?這個概念在社會學上有諸多分歧和解釋,簡單來說,弱者有相對和絕對兩個層面。從相對層面上看,任何人都可能是“弱者”,因為總有比我們更強勢的人,這不是提醒我們以弱者心態自憐,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對弱者有同理心——我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而絕對層面,弱者指涉的是“心理、生理、能力、機會和境遇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地位的人”。或者我們將他們理解為于社會財富與權益平均線下的人群,比如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在溫飽線上掙扎的人、受災地區群眾、孤兒、殘障人士、少數人群等等,他們在經濟、社會、文化、話語權等方方面面都處于弱勢地位,抑或想像“普通人”一樣過上普通的生活需要付出更多。
怎么看待弱者,就是一個社會的“弱者觀”。是“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還是將弱者排除我們的世界之外,假裝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他們的存在?

葉敬忠演講中,圖片來自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官網。
一
一個遺憾的事實是:現實生活中,后一種“弱者觀”更為常見。甚至在輿論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鄙夷弱者的論調。
筆者在微信搜索框輸入“弱者”二字,觸目驚心的是,彈出的文章絕大部分是對弱者的批判。
比如《遠離“弱者婊”》,意即很多弱者會利用“弱者”的身份占你便宜;比如《請警惕你的“弱者思維”》,稱弱者一般是“索取型人格”;比如《弱者都記仇,強者才寬容》,說弱者愛抱怨,會記仇,成功者都選擇寬容;比如《弱者才會要求公平》《弱者追求公平,強者解決問題》,強調公平是理想狀態,強者是適應社會,“不斷調節自己,最終取得成功,弱者總是在抱怨指責,這個社會不公平,是別人的錯誤,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更早些時候,輿論曾有一陣對“你弱你有理”心態的集體批判,不知不覺間,“弱者”這個詞在輿論中已經污名化了。
應該承認,這些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弱者”的心態或者行為令人無法茍同,比如以“弱者”自居,吃拿卡要;比如“我是弱者我有理”;或者以“弱者”為武器,動輒是社會不公,是別人恃強凌弱……
但我們更應該承認的是,如果我們想從個別弱者身上找到這樣一些缺點,簡直是太容易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弱者的道德水準并不一定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我們擅長把從極端的個例當做靶子,然后將它推廣到普遍,搞得好像所有的弱者都值得懷疑,在滑坡謬論下,很容易得出“你是弱者你活該”“弱者才追求公平”等結論,它最終導向的是:我們對弱者的忽略、冷漠甚至鄙夷。
將弱者污名化,暗含著我們內心中的“雞賊”——通過對弱者的污名化,我們徹底地實現了道德豁免。原本很多人對弱者是有同理心、同情心,是愿意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的,但“支付”同情是需要情感成本甚至物質成本的,有些人可能覺得“累”,心里又過意不去。但通過幾個極端例子,將整個弱者群體污名化,我們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對弱者不管不問了——他們可不是啥好東西,別理會,不用幫,不用有心理負擔。我們輕松地甩下了道義責任。
而如果從更深層的文化角度看,我們的傳統一向注重等級秩序,不看重弱者。我們崇敬的,是那些擁有權力和金錢的群體;我們所習慣站立的立場,也是強權者的立場,并根據他們的立場去思考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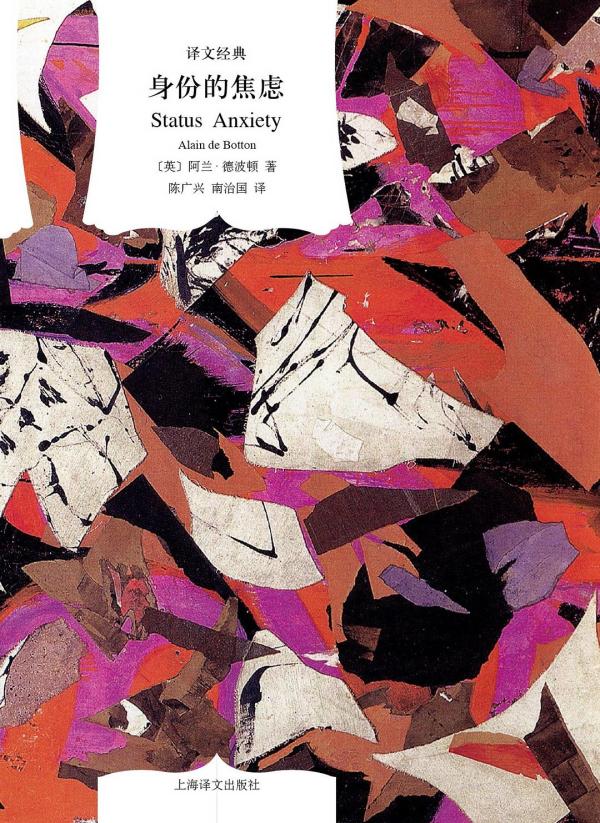
《身份的焦慮》,[英]阿蘭·德波頓著,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6月版
這種心理有點像阿蘭·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里分析的,“人們開始更傾向于認同這樣的觀念,即人的才識往往能影響或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認同反過來賦予了金錢一種新的道德涵義……在精英社會里,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故而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優秀……對那些身份低微的人,這個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負面影響。既然成功者理應成功,那么失敗者就理應失敗。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們致富無可厚非,同理,人們挨窮也不是沒有緣由。正因為如此,一個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我們將一個人的權勢與金錢地位,與他的身份、處境、品格劃上等號。仿佛成功者,都是能力更高、品行更好,而失敗者/弱者,便意味著品行差、能力差,否則他怎么會失敗?
二
鄙夷弱者的“弱者觀”,雖可實現道德豁免,也像魯迅說的宣泄卑怯的情緒,“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但弱者的不幸僅止于他們自身嗎?
我們不該忘卻,弱者還有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必諱言,時下我們社會,無論是富人窮人,無論是商人農民,無論是學者還是盲流,常常共享著一種“弱勢心態”:每一個群體的人都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每一個人都被某種焦慮所裹挾了:生存的焦慮,發展的焦慮,道德的焦慮,公平的焦慮,環境的焦慮。
全民“弱勢心態”、全民焦慮有諸多原因,也有許多非理性的因素,但不容忽視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依舊壓迫著我們,人人唯恐落后,唯恐成為社會的“弱者”,唯恐被淘汰;我們都很趕,我們都很拼,我們都在忙著搶……這種“弱勢心態”也在滋生一種戾氣,并可能產生“為暴力而暴力的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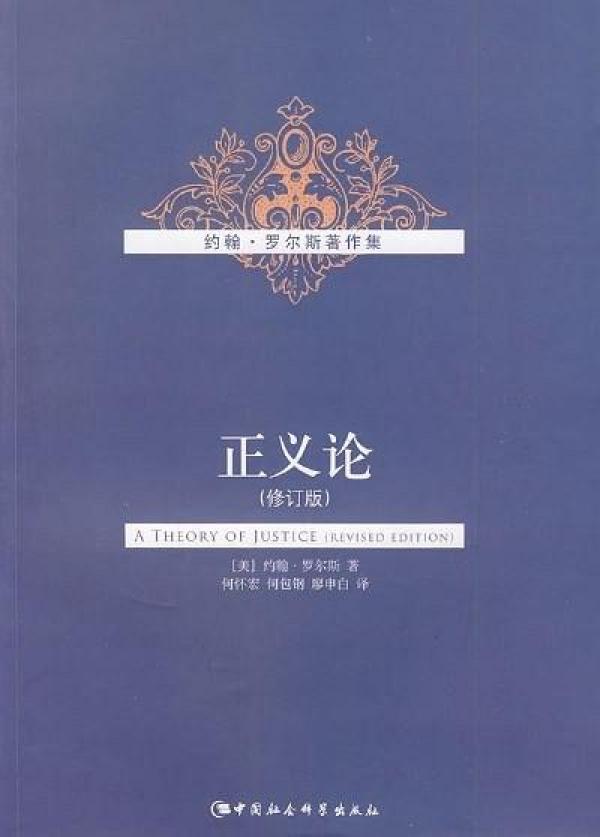
《正義論》(修訂版),[美] 約翰·羅爾斯著,何懷宏、何包鋼、繆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可試想一下,假若我們對社會的信念不是“弱肉強食”,而是“弱有所扶”的守望相助,一切會不會顯得不同?美國學者羅爾斯在《正義論》里曾提出“無知之幕”說法。所謂無知之幕,是“假定各方不知道某些特殊事實。首先,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他的階級出身,他也不知道他的天生資質和自然能力的程度,不知道他的理智和力量等情形。其次,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善的觀念,他的合理生活計劃的特殊性,甚至不知道他的心理特征……再次,我假定各方不知道這一社會的經濟或政治狀況,或者它能達到的文明和文化水平。”羅爾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旨在建立一種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則都將是正義的。”
“無知之幕”雖然并不存在,也是理想化的構建,但它還是打開了另一扇思維之窗,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是弱者。我們都可能是窮人,是殘障人士,是下崗工人,是遭遇不平的弱勢者,是性少數群體……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在做一項決策或形成一個判斷時,才不會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出發,高高在上、頤指氣使、隔岸觀火,而是“像弱者一樣感受世界”:他們是怎樣想的,他們為何會這樣想,怎么才能讓他們生活得更幸福,如何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會……
在人人原子化的時代,人人也都是孤獨的,不安全感總揮之不去;只有我們形成社會共同體的意識——若我遭遇不平,就會有人替我站出來,假若我成為弱者,也會得到眾人的幫扶——我們才能真正收獲內心長久的安全感。我們不僅是為文軍鼓與呼,為殘障人士鼓與呼,也是在為可能成為弱者的自己鼓與呼。
曾于里,文化評論者、專欄作者。本文為澎湃·湃客“眾聲”欄目獨家首發稿件,任何媒體及個人不得未經授權轉載。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