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沈潔談民國的“失傳”:重釋清末民初中國革命

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沈潔最近出版了新書《民國的“失傳”——清末民初中國革命再闡釋》,重新審視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講述其另面的源起、脈絡與縱深。當我們說“未完成”的辛亥革命時,它又是怎樣與民國的“失傳”勾連起來的?在沈潔看來,需要觀察革命史之外的思想變遷與社會變動。
您的新書取名“民國的‘失傳’”,所謂的“失傳”究竟指什么?
沈潔:“失傳”是魯迅先生的話。魯迅是親歷辛亥歷史的時代中人,又是一個超越具體時、勢的敏銳、深刻的歷史與人性的洞察者。他對于“國民性”、“中國”以及“中國歷史”的種種批判,對于辛亥革命、共和成立、民初中國的那些指摘,犀利,沉慟。他在1925年,距離辛亥十四年的“忽然想到”,他講,“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
我用了他的“失傳”。自然,作為一個后世的寫史者,我沒有在哀嘆什么,也不做傷悼。可是,“失傳”非常契合我對于辛亥及其開創的共和的描述。
辛亥革命是一個短短一百二十余天的“瞬間”,而它的發動,頂多上推十年。以十年推倒三千年,這個過程是怎么實現的?我從清末的革命動員講起,講印刷與制度變革引發的知識更新和思想轉型,講革命因輿論、思想嘯聚而來,這是辛亥的特征,也構成辛亥“未完成”、民國“失傳”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的這本書,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話,就是在講述辛亥是何以成立的,它成立的方式締造了一個怎樣的民國。在“未完成”與“失傳”的銜聯中,觀察革命史之外的思想變遷與政治變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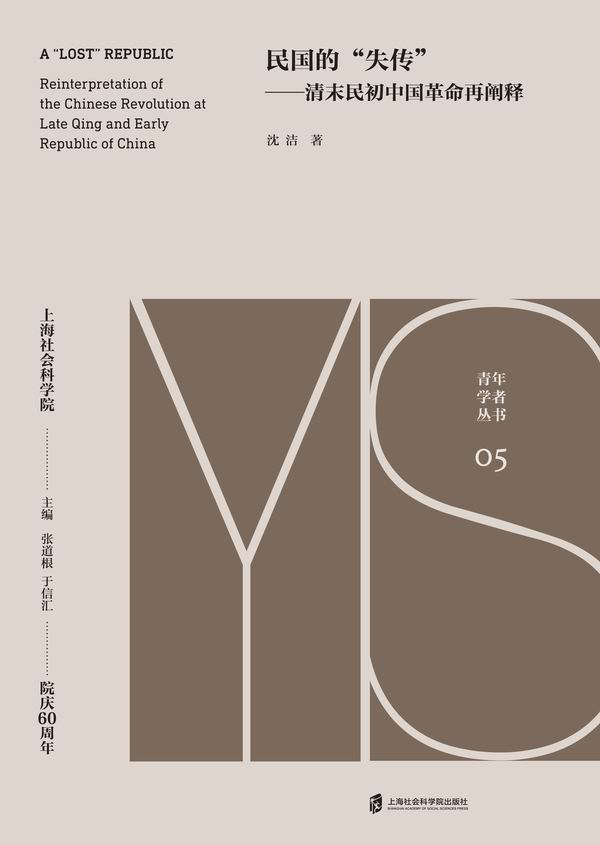
甲午,特別是庚子以后,中國的思想與觀念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中西之爭一變而為新舊之爭,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了這種變化?
沈潔:由“中西”而變“新舊”,有一種明顯的價值轉折。堅船利炮,萬國梯航,西力東侵,致中、西、新、舊交錯,這是我們講中國近代,常識化的一個前提。
傳統分界,是講1840年,但實際上我們知道,除了少數先識者,絕大部分士人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及其對中國歷史、文化、意識、意志力的侵入,是從甲午開始的。戊戌與甲午聯綴在一起,晚清中國真正具有共識意義的革政思想啟程。與革政相伴的,便是革命。一方面,甲午戰爭后期,身處海外的孫中山開始革命嘗試。1895年2月抵達香港后,孫中山在日本商人梅屋莊吉幫助下,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領事中川恒次郎聯絡,請求武器及資金援助,并與同儕策劃在廣州起義。另外一方面,“驅除韃虜”到底是怎么策源的,實際上,也與日本相關,他們在甲午之際便對中國進行種族主義的挑動,宗方小太郎撰寫《告十八行省豪杰書》,就開始講“逐滿清”,“起真豪杰”,“勿為明祖所笑”。
甲午一役,摧垮了士林的精神自信,所謂“四千余年之文物聲名行將掃地而盡”,“變”在此時構成“共識”,從甲午到庚子,倭仁式的那種中國自信,不存在了。這個影響非常深遠,往后一直到辛亥到五四到1949直到今天,有關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諸多爭執和混亂,都受到這種心態的影響。這個過程,還包括諸如“國家”、“民族”、“國族”一系列新觀念的出現。當時許多人,都是在甲午戰敗的情境中,開始言說“國家”,“知道國家是個怎樣的東西”,這些有關國家、國族的表達,意味著中國開始進入世界,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于“中國”的理解,變成了“中國在世界中”“世界中的中國”,有關身份和認同的位移,直接導源了歷史敘事的轉折。這些,都可以在中西新舊的擴展線上考察。
我們現在講“新舊之爭”,時人講“世局原隨士議遷,眼前推倒三千年”,我的第一章“‘新學猖狂’的時代”,“新學猖狂”是張之洞晚年的一個“悔心”。問題是,“新學猖狂”怎么達成的?
所以我費了相當大的筆墨去論述西學、新知與制度改革、技術革命、社會變遷的連動關系。我想在一個制度、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網絡中探討價值秩序重構。這個過程,科舉改章、停廢與書業的互動,至關重要:廢科事件怎樣從朝堂政令及教育、取仕一隅擴散至廣袤的經濟、社會,學制變遷如何與印刷、閱讀乃至整個士林風習蟺變交互影響,舊書業如何在制度、技術與文化的綜合作用下式微、更遞,上海取代傳統印刷重鎮,成為新式出版業中心,空間位移中又包含許多繁復的經濟因素。
學制改革與印刷業的根本轉型,這兩個事件交逢在晚清“中”“西”“新”“舊”的世道遷折中,兩者并非引發與被引發的單一因果關系。在所謂“辛丑、壬寅之后,無一人敢自命守舊”的朝局之變與人心之變中,技術、經濟空間格局的演變其實是真正將這些思想變局實現并固定下來的本質性力量。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綜合的、合力的過程,若非科舉改章,考試內容變更,“啟蒙”便很難與“生意”共謀;若非技術革新、現代的通訊與交通,大規模的印刷與傳播不具條件,書商、報人便不可能在短短數十年間,使“舊的中國”一點點圮裂,使孤另的思想匯流為思潮,推動制度改革、政治遷易。
我想要做的,是思想史的另一種研究路徑:將思想史研究實體化,用“印刷”這樣的一個“樞機”,整理、分析晚清中國的文化潮動。
辛亥是中國現代革命的開始,也是這本書的重心。您書中的上篇為“印刷與革命”,讓人想到谷騰堡與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近一二十年互聯網帶來的變革,是這樣嗎?
沈潔:谷騰堡革命,也就是我們習稱的“印刷資本主義”,包括你講的互聯網變革,我想,在一個傳播學的脈絡中理解,基本上指向的就是信息傳播方式導引的思想變動和社會變遷。我前面已經講了,思想,要從“先識者”的腦際、案頭向一般社會鋪展,不是思想本身能達成的。它需要媒介。
關于印刷資本主義與宗教改革,以及與“現代世界”的興起,這是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著力描述的。安德森以歐西歷史建構的理論,在中國語境中,有適用度,但也有它無法解釋的部分。中國在谷騰堡革命之前已經有了相當繁盛的印刷業,官刻、坊刻、私刻,書院、精舍、書堂及各色家刻,在宋明以降的學術、商業與社會中有豐富展衍。另一方面,安德森的理論也不能解釋中國谷騰堡革命的特殊性:中國從西方各式各樣的印刷技術中做出了怎樣的選擇、為何如此選擇,以及,這些選擇的后續影響,都存在于中國歷史發展的自有邏輯中。所以,芮哲非寫了《谷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從中國傳統的印刷文化與印刷商業談起,講述了1876至1937年間西方的印刷技術取代中國傳統雕版印刷術的過程。
而在我的書中,著重討論了新書業與晚清“君憲”“革命”的關系。我把這個過程總結為“上海影響”:書報通過哪些渠道、什么方式傳布到內陸,文本如何抵達讀書人?相同的思想資源為什么造就了革政與革命兩種不同的道路選擇?郵路、學堂、師友之間,從技術到建制,從商業到人群,我用林林總總的閱讀記憶,有趣的故事,串聯了一個知識、思想的傳播路徑,它如何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深重改變了中國歷史。“革政”“革命”主張匯聚在一起,掀動人心中潛伏的波瀾與希冀,終于使波瀾、希冀化為了行動。

辛亥是在這樣的閱讀洗禮、思想風暴中匯聚的,它不是在經歷了切實的、社會的、經濟的變動之后,引發的革命。我當然不是說,靠著文本傳播,革命便自然成立了,辛亥還有其他動員,但知識與觀念變遷切切實實撼動了社會。我們在一個歷史的、具體的語境中看“人心”,辛、壬之際大廈將傾、“人心盡去”,這不僅僅是玄學化的歷史抒情、清遺民式的悲戚,也是清季知識轉型、思想變動的具體結果。
這個“上海影響”可以延伸到1920、1930年代,印刷一方面依舊接應啟蒙及思想運動;另一方面,進入“大上海”時代,消費、市場繁盛,文人、商人與市民社會川流其間,大報、小報,大型的出版公司與小書鋪,從制造、傳播到消費,印刷又進一步構建、豐富了都市中的文化空間,而“左翼”與革命文化即在此空間中孕育、壯大。在市場、商業、消費以及地域、空間的多維視角中,再看現代中國的興起及其一次接一次的轉向,這是思想衍變的軌跡,但同時也是政治、經濟與文化交織的網絡,牽涉到思想被制造、傳播,以及在更廣闊空間內流動的過程。“上海摩登”構建的這個物質社會、消費社會提供了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的巨大便利,左翼思想與共產革命的組織即在這個便利、兼容度極高的網絡中,悄然生長、蔓延、噴薄,指向了新的未來。
“反滿”當然是我們很熟悉的晚清歷史,您的“再闡釋”與我們以往理解的反滿,以及反滿對于辛亥革命的意義,有哪些不同呢?滿人在民國時期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命運,或者說,對他們而言,民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沈潔:反滿在辛亥革命輿論動員史上的重要作用,不用多講。這其中,思想運動是一個層面:革命派制造滿漢隔閡,明清易代之際的創傷記憶被迅速喚回到當代,成為宣揚革命、推翻異族統治的利器。所以胡漢民說:“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國。”由反滿鼓蕩起來的革命激情要比反專制更容易傳播,也更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鳴。
書中的反滿與族群,不著重思想動員,主要從分殊、行動和“遺民”三個層面揭示族群問題與中國現代革命的關系。
關于分殊,我想要分析的是,除“滿漢異族”,以反滿為主題的近代民族主義存在更為復雜的內涵。比如,經常強調的“瓜分危機”——“彼滿政府以惡劣無能,陷吾民如此惡境,強鄰虎伺,楚歌四面”,朝廷無能,必顛覆之,方可救中國。這是反滿的常見論調。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層有關“不可仇外”的議論邏輯。我們知道,鴉片戰爭以后的救亡敘事中,排外與仇外是普遍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排外不再是亟務,排滿才是首要。“排滿”—“救國”—抵抗侵略是一套論述邏輯,與之對比,辛亥年的修辭發生了明顯轉折,“外人”僅為“及身之禍”,而“滿虜”則為“祖父之仇”。并且,排滿重于排外的思想,此際不僅是言辭,也是實際行動。革命過程中,各地方軍政府發布的公告,均特別強調“保護外人”。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從“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虜非我族類”,意味著,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變換了他們對于邊界的定義。在我看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確認邊界。鴉片戰爭之后的困局,敵我邊界在“中”與“外”、“華”與“洋”;而在推翻清廷的革命邏輯鏈上,“滿”重于“洋”。這說明,“民族”邊界是時勢造就、具體而微、不斷傾斜變動的。救亡圖存大前提下,“反滿”,羼雜著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文明與野蠻,國族、民族與種族,等等各種復雜的題中之義,這種“復雜”直觀反映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義與多歧。
關于行動。這也是我特別強調的一點,通常講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非種族革命,未流血十八省光復。這是部分事實,卻也不是事實之全部。武昌起義后的滿漢對峙,族群界分,部分滿城的殺戮事件,加之戰爭激揚起的謠言,中樞的滿洲親貴與八旗兵丁一起,由恐慌而驚懼,最終放棄抵抗,選擇讓政。南北和議,辛亥大妥協有諸多繁復的人事、時勢關系在里面。僅僅革命對手方這一側,就包含帝后及親貴集團,樞臣與疆吏,駐防,北洋系,江浙立憲系,等等,中間還摻雜著革命集團中與各方勢力皆能周旋的一些重要人物,及革命集團的內部分化。退位詔書和優待條件的起草,從人選、成稿到最終底定,過程是怎樣的,中間經歷了多少博弈、轉圜?四川將軍玉崑、杭州將軍德濟,各自在什么樣的情勢下、與什么樣的勢力達成妥協。光復之際,駐防、士紳、新軍、民黨、會黨,甚或羼入革軍隊伍的“匪”,在各地有復雜的組合、對峙,均構成走向共和的具體情勢。滿與漢是透視共和轉型的一面棱鏡:革命雖撼動帝制,但帝制牽絲攀藤,妥協及退讓是歷史的明面,隱伏處,更有層層疊疊的人事權爭及政治理念的分裂;這些權爭與分裂,直接決定了民初政治的基本面貌。
關于“遺民”。我想要在一個遺民史的視角中討論后“驅除韃虜”時代的族群與政治認同。革命鼓蕩起的族群對峙不會隨“五族共和”自然消亡。辛亥之后,滿族作為一整個族群的流亡史,可以看作是辛亥革命的遺留問題,非但“民國”變成了“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對于一個族群更意味著數十年的流亡與隱匿。清遺民可以義正辭嚴講“民國乃敵國也”,旗人呢?大量的隱姓埋名,有遺民之實,卻不能獲得遺民的“名份”。去做改滿族為漢族、更換姓氏的法律呈文,亦要先高呼幾句五族共和時代的美好。連沉默權都沒有。這可能是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的遺民處境都無法比擬的無言的退場。
當然,我摭拾的,不是歷史中的顏色與情緒,而是作為遺民的旗人,他們的命運所昭示的以辛亥為開端的現代中國,充滿了矛盾、反復與羼雜的歷史過程,另一重意義上的辛亥余緒,也想要在這個余緒中探討共和的“失傳”及其轉向。
在您的辛亥敘事中,特別強調這場革命的“未完成性”,關于民初中國的論述可以說即是圍繞著“未完成”這一線索展開的。書中以奉化為例,具體而微地展示出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黨化、權力重組及向“國民革命”的引渡的過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地方的歷史與整體大歷史之間的關系?
沈潔:這個我不知道算不算個人的一點偏見,或者說,與我秉持的史觀有關系。大凡地方史、個人史,我一定會作為讀者,在假想中提問作者,“地方”的問題指向在哪里?除了你所找到的史料,“寧波”“溫州”或者“X州”,到底意味著什么?“地方”及“人物”在什么情況下可以構成“歷史問題”。這個不是自明的,《春秋》之義,“常事不書”,不是所有問題都值得成為“歷史問題”。
奉化個案這一章,能成文其實也偶然。2014年參與點校《張泰榮日記》,整個閱讀與整理的過程,我幾乎沒有感覺到太多的“史料興奮”。平平無奇、絮絮叨叨的一部個人生命史,除了有關社會生活與經濟的那部分,我不知道,這樣的一部史料,要怎么入史。偶然是在于,我在梳理地方改良社團“剡社”歷史的時候,發現了許多熟悉的名字——中共在奉化建立黨組織、發動群眾運動,最初的關鍵人物。順著這些人名,我摸索到了一個自晚清逶迤而來的,地方社會如何被組織與整合進國民革命脈絡、并終而建立黨治的一個基本線索。這部日記的主人張泰榮,其實屬于典型的“無名者”,使他“進入地方歷史”的節點,是1925、1926年前后,加入剡社,并在不久后加入國民黨。個人史揭示的,是中下層讀書人如何通過加入新的組織、黨組織獲得身份,進而成為“地方力量”的一部分,他由此,從“無名者”進入了“歷史”;而以剡社為代表的自治團體與戊戌一代地方精英及國民黨、共產黨組織的相互滲透、融合、援引與捻接,則揭示了地方力量黨化與組織化的具體經過、情形,以及,在此過程中地方權力關系的重組,勾勒了清末新政以降,一個典型意義的,“地方”由散沙狀進入組織化、黨治化的歷程。這樣,就在辛亥“未完成”的延長線上,解釋了從民初的法統之爭到黨治,為何發生、又如何轉型。

我認為,這就構成了“地方”的問題指向,是我們理解大歷史所需要的,“毛細血管”式的縱深。
有關爭奪黨統的問題。在1920年代地方力量匯流與重塑的過程中,也已經形成了大體的輪廓,預示了大體的走向。國共兩黨的早期基層黨員,是科舉停廢后學堂時代造就的一種新社會力量——學而優則仕的固定上升渠道取消,被拋入社會,由信仰的動員、生計的困頓和精神的空洞,合力,推入革命大潮。一方面,他們托援于戊戌以降結成的權力網絡,創建并發展其組織力量,另一方面,又空前深入到街衢、鄉村,發動了、裹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這批縣、鄉一級的跨黨黨員終而成為共產黨組織的跟隨者和群眾運動的組織者。依托五卅,在“反帝”旗幟下,農工運動迅速滲透到地方社會的各個細部。從“再造共和”到“以黨造國”、“國民萬歲”,在地方史鮮活繁密的細節中,中共為什么比民黨擁有更強大的底層動員能力,線索也變得更清晰了。
清末民初的中國革命,實際上是在現代國家的確立過程。一方面是“國家”一步步向地方滲透,即“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改造;另一方面地方在這個過程中亦并非全然被動地接受“滲透”和“改造”,而存在著一種極其復雜的互動與博弈。這一博弈和反抗是怎么影響國家建構與現代建設的?
沈潔:到1930年代,辛亥余緒中的政爭與黨爭只剩余波,確立一個現代政府的“合法性”,成為主題。現代政治的確立,需要經歷一系列自我形構以及對他者的規訓,所謂“訓政”,既是對人民進行運用民權和承擔義務的訓練,也包含政權自身的訓育。這個過程,通常我們講——規訓,“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現代性的壓制性影響”,“傾聽沉默的大多數”;斯科特講“弱者的反抗”,同樣也是屬于“拯救歷史”這一面的。
在我講述的這個社區故事中,一方面可以清楚看到“現代”如何論述傳統、定義傳統并對其進行改造,“國家”如何進入社區,做怎樣的努力去規訓地方社會。清末民初破除迷信、禁革迎神賽會,現代國家定義什么樣的信仰為“正信”為“合理”,用“理性”“科學”要求民眾,規定其生活方式,這中間,既有現代性的認同,也包括紛繁復雜的利益訴求。這個“規訓”的歷史,我們大致熟悉。
蘇州城的“求雨故事”,弱者的反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面,但“現代”與“國家”并沒有那么強拗,或者說,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民眾與傳統、儀式的對立者。國府大張旗鼓“反迷信”的1930年代,對如火如荼的祀神活動,從開始到極盛,政府都是默不作聲的旁觀者,而只是在儀典已成疲態時才象征性地逮捕了幾名“無業游民”。這說明什么?正如現代人對“迷信”的曖昧,民國年間,國家之于社會的規訓,也處在一種松散、游移的過程當中。
故事的主角,現代政治規訓與懲罰的對象——“習俗”、“信仰”、“儀式”、“慣習”。在非常多的實踐場景中,民眾與“規訓”基本隔膜,相當于兩個平行世界。日常生活有強固的自足邏輯,遭遇批判與改造亦有不同階段,視情境有不同反應,這些力量,構成對現代性自我認同及權力建構的反向塑造。我說的“反向塑造”是指國家按照現代規則改造民間生活,他們也只能依著慣習循序漸進,甚至更多情況是無法改造,行動反被民眾世界牽引。這說明,“現代”既是指導性和支配性的,又是實踐性和流動性的,是民族國家的建構理想與社區歷史爭持與妥協的過程。
在“結束語”中,您說這本書是你試圖繞開“拾骨之學”所做的一點點努力。“拾骨之學”怎么講?這種努力本身應該也寄托著您對史學的理解。
沈潔:這個話是劉咸炘講的,他講史學有考證事實之史考、論斷是非之史論、明史書義例之史法、觀史跡風勢之史識四端;他又講,史法明,史識乃生……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書只是一碑傳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只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淺陋之學究,專以論人為史學,徒騁己見,固不足貴;而博雜之考據家,專以考事為史學,亦只為拾骨之學。
“淺陋”與否,不在討論之列,是勉力之事。我理解的“拾骨之學”,不但包括歷史研究對象及敘事方式的選擇,也包含能在心里升騰起來的精神力量,心性所依。讀史閱世,在事上磨,大概并不會讓人變出“現世”聰明,卻是能夠讓自己沉到河流底部,觀察人間的一點點定力。在歷史中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打撈人心與人性中的恒久價值,對我來說,就是這個職業帶來的最大收獲,就不是“拾骨之學”了。也算是一種未必能至而心向往之。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