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演技封神?聊聊國產明星這股風
原創 穿Prada的南瓜 Sir電影
大家好,我是@穿Prada的南瓜。
今天毒Sir翹班,我來代班。
不為別的,就聊一個國產片的新興現象——
“特殊的他們”,越來越多了。
就說這一兩年來的大銀幕上,趙麗穎《第二十條》,周冬雨《朝云暮雨》,佟麗婭的《假如,我是這世上最愛你的人》,易烊千璽《小小的我》,張藝興《不說話的愛》。
聾啞,腦癱,無臂,植物人。
這些角色都有著難以忽視的障礙和缺陷。





還有即將上映的,《下一個臺風》張偉麗和張子楓,一個是失語,一個是眼睛受傷。
五月份上映的《獨一無二》,國產版《健聽女孩》。


過去我們說過,為什么殘疾人總是“不被看見”。
無論是公共場合中,還是國產銀幕上。
我當然希望,他們的故事能夠被更多講述,得到更多關注。
但。
現在也有另一種聲音——
內娛明星們開始排隊認領“特殊角色”了。
問題在哪,是看的太多了嗎?
我恰恰覺得,大家隱隱的不適感在于,我們還沒有真正看見。
01
其實在去年,易烊千璽《小小的我》就陷入過爭議。
還沒上映,就被一些網友質疑為“靠演殘疾人拿獎”。
好像大家對于這個問題尤其敏感。
明星不能演殘疾人嗎?
好的電影不能獲獎嗎?
不該這么武斷地去評判。
別忘了,有的殘障人士的角色,被大明星演繹后,分外精彩。
達斯汀·霍夫曼的《雨人》,西恩·潘的《我是山姆》,小李子成名前的《不一樣的天空》。



就說離我們更近的。
《無名之輩》中任素汐的表演就讓人過目難忘。

而對于演員來說,要成功塑造一個殘疾人角色,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殺青后兩年,易烊千璽依然保留著劉春和的肢體記憶。
張藝興在拍攝前花了兩個月學習手語,拍攝中也有和真正的聾人交流。


但與此同時也有一種錯覺。
就是演特殊角色比演普通角色,演技更偉大,乃至“封神”。
于是才會有人疑惑——
主導電影的,究竟是故事,還是“演技秀”。
我倒覺得。
要破解這個問題,癥結并不在于演員的演技。(客觀來說,張藝興和易烊千璽在電影中的表現都有進步)
而在于國產片的創作上——
我們的銀幕為什么突然開始需要殘疾人。
又是怎樣看待他們的。
02
可能有點武斷。
但我也想說——
國產片需要的不是殘疾人,而是苦難,以及對苦難的煽情和渲染。
而殘疾,通常像一個擴音器一樣,將普通人面臨的困境瞬間放大。
比如《第二十條》。
毫無疑問,趙麗穎飾演的郝秀萍,是整部片最大的戲眼。

郝秀萍夠“慘”吧。
欠高利貸,被強奸,跳樓。
這些事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悲劇,而她還“有苦說不出”,進一步凸顯了她的困境。
《不說話的愛》。
張藝興飾演的聾人父親,在一夜之間遭遇了前妻搶娃、失業、籌錢三重困境。
任何一個都能壓垮普通人的困難,電影中全給了一個殘疾人。
為了解決困境,他被逼得違法犯罪,頭破血流,“妻離子散”。
旁白聲嘶力竭:
你們知道殘疾人有多恐懼我們這個世界嗎?不僅要把他們逼到派出所,甚至想逼到監獄里!
大結局更是召集了真正的聾人群體旁聽。
將判男主有罪的法庭塑造成不近人情的冰窖,特寫聾人們痛哭的畫面。



周冬雨的《朝云暮雨》。
自殺未遂后成了植物人,被不喜歡的男人撿回去,洗澡、擦身、任憑擺弄。
周冬雨直言:這是自己演過最絕望的角色。
但哪怕再慘再用力,整部電影的人物與表達仍然脫節,只有豆瓣5.8的水平。


大家為什么好像“看夠了”?
因為當殘疾人在盡力活出殘缺以外的世界時。
銀幕上的流量們,卻仍在還原“殘缺”本身。
他們演得越還原,越慘痛,越悲苦。
其實呢?
越無法避免共同的套路——
只見缺陷,不見缺點。
鏡頭努力地塑造所謂“殘疾人”的身心對比:
殘疾人一定脆弱又純潔,單純又善良。
他們越被騙感情、騙錢、被瞧不起。
人品就越好,越簡單,越出淤泥而不染。
不論是與親人和解的劉春和,愛女心切的聾人父親,還是“完美受害者”郝秀萍。
哪怕走上犯罪的道路,你在他們身上也看不到任何人性的幽微、灰色。
更別說由于殘疾,面向這個歧視的社會時,內心是否曾閃過一絲微妙的皺褶。
身為殘疾人。
仿佛他們天生就該比健全人更加完美無暇,品性高潔。
殘缺是他們最大的特點,也只能是他們最大的特點。
03
1997年,陶虹在《黑眼睛》里,飾演一個喜歡運動,搞三角戀的盲女;
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雖然看不見,依然藏不住對青春韻事的懵懂與好奇。

婁燁的《推拿》,豆瓣8.0,捧回了包括金馬、銀熊在內的數座獎杯。
電影里,更是找來真正的盲人演員,張磊。

△ 圖片右一
這位名為張磊的盲人女演員,觀眾記住她最大的戲點,是“盲”嗎?
不。
是哪怕她看不見。
但依然演出了一個女性面對兩個男性,那種縈繞心頭的狡黠與曖昧。
她飾演的小孔,跟郭曉冬飾演的王大夫是一對。
兩人第一次做愛時,小孔撫摸著身上的男人,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寶貝,我們現在是幾個人?”
男人正忙著,想了想:一個。
小孔滿意地笑了。
渾濁的瞳孔也蓋不住她的得意,那是一種從肉體到靈魂,屬于女性的“征服欲”。
“回答正確,寶貝,我們是一個人”。
“你想什么,要說什么,我都知道。”
什么意思?
我們的國產片,不是沒有拍過殘疾人。
但現在的電影呢?
除了殘缺之外,殘疾人的故事,除了悲慘,還有什么?
丹尼爾·戴-劉易斯的《我的左腳》,或者安東尼·霍普金斯的《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一個腦癱,一個阿爾茲海默癥。
兩人都拿到了奧斯卡最佳男主,是憑借出演殘疾人,實打實的真·影帝。
但他們是怎么演的呢?
《我的左腳》,丹尼爾飾演全身上下只有一只腳能動的克里斯蒂,他雖然具有藝術天賦,但比勵志和雞湯更扎眼的,是他暴躁的性格、酗酒的惡習。
因為殘缺,他不僅對家人充滿控制欲,甚至還有一定的自卑和攻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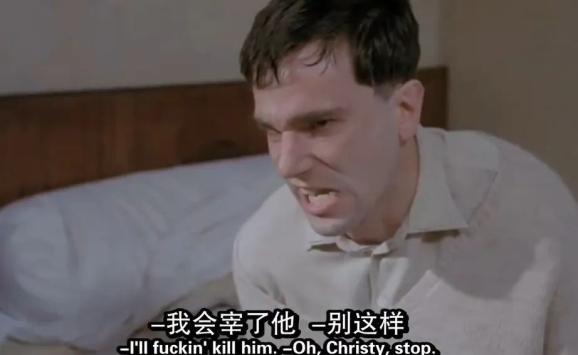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因為疾病折騰子女的爸爸。
相比一個無害的,充滿愧疚的慈父,他更像一個脾氣暴躁的老小孩。
你既會對這個角色產生憐憫,同時也能感受到背后家庭的不堪重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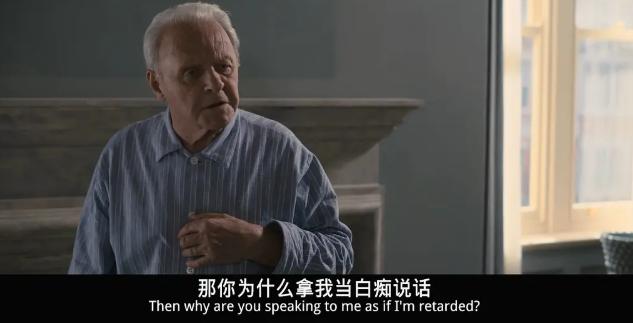

殘疾對人來說,不是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
而是盤旋在上空,讓余生都布滿潮濕的一朵烏云。
要拍殘疾人,就不能只拍殘疾,不拍人。
如果更以刻板的樣子去塑造本就是弱勢群體的他們,這樣的銀幕形象,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偏見?
健全人面對的問題,殘疾人依然會面對。
原生家庭、工作壓力、性別議題……他們面臨的更多、更雜。
殘疾人也有壞人,殘疾人也會貪婪,殘疾人也有缺點,有不堪的一面。
原版《健聽女孩》——
聾人媽媽管正常的同齡人叫“那些能聽見的婊子”。
面對健全的女兒,她也承認自己希望過女兒也是聾人,這樣會更像一家人。

聾人父母天天做愛,性是夫妻生活的重心。
還因為“下流”的烏龍,鬧出不少的笑話。
而這些又能在國產版里保留幾分,從個體到群體的真實,又會被裁掉多少?
-很高興與你們做愛
-好吧,我也很高興與你做愛


國產片越來越喜歡只抓“議題”,不抓“人”了。
也是到了殘疾人這里,才終于踢到我的鋼板,捅到了大血管。
就像《不說話的愛》幕后一個細節——
飾演聾人父親的張藝興能花兩個月學習手語,卻臨時抱佛腳,把女兒的頭發扎得歪歪扭扭。
很明顯。
不僅是他,甚至是整個劇組自己,都從未把“父親”這個元素放在“聾人”之上,做出比話題度更多的考量。


不是國產片不能拍殘疾人。
而是我們應該如何去面對人的困境。
是沉湎于苦難,期望博得眼淚。
還是拍出與苦難的周旋,凸顯角色本身的人格。
我相信觀眾更愿意看的,是后者。
比如任素汐的角色,淚點不在于她有多慘,而是她的倔強,對命運的不服,以及對尊嚴的渴望。

《推拿》中,郭曉東的角色說,盲人最在乎的就是錢。
因為錢是他們在這個世界最值得依靠的東西。
也因為有錢,證明他們能賺錢,不是廢人,是他們尊嚴的象征。
誰想要奪走,他們能豁出命。

看到沒有。
真正的殘疾人不愿意到處向人展示“我好苦”。
而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拍出的殘疾人角色是,ta在ta的世界里就是一個普通人。
而往往呢,國產銀幕題材再催淚,立意再升華,越想讓觀眾共情,越會適得其反。
你看不見,我聽不到,這是不同。
最重要的是,這些生來就有的東西,并不是人與人的生命最重要的主題。
就像史鐵生的那句玩笑話——
他喜歡余華,因為只有余華不會把他當殘疾人,也不會把他當人,喊他去踢球。
我們想看到的不是“殘疾人”,而是一個和我們稍微有些“不同”的人。
看見他們的缺陷,也看見他們的缺點;
看見他們的遭遇,但也看見他們的人性;
看見他們的弱小,更看見他們的強大;
不當他們是“殘疾人”而去刻畫,而是刻畫一個人,只不過ta剛好是殘疾。
我想,大概這才是真正平視、尊重他們的方式。
也是國產銀幕真正喚起對弱勢群體關注,所謂文藝作品,最大的意義所在。
只有當我們將殘疾人不再看作一個“殘疾”的人,而是一個殘疾的“人”的時候。
到那時。
相信我們離真正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遠了。
好了,今天先寫到這,我是@穿Prada的南瓜,我們下期再見。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原標題:《演技封神?聊聊國產明星這股風》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