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錢立卿評《現象學的心靈》|現象學的“當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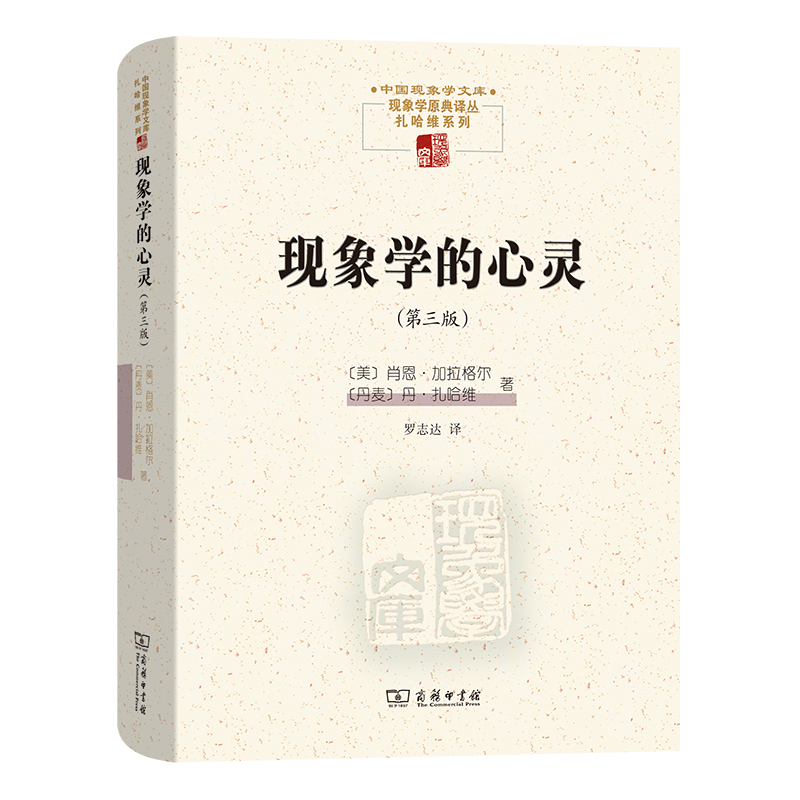
《現象學的心靈(第三版)》,[美]肖恩·加拉格爾、[丹麥]丹·扎哈維著,羅志達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6月出版,525頁,98.00元
“現象學”一詞最早由十八世紀著名光學家朗伯(J. H. Lambert)提出,時至今日已散見于各種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中,學者們通常視其為一個方法論概念。只有在哲學領域,現象學才真正發展成為一門系統性的學說,亦即“現象學哲學”。自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創立此說以來,現象學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歷經變革,以思想史運動的形式傳播開來,影響遍及整個人文領域。
既然是運動,就必然帶有傳承和偏離的雙重趨勢。事實上,在胡塞爾發表奠基性的《邏輯研究》之后僅過了數年,他在哥廷根和慕尼黑的學生們就各自發展出了一堆“離經叛道”的學說。當然,這對現象學家來講并不奇怪,除了思想本質上的衍變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胡塞爾和他的徒子徒孫們都認為現象學必須是完全基于具體和現實的情境而開展思考的一種“工作哲學”,所以盡管它會有某種內在的規范性和傳承性,但不可能拘泥于任何宗派或教條。

丹·扎哈維
作為本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現象學家之一,丹·扎哈維也以自己的風格不遺余力地塑造著現象學的當代形象——這一點在商務出版的《現象學原典譯叢》之“扎哈維系列”中清晰可見。不論是他自己獨立完成的文本還是與別人合著的文本,都顯示出對現象學經典源流和時代精神的同等重視。然而,每個時代關切的東西不盡相同,想讓經典思想直接參與今天的對話和議題,并不是件隨隨便便就能做到的事。現象學的發展也始終面臨著一切經典的現代化都會面臨的問題:人們為什么要關心這些?如何向人們解釋其中的價值?
上述考量也解釋了扎哈維與另一位著名現象學家加拉格爾合著的《現象學的心靈》一書為何從2008年初版以來做了大幅度的修訂,特別是我們現在讀到的第三版已與當年的面貌大相徑庭。就此而言,這部著作不僅是導論性和爭辯性的,同時也是歷史性的。它既表明了兩位作者自身的關切和思想歷程,也間接反映了近二十年來相關研究領域本身的發展狀況。中國讀者不僅可以通過此書了解到當代現象學領域的一些核心論題與進展趨勢,也能夠明白不同哲學流派與科學分支在相關問題上的基本論辯方向。
正如兩位作者在第二版序言里面說的那樣,這本書有一個明確的出發點和一個明確的目標:出發點當然就是植根于經典及其流變史的“正統”現象學立場,而主要目標則是與心靈哲學和認知科學等進路就共同關心的話題進行論辯并做出自己的貢獻,或者說“給心靈哲學發展出一條現象學路線”(17頁)。筆者所謂的“正統”并不是指任何原教旨主義現象學理論,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種原教旨現象學,即便是胡塞爾本人的思想亦是在其一生中不斷變化和擴展的,以至于很多現象學家都熟知如何“用胡塞爾反對胡塞爾”。毋寧說,對兩位作者來講,“正統”的現象學觀念應當是一種始于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同時又不斷向后兼容并蓄的統一化立場。扎哈維在不同地方都指出過,內部紛爭與共同傳承在整個現象學運動的歷史中始終交織在一起,但對他來說,后者的重要性超過了前者,因為正是這種處于流變中的共同理念與核心主張才是現象學家能夠向其他人表明“什么是現象學”的立足點。至于內部分歧,在積極的意義上也可以提供一種多元視野,讓我們看到現象學分析本身也可以被修正,還有其他選項的可能性。
有鑒于此,本書作者從當代關切的視角出發,開篇就力圖闡明現象學的基本定位。他們希望讀者在面對心靈和意識問題的時候,先要明白現象學應該被理解為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第一章),最典型的思考方式又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第二章)。不過,與百年前的胡塞爾、舍勒、萊納赫、海德格爾等人的關切相比,當代現象學的處理方式既與傳統交合,又有不同指向。
扎哈維在各種導論性著作中都強調過如下觀點:現象學方法既不是內省式的也不是主觀的,現象學家既不是傳統的表征主義者也不是唯我論者;心靈本身不是一個封閉的東西,它不等于生理意義上的大腦活動也不是作為物理對象居于其內,而是就其概念來講已經內蘊地(intrinsically)與世界共屬一體了。這些觀點固然是當代現象學的立足點,但它們顯然也屬于傳統看法,因為至少在胡塞爾明確提出先驗轉向(transcendental turn)之后,整個現象學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主線方向就是以上述觀點為基礎的,不論現象學家們在具體表述上有多大差別。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即便是同樣的現象學立場,比如先驗的觀念論(idealism)主張,也是基于不同背景、目的和論敵來講的,致使后續討論也有了不同取向。胡塞爾對心靈或意識概念的先驗觀念論定位一方面基于他對時間問題和認識論基本問題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長期與心理學家及實在論者對線的結果。這不僅使他提出并反復闡釋了現象學還原的思想,對整個現象學進行了先驗化處理,而且還進一步導致他后期不斷深入先驗化方法本身的問題,與他的學生海德格爾和芬克一樣,花了很大精力在元層次上對現象學自身進行了諸多批判性反思。這些工作的后效之一就是現象學的思辨化和形而上學化——盡管這是胡塞爾一開始想要避免的東西——并由此開啟了現象學運動的一個獨特方向。
反觀扎哈維與加拉格爾,他們的現象學主張并不帶有多少純粹哲學的“元”味。這倒不是說他們不堅持先驗化或者說不對現象學方法進行反思,而是說他們的主張具有明顯的當代特征。首先,扎哈維表述的先驗化方案總體上忠實于胡塞爾并在相當程度上兼容了后來的重要思想家諸如(早期)海德格爾、薩特、梅洛-龐蒂等人的核心論點,但扎哈維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種表達形式,而是盡可能提綱挈領地解釋了一些最關鍵概念(比如懸置、還原、意向性等)的理解方式——這本身就是一項當代貢獻。其次,兩人對現象學方法的反思性考量與修正不完全依賴現象學理論的內在爭辯,而是把它置于當代心靈哲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與腦科學的成果的大環境中進行綜合性反思。這項反思需要一種特殊的平衡感,它既不是變相的懷舊主義或試圖用舊思想打倒新理論,也不是要把哲學研究的立場與方法論地位直接拱手相讓,更不是想在新理論中尋寶之后再返回經典的現象學去。兩人明確指出,現象學的發展與近半個世紀興起的其他研究進路是交互和反饋的關系,當代現象學的正途就是在不斷的相互學習、交鋒爭辯中實現某種“相互啟發”(430頁)。
不過,這些想法聽上去很美好卻并非毫無爭議。除了來自前面所說的“形而上學的”與“純粹的”現象學家們的內部批評外,另一個重要的質疑就是認為這條思路在出發點上是矛盾的。因為自然科學和自然主義哲學總是帶有實在論前提的,而先驗現象學明確拒絕了這種前提,所以兩者的互動似乎無從談起。這就涉及另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即作者所說的“自然化現象學”方案。什么是自然化?學者們也對此莫衷一是。一種激進的觀點是讓現象學在本體論上放棄中立性,重新復活當年以萊納赫等人為代表的實在論傳統。當然,這種復活并不是僅僅承諾實在事物的本體論地位與使真者(truth-maker)地位,而是要讓實在論成為整個現象學進路的合理性基礎。毫無疑問,這樣的想法不太會被現象學家接受。那么溫和一些的版本又如何呢?讀者不妨細品一下作者自己的說法。
其實近年來國內學者對現象學與自然主義、分析哲學與現象學之類話題的討論也逐步增多,核心的關切之一便是扎哈維與加拉格爾所說的“相互啟發”。從現象學家這邊來看,他們當然不可能反對基于實在論預設的科學研究結果,但會關注科學結論的現象學意義,甚至還會反過來試圖用現象學的視角分析科學實驗的設計是否足夠合理,是否有修正或改進的余地。這是他們與認知科學家、神經科學家合作的常見情境。同時,現象學家也會批判性地考察基于科學研究結果的哲學解釋,分析其相容性和對抗性,并借助其他哲學進路的洞見拓展現象學自身的結論甚至研究領域。
此外,這種應用性質的現象學工作也和基礎理論之間存在互動關系。《現象學的心靈》一書雖然談的都是“心靈”哲學,但這個概念的現象學意義決定了它所關聯的論域實質上就是整個現象學哲學的基礎與核心部分——意識、意向性、時間性、空間性、感知分析、交互主體性等等。從胡塞爾一貫主張的“工作哲學”角度來看,任何一個核心議題的處理都不可能是通過純然“思辨”或沉浸于術語海洋里就能解決的,即便是在最為艱澀的時間性分析當中也是一樣。比如,加拉格爾在此書以及別處(比如張浩軍教授翻譯的《現象學導論》)都闡述過使用神經現象學的實驗與分析結果探究時間性結構的例子。通過這種交叉研究,我們不僅能清楚地理解時間意識現象學理論在現實中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樣子,甚至還能反過來對不同的現象學理論進行鑒別,分析其合理與不合理之處,這對理解意識現象與現象學思想本身都具有顯著的意義。
最后想談一個翻譯方面的問題。羅志達教授是扎哈維的高足,無論從學術能力還是從對老師思想的理解上看,作為譯者都屬上選無疑。志達兄文筆曉暢干練,書中的繁難之處也舉重若輕,專業方面的處理自不待說。筆者并非想雞蛋里挑骨頭,因為相關細節對于熟知西文和漢譯情況的中國現象學家來說早已是常識,只不過想借此表明譯事中的某些難點。
原書里出現了許多處experience,志達兄據不同語境將之譯為“體驗”和“經驗”,并在第19頁上專門做了注予以簡釋。但不管怎樣,兩者在現象學上是不同的概念,一詞兩譯終是無奈之舉。不過這個歧義的根源不在漢譯,而在于西文內部。英語里的experience通常既用作德語Erlebnis(體驗)的譯名,又用作Erfahrung(經驗)的譯名,因此對德譯中來說并不困難的事情,經過英語再到中文反而會有歧義(盡管英語有時候也用encounter來翻譯Erfahrung)。當然,英語世界的現象學家有時候會特地加一個詞以示區分,亦即用lived experience來翻譯Erlebnis,但這又會導致有些中譯者忽視這一點,直接按英語字面意思翻譯成了“活生生的體驗”。另一個常見的類似情形是把lived body譯作“活生生的身體”,把法語le corps譯為“肉身”,其實兩者都是在現象學傳統中對德語Leib(身體)的翻譯,而不少中譯者未能做到名詞上的統一。當然,還有更麻煩的情況,就是英語文本中也缺少提示,只能根據上下文來推測experience到底指“體驗”還是“經驗”,但這又首先取決于譯者是否準確理解了兩個詞的實質差異。
在現象學上,特別是在胡塞爾那里,這兩個概念的指向是有明顯區別的。所謂“體驗”,可以指涉一切意識行為,但它是從意識活動必然具有的“親身經歷感”的角度來看的。因此,雖說這個概念在理論上包含了整個意識行為的兩部分——即對整個意識活動的親身經歷感與被意識到的對象性內容——但它始終側重于“經歷感”這個出發點,以至于很多時候就僅用來表達這個方面的內涵。“經驗”的基本意思則是指我在生活過程中與各種人、事、物的“遭遇”。這些遭遇當然是我在世界中生活的結果,而且它們也必然會進一步帶來各種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認知效應。就此而言,完整意義上的“經驗”總是包含了我在經歷了某些遭遇之后的理解和領會——不僅是對特定事物的領會,而且也必然在更根本的層次上蘊含了我對整個世界的某種領會和信念態度。在胡塞爾看來,現象學的“經驗”概念最終就是為了揭示我的經驗或意識行為中的“構造性”和“在世性”特征:一切經驗就其必然具有某種意義而言,必須被把握為我在世界之中生活的產物,是一種被構造起來的意識活動成就,因此只有在先驗現象學還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分析。
有趣的是,experience的雙重含義似乎正好反映了從胡塞爾到扎哈維的一條現象學運動的明線:現象學始于第一人稱的體驗分析,但它的整個領域卻包含了人的全部在世經驗——現象學所研究的正是最廣義上的一切意向性體驗的構造問題。處于意向關系兩端的心靈與世界并不是被偶然關聯起來的“東西”,而是共屬一體的場域,是一個“終極”意向性結構的兩面。
不過,即便一個訓練有素的現象學家能準確把握上述概念差異,理解它包含的全部復雜性,但在涉及翻譯時仍要面對作者本人在特定語境中的傾向并兼顧漢語里的表達習慣。這是非常困難的。概而言之,譯者的難題就是如何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兼顧所能想到的各種因素,選擇盡可能好的說法,并在保持一致和體現差異之間反復權衡。
另一方面,譯者的難題不該成為讀者的難題,讀者也不必受名相所限。不管是閱讀中文還是外文,在遇到字詞障礙時,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字符串”來看,與其糾纏于字面聯系,不如聚焦于背后的義理。就筆者自己的經驗而言,這種做法或可更好地把握思想自身的演變與固化、偏離與統一之間的辯證關系,不僅對于概念的理解來說是如此,推及整個哲學史甚至一般思想史來說,亦是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扎哈維與加拉格爾對于現象學傳統的“求同存異”式理解也有類似傾向,值得我們參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