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葛劍雄:童年生活中的江南“糞土”
李伯重教授《糞土與歷代王朝興衰的關系》一文中有關江南“糞土”的敘述勾起了我對童年生活的回憶,也可印證伯重兄所引的史料。
1945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今屬湖州市南潯區)寶善街,1956年夏遷居上海。因我幼時記憶力頗強,加上一個衰落中的市鎮沒有什么宏大題材,日常生活反能留下較深印象。

南潯古鎮
從近年發現的《南潯研究》(當時小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形成的社會調查資料)原稿得知,20世紀30年代鎮上已有幾處公共廁所,但到50年代初每家每戶還都使用馬桶,倒馬桶便成了家庭主婦或女傭的日常家務。不過,家里的女人不必親自倒馬桶,至多只要將馬桶拎到家門口,因為每家的馬桶早已由惜糞如金的農戶承包了。每天清晨,都會由固定的農婦或她家的大女孩將馬桶拎去,倒入她家的糞桶后再洗刷干凈,送回原處。如果主人不介意,也可不必將馬桶拎出,由農婦直接到房間取。但送回時都送在門口,還將蓋子斜放,開著一半,一則告訴主人馬桶已倒過,一則便于風吹干洗刷時弄濕的馬桶沿,免得主人使用時不舒服。到80年代我第一次在廣東的餐館用餐,見友人將茶壺蓋打開一半斜放在壺上,得知這是提醒服務員添水,不禁想起那時家門口斜放著蓋子的馬桶,差一點笑出聲來。?
也有講究的主婦嫌鄉下人洗得不干凈,會自己拎到河邊,用專用的馬桶刷子再刷洗一遍。這種刷子一尺多長,用竹子劈成細條扎成,南潯方言稱之為“馬桶甩(音hua)洗”。如果主婦抱怨,農婦會忙不迭地賠不是,保證第二天一定洗刷得更干凈,因為怕失去一個糞源。我家自然也備有馬桶甩洗,但母親用的次數不多。南潯人在指責別人或自己孩子滿口臟話時,會罵一句重話:“嘴巴要拿馬桶甩洗刷刷了。”
對農家來說,糞源就是肥源、財源,特別是承包馬桶,更是固定的日常糞源,必須確保。按慣例,四時八節,農戶都要給馬桶主人家送時鮮蔬菜和自制食品,過年前送得更多,一般有新米、糯米、雞蛋、雞、肉等。農戶自給自足,送的東西都是自己種的或自家地上長的,如有的農家有片竹子,就會送春筍、冬筍;有的農民會捕魚抓蝦,就送魚蝦。自制食品一般會有熏豆(毛豆煮熟后用炭火烘干)、風消(糯米飯攤在燒熱的鐵鍋上用鏟子壓成薄片烘干)、年糕、粽子、炒米粉等。禮物的多寡雖與農戶的能力及雙方的親疏程度有關,但主要還取決于糞源的數量和質量,人口多的人家不止一個馬桶,量大;成年男性多,馬桶中糞的含量高。以承包馬桶為基礎,雙方往往會建立更加密切的關系。農戶為鞏固糞源,防止他人爭奪,會盡力討好主人。主人也會有求于農戶,如家里有婚喪喜事要采購食品,到鄉下上墳時有個歇腳地,孩子要雇奶媽或寄養,臨時找個傭人或短工,出門搭個航船,都得找熟悉的鄉下人幫忙。而來家倒馬桶的人天天見面,聯系方便,又信得過,往往認了干親,相互以“干娘”“過房女兒”相稱,結成比一般親戚還密切的關系。
當地習俗,男人除了使用外不能接觸馬桶,否則于本人與家庭都不吉利,拎馬桶、倒馬桶、洗馬桶都是雙方女人的事。承包馬桶的農戶一般離鎮不遠,都用糞桶將收集到的糞便挑回去,集中在自家的糞缸中。大多是由女人將空糞桶挑到承包戶附近較隱蔽處,倒完馬桶后由家里男人來將糞擔挑走,也有女人自己挑回去的。有的農戶承包的馬桶多,或者路遠,會搭航船回家,將裝滿糞便的糞桶挑到船上,放在后梢。為了不招致鎮上人討厭,倒馬桶的人一般都起得很早,挑糞的人也盡量走偏僻的小路或弄堂。偶然見到直接將糞便裝在船艙里的糞船,那是運公共廁所或學校等單位里廁所的,當然也需要預先訂購。
不過到我離開南潯的前一二年,鎮上有了“清管所”(清潔管理所的簡稱),并且出現了由清管所工人推著的統一式樣的糞車,上門倒馬桶的農婦消失了,居民自己將馬桶倒入糞車或新建的公共廁所內。我父母在1954年就去上海謀生,我們姐弟雖還住在家里,卻是由外婆來照
料的,我已記不得來我家倒馬桶的人什么時候開始不來了。現在想來,這大概是農業合作化的結果,糞源歸集體了,農戶自然不能再個別承包倒馬桶。種田開始用“肥田粉”(化肥),糞肥獨秀的格局改變了。

馬桶
1956年我也到了上海,隨父母住在閘北棚戶區的一處小閣樓里。每天早上都會聽到馬桶車軋過彈硌路的聲音,大弄堂里會傳來“馬桶拎出來”的喊聲,母親會隨著鄰居將馬桶拎到糞車倒掉,然后在給水站(公用自來水龍頭)旁洗刷馬桶。有人在馬桶中放一些毛蚶殼以便刷得更干凈,于是傳來特別響亮的刷馬桶聲。1957年我家搬到共和新路141弄,住在弄堂底,馬桶車進不來,后來建的倒糞便站也在弄堂口,加上母親早上要上班,只能將倒馬桶包給一位大家稱為“大舅媽”的中年婦女,每月付費1元。一次母親與南潯的親戚談及,他們覺得不可思議,家里的馬桶給她倒,非但得不到好處,還要倒貼錢,“難道收糞的不給她好處?上海人真門檻精!”
在南潯時,親友和同學中沒有大戶人家,住房都不大,大多沒有“馬桶間”,馬桶就放在臥室一角或蚊帳后面。我們從小被教的規矩是,到別人家里去時不要喝茶,盡量不要用馬桶,特別是女孩子。只有過年可以例外,因為南潯過年待客時要上甜茶(放風消和糖)、咸茶(放熏豆、丁香蘿卜干和芝麻),不喝是失禮的。有時小孩喝不完,大人會幫他喝光。但到鄉下去就沒有這樣的限制,因為農家都歡迎使用家里的馬桶,送肥上門。不用說親友上門,就是路過的陌生人,無論男女老幼,只要說是“借你家解個手”,或“急煞了”,馬上會延至馬桶前。有的農婦還會熱情介紹:“這只馬桶剛剛刷得清清爽爽”“汰手水搭你放好了”。
草紙當然會放在馬桶旁。如果主人家正好有空,還會泡上茶留來客休息一會兒。如來客喝了茶,又及時轉化為小便,那就上上大吉,一定會更熱情招待。就是家中沒有人,只要門沒有關上,過路人也可以堂而皇之進屋使用馬桶,主人回來絕不會怪罪。
為了廣開糞源,鄉村的路旁不時可見掩埋著的大糞缸,缸口高于地面,缸緣鋪上一塊木板,供過路人蹲在上面方便。有的還在上面蓋上簡易的稻草頂,為使用者遮陽擋雨;木板前方橫一根竹木把手,以減輕使用者久蹲的疲勞,并便于結束后起立。但這類簡易廁所總不會全部封閉,大多全無遮擋,使用者在內急時也顧不得那么多,所以我們在鄉間行走時,不時從后面看到蹲客的半個屁股,或者見到撅起的屁股正在完成最后動作,早已見怪不怪。我們男孩小便時自然不愿站到糞缸上聞臭,隨便在路邊田頭找個地方。要是給農婦看見,一定立即制止,并熱情邀請:“小把戲,乖,到這里來撒!”或者說:“我這里有豆,撒好后拿一把吃吃。”如果有自己的孩子與我們在一起,必定招來怒罵:“個青頭硬鬼(音舉),笨得勿轉彎,還勿快點叫兩個小把戲撒在自己田里!”
路旁隨處可見的大糞缸固然是農家上好肥源,可換來滿倉糧食,但也給路人與鄉村本身帶來很大麻煩。一是臭氣熏天,因為糞缸都是敞開的,最多在上面蓋一層稻草。特別是夏天,在驕陽下,糞缸中水分與臭氣一起蒸騰,掩鼻而過也受不了。二是不安全,走夜路的人不小心跌入糞缸的事時有所聞。暴雨后糞水橫流,農民在河里洗糞桶,造成河水污染,而農民為節省柴草,夏天一般都喝生水,用冷水淘飯。糞缸上蒼蠅成堆,農民家中也滿桌滿灶。造成傳染病流傳,又得不到及時防治,常有農民不明不白“生瘟病”死掉。幼時常看到一群人抬著病人從鄉下趕往醫院,有時跟著去看熱鬧,不久就聽到哭聲震天,抬出來的已是一具尸體。
到上海后常在暑假回南潯,再到鄉下走走,見露天糞缸逐漸消失,代之以公共廁所。鎮上居民用上了自來水,有了集中處理糞便的水沖廁所,已有人家用抽水馬桶。盡管鎮上人家的馬桶還沿用了很久,但農戶承包倒馬桶從此成為歷史陳跡,只有我們這一代人還保留在記憶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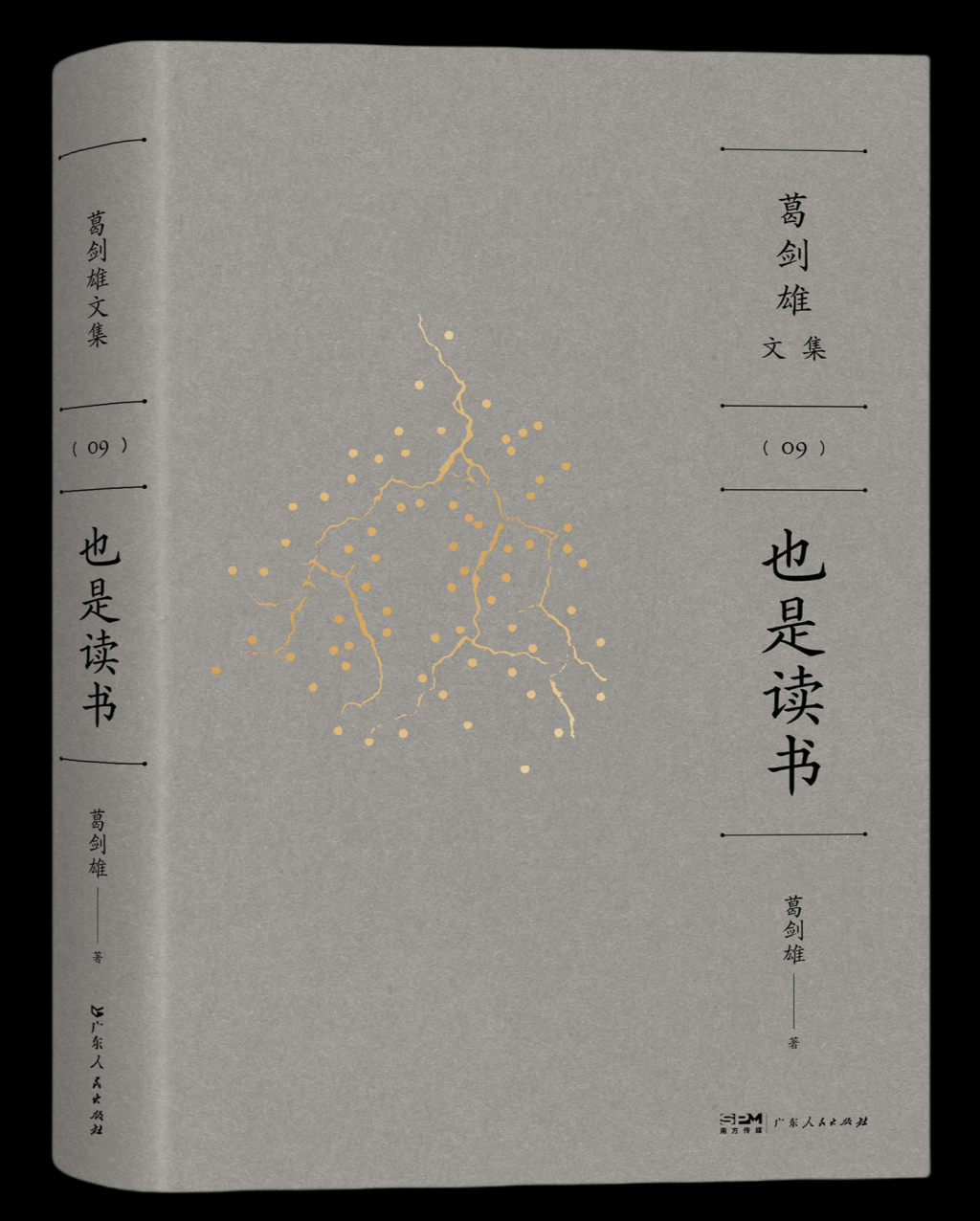
(本文摘自《也是讀書:葛劍雄文集第9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