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學2025丨浙大學者彭國翔談人文與AI:活生生的作為“人”的學者仍難被取代
【編者按】
在人工智能與人形機器人的一騎絕塵中,中國大學迎來2025。
2025年,注定要成為變革的年份。是以戰略敏捷贏得戰略主動,還是在延誤中錯失轉型機遇,中國大學踏上征途。
人工智能技術如何賦能學科建設?人工智能技術給創新人才培養帶來哪些啟示?澎湃新聞特推出“大學2025”專題,以深入探討人工智能時代的大學之變。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馬一浮書院兼任研究員彭國翔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AI或許可以協助研究者快速檢索已有研究,提供相關資料,但它尚無法替代學者在選題策劃與問題意識方面的獨立思考。在個性化的表達方面,AI仍然難以取代真正活生生的作為“人”的學者。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或者說大學文科教學,不只是培養學生做簡單的文案工作,還要培養學生的人文教養,包括人格的塑造。這恐怕就不是AI所能夠提供的了。
澎湃新聞近期策劃“大學2025”專題報道,聚焦“人工智能時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問題。作為人文學科的學者,我只能從自身的學科背景和專業訓練來講,所以我的題目就叫“人文與AI”。
具體來說,我想講兩個方面。一個是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與AI的問題;另一個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學科與AI的問題。當然,這兩個問題各自都涉及很多進一步的問題,我目前只能就現在想到的,略談幾點我的看法。
我歷來認為,學術研究是高校教師從事教學的根本。如果沒有在學術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包括不斷建立新知識,以及在此基礎上提煉新思想,我覺得是沒有辦法真正向學生講授新知與新思的。老師如果自己不做研究,向學生講什么呢?不可能日復一日只是講授一些陳舊的知識。因此,我要先談一下人文領域的學術研究與AI的關系問題。
首先,AI對人文學術研究的助益是顯而易見的。舉個例子,其實許多年前,就已有學者提出所謂“E考據時代”的概念。這里的“E”指的是“electronic”。我們知道,“考據”需要運用大量的文獻資料。以前有學者從事一項研究、寫一本書,一個人要查閱卷帙浩繁的資料,做很多的卡片。如今隨著數據化的發展,電子技術的發展,現在我們搜集資料、對資料進行分門別類的條件,比以前要好多了。所謂“E考據時代”,就是利用“數字化”或“數位化”——英文叫“digital”——的便利,去迅速檢索大量的資料。
無論是國內的DeepSeek,還是海外的ChatGPT,都具備這方面強大的功能。盡管有時需要辨別真偽,但它們可以把以前相關的資料,網上可以找到的數據,都提供給你。這對人文研究來說,至少在資料匯集方面,無疑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被譽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的嚴耕望先生,以勤奮治學著稱,他在治史過程中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整理史料、制作卡片,寫出了《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唐代交通圖考》《唐仆尚丞郎表》等以大量史料為基礎的堅實巨著。如果他能夠活到今天的話,相信數字化工具的運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他更快地解決至少是史料搜集方面的工作,從而為他節省更多的時間去從事其它的研究。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AI的限制。目前來看,它的限制至少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是在選題方面。在人文研究中,選題至關重要,決定了研究的學術價值。AI或許可以協助研究者快速檢索已有研究,提供相關資料,但它尚無法替代學者在選題策劃與問題意識方面的獨立思考。哪些題目有價值?哪些題目還沒有被研究過?哪些問題的探討還有待深入?AI能夠提供給你嗎?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問題。
其次,是在學術寫作方面。與理、工、農、醫類的學術寫作不同,人文領域的學術作品,往往更承載著作者個人的風格。我們閱讀人文領域不同作者的作品,往往能夠透過文字看到作者這個人。作者的品味、文氣、語勢乃至個性,常常都會在其文字中得到體現。
關于這一點,我曾親身經歷一則趣事。有一次,我評審一篇博士論文,當然是雙向匿名的,我只知道作者所在的大學,并不知其人是誰;作者也不知道這份評審意見出自何人之手。論文作者收到意見后,想請朋友幫忙看看,如何根據審查人的意見修改,結果找到了我曾經的一位學生。這位學生現在是學術期刊的編輯,他看后主動向我詢問:“彭老師這是不是您寫的意見?”我十分驚訝,問他如何推測是我寫的。他回答說:“我當時一看,就覺得太像您的風格了。”這就說明,在人文學術寫作中,有很強的個人色彩在里面。但如果是AI或者各種各樣的工具寫出來的文字,也許這種個人的東西,包括品味、風格、文氣、語勢,可能就都會被磨平了。
曾經有朋友嘗試用DeepSeek生成詩歌,覺得很好,甚至嘗試告訴它,仿照某位詩人的文風創作一首詩,它差不多也可以做到。初看之下,這種AI生成的仿作似乎結構工整、辭藻得體,但是仔細品味,與作者本人的還是不一樣的。這就表明,在個性化的表達方面,AI仍然難以取代真正活生生的作為“人”的學者。
我們知道,以前有一種文體叫“館閣體”(指因科舉制度而形成的考場通用字體),四平八穩。這種“館閣體”,也許AI可以做到。但是,人文學術的寫作不僅關乎內容,由于不同作者作為“人”的差異,也自然會在風格、品味、文氣和語勢方面表現得各有不同。如果人文領域的研究者使用AI進行寫作,便可能導致文本的個性化表達消失,最終形成一種類似于“館閣體”的標準化學術表達,使得文章雖工整嚴謹,卻缺乏學者個人獨特的風格和思想烙印。
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學科與AI的問題,或者說,是如何看待AI在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教學當中,學生利用AI,可以快速搜集到很多資料,如果寫個簡單的文案、新聞稿、宣傳稿,AI可以提供參考模板。但是,高等教育的人文教育,或者說大學文科教學,不是培養學生只做簡單的文案工作,而是還要培養學生的人文教養,包括人格的塑造。這個恐怕就不是AI所能夠提供的了。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恐怕更為嚴重。如果AI可以幫助學生寫文章,那么,就不只是會出現前面講的千篇一律、缺乏個性和風格的“館閣體”的問題,甚至可能引發誠信問題。誠信問題不僅是學術的,更是人格的問題。試想,教師讓學生寫文章,學生直接讓AI生成。這樣的文章質量如何?能否反映學生真實的知識儲備和思維水平,是可想而知的。如今,這樣的情況已經不乏其例。而這就不僅是AI的限制,甚至可以說是其害處了。對于學生的人文教養來說,這顯然絕不是好事。這不僅是人文教育存在的問題,也是整個高等教育界需要加以警惕和應對的。
因此,對于大學的人文教育來說,我們從事教學的時候就要考慮:如何讓學生一方面能夠充分利用AI的便利;另一方面又要充分避免它的限制特別是壞處。
最后我要說一點,當我們討論“人文與AI”時,似乎已默認了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然而,這一前提本身值得進一步思考。這里有一個問題,什么叫“人工智能”?我們如何界定AI的本質?對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說按照前面講的,那基本上還是把AI理解為一種便利的工具。然而,對于AI的理解,恐怕不止于此。現在有很多擔心人工智能將來會控制人類的討論,那樣的一種人工智能,就不只是一種便利的工具了。這里又涉及兩個問題。首先,它是不是可以有自主意識?有了自主意識之后,它就不見得完全聽你的,就不只是一個你可以利用的工具了。我們前面講的那些,都是基于把AI當成工具。即使它很高級、很發達,也是一個可以聽命于我們的工具,是為人類服務的。但是,如果我們講的人工智能不只是那樣一個東西,而是有它自主的意識,那么,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AI不只是有自主意識,還有自己的情感、意志,那么這個AI跟人類其實就差不太多了。我曾經將這種AI稱為“類人類”。這種AI跟人類相處的話,那就不只是高等教育的問題了。整個人類如何與之共生并存,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目前這個問題也有討論,我以前也寫過文章,“人工智能最終一定是人類的威脅嗎——一個儒家的視角”(《道德與文明》2020年第5期),就是從儒學的角度來看待這種人工智能問題。
如果是這樣一種意義上的人工智能,不僅是工具,更具有自己的意識甚至情感和意志,那么,這個人工智能就不是我們前面講的了。現在我們各方面、各領域都密切關注人工智能,這當然是好事。但首先得理解,我們討論的人工智能是在什么意義上來說的。
總之,前面討論的兩個問題,都還只是順著目前媒體和大眾的理解,把人工智能當作一個可以為我們提供便利的工具。這種意義上的人工智能,基本上可以在人類的掌控范圍之內。然而,如果人工智能是一個有自主意識,甚至也有情感和意志的存在,那么,這個意義上的人工智能時代是否已經到來?恐怕還成問題。而到來之后,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全新的。這一點雖然超出了我們今天所談的話題,但因為十分重要,所以我最后必須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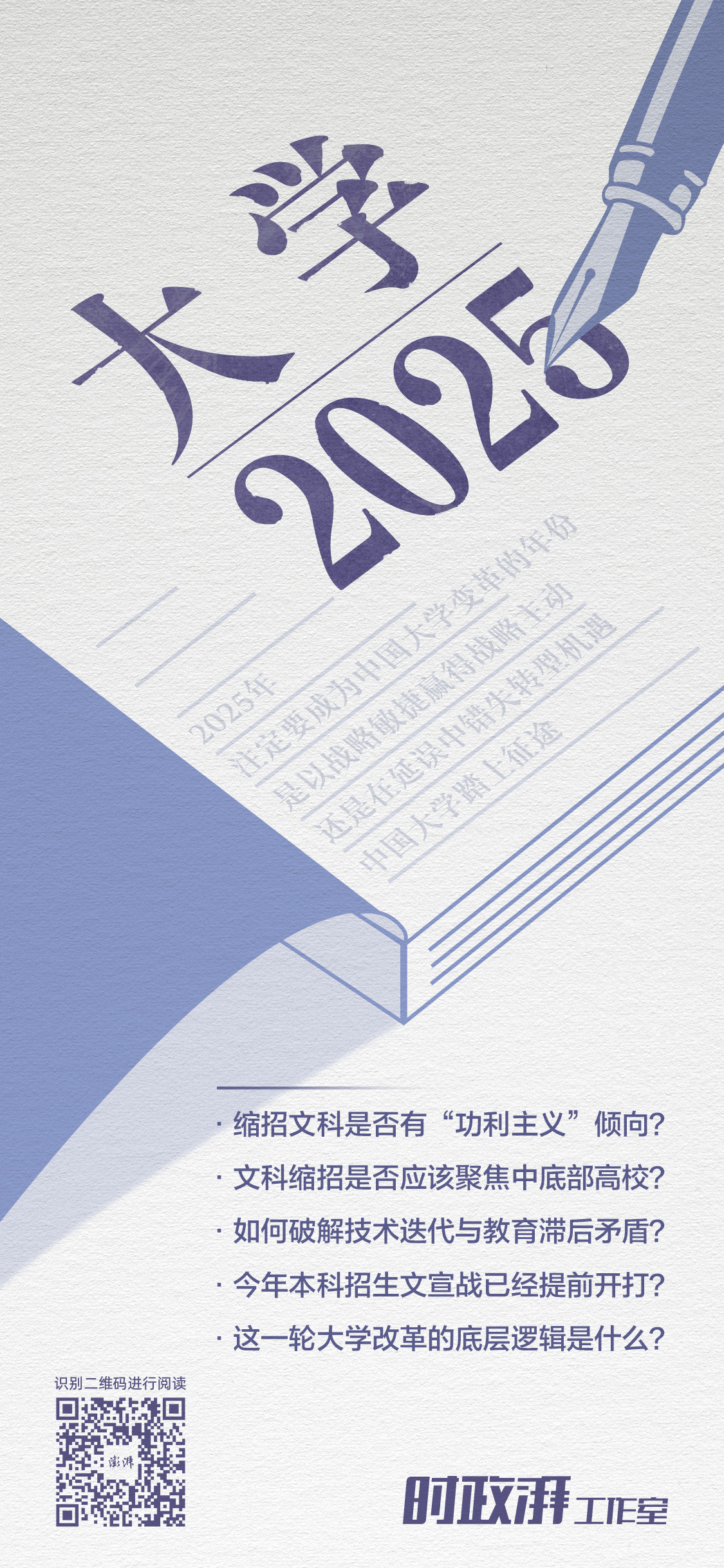
設計:祝碧晨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