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詹丹|亟待修訂、更新語文學科的《教師教學用書》
《教師教學用書》幾乎是基礎教育界每一位教師開展課堂教學的重要參考書。近年來,筆者因為撰寫《統編語文教材與文本解讀》的系列論著,翻遍了語文學科各年段與教科書配套的《教師教學用書》,在獲得不少啟發的同時,也對其中出現的諸多解讀失誤問題甚為擔慮。即使有些失誤在重印時得到了修訂,但如果新教材篇目調整不大的話,教師大多沒有自覺意識去使用修訂了的《教師教學用書》,于是那些存在的問題,在教學實際中依然得不到及時糾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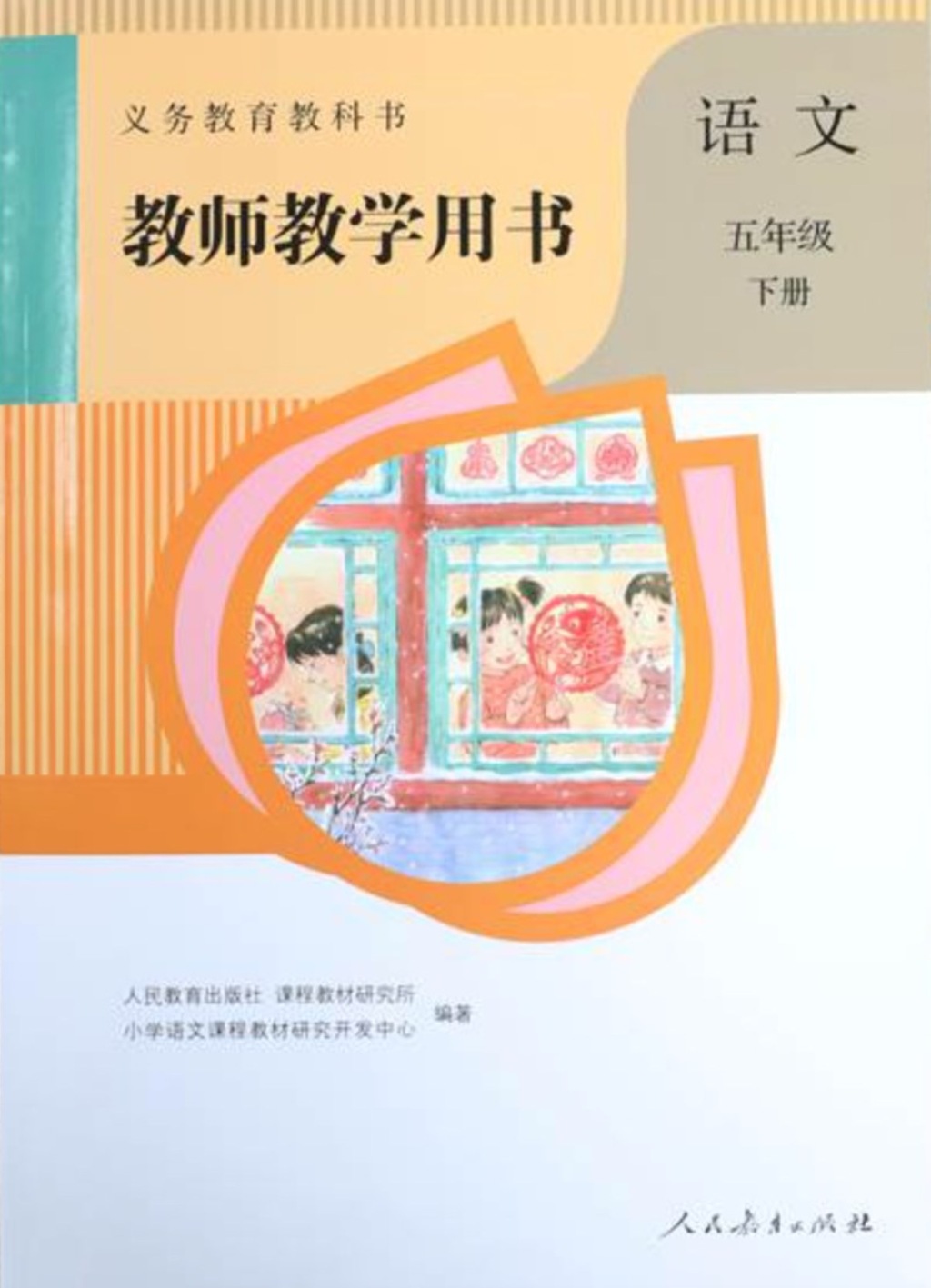
《教師教學用書》,2019年12月版
對于《教師教學用書》解讀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筆者撰寫的《統編語文教材與文本解讀》“小學卷”“初中卷”和“高中卷”都有較為深入的分析,為引起一線語文教師對這一問題的重視,以免以訛傳訛誤人子弟,這里特撰文予以強調。根據語文學科涉及的語法、修辭和邏輯三個方面各舉一例加以說明。
先看語法問題。
《教師教學用書》的有些編寫者,似乎對長句和短句的理解比較混亂,草率落筆,從而帶來解讀的誤導。比如關于散文家吳伯蕭的《燈籠》一文,對于其語言特點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但這個判斷又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分析道:
多是短句,很少有長句,如“歲梢寒夜,玩火玩燈,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坡野里想起跳跳的磷火,村邊社戲臺下想起鬧嚷嚷的觀眾,花生籃,冰糖葫蘆;臺上的小丑,花臉,《司馬懿探山》”等,都包含了許多三四字的短句。散文的語言表達與情感抒發息息相關,短句多,一方面顯出語言的簡凈,另一方面還表明抒情的節制、含蓄。但是簡潔不等于簡單,課文中的諸多短句都是值得吟味的,朗讀起來既有語言聲韻之美,又有深厚的意味和情味。
細究起來,《教師教學用書》判斷《燈籠》一文短句多,長句少所舉的例子,主要集中于課文的第1、第2自然段,而整篇課文有12個自然段,每一段中的句子長短形態與其他段落之間,并不構成相似的均質分布的樣態。就整篇來看,每段語句的構成,是根據內容表現的需要,寫成長短不一的句子。而從通常意義上說,因為篇章的開頭部分和主體部分,有著概括和展開的差異,所以,開頭部分句子的長短特征,往往并不能說明整篇的語言特征,甚至顯示出相反性,也是非常可能的。
“多是短句,很少用長句”這一判斷的錯誤還不僅僅在于用開頭部分的例子涵蓋了全篇,關鍵是,分析者自身并不清楚語法意義上的關于短句和長句的定義,所以,其舉出的所謂“短句”,大多不是句子,不過是一個長句中的短語成分而已。可以說,寫《教師教學用書》的人正好把話給說反了。比如其第1段舉出的“歲梢寒夜,玩火玩燈,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這個例句,其中,前面相對比較短的詞語“歲梢寒夜,玩火玩燈,除夕燃滴滴金,放焰火”,都是作為一個長句中的短語成分,來充當后面“是”一字的主語的。即便退一步說,組成主語的那些短語算是他所謂的“短句”,也不是為了表明“抒情的節制、含蓄”,恰是為了表明其抒情的直白,是作家要一口氣都把這些內容講出來,以表明孩子對這些活動的奔赴、興高采烈的喜歡心情、那種向往的并無例外。總之,《教師教學用書》有關《燈籠》語言特點的這段分析,可以說每一層意思都說錯、說反了。
再舉一個對修辭分析失誤的例子。
初中語文教材收入魯迅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結尾是:
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教師教學用書》對這個結尾的解讀是:
“狀元宰相”指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客及其御用文人。“地底下”指當時處于地下斗爭狀態的群眾革命力量。這句話是說,中國人是否有自信力,不要看那些反動文人發表出來的文章,而要去看那些真正的堪稱中國脊梁的人的所作所為。
如果說,《教師教學用書》以為“狀元宰相”直接指“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御用文人”還勉強可通(筆者在“可通”前加“勉強”,是因為魯迅這里其實用了借代手法,來指代自古以來的一切正統者,當然也包括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御用文人,出于現實針對性的考慮,“教師用書”這么說也可以,但也不應忽視其對自古以來的涵蓋性),那么認為“地底下”指“當時處于地下斗爭狀態的革命群眾”,把“地底下”轉換成“地下斗爭狀態”,顯然就變得機械和教條了,撰寫者大概是《潛伏》一類的諜戰片看多了,才會有這種近乎荒唐的分析。這樣的理解,已經抽離了魯迅筆下的具體語境,抽離了魯迅提及的與“公開的文字”建構出的一組對應的本質關系,即與“公開的文字”相呼應 ,與之相對的“地底下”主要是指沒有形諸文字,或者起碼是不見于正統的官方記錄的文字的那部分人和他們的行為。
最后我們來看邏輯方面的問題。
教材中收入的臧克家的《說和做——記聞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主要從聞一多的古典學者和民主戰士(臧克家所謂的“革命家”)兩方面,寫出了他的踏實品格和大無畏革命精神。而教材為引導學生整體把握課文結合和內容,設計了如下的思考題:
聞一多作為學者的“說”和“做”,與作為民主戰士的“說”和“做”有哪些不同?彼此有無關聯?試根據課文內容做簡要分析。
對此,《教師教學用書》給出的參考答案是:
作為學者的聞一多潛心學術,是“做了再說,做了不說”;作為民主戰士的聞一多敢于為人民講話,對敵人無所畏懼,是“說了就做”。這反映了聞一多對社會認識的變化,以及對不同道路的選擇。他的“說”和“做”相互貫通,正是他作為一名卓越的學者、偉大的治國者、大勇的志士的體現。
對于給出這樣的參考答案,就是從基本的答題要求來說也是不符合的。因為題目要求的是分析,而答案文字給出的主要內容就是信息篩選和梳理。如果把題目要求的“不同”和“關聯”從邏輯思維要求的概念界定角度來展開分析,就能說得明白一點。
從聞一多個人角度看,他作為學者的“做了再說,做了不說”,其實是傳統文人“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踏實為人的體現,其中的“說”,或多或少有一種標榜、夸耀、夸夸其談的意味。而作為民主戰士的“說了”,以及“說了就做”,跟作為學者的夸夸其談的“說”,已經不是同一個概念,而是一種鮮明的政治立場的表態。不對這基本概念予以辨析區分,談所謂的“不同”,只能是停留于文本表面的簡單梳理。此外,從社會交往角度看,作為學者的“做了不說”,就是固守在書齋里,默默工作而不向他人去夸耀。而作為民主戰士的“說了就做”,是書齋轉向會場、廣場,著力向他人去言說、去勸說。這樣,“說和做”的概念在聞一多前后兩個身份轉換中,也發生了意義的翻轉。當作為學者的他在開展學術研究而“做”時,他其實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的“說”,而當他作為民主戰士去向廣大民眾“說”時,就具有了鼓動、組織民眾起來反抗的實踐意義,“說”反而成了“做”。那么,前后的關聯性又在哪里呢?《教師教學用書》提到的所謂貫通,是用“卓越”“偉大”以及“大勇”這些概念來呼應的,其實在筆者看來這些只是正確的廢話。這里貫通的關鍵是,當他作為學者來進行“做了不說”的研究時,他是從文化層面“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臧克家文章中的文字),這是一種文化理論的革命者,而當他作為民主戰士“說了就做”時,就成為社會實踐的革命者,這樣,從文化理論到社會實踐,完成了從傳統優秀文化向革命文化繼承與開拓的轉型,其革命性,則相互貫通。在這里,作品所體現的文化繼承和發展關系,是需要通過我們結合文本,對標題的“說”和“做”這一對核心概念進行仔細辨析,才能有所領悟。
走筆至此,想起數十年前,筆者剛入職嘉定實驗中學,把《教師教學用書》(當時名為《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奉為圭臬,被一位帶教的老教師大加嘲諷,說他從來不用“教參書”,最多也是把它作為反面教材來使用。時至今日,我雖然也確實看到了《教師教學用書》的種種不足(盡管我的“看到”未必正確),但也不會像那位老教師那樣偏激地來全盤否定,其對語文教師實際教學所起的積極的輔助作用,還是有目共睹的。對于編者來說,廣泛聽取使用者的意見來及時修訂,而教師又能及時替換修訂了的版本,并且在使用時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判斷,也就可以了。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