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紀錄片評論|徐沐恩:《迪克·約翰遜的去世》:死亡演練與紀錄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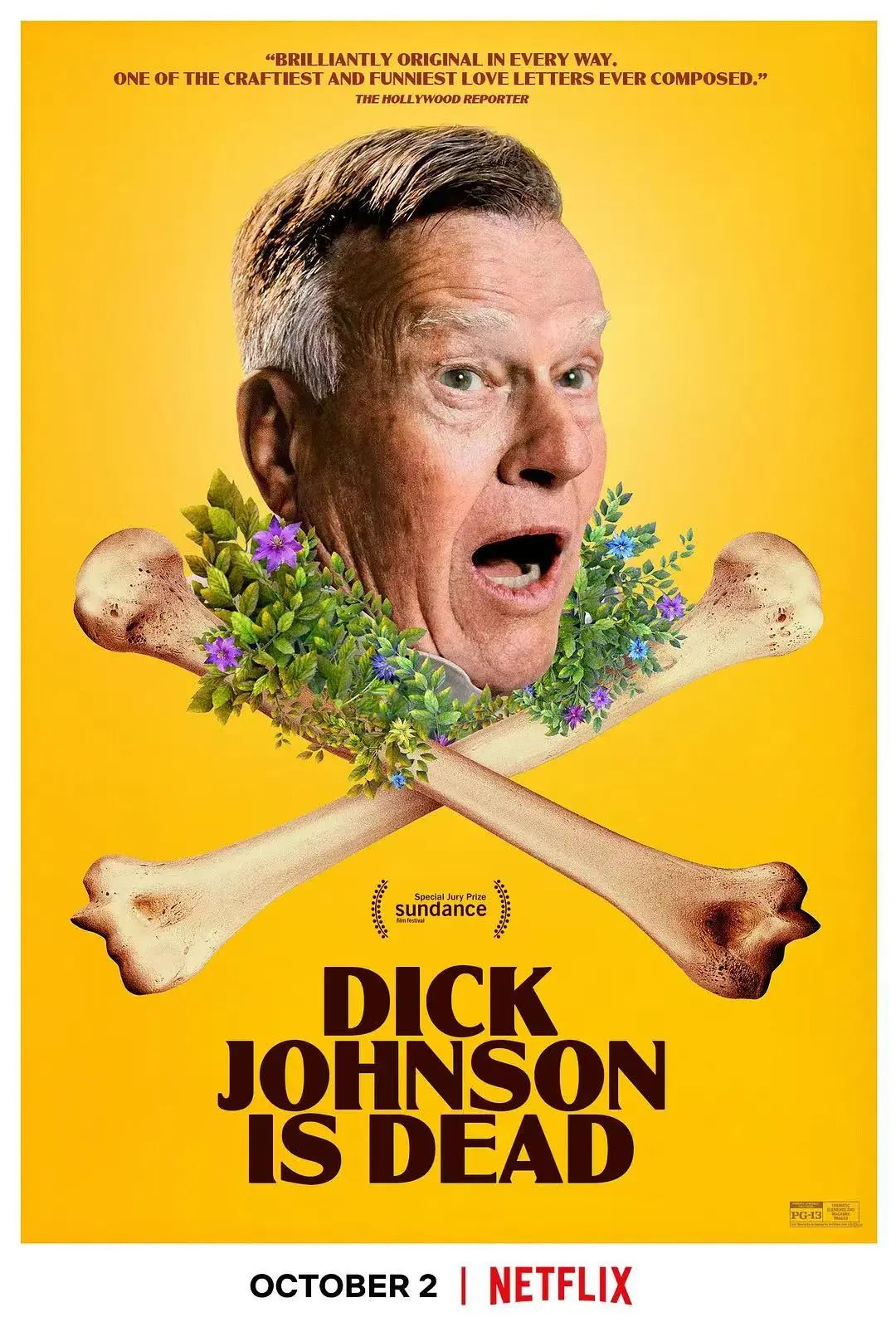
《迪克·約翰遜的去世》紀錄片海報(圖片源自互聯網)
“Just the idea that I might ever lose this man is too much to bear. He’s my dad.”
——Dick Johnson Is Dead(2020)
影片以跌倒的危險開始。年邁的外公推著孩子們在谷倉里蕩秋千,孩子們一邊尖叫一邊笑著說:“太高了,差點就死了!”孩子們的母親在攝像機后出聲提醒父親:“爸爸,麥稈很滑,小心些!”老人嘴里答應著,卻還是不小心“撲通”一下滑倒。他仰面躺在地上大笑著問驚呼著的女兒:“怎么樣,你拍到了嗎?我一直想出演電影呢!”
這是2020年網飛紀錄片《迪克·約翰遜的去世(Dick Johnson Is Dead)》的第一個片段。年邁的老人名叫迪克·約翰遜,是一位86歲的退休心理醫生,他的女兒是克斯汀·約翰遜(Kirsten Johnson),也是本片的導演和拍攝者。在這個場景的結尾部分,克斯汀冷靜的聲音作為旁白出現:“光是我可能會失去他這一點,就令我難以承受,他是我的爸爸。...但現在時間快到了,他正邁向死亡,而我們無法接受。...我建議我們可以拍一部關于他臨終的電影,他答應了。”在人生正不可逆轉地走向墜落之時,迪克老人和女兒克斯汀決定通過電影來留住它。而《迪克·約翰遜的去世》就是他們在攝制這部并不存在電影過程中的“幕后花絮”。
1
我們到哪里去?“死亡”的記錄母題
以死亡或者疾病作為核心議題的紀錄片不在少數。從諱莫如深的宗教禁忌中被解放,“死亡”逐漸成為生活在流離精神之中的現代人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如何用影像表現死亡?如何用影像藝術在此話題上展現出思考力和先鋒性的一面?真實的特性給紀錄片這種影像形式帶來探討社會議題的天然優勢,在生死母題上更是如此。
大多數涉及死亡議題的紀錄片在整體的表現手法上都具有相似性,具體而言,是以一種陪伴的狀態等待故事的自然發生,并用鏡頭記錄人們在面對死亡時所展現的情感和態度,用細膩哀傷的生活點滴直擊觀眾的心靈。例如紀錄片《人世間》第一季第四集的主題為“告別”,講述了在上海靜安一個臨終關懷區中的故事。病患和家屬、病友的告別感人至深,也將臨終關懷的話題推至大眾眼前;2016年BBC紀錄片《我生命前的最后一個夏天》跟拍了五個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絕癥病人。在死亡悲傷的底色上,紀錄片探討了在死亡面前親密關系、家庭朋友、與病痛共處等等話題,觀眾仿佛與臨終之際的被攝者們一同盤腿圍坐,傾聽他們與死亡短刀相接的故事,同時也思考自己生命的輕重。
然而《迪克·約翰遜的去世》并未沿用這種已經較為成熟的敘事,導演克斯汀似乎更想送給父親一份更特別的“告別禮物”。極盡渲染悲傷是表現死亡的唯一手段嗎?探討死亡一定要等待死亡真正發生嗎?紀錄片的真實性一定建立在故事的自然流動之上嗎?她的答案可能都是否定的。在影片約五分之一處,導演插入了一小段母親臨終前的畫面。視頻中患有阿爾茲海默的母親已經記不得女兒的名字,導演作為旁白講述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我拍攝紀錄片已經30年了,但是關于媽媽的影片幾乎就只有這一段。”這是等待的結果,即便是一個職業的攝影師也來不及抓住至親更多的瞬間。在死亡面前,人們總感到留給他們告別的時間太少,遺憾又太多,母親的去世已經讓父女二人經歷過一次切膚之痛。看著父親每況愈下的身體狀況,克斯汀決心不再寄希望于機會的降臨,而是在必然的痛苦到來之前,與父親共同做一次“臨終排演”。
許多人也許曾想過生后的世界會是怎樣——自己會以何種方式死掉,在葬禮上會發生什么,賓客會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離開后家人朋友的生活會有何變化...這些,迪克老人在拍攝過程中通通都經歷了一遍。克斯汀為父親設置了五個“假死復活”的場景,包括走在路上被從天而降的電視機砸中、從老房子的樓梯上摔死、車禍身亡、心臟病搶救無效去世、從建筑工地路過被建材砸死。每一場“意外死亡”的發生都未曾與觀眾打好招呼,但是在觀眾還處于震驚的余韻中時,導演又立馬用幕后鏡頭或是“穿幫”讓觀眾“出戲”。每次意外發生之時,觀眾明知大概率又是導演的“玩笑”卻忍不住為他狠狠揪心。
頻頻掉入導演“圈套”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我們太愛迪克爺爺了。無論是否有意,克斯汀用愛的鏡頭將父親和他晚年生活最溫情、可愛的一面記錄了下來。迪克冷不丁冒出的金句、做出的動作時而令人捧腹,時而又令人熱淚盈眶:他要搬出老房子的時候對女兒說:“我可以用這房子,交換跟你一起住的機會,毫無疑問!”;他去見大學暗戀的人時開玩笑:“你的衣服很漂亮但是你不穿更漂亮。”那位奶奶也幽默地說:“你不知道這些年都下垂了。”;他吃冰淇淋的時候感嘆:“巧克力冰淇淋真好,人生真好!”;女兒要出差把他留在家里的時候他說:“你注意安全好嗎?你還得回來照顧我這小老弟。”。他是記錄者的父親,也好像是我們的父親,他對女兒傾注信任與愛,他熱愛生活,時常又有些小幽默,好像死亡的陰霾不曾光顧他的生活。
然而,無論是看上去無厘頭的“假死復活”場景,還是老人被溫情灌注的表面形象,隱藏在這些背后的,是搖搖欲墜的晚年生活,還有隨處可見的隱憂。導演有意將快樂、溫暖的部分用鏡頭影像大肆表達,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卻將悲傷藏在自己冷靜克制的旁白之中。在影片中,導演獨自坐在家中狹小的衣帽間內,拿著手機對著一個攝像頭,用極度沉穩的語氣講述父親的故事。好像是在閱讀別人的小說,或者念誦一篇悼詞。迪克爺爺看向車窗外的時候,旁白講述了他因為記憶力越來越差,給患者開錯處方、重復看診的故事(他以前的職業是心理醫生);迪克爺爺坐在床上的身影打在模糊的窗戶上,旁白說,他時常會在半夜起床,把客廳當做候診室,穿戴整齊地等待病人,也會在凌晨3點出門趕火車,因為他以為自己在執行秘密任務... ...
這是我們熟悉的有關于死亡或者關于阿爾茲海默的故事,但這些卻被導演小心地藏在了影像之外。與老友、家人相聚、品嘗美食、翻閱美好的回憶....導演告訴我們,關于死亡并不只有“以哀寫哀”和“以樂襯哀”兩種寫法,還可以當作一份能隨時翻看的家庭影像。如果還不夠,那么最好可以直面它,談談對它的感受,恐懼、疼痛或者是遺憾,然后相擁哭泣,獲得下一次與它正面交鋒的勇氣。
2
真實到哪里去?暴露與實驗
縱觀克斯汀的作品序列,無論是令人震撼的導演處女作《持攝影機的人》,還是參與攝影、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第四公民》,冷靜自持、客觀記錄是她的一貫風格。但是在這部對她而言極為特殊的作品中,克斯汀卻一反常態,將自己、將整個攝制團隊、將對環節的安排深深嵌入整部作品的可見范圍之中。
也許一開始觀眾會認為這是某一部電影的幕后拍攝紀錄片,但其實并沒有一部名叫“迪克·約翰遜的N種死法”的劇情片,整部紀錄片實際上是將“迪克·約翰遜假死”這件事插入到對父親晚年生活的凝視之中,而這個凝視的視角來源于女兒克斯汀——理應站在攝像機后沉默的導演被迫、同樣主動地暴露在觀眾面前。影片的很大一部分由克斯汀的手持影像組成,她像一雙游移又不忍的眼睛觀察著父親的生活,盡管在畫外,但是并不客觀。她常常在和父親的對話中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曾經患心臟病)這件事!”;也不回避情感的流露——她和父親共同回憶母親的時候忍不住哭了,她把攝影機放在房間的地上長時間對準地毯,走過去在鏡頭之外擁抱父親。我們跟隨搖晃的、隨意的、自私的鏡頭無限接近這個家庭,但卻被擋在了最有限的視角之外。導演與觀眾分享那些可說的、可被記錄的部分,但拒絕分享脆弱、以及愛的痛苦。
除去導演雙重身份所帶來的暴露,影片從一開始就提示觀眾,整部紀錄片的內容是:在征得父親同意的情況下,以多種方式上演父親的死亡。而這種“上演死亡”的方式,拉開了有關電影制作、拍攝與特技工作的帷幕。在傳統觀念中,劇情片和紀錄片中對于死亡的展現形式截然相反,劇情片追求怎樣讓死亡逼真,而紀錄片追求記錄真正的死亡。在一次街景拍攝的過程中,一名替身演員代替了迪克狠狠地摔在地上。迪克同情的對克斯汀說:“你讓那個可憐的家伙摔倒了,而不是我。”逼真的幻覺背后是表演者和工作人員所付出的艱苦體力勞動,甚至為了表現疼痛而冒險。
如果將“假死+幕后”的公式——在每一次讓觀眾受到迪克“突然死亡”的驚嚇后立刻展現帶有安撫意味的幕后制作過程——看作一種輕微的試探又縮回,那么導演對真實性的挑戰并非如此簡單。這部影片的大部分內容都貫穿了迪克對于死后天堂的愿景,導演和團隊將其實現為一場攝影棚拍攝的音樂盛宴:載歌載舞的歡樂場景,整個畫面呈現明亮而柔和的粉色和藍色;迪克是天堂的晚宴嘉賓之一,周圍的演員用面具表示身份:已故的愛妻、李小龍甚至還有耶穌。在傳統紀錄片中很難看到的強烈的、融合的風格化視覺效果,在這些場景中被大肆使用。好像是為了迎合迪克轉速減緩的大腦,“天堂”里的一切都是慢動作的,亮片、羽毛和氣泡緩緩掉落,迪克也安全地、慢慢地仰面倒下。
這樣的場景當然不會在現實中真的出現,但是這樣的愿景卻又真實存在。在阿爾茲海默患者的腦海中,真實與虛幻的界線逐漸模糊。在影片后期,迪克進入了以萬圣節為主題布景的舞臺劇中,他重演了自己在現實中的困惑:害怕親人找不到自己、害怕被丟棄、害怕孤獨、害怕離去......然后天堂的愿景突然刺穿了幽暗的古堡,代表安全與穩定的光芒再次綻放在畫面中。克斯汀在接受采訪時說,天堂場景是最后拍攝的場景之一,由于癡呆癥,她的父親在三天中經常陷入重復,盡管這些循環可以被瞬間的微笑或他意識的燦爛光芒所照亮(Mayer, 2022)。是什么照亮了他?我們很難得知。但是影片想要表達、融合的強烈意愿、想要對傳統真實性的發問,又未嘗不是一種對不可見真實的接近呢。
3
紀錄片到那里去?從“治愈”到“關懷”
除了天堂、亮片、耶穌、誘發心臟病的巧克力蛋糕,還有一個重復性的關鍵象征在影片中反復出現——一把黑色的皮革躺椅。它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現是在西雅圖的咨詢辦公室里,這里是迪克當了十幾年精神科醫生的地方。這把椅子是迪克搬去女兒公寓到達的第一件物品,也被帶到了的拍攝現場,在不同的場景中圈出了一個舒適、熟悉的、屬于迪克的空間:“天堂”里的迪克闔眼躺在躺椅上,“耶穌”為他的雙腳倒上圣水治愈丑陋的腳趾;攝影棚里的喧嘩吵鬧,迪克躺在躺椅上很快就打起了鼾。
影片中唯一沒有被立即解釋的、混合特效的畫面同樣與這把椅子有關:迪克安穩地躺在上面,躺椅抬著他緩緩漂浮起來離開地面,平穩地上升最后浮出畫面。亨利·馬蒂斯在《畫家筆記》中說:“我夢想的是一種平衡、純潔和寧靜的藝術,沒有令人不安或沮喪的主題,這種藝術可能適合每個腦力勞動者,例如商人和文學家。對心靈產生舒緩、平靜的影響,就像一把好的扶手椅,可以緩解身體疲勞。”死亡、癡呆、家庭破裂,當然是令人不安或沮喪的主題,但是這部紀錄片仿佛找到了一種處于失衡下的寧靜狀態。沉重的題材隨著懸浮的扶手椅一同變得輕盈,朝向死亡的墜落反向飛往天堂——如果我們能夠為沉重的衰落或疾病騰出空間,減緩下降的速度,而是斜倚著、輕柔地進入必要的照護和舒適之中,那會怎樣?
“重視照護過程”的暗線由此浮出水面。2020年這部紀錄片上映之時,世界正處于疫病流行嚴峻時期,老年人及其照護者又是社會中及其容易被忽略的群體。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的文化中,護理工作者高度女性化和被貶低的現狀是相似的,而他們也是克斯汀導演經常關注的人群。比如在《攝影師》中,她拍攝了助產士讓孩子起死回生的場景、祖母烘焙的場景、以及一個提供墮胎的服務者傾聽的場景。與傳統拍攝照護者的方式不同,《迪克·約翰遜已死》并沒有過度著墨于照護者對于被照護者實施的具體勞動(比如洗澡穿衣、進食如廁或者處理危機),反而在一些對話中重構照護者與被照護者的關系——并非僅僅是施惠與受惠,而是一種關愛的傳遞。
迪克老人首先自己是一位總在照護病患的醫生,且他在妻子生前無疑承擔了主要照護者的角色;在電影的開頭,我們看到迪克與一個前來幫忙清理辦公室的男士交談,他們談論了男人在十幾歲時失去父親的事情;在后半部分,女兒克斯汀以攝影機視角與前來照護父親的女士談話,聽她講述自己照護很多癡呆病患的經歷——影片不斷暗示著照護人員之間、照護者和被照護者的鏡像式對話,形式上平等的交談傳達出一種雙向照護的理念,且特別關注到了我們所忽視的“照護者被照護”的場景。
而紀錄片制作同樣被賦予這一層含義。“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和“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兩組關系之間存在隱秘的相似性,都暗示著一種權力不對等的、付出與得到的關系。但在影片的最后一個鏡頭中,電影制作也被定位為關愛勞動的繼承。導演克斯汀站在壁櫥中講完最后一句畫外音“我只知道迪克·約翰遜已經死了”,然后她打開壁櫥的門,她的父親迪克在門外愉快地傾聽并笑著與她相擁。迪克照護了她的照護,也同樣照護了鏡頭外的我們——在我們本以為死亡的墜落終于跟隨著影片的結束要到來之際,影片像棉被一樣穩穩接住了我們的不安。這本身就是一種關懷行為的傳遞。
再次回到對于影片表現形式的探討。從一些有關字幕或者旁白的小“伎倆”,在到用“制造假死事件”對于紀錄片“真實性”做出挑戰,導演強烈的實驗意愿貫穿始終。但是她并非為了實驗而實驗,從傳統的旁觀與詮釋出走的原因,也許是她不再滿足于記錄和理解,而是想要尋找能夠解決生活深層問題的工具——在紀錄片制作過程中,女兒留下了父親的影像,免于重演在母親身上發生了遺憾;父女二人相互交談接近,對于對方的生活從未如此了解和參與其中;他們策劃“死亡”,用一種可知的破碎去推演與適應不可知的恐懼;他們舉行“葬禮”,與親朋共享一個生命作為主角的最后一個儀式。這一切的發生都無比刻意,但是又無比接近現實中人們的真實渴求。
4
結語
“如果愛的回饋都是美好的,人生會輕松許多。但是愛所要求的是,我們要面對失去彼此的恐懼。”在死亡面前,任何形式的解構嘗試看上去都是無力的,導演選擇用影像作為對抗恐懼的撫慰劑,選擇用預演尋找至親離去后撐下去的方法。但是在迪克的葬禮結束后,迪克的哥哥在眾人看不到的角落掩面哭泣。“我們以為那樣做,可以阻止即將發生的事,那是我們所能找到撐下去的方法,或者說差點找到方法。”無論是回望疫病的灰色,還是生活在以“不確定性”作為底色的現代,我們在失去面前從來沒有多言的權力,更無法找到實際上降低預期中損失的良藥,但是記錄本身就是意義。
“在我看來,面對痛苦的時候,當你能與你愛的人一起,并有能力嘗試從中創造一些新東西——無論是新的關系還是轉化為某種形式的藝術——我認為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Carey,2021)無論是紀錄片、文字或者任何一種形式,這也許是我們作為人類生存下來的方式——我們是這樣見證生命與回饋彼此。
參考文獻:
[1]Mayer, S. (2022, January 25). Dick Johnson Is Dead: Falling Angels. Criterion.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7668-dick-johnson-is-dead-falling-angels
[2]Carey, M. (2021, March 9). “He Thought The Idea Was Hilarious”: Director Kirsten Johnson On “Killing” Her Father Repeatedly In ‘Dick Johnson Is Dead’. Deadline. Retrieved from https://deadline.com/2021/03/dick-johnson-is-dead-director-kirsten-johnson-netflix-documentary-interview-news-1234710401/#!
(本文為北京大學通選課《專題片及紀錄片創作》2024年度期末作業,獲得“新青年電影夜航船2024年優秀影視評論”)
新青年電影夜航船
本期編輯 | 童文琦
圖片來源于網絡
原標題:《紀錄片評論|徐沐恩:《迪克·約翰遜的去世》:死亡演練與紀錄實驗》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