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工作后就不讀書了?——近代日本的勞動與閱讀史
“工作以后有多久沒讀過書了?”三宅香帆自問自答后嚇了一跳。她原本也是自幼買書讀書的文學少女,此后又進入了號稱“自由之學風”的京都大學文學部,但畢業后就職于一家IT企業后,就再也沒有讀過書了。她實在無法割舍閱讀的趣味,于是辭職做起了評論家,并以自己的經歷為思考原點,分析了近現代日本勞動與讀書難以兩全的困境。這就是她2024年新著《為何工作后就不讀書了?》(集英社新書)的緣起。本書的基本觀點是,讀書并非僅僅是個人趣味的問題,它反映的是時代背景中的階級結構、閱讀媒體、經濟模式的變遷。用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結構主義觀點來說,是主體不是獨立的實體,而是結構的后果,主體只是一個承受者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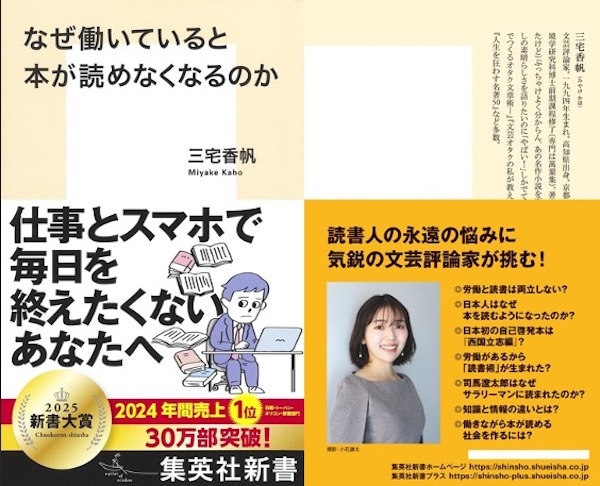
三宅香帆《為何工作后就不讀書了?》
一、為了“出世”而讀書
盡管日本人素有“讀書國民”之稱(永嶺重敏,《読書國民の誕生:近代日本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但其“加班文化”也是舉世聞名的。在這種矛盾的處境中,讀書這一行為的社會學意義,往往受制于具體的時空條件。在明治初期,政府模仿西洋諸國的“民族國家”體制,有意識地推行“言文一致”,施行義務小學制,建造公立圖書館等等,普通人接觸文字閱讀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此外,由于政府管控的松弛,還出現了以市場為導向的報紙輿論界。為了利于銷售,報紙還率先添加的“句讀點”(標點)與“振假名”(讀音),使得普通讀者閱讀難度大大下降。而且,新式的印刷技術還使得書籍與報紙得以大量出版,出版業出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但究其原因,其實是維新后日本廢除了武士階級的特權,斷行“四民平等”,由此帶來了空前的社會流動性。普通日本人也能夠獲得階級躍升的機會,于是大家都為了“出人頭地”而讀書(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這一點,從明治時期最暢銷的作品是《西國立志篇》就可以看出。它是英國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1812-1904)在1859 年出版Self help(中文譯本為《自助論》)的日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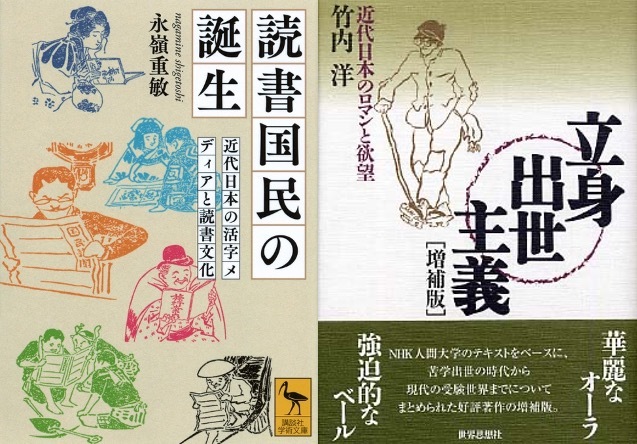
斯邁爾斯生活在大英帝國殖民擴張的“維多利亞時代”,其思想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征服世界的樂觀精神。正如他的名言“天助自助者”(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所示,個人的努力、勤奮和道德品格才是成功的最重要條件。因此,斯邁爾斯寫了許多出身貧寒,但通過自身的毅力、節儉和自律最終獲得成功的偉人事跡,如發明家詹姆斯?瓦特、喬治?斯蒂芬森等等。這一點,對于崇尚“文明開化”的日本青年別具吸引力。至明治末年為止,《西國立志篇》銷量高達一百萬冊。
不可否認的是,這種類型的“自我啟發書”是以男性為中心的。三宅指出,明治末年,由于日本施行的殖產興業政策初具規模,重工業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隨著鐵道的鋪設,礦山的開采,越來越多的男性從農業生產者變為工人。他們的工作時間長達每日13-16小時。勞動占據了他們大量的時間,但其收入,其實比同時代的印度更低。所謂的“天助自助者”,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過是明治工人們的白日夢罷了。石川啄木的短歌準確地傳達了這樣的無奈,“工作啊工作,生活拮據無樂,兩手常見空空”。

此外,由于《西國立志篇》的日文譯者中村正直將英文Cultivate、Culture翻譯為日文漢字詞語“修養”,一時間“修養主義”成為了當時日本人生活進步的律令。正如竹內洋所指出的一樣,“修養即為修身養心,是一種以克己、勤勉等作為人格完善的道德核心,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種精神、身體主義的人格主義。修養主義源于江戶中期在民間形成的,一種以勤勉節約為美德的世俗生活道德規范,到明治時代后期被逐漸推廣到了普通民眾之中”(《教養主義的沒落:精英學生文化的變遷史》)。讀書生活即是這種修養主義的一部分。
二、為了“教養”而讀書
如果說,修養是明治時代人的一種行為方式,那么大正時期流行的“教養”則是學生群體中發展出的一種“以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的閱讀為中心,力求完善人格的態度”。這是因為,相對于此前,近代日本的學生群體呈現爆發式的增長。這一時期,圖書館的數量增長了四倍,從中央擴大到了地方。私立大學獲得辦學許可,在高校中形成官?公?私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外,在出版行業中,由于形成了書籍再版價格維持的出版制度,以及委托銷售的經營策略,書店的數量更是從三千家增長到了一萬家之多。新興的學生群體為了與勞動階級形成差異化的自我認同,積極地投入到教養主義的讀書熱潮中。
但是,歷經甲午(日清)、日俄戰爭后的日本帝國,是一個連年對外征戰,社會各界都已處在筋疲力盡的狀態之中的國家。不同于明治時代奮發向上,人們都追求自我完善的“修養”,大正的讀書人所追求的“教養”中往往暗含一種“內省”的視角。三宅指出,此時期最暢銷的三本書,倉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巖波書店,1917年)、島田清次郎《地上》(新潮社,1919年)、賀川豐彥《超越死亡線》(改造社,1920年),要么是宗教意義上的救贖物語,要么是社會主義者的自傳小說。這是因為,1907年爆發的足尾銅山暴動事件,以及1910年遭檢舉的“大逆事件”,正是人們對現存體制的忍受已經達到了極限的表現。正如澤村修治指出的一樣,“人們預感到大正會墮入社會不安與表面的繁榮背后的深淵,才轉向宗教的文學與人生修養的著作,或者轉向其替代物——由此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的牽引力”(《ベストセラー全史?近代篇》)。在三宅看來,大正時期的暢銷書與其是在贊美自我完善,不如說是聚焦在了自己的痛苦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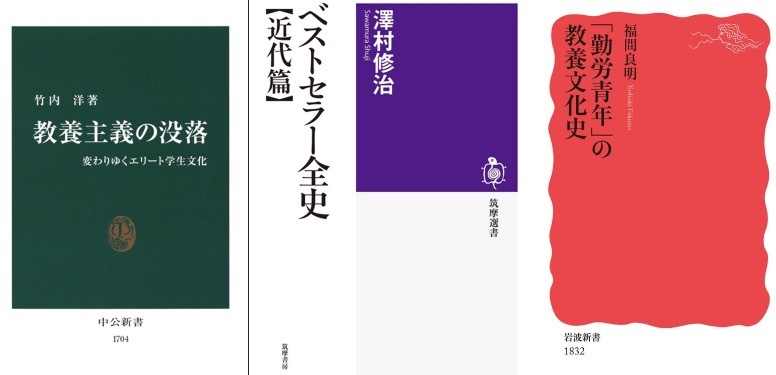
當然,作為學生精英與勞動者讀書差異化最為明顯的是,讀不讀大正時期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綜合雜志。作家杉森久英就曾說,在學生時代,如果不讀《中央公論》和《改造》這兩本雜志,“就會感覺自己落后于時代”,因為這兩本雜志刊登的論文和小說會成為當月知識人階級討論的中心話題。由此可見,學生們的教養,不僅通過高校和大學的正式課程,還通過綜合雜志而獲得。此外,被奉為教養主義殿堂的巖波書店《思想》雜志,在其發刊詞中也鄭重地寫道:
……跟風隨流、投其所好、迎合讀者之意的雜志不少。又,專業學術雜志似無增加之必要。然而,不媚俗潮流,將永恒的問題貼近普通讀者的雜志,難道不是當今日本最需要、最欠缺的嗎?敝店立志要彌補這一缺憾。《思想》并非要宣傳某一種主張。只要是為真、善、美服務的勞動,無論何種立場、何種領域,《思想》都想把它輯錄下來,以資我國人一般之教養。對過分的輿論界感到不滿者,看到敝店認真的努力,一定會信任我們的。
《思想》的精英主義立場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大正時期的日本,在精英與底層之間,出現了一批領著工資的工薪族群體。他們作為新生的中產階級,也會購買便宜的“元本”或者“全集”作為自身階級認同感的標識。
三、為了“娛樂”而讀書
“教養”作為勞動階級的追求,是從戰后才開始的。1950年代的中學生中,大約有一半人會繼續升入高中求學,而另一半則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去就職謀生。然而,后一部分人并不甘心做一個普通的上班族,于是就開始了白天上班,晚上去夜校學習的生活。對他們而言,追求“教養”是彌補學歷缺憾的一種手段。但是,他們所謂的“教養”,其實仍然與舊制高校中精英主義的“教養”相去甚遠。例如夜校學生中流行的《葦》或《人生手帖》等雜志大多是與人生教訓相關的“人生雜志”,并非《思想》等精英主義的綜合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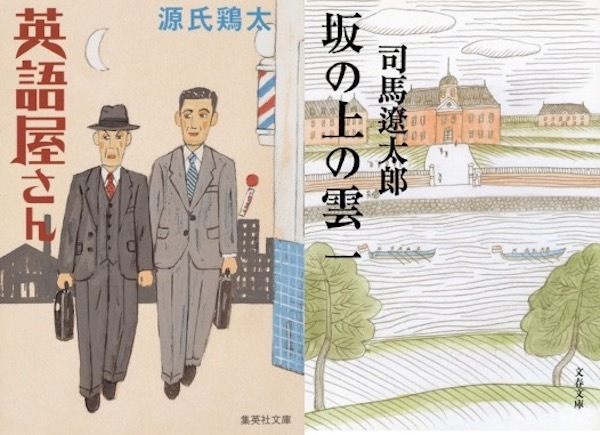
這個時期的暢銷書,反映的也是“勤勞青年”的生活實態(福間良明,《“勤労青年”の教養文化史》)。1951年植木獎獲得者源氏雞太的小說《英語翻譯先生》的舞臺背景正是“會社”(公司),也被稱為“會社小說”。其主人公是一個公司內的囑托,非正式職員。小說以他的視線,描繪了公司內部各種明爭暗斗。為了迎合上班族,源氏構思的小說情節并不復雜,而且人物性格也非常簡單,黑白分明。此外,他還在寫作過程中避免難懂的漢字,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這種讀物與其說是“教養”,不如說是“娛樂”。
1960年代末,日本結束了戰后政治上的左右紛爭,迎來了經濟上的高度成長時期。經濟成長的果實比此前更大范圍地浸透進了社會的方方面面。1970年代的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的歷史小說正是反映了這種全社會昂揚向上的心情,其代表作《坂上之云》寫道:
按照仙波的說法,平民的孩子只要勤奮刻苦就能出人頭地,這都是多虧了御一新,為了保衛這個國家不惜犧牲生命。
出人頭地主義驅使著這個時代的所有青年。沒有任何人懷疑個人的榮華富貴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說這是日本歷史上罕見的時期。
這種同時代的集體心態,其實與明治時代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加劇而出現的奮斗精神相似。福間良明指出,“司馬的作品被商務人士所偏愛”,“它并不是被當做商業性的短期、中期利益有關的書籍被閱讀的,而是完全是作為‘歷史的教養’來陶冶人格的手段。這里可以說,它是一種商務教養主義”(《司馬遼太郎の時代 : 歴史と大衆教養主義》)。“商務教養主義”是一種浪漫地、戲劇地、輕松地獲得的一種教養感覺。
四、泡沫時代的“百萬暢銷書”
根據日本出版科學研究所的調查,日本的出版物在1980年代從一兆日元上升至兩兆日元,實現了“倍增計劃”。伴隨著這股消費熱潮,誕生了許多百萬級暢銷書,例如黑柳徹子《窗邊的小豆豆》500萬冊,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350萬冊,俵萬智《沙拉紀念日》200萬冊,吉本芭娜娜《鶇》140萬冊等等。柄谷行人曾指出,這一時期正是日本現代文學“終結”的時期,文學的“內部性”敘事開始瓦解,不再承擔構建民族精神的功能,轉而成為消費文化的碎片。這種終結不僅是文學形式的變遷,更是讀者與作者關系的根本性斷裂(《向著批判哲學的轉變》)。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學”作為百萬級的消費商品才得以出現。與1970年代的作家松本清張或者小松左京江將“自我”與“社會”的關系置于中心地位不同,1980年代的小說家們喜歡用“私”(“我”)的視點看世界。它并不在乎是否對世界產生影響,只是單純地表達自我。在三宅看來,這一點,反映的不是人們對“教養”,而是對“交流”的渴望。這一時期最暢銷的雜志《BIG tomorrow》刊載內容以“職場處世”與“泡妞技巧”為主,“人情世故”是這一代上班族的追求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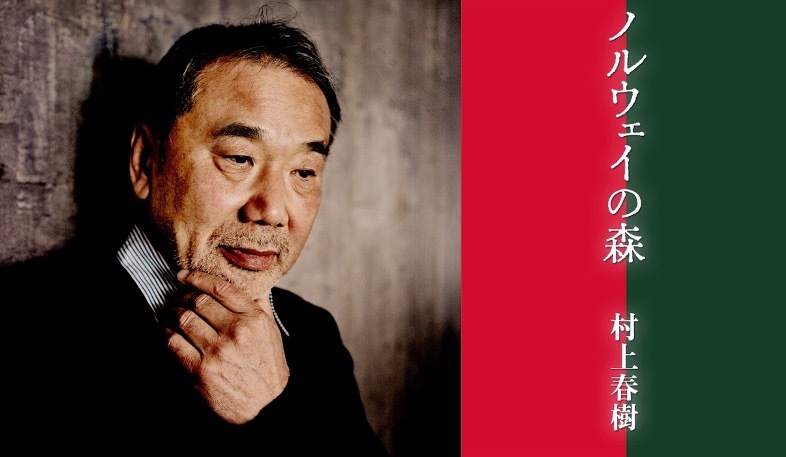
村上春樹與《挪威的森林》
1980年代另一個特點是,女性作家開始異軍突起。但與讀書不同,女性作家依賴的是各式各樣的文化中心講座(culture center)而獲得“教養”。講座中既有料理、花道之類的家庭主婦的趣味,也有小說、思想、歷史類的學習。由于泡沫經濟時期,男性勞動力處于高負荷的加班工作狀態中,文化中心的女性聽講者達到了八成以上。特別是女性作家重兼芳子因為參加文化中心講座后,其創作的小說獲得了芥川文學獎,文化中心的學習人潮迎來了高潮期。重兼坦言,參與文化中心彌補了自己學歷的缺憾。她舊制高等女校畢業后即結婚,再也沒有過升學經歷。在某種意義上,文化中心對于這一批女性而言,正如明治大正時期各種各樣的“成功談”雜志,或者“勤勞青年”的“人生談”雜志,或者70年代被上班族偏愛的司馬遼太郎“歷史小說”一樣,是獲得“教養”的一種手段。
但是,這種通過文化中心學習而創作的文學其實引發了諸多爭議。例如,有批評家就把她們稱之為“寫手記的女人”,讀了一些“招募指南”之類的就當了作家。重兼憤而表示,“這些皺著眉頭,抱著優越感”攻擊文化中心的正是一些中年精英男群體。“他們也好不容易安定后才開始重拾學業”,“真不知道他們哪來的嘲笑我們的權利”。其實,“讀書”以前是階級,現在成了“男女”差異化的工具。按照布爾迪厄的理論,讀書是一種“象征性暴力”,“它通過象征性資本(如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分配來維持統治關系”(《學術人》)。也就是在這一個時期,以上野千鶴子為代表的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m)開始大行其道。

布爾迪厄與上野千鶴子
五、全球化時代的讀書
冷戰結束后,日本經濟繁榮的泡沫破裂,日本人引以為豪的年功序列制,以及家族式的企業文化破滅。同時,全球化資本與原子化個人相結合的新自由主義打擊了作為國民共同體概念的福利國家體制,它“將差異(貧富分化)視為非官方現象,并將由此產生的所有后果歸結為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個人應承擔的責任”。事實上,這是一種“差異管理的民營化體制”。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對市場競爭的結果負責(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人們已經不再相信只要個人努力就可以改變社會。1995年的暢銷書《腦內革命:腦內的荷爾蒙可以改變生活方式》代表了這一趨勢。不同于明治時代的暢銷書通過教育人勤勞奮斗改變個人命運,《腦內革命》“以初看之下不可視的內面為對象,以‘實踐的技法’來控制它。在這一點上,它是劃時代的”。它的目的不再是改變個人的命運,而是通過積極的思考防止老化與提高免疫力等等具體問題。
日本出版科學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在1980年代是沒有一本類似《腦內革命》的“自我啟發書”成為暢銷書的,但1990年代前半期的前三十本暢銷書排行榜中出現了三四本,1995年有五本,而1996年《腦內革命》、《“超”學習法》就霸占了第一第二名。這反映了在“全球化”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浪潮中,個人只能夠順從,而非改變的處境。所有的事情的目標都在于“可控”。于是,面對無可改變的社會,人們退縮進了個人領域。“斷舍離”的收納指南書也火爆了起來。牧野智和指出,這是一種將“社會”相對化,將私人領域“圣化”的表現。

“當人們必須在不被外界提及的私密空間里自我治愈時,這種圍繞著‘自我’的目光背后,難道不是透出了自我啟發書所設想的那種‘社會’嗎?這種‘社會’并不需要用太多言語來形容,只是作為無法通過自身努力改變的對象而困擾、傷害自我。但無論如何,自我啟發書首先向我們展示的,是在讓我們專注于自我改變和肯定的同時,將自我每天所應建立聯系的‘社會’視為可憎之物,或者視為毫無關聯的事物而加以疏遠,是一種與生活對抗的形式。”
2000年以后的IT革命加速了原子化個人的現象。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們追求的是單純的“信息”,而非“知識”(教養)。三宅認為,“在讀書所得到的知識中包含了許多雜質——即偶然性。在被稱為教養的古典知識或者小說那樣的虛構作品中,有讀者意想不到的展開與知識。在文脈(語境)或說明之中,讀者意料不到的這種偶然性的情報,我稱之為知識。但信息之中其實是沒有雜質的。這是因為,信息正是讀者想要知道的內容。就像為了提高溝通能力得到生活指導,為了賺錢得到投資的訣竅一樣,這就是‘信息’”。伊藤昌亮也認為,“與注重歷史性與文脈性的人文知識相對,這里充斥著簡單輕松的信息知識。在網上所重視的是,通過輕松的交流所得到的信息收集能力、信息處理能力、信息操作能力”。網上的信息世界不會“面向社會與自我的復雜性”。
結語
2008年,美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 Carr)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Google讓我們變得更愚蠢嗎?》的文章,引發了人們對互聯網時代閱讀的擔憂。卡爾指出,互聯網時代的信息獲取方式——快速跳轉鏈接、多任務處理、即時反饋——正在改變人類的閱讀習慣。他將傳統閱讀比作“深潛”,而網絡閱讀則像“在信息海洋上沖浪”,這種轉變使得人們難以專注于長文本,注意力被分散為碎片化的“掠讀”模式,削弱集中注意力和沉思的能力。但他同時指出,此類爭議在歷史上并非首次出現。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批評文字的發明削弱了人類的記憶能力。尼采使用打字機后,寫作風格從雄辯轉向簡潔的格言體,印證了“工具塑造思維”的理論。
事實上,卡爾的結論并非黑白分明。技術既可能削弱某些認知能力(如深度記憶和專注力),也可能推動人類向更高階思維進化。關鍵在于如何平衡依賴與自主性,避免技術成為“思考的鐐銬”,正如尼采所言,“工具要參與思考的過程”。人類的智慧在于主動塑造工具的用途,而非被動受其支配。三宅香帆自己也在利用網絡擴大閱讀與交流的邊界。她自己既是一家線下書店的店長,也是一位網絡上小有名氣的Youtuber。她在網上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從京大文學少女到IT公司的人事顧問,從學術研究到大眾寫作。她的作品與活動既服務于特定群體(如御宅族、職場人),也觸及勞動異化、文化消費等宏觀議題。她基于自身的工作體驗后,開始擔心職業與讀書無法兩全的生活,并且針對“讀書衰退”的社會現象表達了自己的思考。《為何工作后就不讀書了?》原載于《東洋經濟新聞》網絡版,獲得無數網友共鳴后,于翌年出版成書。正如序言中談到的一樣,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榨取“文化”的現實,三宅收獲最多的網友評論是,“我亦如此”。該書一經發行便獲得30萬冊的銷量,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這是普通上班族的普遍困境。每個人都在業績的壓力下沒有得到真實的自我感受。

韓炳哲與《倦怠社會》
韓炳哲曾指出,現代社會已從福柯筆下的“規訓社會”轉向以“積極自由”為特征的“功績社會”。在這一范式中,個體不再是外部權威的被動服從者,而是主動成為“自我剝削”的主體。人們被“你可以做到”、“成為更好的自己”等積極口號驅動,不斷追求效能最大化,最終導致過勞和倦怠。功績社會通過將自由與剝削綁定,使個體自愿投入無休止的優化和競爭中。例如,職場中的“內卷”、社交媒體上的自我展示,本質上都是個體對自身施加的暴力,這種剝削因缺乏外部強制而更具隱蔽性(《倦怠社會》)。這種自我剝削機制,其實正是尼采所謂的“死亡說教者”。
“你們所有人都喜愛苦工,都喜歡快速、新鮮、陌生之物,——你們無法忍受自己,你們的勤勞乃是逃避,以及力求遺忘自身的意志。
倘若你們更多地相信生命,你們就會更少投身于當下瞬間。但你們身上沒有足夠的內涵來等待——甚至不足以偷懶!
到處響起那些死亡說教者的聲音:而大地上也充斥著這樣一些人,他們必定要接受死亡說教。
或者說必定要接受‘永生’說教:這對我是一樣的,——只要他們快快離去!”(《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三宅建議人們警惕這種“死亡者說教”,重新發現自我的意義,而讀書正是這種自我發現的重要手段。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