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陳恒:只有理解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知,既有“全球供應鏈重構、科技創新機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濟、信息保護、代際共育”等當下時代關心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等關系中國學術研究的機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已連續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科權威專家、學術期刊主編、資深學術編輯等專業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數字時代學術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如何創新,以及學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時代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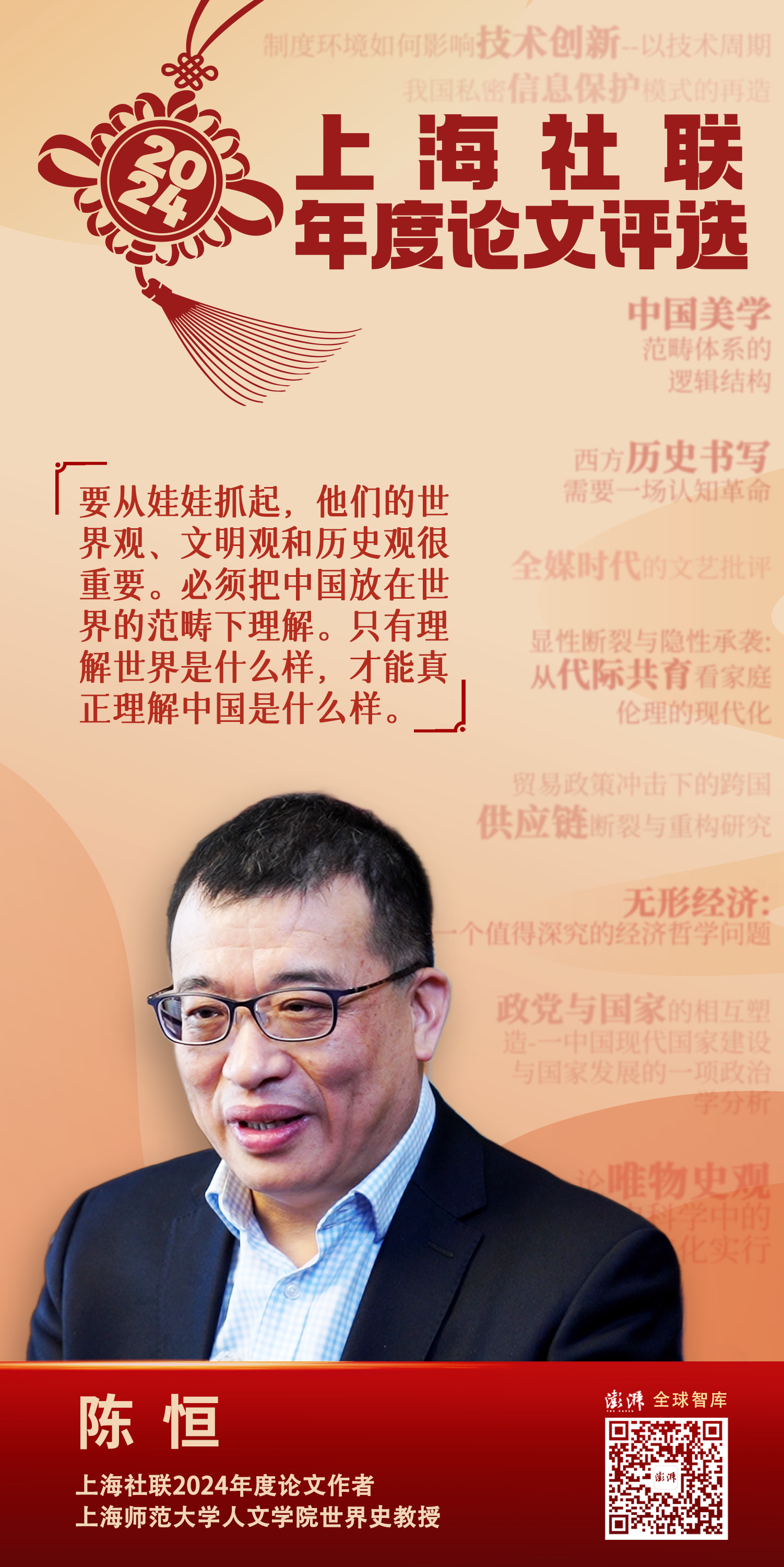
作為從事教學科研,也長期參與學術出版的世界史學者,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教授陳恒認為,在去他者中心、去學科中心、去自我中心和去人類中心的方向下,史學在21世紀會發生一場重大變革。
在上海社聯2024年度論文《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原載于《歷史研究》2024年第4期)中,陳恒指出,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書寫模式使得非西方國家失去了平等、公平、公正地表達觀點的機會。
2025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就如何理解歷史書寫的一系列問題專訪陳恒教授。他認為,中國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很多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如何將其從中國的轉為世界的,取決于大的環境。受到人工智能影響,當下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文科的預算、課程和教師大大削減。對中國來講,這可能是機遇,要考慮怎么把握住。
陳恒是《世界五千年》的總主編,他在這套書上用了最大的心力。他表示,某種意義上,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和小朋友身上,給他們輸灌生態文明的理念,以及更加客觀真實的世界歷史。需要把中國放在世界的范疇下理解,只有理解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各方如何書寫歷史和進行對話
澎湃新聞:您的這篇《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是在什么狀態下寫的?希望回應怎樣的一種問題?從傳統而言,為什么中國的史學格外發達,甚至有“史學史”這樣的研究方向發展出來?
陳恒:這和我的專業背景有關,我是做外國史學史的。一般來講,史學史被認為是史學的名著加上史家的概論。后來,我把外國史學史的概念內涵不斷拓展,把它理解為一種知識史、學術史的概念。既然概念拓展了,視野也就拓展了。歷史學家以外的非歷史學家,以及宗教史、藝術史、文學史等,也都要在史學史中考量。
近代以來,整個歷史書寫發生了很大變化,無論西方內部還是非西方世界,對歷史書寫都有不同理解。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在整個世界領域取得的成就非常大,也從反面驗證了文明的發展有不同模式,歷史書寫也因此發生相應變革。
中國的史學確實發達。我去年做了一套書——《牛津歷史著作史》,中文版有10大卷,是全球學者聯合寫的,代表當今世界歷史書寫的較高水平。其中一位日本學者寫了一段話。他說,1750年之前,中國的歷史書寫在全世界遙遙領先,尤其在歷史書籍出版方面,中文世界的總和遠遠大于非中文世界。
這句話對我們有很大啟發。1750年后,中國的歷史話語權為什么逐漸旁落?這跟整個時代的大背景有關。近代以來,文藝復興使得意大利成為世界的中心,啟蒙運動使法國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工業革命使英國也成為世界的學術中心。到了19世紀德國對科學精神的擁抱,20世紀美國對世界主義的擁抱,使他們也成為世界學術中心。換而言之,世界上的整個社會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從過去的農耕社會到后來的農業社會,再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不同的社會形態使得大家對歷史的認知不一樣。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中,我們的歷史話語權就逐漸旁落。
歸根結底,1750年之前,中國在農業社會當中看待世界記錄世界的方式方法,既多樣豐富又高屋建瓴,但工業社會以來,我們還沒有完全適應,整個學術、思想和知識層面,還處于追趕狀態。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使得這一輪文明發展的態勢中,出現了另一種形態,有可能改變歷史書寫的模式。我們史學非常發達,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史學研究的發達,這和西方有一點不同。今天則可能面臨一次新的轉型和改革。
澎湃新聞:通常大家認為,對歷史的敘述是話語權的體現。在您看來,各方應該如何書寫歷史和進行對話,才能夠和諧共生,不致于走向吞噬和取代?
陳恒:歷史話語權是非常敏感的問題,也是一個潛意識的意識形態問題。做歷史的人一般從三個層面討論。第一個層面是,真實的歷史是什么,是如何發生的。第二個層面是,人們眼中的歷史是什么樣,既包括普通大眾的對待方式,也包括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權力。第三個層面是,歷史學家之所以成為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是什么樣的,這體現著歷史書寫的權力。
可以發現,大的國家非常關注歷史的書寫,小的國家不太關注或沒有能力關注。如果沒有非常深厚的經濟、文化和人口基礎,是培養不出優秀歷史學家的。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文明的話語權非常強大,不可以否認西方文明對近代世界和現代世界的巨大貢獻,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東西需要警惕。
比如,“去殖民化”這個詞對我們當下有重要意義。16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整個世界被裹挾到西方世界中。到了19世紀晚期,整個世界85%左右的領土都被西方列強瓜分,成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些國家失去了自己歷史書寫的權力。一定意義上,我們國家也被裹挾其中。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句話非常經典:“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其實是一針見血地道破了殖民史學所代表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也有很多層面。比如,認為西方文明是按照從希臘羅馬直到近代社會的邏輯發展,而這一模式是必然且固定的。這樣就把整個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及歷史書寫的多樣意義,乃至人類未來發展的文明道路都抹殺了。這些是不合理和需要警惕的。
澎湃新聞:西方歷史書寫需要一場認知革命。改變單向敘事,這種現象也正在西方史學界發生,在您看來,其中存在怎樣的趨勢?這類去中心化的敘述,是否會令歷史敘事變得晦暗不明,難以形成明確線索?
陳恒:西方內部也在發生革命。我想到的至少有兩點。一是后現代主義,強調的是去中心,打擊的是宏大敘事,不需要那種歷史的真相,與之越來越疏遠。二是全球史的興起,在我看來,全球史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歷史書寫的重要方式,把全球作為整個區域,在相互交流的趨勢中去整體看待,不再強調分成東亞、西亞、非洲、拉美等區域。無論在思想層面,還是歷史書寫層面,西方發生的自我革命或解構,是我們要去重視的。
從具體領域看,比如非洲史,20世紀初直到1940年代,歐洲思想家都認為非洲是沒有歷史的,沒有文明和文化,沒有一切值得炫耀的東西。到了1950年代,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有關“歐洲一切都是文明的、非洲一切都是野蠻的”這種觀念被顛覆了。這種顛覆的力量,首先來自歐洲內部。很多人認為,自己作為歐洲人或白人,對整個非洲還有很多虧欠的東西。另外,這一時期有大量非洲的學生去歐美留學,學成之后掀起很多反思非洲歷史書寫的革命。此后,對非洲的歷史書寫就有了新的趨勢。這些也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另外,歐洲之所以現在宏大敘事不太盛行,或歷史碎片化比較盛行,也和歐洲19世紀中期以來,從主流而言完成了國家統一有關。中國還沒有完成民族國家統一的歷史任務。所以,他們可以不要宏大敘事,我們不可以不要宏大敘事。這些事實也決定了,現在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
中國的歷史資源非常豐富,很多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如何將其從中國的轉為世界的,還取決于整個大的環境。我們過于關注民族的視角,但在世界視野之間,橋梁還沒有搭建起來。這是我們要努力去做的。不能只關注中國,忽略了世界。
在這篇文章中,我提了幾個去中心:去他者中心、去學科中心、去自我中心和去人類中心。這意味著,史學在21世紀會發生一場重大的變革。尤其在如今人工智能的環境下,這個關口到了。如果不認真對待這個關節點,我們在這一輪的歷史書寫當中,有可能再一次喪失話語權。
人工智能是大勢所趨。近年非常火的一本書是《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作者是以色列的尤瓦爾·赫拉利。他2012年出過一本《人類簡史》,十年后出了紀念版。紀念版的序言很大一部分是人工智能幫他寫的。讀者閱讀時,并不知道這件事,以為就是作者寫的,毫無違和感。但作者最后告訴你,這篇文章是人工智能幫助寫的,里面很多觀點是他自己也贊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人工智能剛起步一年多。
人工智能使得歷史書寫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數據的積累和整理方面,我也在用人工智能。遇到問題不清楚時,我會和它對話,它會幫我系統整理一些相關文獻,給出一些相關答案供我參考。有這么多電子書,很好的軟件,加上人工智能龐大的運算系統,這使人們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
前幾天有一篇關于文科倒閉浪潮的文章。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文科的預算、課程和教師都大大削減。這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對我們來講,可能恰恰是個機遇,要考慮怎么把握住。尤其是,提倡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三大體系”建設,如何進行自主的知識生產、有組織的知識生產等。我們和域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多空間去拓展。但無論如何,不能制造兩個話語體系。按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世界文化有共性。如果歐美一套話語,我們一套話語,變成兩個世界,就會影響我們的發展。
中國應該多實踐,多做國際化的事
澎湃新聞:中國當下的世界歷史敘述可以怎么做?對人類歷史重大理論問題的分析,無法擺脫西方的框架。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進行交流和借鑒,又形成自己的史學體系?
陳恒:當下應該多實踐,多做國際化的事。德國學者萊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在1979年就提出“不對稱”的概念。史學領域中,這種不對稱很明顯。歐美學者寫著作,不看非歐美作者的著作,一樣可以寫出經典的成果。但今天在中國的史學界,尤其是很多研究外國的史學同行,不可能只看中國人的作品,不看歐美學者的作品。也就是說,在標志性的概念,以及重要的學術著作、重要的思潮、重要的流派、重要的人物等方面,我們還是缺乏的。我們必須認真寫出有代表性、有份量的內容。這不能僅是講口號,最關鍵的是拿出扎實的作品。
中國的世界史史學界還在不斷努力。但我們體量太小。我看到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的數字,2022年中國歷史學者高校在編在崗的大約有14900多人,其中世界史學者只有1000人左右。這個比例非常小,與我們國家認知世界的客觀需求存在很大差距。有人統計,美國研究域外的歷史學家是12000人左右。我們相當于他們的1/10。而我們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按照這個比例算,我們研究外國的歷史學家,需要有40000人左右。缺口可謂非常大。在足夠多的學者基數上,可能會產生很好的作品。當然,還有很多因素,比如社會的包容性、國家的文化政策等,都會影響歷史書寫。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當下生態主義話語的興起?我們是否可以更關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更好地將中國歷史中“天人合一”等觀念體現出來?
陳恒: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國環境學者唐納德·沃斯特寫的《欲望行星:人類時代的地球》。他是80多歲的老先生,后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他認為,人類過去有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從農耕社會到農業社會的轉變,帶來了帝國主義,同時也帶來各種社群主義。第二次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帶來的是貿易全球化,財富的激增導致不平等,同時帶來科學、理性、民主這些觀念。未來社會發展可能走向生態文明,在整個星球中,人的重要性需要降低。否則,以人為中心,會對自然世界造成很大破壞。他提到,這個星球上,不包括已消亡的,大約有1000多萬種動植物。人不過是其中一份子。而人與世界的互動所形成的文化社會,其實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他的觀點非常獨特。現在人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核戰爭、毒品,甚至是人類自我消亡的問題——這么多物種消亡了,人也是物種之一,理論上也有消亡的可能。按照AI時代的發展趨勢,其中存在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他對倫理、生態提出了很多要求,也提出一些設想。但這些設想能否實現,或者說,人類能不能抓住這個機會,真的是難說。我自己有時是悲觀的。
我們也希望,中國的生態文明話語等能夠有所彰顯,包括理論的設想和實際的做法。關鍵是,能夠出現一種更客觀全面的、更具普遍價值且別人能接受的說法。
最近,我們在北京召開了新版《世界五千年》第一卷的發布會。這套書之前出過兩版。第三版是重寫的,這套書有54冊6卷,一卷9本。基本理念是“共生一個星球,共享多個世界,共融無限未來”。一定意義上,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小朋友身上,給他們輸灌一種生態文明的概念,一種更加客觀真實的世界歷史。因此,我們花了很大的精力來做這件事。
我們把希望放在這套書上,要從娃娃抓起,他們的世界觀、文明觀和歷史觀很重要。必須把中國放在世界的范疇下理解。只有理解世界是什么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是什么樣。不能只理解中國,不理解非中國。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智慧,都有自己的貢獻,都有自己對世界的解釋方式,都有對未來構想的理念在驅動自身發展。
澎湃新聞:您認為,對于時間與空間的延展,乃至新發展出的知識工具的概念,都可成為一種有力而新鮮的歷史敘事。不同的體系和概念之間,該如何對話,使其拼合成一個綜合體?
陳恒:歷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最基礎的學科。歷史學離不開時間的工具、空間的工具和概念的工具。
今天我們的歷史書寫,很大程度上在印證近代西方歷史的時間概念。比如,古代、中世紀和近代這三分法,其實是西方的舶來品。這個概念影響很深,我們要突破是非常難的。因為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標志性概念,對世界產生很大影響。
但反過來說,人類歷史其實非常短暫。地球有43億年,有生命的歷史大約20萬年,而真正的文明史只有5000年左右。而且,在5000年當中,西方真正占據優勢的就是近代五百年,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可以忽略不計。中國未來的發展空間非常大,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世界性的意義。我們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此做準備和預留。
空間也是這樣。以一般的理解,空間只是地域上的空間。其實,數字空間、太空空間都是空間。其中都包含人類歷史書寫的模式,是一種想象的未來。如果要把這些都突破了,那么很多歷史認知都會發生很大變化。
這方面,目前還是歐美領先。最近十幾年來,其歷史書寫有一種方向。即人類歷史不僅是有文字以來的文明史,史前史也是需要考量的。比如《欲望行星:人類時代的地球》這本書,沃斯特是雄心勃勃的,想做的是書寫地球這一行星的歷史,其出發點是人的欲望。而且,他對中國的文化也比較熟悉,采用中國很多經典著作去解釋他的觀點。
概念工具很重要,會影響整個歷史書寫的方式。比如,古代中世紀方面,最近幾十年來,有一些新的概念,是對已有概念的修正。比如“古代晚期”。羅馬帝國衰亡之后,就逐漸從中世紀轉變。之前的歷史書寫,認為這兩個時期之間是分裂的,強調的是其中的變革。而“古代晚期”這個概念強調延續性。所以,會不斷出現新的時間概念,來修補已有的概念。這方面我們有待進一步發展。
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是需要的。歷史學有統合的能力,是立足綜合學科的總體判斷。歷史學不做預測,是對已有的東西做出基本梳理和價值判斷。比如,湯因比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二戰期間,他是英國最重要的智囊團成員。為什么是歷史學家?因為歷史學家有一種綜合的、高站位的宏觀判斷。他知道歷史的來龍去脈,對未來發展會有一種感知,能夠比較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學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年代人物故事,有非常系統和全面的要求。一定意義上是很多學科不可取代的。
包括歷史研究在內,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是活的,反映當下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需求。古今中外無一例外,只是程度上有高有低,有強有弱,有大有小。比如,西方偽史論今天在中國有一定市場,從對金字塔建造的否定,到否定希臘文明,也就否定了整個西方文明的邏輯順序。我想問的是,有沒有必要這樣做,做到以后能實現什么樣的目的?如果真的對此否定,變成一種“中國中心主義”,也是非常可怕的后果。我們反思和修補別人的時候,是要拿捏好的,不能以另一種中心來代替。我們說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并不是要取代別人,而是建立一種更加全面客觀的敘述。
要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具有世界眼光的社會氛圍
澎湃新聞:您所主張的認知革命之下的歷史書寫,是“不再被細化的學科、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決定,也不再被市場決定”。具體而言,可以是怎樣的體系支持?
陳恒:這是一種理想狀態。要到達這個狀態,可能會非常久遠。未來會來,但一定會慢慢來的。
關于意識形態,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類有共同的追求和理想,不同的國家是有交集的。比如說,今天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里,就說明中國在政治上是先行的,學術上相對落后于政治。國家層面都考慮到了未來的發展,而學術界可能沒有深入到這個問題中。
還有學科分化。這其實是學術發展忌諱的,但又不可避免。因為世界發展太快,涉及各個領域的專家太多。同一個學科的學者之間可能都很難理解。但不同的研究做出之后,一定會得出普遍的東西。作為歷史學家,怎么借鑒這些學科的東西,是我們要關心的。一定意義上,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的,是后知后覺的學問。其他學科的成效好的方法,都可以借鑒。也可以說,歷史學是借鑒其他學科發展的一門學問。我們不能太細化,不能保守,一定要視野寬闊,用包容的眼光看待。
另外,不能被太過于追求利潤的市場所決定。這個市場主要指的是民間的文化生態。我感覺,要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具有世界眼光的社會氛圍,才會有相應的文化氛圍。比如中國出版的新書,總量是全世界第一,每年大約有30萬冊。影響力高低且不論,總量第一已屬不易。從后進到先進,總有發展過程。另外,這個總量中,有10%左右的翻譯出版。中國是當下全世界引進版權書最多的國家。中國文化的底色和底蘊,是開放包容的。這一點不可否認。同時,對包括歐美在內的域外文化的引進和關注,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好的人口基礎。所以我對整個未來充滿希望。
我想,需要讀歷史書。通過近代五百年的中外歷史對照,才能知道我們的問題所在,知道他人成功的原因所在。不能空想,要腳踏實地,再忙都要找時間讀書。讀書才知道自身的不足,知道域外的豐富多彩。
澎湃新聞:對個人來說,如何從歷史敘述中尋找參照系和養料,甚至能夠進行自己的歷史書寫?
陳恒:我想今天人人都是歷史學家,都在書寫自己的歷史,也記錄這個時代的歷史。而且,人人都是世界史的歷史學家。前面說到要讀書。而讀書有不同的需求和目的。有的人只是泛讀,提高文化修養。在公共層面,應當提倡無用的、休閑的讀書,這個層面的閱讀增加,會提高整個民族國家的文化修養,提升對待世界的看法。
要超過普通民眾的層面,可能就要去讀一個學位。這時讀書的目的和要求就不同了。如果從事學術研究,讀書一定要開卷,開卷就有益,可以獲得驚喜。干坐著不讀書,是什么都想不出來的。但讀書做研究,好比一個人去菜市場買菜,之前得知道做哪幾個菜,需要哪些材料。讀書就要做筆記。如果沒有讀書筆記,就沒有后來的線索。把菜買好之后,還要對原材料進行加工。這意味著,有了讀書筆記要不斷回頭看,要從中理清邏輯順序。最后把文章寫出來,就像做菜,講究程序和火候,要把事情講好,包括邏輯順序、開頭結尾等。
在學科層面,這個訓練過程非常緩慢。學生可能一開始感受不到,過了三五年回頭看,認知水平就大大提高。普通民眾也是一樣,如果全社會都有開放包容的閱讀氛圍,不排斥閱讀,時間久了,國家民族的整個認知就不得了。
澎湃新聞:2025年,您有哪些閱讀和研究計劃?
陳恒:我在大學從事教學科研,也是半個出版人。我有我的閱讀和出版計劃。比如,上海師范大學2024年5月成立了區域國別研究中心,我會參與并策劃一系列的書。我們也做了一系列沙龍,討論要選取翻譯哪些有關區域國別研究的著作,又如何進行原創,等等。我認為,如果只局限在歷史學家筆下的區域國別,只是一些通史、斷代史,其實完全不夠。應該超越歷史學家,形成多學科的區域國別研究。首先要有社會科學學者的參與,有很多需要借鑒的理論方法。另外,還需要有自然科學的參與。這樣,區域國別研究才能到達一個新的層次。
另外,中信出版社今年引入了《哈佛世界史》。我可能會參與其中的工作。還有,202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是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組織編寫的。可以講,是代表了這個時代中國人對世界認知的水平和范圍。前兩年劍橋出了一本《世界歷史中的美國》,其實是從美國出發的全球史,一共四大卷。我會在今年推進其譯介,希望這套書引進之后,對我們也形成沖擊,可以看到美國怎樣看世界,美國怎樣融入世界。
這類出版計劃蠻多。最關鍵的就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世界五千年》。我相信這套書如果成功,會是史學界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貢獻。
當然,也有一些寫作計劃。方向都一樣。我們是這個時代文化的建設者,也是解釋者,既是觀察者,也是未來希望理想的構建者。50年以后,80年以后,100年以后,后人看我們這一代人時,我們做得好與壞、多與少,我感覺倒是其次,只要一些方向性的東西是對的,就不愧于我們這個時代。
澎湃新聞:對當下從事歷史研究的青年學者、晚輩讀書人,您有哪些期待?
陳恒:期待剛才也說了,就是開卷有益。我每天翻大量新書,尤其是歐美的新書。我首先看他們的開頭和結尾。他們擅長敘事,學術著作都用故事說明問題。歷史的著作更是這樣。這是我們當代學術研究中缺少的。以教材為例,我們的教材不善于敘事,更多是在講道理。這是很令人排斥的。我感覺,這是我們教材最大的弊病。當然,我也有這方面的問題。我很羨慕這種學者,打開他的著作,就把你深深吸引了。
很多學者說,我們走出了學徒階段,要有自己原創性的東西。這都是我們的追求。具體到現實發展,還有很多可以商量。換句話說,不能太急。我感覺我們這個社會有時候太急,急了就沒有好作品。需要有一個足夠包容的空間,看準了人就養著他,會給你驚喜的。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