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吳曉明:學(xué)者要深入現(xiàn)實,真正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
【編者按】
上海社聯(lián)2024年度論文已出爐。觀察和研讀最新評選出的10篇年度論文,我們對近一年來上海社科學(xué)者的研究方向會有一個概括性認(rèn)知,既有“全球供應(yīng)鏈重構(gòu)、科技創(chuàng)新機(jī)制、全媒體時代、無形經(jīng)濟(jì)、信息保護(hù)、代際共育”等當(dāng)下時代關(guān)心和關(guān)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也有“歷史書寫、政黨與國家、唯物史觀、中國美學(xué)”等關(guān)系中國學(xué)術(shù)研究的機(jī)理問題。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lián)2013年組織發(fā)起,至今已連續(xù)開展12年。年度論文評選無需作者自行申報,而是依托各學(xué)科權(quán)威專家、學(xué)術(shù)期刊主編、資深學(xué)術(shù)編輯等專業(yè)力量,開展多輪遴選評審。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lián)2024年度論文作者,聽學(xué)者講述數(shù)字時代學(xué)術(shù)研究的堅守和改變,新文科建設(shè)如何創(chuàng)新,以及學(xué)者如何研究真問題,回應(yīng)時代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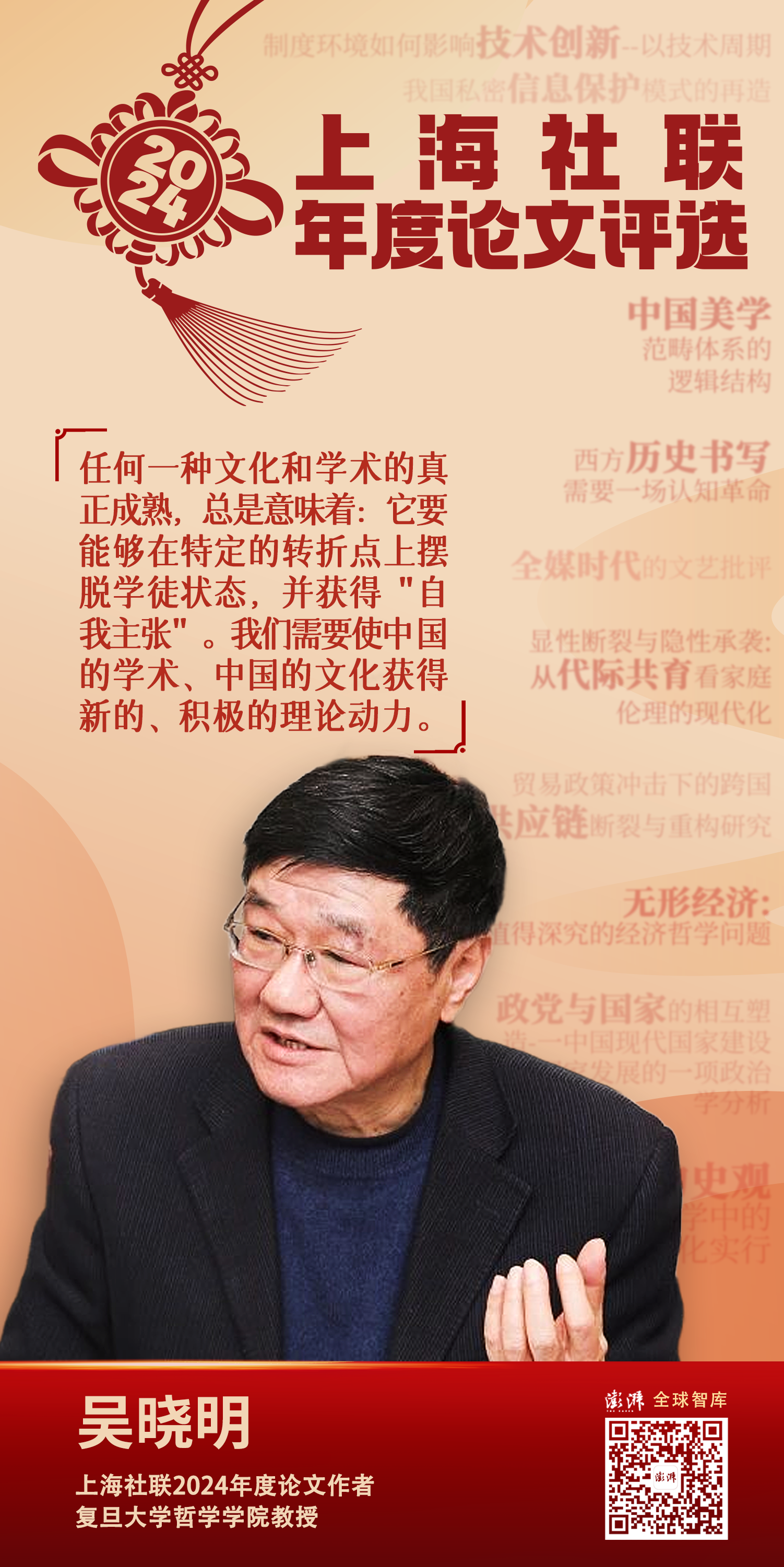
如何看待當(dāng)下世界歷史性的發(fā)展?2025年1月,復(fù)旦大學(xué)哲學(xué)學(xué)院教授吳曉明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如果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逆全球化的過程,而且是在原先代表著現(xiàn)代文明最初的積極動力的地方發(fā)生,并因此有悖全球化擴(kuò)張的本性,這只能意味著,當(dāng)這種文明出現(xiàn)反對自身的癥狀時,它就達(dá)到了自身歷史性的限度。這種變化實際上也是歷史性的。一種年輕的文明往往會進(jìn)行宏大敘事,到了終末階段的文明就會陷入各種細(xì)枝末節(jié)。
在上海社聯(lián)2024年度論文《論唯物史觀在歷史科學(xué)中的具體化實行》(原載于《社會科學(xué)》2024年10期)中,吳曉明提出:“任何一種文化和學(xué)術(shù)的真正成熟,總是意味著,它要能夠在特定的轉(zhuǎn)折點上擺脫學(xué)徒狀態(tài),并獲得‘自我主張’。需要令學(xué)來的普遍者,能夠根據(jù)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來具體化。”
回顧自己的學(xué)術(shù)研究進(jìn)路及“路標(biāo)”時,吳曉明曾表示,當(dāng)馬克思的存在論革命同時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奠基石,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便史無前例地開辟出一條通達(dá)社會現(xiàn)實的道路。近年來,在研究思考中西哲學(xué)的根本差別的同時,吳曉明也在力圖把握中西社會的根本差別,當(dāng)下正在撰寫有關(guān)儒教倫理與中國社會的一部著作。
針對當(dāng)下的技術(shù)浪潮,吳曉明也指出,真正的學(xué)術(shù)研究是無法由AI取代的。如果說,今天的AI能夠幫助人類做很多事情,能夠幫助人類解決很多問題,那么,我們就應(yīng)該更加專注于那些它無法真正取代的——在本質(zhì)上是不可能取代的東西。
中國學(xué)術(shù)需要走出“學(xué)徒狀態(tài)”
澎湃新聞:您與俞吾金等老師,三十多年前就提出,馬克思創(chuàng)建了唯物史觀,并非“辯證唯物主義”。在這篇論文中,仍能看到這一脈絡(luò)。相比多年前的討論,當(dāng)下又有哪些沉淀和發(fā)展?
吳曉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原先教科書上有這樣的區(qū)分,一部分是“辯證唯物主義”,一部分是“歷史唯物主義”。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學(xué)術(shù)界就有很多討論和研究。我認(rèn)為,“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乃至“實踐唯物主義”等術(shù)語,本身都不錯,只是不能局限在先前那樣一種理解框架中。好像兩部分截然分開:“辯證唯物主義”似乎是非歷史的,而“歷史唯物主義”似乎是和辯證法無關(guān)的。這種理解恐怕有問題。
我認(rèn)為,馬克思的學(xué)說,叫“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或“實踐唯物主義”,都是可以的,因為它既是歷史的,也是辯證的,而且是以實踐為基礎(chǔ)的,是一個統(tǒng)一的和有機(jī)的思想體系。我們講唯物史觀,同時就是講辯證法。
近代以來,中國的學(xué)術(shù)進(jìn)入了長期的“學(xué)徒狀態(tài)”。由于現(xiàn)代性開辟出“世界歷史”,現(xiàn)代世界中便形成了這樣的權(quán)力架構(gòu):它使非資本主義的民族從屬于資本主義的民族,使農(nóng)業(yè)的文明從屬于工業(yè)的文明,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在這種態(tài)勢下,中國學(xué)術(shù)從總體上進(jìn)入了“學(xué)徒狀態(tài)”,從而開展出大規(guī)模的對外學(xué)習(xí)——這不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而且是積極的和意義深遠(yuǎn)的。
但是,任何一種文化和學(xué)術(shù)的真正成熟,總是意味著:它要能夠在特定的轉(zhuǎn)折點上擺脫學(xué)徒狀態(tài),并獲得“自我主張”。我感覺到,現(xiàn)在學(xué)術(shù)上的思想理論還準(zhǔn)備不足,需要使中國的學(xué)術(shù)、中國的文化獲得新的、積極的理論動力。
在“學(xué)徒狀態(tài)”中,我們從外部學(xué)到許多普遍的原則或原理。如果把它們先驗地強(qiáng)加到各種對象和內(nèi)容上,就是教條主義。比如,中國革命時期,有過“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口號。這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理來的,也是從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來的,但這種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的運用,最后一定會遭到失敗。
唯物史觀首先表現(xiàn)為一系列的原則或原理。但一部分做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研究的人,不去研究現(xiàn)實的歷史,而是對原則和原理張口就來,僅只停留在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上。一位學(xué)者曾有比喻: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或原理,是教人如何打井,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學(xué)者,從來不去打井,而只是在做打井的PPT。這就是還沒有很好地消化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遺產(chǎn)。
黑格爾在《精神現(xiàn)象學(xué)》中說,哲學(xué)上的原則或原理,即使是真的,只要它僅僅是一個原則或原理,它就是假的。恩格斯晚年也說,現(xiàn)在唯物史觀有很多朋友,但這些朋友是拿了唯物史觀的原則或原理當(dāng)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對于這樣一些模仿者,馬克思早就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當(dāng)下轉(zhuǎn)折的過程中,從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中解放出來,是特別重要的。要擺脫長期以來的學(xué)徒狀態(tài)并獲得自我主張,這就意味著,需要令我們學(xué)來的普遍者,能夠根據(jù)中國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來具體化。這是我寫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原因。
澎湃新聞:您如何評價當(dāng)下的歷史研究?很多敘事是從小人物、女性視角、生態(tài)歷史等角度切入,似乎“顛覆”了大的歷史敘事?
吳曉明:由于長期的學(xué)徒狀態(tài),我們的學(xué)術(shù)往往局限于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上,原則、原理和方法沒有被具體化,而是被先驗地強(qiáng)加在各種對象和內(nèi)容上。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從歷史哲學(xué)的理論上看,宏大敘事和細(xì)節(jié)研究,這種區(qū)分是相對的。如果沒有細(xì)節(jié),所謂宏大敘事就會缺乏根基;而如果沒有宏大視域的觀照,細(xì)節(jié)就可以走向隨便什么地方。如孟子所說,“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足以亂也。”
但從表象的特征來講,年輕的時代總會是宏大敘事,而老年人就會關(guān)注細(xì)枝末節(jié)。正如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曾專門討論過這種表象特征:當(dāng)現(xiàn)代西方文明處在年輕的開端時,17世紀(jì)、18世紀(jì)的思想家都是宏大敘事的。但20世紀(jì)之后,特別是一戰(zhàn)之后,敘事方式就發(fā)生了改變。
因此,這種變化實際上也是歷史性的。一種年輕的文明往往會進(jìn)行宏大敘事,到了終末階段的文明就會陷入各種細(xì)枝末節(jié)。如果從大和小的方面講,經(jīng)濟(jì)學(xué)也有宏觀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微觀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上應(yīng)該是能夠彼此配合的,當(dāng)它們這樣被分割地談?wù)摃r,大體意味著正在轉(zhuǎn)向歷史發(fā)展特定狀態(tài)的一種終結(jié)階段。斯賓格勒就把文化的早期階段叫做“大地”,把文明的最終階段叫做“僵化的世界都市”。尼采也曾說過,生命終結(jié)處,必有規(guī)則堆積。文明初發(fā)時,是朝氣蓬勃的;到了終末,細(xì)小的規(guī)則就會出現(xiàn)并占主導(dǎo)地位。
分清“現(xiàn)實”與“事實”,客觀看待“逆全球化”與“民粹主義”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如果馬克思看到當(dāng)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力量相互交錯,會如何評價這一局面?
吳曉明:馬克思的學(xué)說是高度歷史性的。它不會認(rèn)為某種狀態(tài)是永恒的。馬克思曾批評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說,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把歷史的事物看成抽象普遍的,看成自然規(guī)律,實際上只是在祝福現(xiàn)存事物的永垂不朽。
這就意味著,要在歷史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馬克思說,如果我們要了解,為什么11世紀(jì)遵循權(quán)威的原則,18世紀(jì)遵循平等的原則,那就必須研究11世紀(jì)和18世紀(jì)的人分別是怎樣的,他們分別如何進(jìn)行生產(chǎn),并且在生產(chǎn)中結(jié)成什么樣的社會聯(lián)系。
總體而言,現(xiàn)代性就其開端的本性而言,是全球化的。以往那種地域性的歷史、民族性的歷史結(jié)束了,整個世界形成普遍聯(lián)系,各種商品導(dǎo)向全球,構(gòu)成世界的歷史和世界的市場。任何一個民族,如果不想滅亡,就一定要被卷入現(xiàn)代世界的歷史進(jìn)程中。但如果說,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逆全球化的過程,而且不是在我們理解的比較不發(fā)達(dá)的地區(qū)發(fā)生,而是在原先代表著現(xiàn)代文明最初的積極動力的地方發(fā)生,那么,這只能意味著,當(dāng)這種文明出現(xiàn)反對自身的癥狀時,它就達(dá)到了自身歷史性的限度。
馬克思會說,當(dāng)這種自相矛盾發(fā)展起來時,這種文明便達(dá)到了它的終結(jié)階段。這是從哲學(xué)上來講的。我們決不能說,終結(jié)階段會是10年、20年,或是50年,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但他會從歷史的本質(zhì)進(jìn)程和必然轉(zhuǎn)變來思考這個問題。
澎湃新聞:當(dāng)下全球?qū)用嬗蟹N“民粹崛起”的趨勢。我們做傳播時,也經(jīng)常需要面對這一類挑戰(zhàn)。在您看來,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對此進(jìn)行評價?這類人是否可被視為無產(chǎn)階級?
吳曉明:這些人不是無產(chǎn)階級,至少不是現(xiàn)代無產(chǎn)階級。馬克思講過,羅馬就有過流氓無產(chǎn)者,他們只是一種反社會的因素。目前用的術(shù)語,叫做“民粹主義”。究竟應(yīng)當(dāng)怎樣來理解,需要專門的研究。但與此相關(guān)的情形,黑格爾和馬克思也都洞察到并且討論過了。
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xué)》中,談到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家庭是倫理實體。它的原則解體之后,才出現(xiàn)以原子式的個人為前提的“市民社會”。但這樣一種社會聯(lián)系,按照黑格爾的看法,實際上是“壞的主觀性”——每個人都有其任意性,從而形成“市民社會”,即“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它最終會陷入自行解體。因此,黑格爾要求國家把它的實體性加給市民社會,從而為“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劃定界限。
但馬克思的觀點則不同。馬克思說,不是國家能夠規(guī)定市民社會,相反,是市民社會規(guī)定國家。因此,在這樣的市民社會基礎(chǔ)上的國家,是一個抽象的、虛假的共同體,這最終會使國家陷于崩潰。看來馬克思說得對。現(xiàn)在西方的情形正是這樣。政客每天向民眾不停許諾,能不能做到,不知道。政治國家的實體性被“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所掏空。
馬克思的觀點是,雖然政治國家不可能把實體性賦予市民社會,但是,當(dāng)市民社會發(fā)展到歷史性的限度并開展出新文明的可能性時,就會重新構(gòu)建起超越“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的社會形態(tài)。
這里并不是要用馬克思的理論完全解說今天的現(xiàn)象,但從歷史出發(fā)所做的這類闡明,恐怕應(yīng)該成為我們今天進(jìn)行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的一個指南和方法。
澎湃新聞:人們要理解歷史,如何識別那些“在其開展過程中表現(xiàn)為必然性”的內(nèi)容?
吳曉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xué)者,天天講要聯(lián)系現(xiàn)實。但“現(xiàn)實”這個術(shù)語,和一般所講的“事實”是非常不同的。按黑格爾的說法,“現(xiàn)實”是本質(zhì)與實存的統(tǒng)一,是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但我們現(xiàn)在的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似乎自信滿滿地立于自認(rèn)為是最可靠的“事實”——即單純實存——的基礎(chǔ)上,既不要求本質(zhì)的東西,也不要求必然性。“事實”是通過知覺可以直接給予我們的,但“現(xiàn)實”要求抓住本質(zhì)的和必然的東西,所以是很高的理論要求。
比如,黑格爾說過,如果只站在“事實”立場上,那么拿破侖的傳記似乎應(yīng)該由他的仆人來寫,因為仆人知道的事實最多——拿破侖哪天喝了什么酒,和什么人鬼混,等等。但仆人只知道這些事實,而不知什么是本質(zhì)的東西。如果我們要看到的不是事實堆積起來的拿破侖,而是現(xiàn)實的拿破侖或拿破侖的現(xiàn)實,那就不能讓仆人來寫他的傳記。講到這一點時,黑格爾說,我必須引用歌德的話,“仆人眼中無英雄”;不過還要加上一句,“那不是因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為仆人畢竟是仆人。”這就是說,拿破侖的仆人只能看到許多事實,但卻看不到本質(zhì)的東西,看不到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
我們今天要研究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社會,恐怕都是這樣。歷史理論真正的核心是社會現(xiàn)實,而“現(xiàn)實”既是實存又是本質(zhì),既是展開過程又是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這時才真正談得上所謂現(xiàn)實的歷史或歷史的現(xiàn)實。
真正的學(xué)術(shù)研究是無法由AI取代的
澎湃新聞:當(dāng)下人們都在面對海量信息,更需要一些抽象性的概括。比如用AI去閱讀,甚至生成論文。但實際上,這可能會讓人離“現(xiàn)實”更遠(yuǎn)。如何運用技術(shù),才能讓人更好地進(jìn)入一種更為通達(dá)事物實體性內(nèi)容的思考狀態(tài),達(dá)成更為主動的行動?
吳曉明:AI技術(shù)確實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意義非凡,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改變我們對生活世界的理解。但它是有限度的。哲學(xué)是批判的,“批判”的意思是澄清前提和劃定界限。現(xiàn)在,對AI的許多說法,卻是完全非批判的。AI雖然對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商業(yè)的擴(kuò)展是有重大推動和積極作用的,但如果缺乏前提的澄清和界限的劃定,就會變成一種“神話學(xué)”,而這種神話學(xué)反而在學(xué)者當(dāng)中尤為流行。
AI所解決的并且所能解決的問題,乃是分析理性中的可計算性的部分。比如,對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系統(tǒng)的要求包括,能夠主動找事情做,還要有特定的價值觀。這兩條就不是通過可計算性能做到的。人的思維中,只有一部分是分析理性,是可計算性,還有大量的包括熱情、激情、想象力、以及審美能力等諸多方面,則不是通過可計算性能夠解決的。
至于應(yīng)該怎樣來使用的問題,我想,AI技術(shù)有自身發(fā)展的邏輯,會產(chǎn)生出自身一系列的后果。我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它是有界限的,首先是倫理學(xué)上的界限,同時還有它在哲學(xué)中被理解和把握到的界限。AI應(yīng)用可以減輕人的許多勞動,特別是智力勞動,但在本質(zhì)上,它和人的勞動是有差別的,因為后者是無法完全用可計算性來代替的。
現(xiàn)在AI技術(shù)的發(fā)展,都集中體現(xiàn)在形式上,而與實體性的內(nèi)容無關(guān)。因為可計算性本身就是純形式的。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它確實給人帶來很多方便,但如果人不是主動地去思考,那么思想的本質(zhì)便無法真正呈現(xiàn)于其中。因此,真正的學(xué)術(shù)研究是無法由AI取代的。如果說,今天的AI能夠幫助人類做很多事情,能夠幫助人類解決很多問題,那么,我們就應(yīng)該更加專注于那些它無法真正取代的——在本質(zhì)上是不可能取代的東西。
當(dāng)然,很多歷史性的發(fā)展,會在事實上導(dǎo)致異化現(xiàn)象,而在異化狀態(tài)下,人會失去自我,喪失主動性。但這也是必經(jīng)的階段。只有當(dāng)它發(fā)展到特定階段,能夠產(chǎn)生出否定自身的那些新的因素時,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才會真正出現(xiàn)。
所以,如果說AI是有界限的話,而我們要在某些方面更多地保持自我,那么我想,當(dāng)AI的運用令實際工作變得更加輕松,并且導(dǎo)致工作日的縮短和自由時間的增多時,我們倒是可以更多地去搞“琴棋書畫”——這當(dāng)然只是一個比擬的說法,意思是說,可以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留出廣大的空間。
澎湃新聞:德國古典哲學(xué)、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哲學(xué),或是中國古典詩詞,哪個更能令您從中得到精神安慰?
吳曉明:確實,我們的頭腦和思想有很多部分。哲學(xué)理論是我?guī)资陙淼墓ぷ鳌K埠苡幸馑迹笏季S的高度緊張,實際上是需要專注的。
馬克思曾講到,并不是說人們從事一種自由的勞動,就會變得疲疲沓沓無所事事。比如,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一幅畫或一首詩,是要高度專注的。我在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工作,也需要高度專注。適度的緊張是非常有益的。我做老師四十多年,走進(jìn)教室前還是有點小緊張。我問過王德峰老師(復(fù)旦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他也一樣。如果一個老師百無聊賴、松松垮垮地跑到課堂上去,恐怕并不是什么好事。
詩詞文學(xué)我歷來非常感興趣。我們哲學(xué)學(xué)院也有傳統(tǒng),甚至做西方哲學(xué)的孫向晨教授、丁耘教授等人,還有專門的讀書班,討論的是《左傳》《讀杜心解》等。我說,你們很有意思。他們說,這是“人的全面發(fā)展”。
在藝術(shù)的領(lǐng)域中,特別是審美的、想象力的東西要得到發(fā)展和擴(kuò)張。如果完全局限在某種可計算的領(lǐng)域,人就會變得枯燥乏味,而且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異化了——不是去把握那個東西,而是被它所控制。但這也得在歷史發(fā)展的某個階段上才能被積極糾正。當(dāng)一種新的可能性在歷史性的進(jìn)程中真正出現(xiàn)時,才能完成這一轉(zhuǎn)變,使人能夠清晰地認(rèn)識到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們的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要能夠使普遍者得以具體化
澎湃新聞:2025年,您有哪些閱讀和研究計劃?
吳曉明:我認(rèn)為,要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根本區(qū)別,就必須進(jìn)入到哲學(xué)。所以我花了幾年時間,做了中西哲學(xué)之根本差別的研究。進(jìn)而言之,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樣一種哲學(xué)上的差別,實際是有它的現(xiàn)實基礎(chǔ)的,即中西社會的根本差別。
我接下來要做的研究,就是力圖把握中西社會的根本差別。我準(zhǔn)備了多年,打算寫一部書,叫《儒教倫理與中國社會》。中國的倫理和社會,同西方的倫理、基督教文明,特別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有極大的區(qū)別。這一點如果能被很好地把握,那么,建立在不同社會之上的政治的、法的、道德的、意識形態(tài)的巨大差別,就可以在其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目前形成了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是,西方社會,特別是現(xiàn)代西方社會,其前提條件乃是原子式的個人;但中國社會不存在原子式的個人——這是理解中國社會的鑰匙。第二是,中國社會正在發(fā)生重大的轉(zhuǎn)型,但這種轉(zhuǎn)型的可能性在于中國社會成為“市民社會”的不可能性——這是它的界限,
如果追蹤到古希臘,那么家庭原則的解體,在蘇格拉底的時代就逐漸開始了。黑格爾說,自從主觀性在基督教中開花以來,已經(jīng)過去了1500年,而所有權(quán)的自由對我們來說仿佛還是昨天的事。這意味著,世界歷史在其展開過程當(dāng)中要達(dá)到它的自我意識,需要經(jīng)歷很長的時間,這也告誡諸位,稍安勿躁。
在黑格爾(以及馬克思)看來,1500年的基督教教化才歷史地形成原子式的個人。“市民社會”不僅以原子式的個人為前提,而且要求與政治國家的決定性分離。而這兩條在中國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當(dāng)中,如果仔細(xì)觀察并加以分析,實際上都不存在。我的研究大體聯(lián)系著中西社會的歷史線索,形成了兩個初步的觀點。如果進(jìn)一步研究材料并進(jìn)一步思考,可能還會有更多想法。
還有一點很重要,是儒教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的關(guān)聯(lián)。為什么中國人易于接受馬克思主義?有一種研究的說法是,因為德國17世紀(jì)和18世紀(jì)的哲學(xué)家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特別欣賞中國文化,馬克思的學(xué)說又銜接著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脈絡(luò),所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便有某種親緣關(guān)系,中國人就比較容易接受。其實這恐怕完全不對頭。
如果說,中國社會沒有出現(xiàn)原子式的個人,以及由原子式的個人組成的所謂市民社會,那么,它的“精神”就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的。當(dāng)然,這并不是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講的科學(xué)社會主義,而是比較原初的、未經(jīng)分化發(fā)展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當(dāng)中國社會不可能成為完全由原子式的個人組成的社會時,實際上就不是以個人為本位的,而是以社會為本位的,亦即在這樣一種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精神”。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儒教倫理與社會主義存在一種親緣關(guān)系。
澎湃新聞:對當(dāng)下的青年學(xué)人,您有哪些期待?
吳曉明:我覺得現(xiàn)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黑格爾哲學(xué),或者其他哲學(xué)的,都不能夠停留在抽象的原則或原理上。我們的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要能夠使普遍者得以具體化,也就是說,要能夠使普遍的原則或原理根據(jù)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來具體化。這就要求我們深入到社會的現(xiàn)實之中,特別是要去真正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yè)務(wù)經(jīng)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yè)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