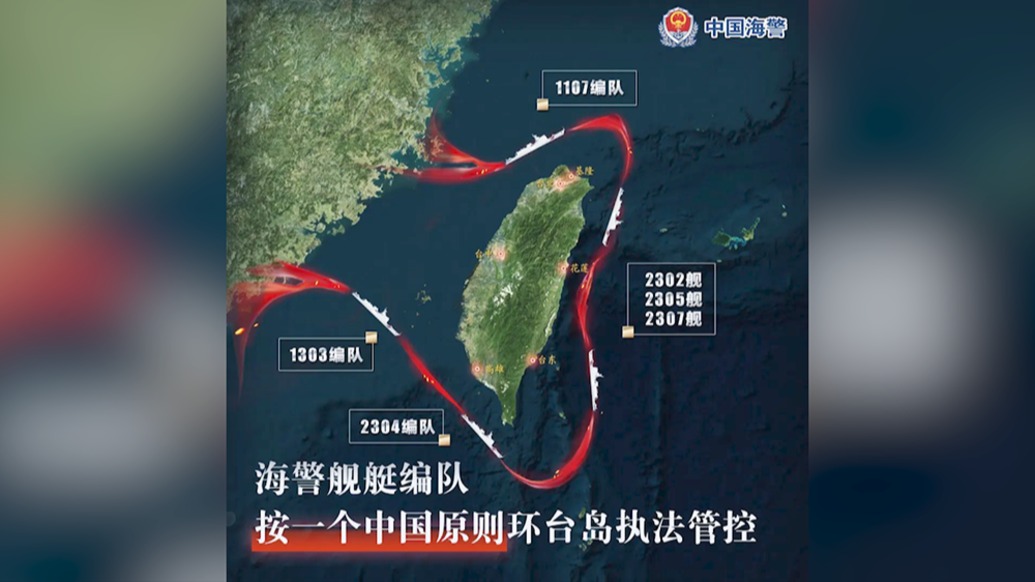- +112
楊念群:重提政治史的重要性與中國的“大一統(tǒng)”
2024年10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受邀出席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文研書問”活動,與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研書問”特邀主持人舒煒圍繞《“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tǒng)”觀的形成與實踐》的寫作構思、對話對象、所涉核心觀點及概念等展開對談。本文由本書策劃編輯章穎瑩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審校中心主任張利雄審校,內容經楊念群、舒煒審定。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經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授權刊發(fā)。

舒煒:本次“文研書問”活動,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楊念群教授來談談他的著作《“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tǒng)”觀的形成與實踐》。這本書從2022年9月問世到現(xiàn)在正好兩年,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為這本書還開過研讀會。我感覺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拓展,這本書的序論、余論,以及中間幾個大的部分,關于清朝“大一統(tǒng)”觀的形成和實踐,甚至還涉及中國歷代正統(tǒng)觀、“大一統(tǒng)”觀。楊老師的治學路數(shù),首先是比較重視思想史和觀念史。其次,楊老師比較重視中國的政治史,特別是強調政治史和思想觀念史不能做簡單的硬性分割,尤其是落實在清代研究上。楊老師一直關注清史的問題,“大一統(tǒng)”觀念是這本書非常突出的核心關切,這應該被視為非常有理論抱負的清代研究專著。這本書力圖提出一些史學研究的方法論,目標指向大概也有針對目前史學研究的某種“不滿”,希望提出新的看法以及實踐的方法,所以這本書的啟發(fā)性還是相當大的。請楊老師談一下您就這本著作的構思和大致想法。
楊念群:非常高興到“文研書問”聊天,我跟舒煒兄也是老朋友。我從《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tài):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tǒng)觀念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一直到《“天命”如何轉移》這本書的寫作,中間有一種連續(xù)性。到了這本書,我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想法:我想把政治史的重要性重新提出來,因為中國的政治對老百姓影響非常大,從古至今都是如此。史學發(fā)展到現(xiàn)在有不少其他新的領域出現(xiàn)了,包括中國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還包括一些新的分支,比如醫(yī)療史、生態(tài)史這些都崛起了,所有這些興起的史學門類或者專業(yè)領域,都要跟政治關聯(lián)起來才有更重大的意義,所以我一直特別強調中國政治史的核心重要性,尤其是清代的政治史特點是非常鮮明的,跟以往政治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有非常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清朝滅亡之后,緊接著就是民國,民國經歷了短暫的幾十年,馬上就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所以清朝歷史跟我們目前整個的形勢和國家發(fā)展的方方面面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清朝變成我們當下最方便借鑒的一個朝代,如何把握清朝的政治結構和特點,變成我們現(xiàn)在清史研究最重要的核心任務,其他都是圍繞這個目標進行的。《“天命”如何轉移》這本書實際上就是要從如何把握清朝的特點、特性入手,其中用了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大一統(tǒng)”。我認為,要更精準地概括清朝歷史,沒有比“大一統(tǒng)”更合適的概念,當然清朝還有很多其他的特點,但“大一統(tǒng)”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關鍵詞。
舒煒:我們多多少少都了解通常的“大一統(tǒng)”“正統(tǒng)論”,特別是通過20世紀90年代饒宗頤先生那本對咱們影響還挺大的《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后來當然明白用西方術語來說,這就是政治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問題。中國歷史上常常討論政道和治道,實際上“正統(tǒng)論”是很典型的關于正當性的討論。這本書中,特別是第一章提出這個問題,先談了“正統(tǒng)”“大一統(tǒng)”在整個中國歷史從春秋以來,不同時期有不同方向的演變,在北宋、南宋時期,春秋“大一統(tǒng)”也重新發(fā)芽,朱熹專門讓自己的學生來做這個題目,但這個題目的核心含義“大一統(tǒng)”變成了夷夏。這本書對我個人啟發(fā)特別大的一點,就是指出清朝之后,尊王反而很有漢學含義。實際上您在解決漢宋問題的演變,就清朝怎么轉成漢學有很多討論,好像是反宋學的。但這本書提示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面相,等于把夷夏又轉回了尊王論,是否可以這么說?
楊念群:對,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變。所以僅僅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討論漢宋的轉移是非常狹隘的,因為在學術層面討論漢宋之爭不是一個政治命題,如果我們把漢宋之爭放在古代所謂的政治正統(tǒng)性的脈絡之中可能更有意思。我覺得政治正當性和政治合法性是現(xiàn)代概念,因為有了現(xiàn)代法律體系才能講合法性,古代就是講正統(tǒng)性,一個政權要想獲得正當性,就必須為自己尋找到一個理由,或者說政權建立的根據(jù)。所有漢宋之爭都是圍繞政權的正統(tǒng)性展開的。我就是想突破僅僅從思想史脈絡討論漢宋之爭這類問題,必須把這類問題轉換成政治史的討論,否則思想史本身的深層意義就很難表達出來。你剛才提到這本書的第一章,我確實做了一個梳理。第一章是提出問題,比如說跟“中國”“天下”這類概念的關聯(lián)和區(qū)別。第二章是把整個“大一統(tǒng)”跟“正統(tǒng)”的內在聯(lián)系及其在不同朝代的表現(xiàn)做了一個梳理,這個梳理其實挺重要,因為在不同時期,兩者的關系均有巨大的轉變。一開始正統(tǒng)性的建立是從先秦開始萌芽的,實際上就是關于“元”和“始”的問題。一個政權的正當性如何跟上天建立關系是被重點關注的問題,也就是所謂承接“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到后來有所分化,我們知道周王的權威到了春秋時候其實已經被逐漸瓦解掉了,所以為什么儒家在春秋時代擁有了孔子所倡導的人文氣質,這是因為儒家慢慢喪失了其扮演為王者溝通上天和人世的中介角色的權力。儒家最早實際上我們知道有點像跳大神的巫者,負責為王者獲取“天命”的支持而服務。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周王權威崩解,孔子及其繼承者只好依靠私人授徒傳習周禮來維系這個使命。這并不是官方的行為,私人授徒只能表現(xiàn)為一種人文意義上的學問傳承。體現(xiàn)人文氣質的這套春秋時期的儒家學問已遠離了最初儒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著其最初的使命感已經完全消失,所以我一直認為所謂如何為王者獲取“天命”的這套原始技能其實在儒家思想里面仍占據(jù)著重要地位。
后來到了漢代,董仲舒的突然出現(xiàn)改變了儒家思想的人文格局,他恢復了原始儒家屬于神人大巫的這部分角色,最后孔子變成漢代統(tǒng)治者承接“天命”的預言家了。孔子變成了沒有實際權力的素王。漢代出現(xiàn)了一些神話比如有一些讖緯,就是偽造的經書,說孔子完全是一個神人,因為董仲舒自己就會行禹步,能求雨。所以你看他的形象跟先秦的孔子完全不一樣。到漢代儒家對“天命”的解釋完全是要解釋所謂權力的正當性問題。已經人文化的孔子不談論這類問題,他只是從建立道德人倫的角度去解釋儒家的要義,很少談論王權如何建立正統(tǒng)性的問題。直到董仲舒寫出《春秋繁露》之后,儒家思想就變得特別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了。所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理論,包括帶有方士化色彩的儒家發(fā)布的一系列帶有預言性質的言論,我均稱之為具有原始儒家特色的政治神話,這就是在漢代建立起來的。但是到了宋代,儒家思想突然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轉折,那就是漢代“大一統(tǒng)”思想受到了很大沖擊。董仲舒代表的新儒家實際上是最喜歡談論“大一統(tǒng)”的,因為談論“大一統(tǒng)”很容易為漢武帝開疆拓土提供一個非常正當?shù)睦碛桑环矫嫒寮覟閯⒓耶敾实厶峁┮粋€神圣的理由,另一方面漢代皇帝所有開疆拓土的行為都是承天受命的結果。
可是到了宋代之后,這個論述方式卻面臨著巨大挑戰(zhàn)。按饒宗頤先生的說法就是北宋還提倡尊王的重要性,到了南宋卻開始轉變成了強調“攘夷”。因為北宋疆土還算比較遼闊,到了南宋則大幅度縮窄,可憐到只龜縮在了東南一隅,這樣一來再談“大一統(tǒng)”就完全沒有根據(jù)。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必然要發(fā)明一種新的道統(tǒng)幫助宋代帝王構建自己的一套文化優(yōu)勢,來跟北方的遼金政權對抗。像你剛才說的“大一統(tǒng)”的問題被迫轉化成了一套“辨”的問題了,而不是原來的“大一統(tǒng)”問題,宋代儒家通過種族區(qū)隔來建立文化優(yōu)勢。到唐代韓愈那時候才有道統(tǒng)之說,原來儒家根本沒有道統(tǒng)的概念,即便到了北宋,道統(tǒng)傳承的脈絡也不十分明顯,到了南宋儒家道統(tǒng)傳承的譜系才日漸明晰。道統(tǒng)的建立實際上跟宋代缺乏“大一統(tǒng)”的政治整合能力息息相關。到了南宋之后,這種思路就更加走向極端,變成用夷夏的差異來轉換“大一統(tǒng)”話題。道統(tǒng)把“大一統(tǒng)”話題一旦轉換之后,“大一統(tǒng)”的本意基本上就被遮蔽掉了,這是從北宋到南宋特別明顯的一個轉變。
到了明代,想恢復“大一統(tǒng)”的正當性,但明代統(tǒng)治者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北邊有元代殘余勢力的持續(xù)威脅,東北則興起了滿人貴族統(tǒng)治集團政權。其實明代整體的政治生態(tài)跟南北宋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必須不斷和北方少數(shù)族群進行拉鋸式的對抗,所以明代在思想意識形態(tài)方面同樣比較強調華夏族群的優(yōu)越感,同時強化擁有道統(tǒng)的優(yōu)越性,以補償軍事實力的缺失。“大一統(tǒng)”在帝王的思想脈絡中也只能優(yōu)先讓位于夷夏的話題,而無法把疆域廣大作為統(tǒng)治正當性的基礎,因為宋明并不具備一統(tǒng)天下的現(xiàn)實條件。但是到清代以后,歷史劇情卻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反轉,那就是清朝實際統(tǒng)治的疆域遠超以往的大部分朝代。清朝皇帝為什么在思想領域里特別強調要回到漢代?就是因為清帝覺得在開疆拓土的規(guī)模和能力方面擁有類似漢武帝那樣的底氣,也不輸任何其他朝代。這也導致清代思想所關注的話題發(fā)生了轉移。這個轉移的背景就是清帝不僅在疆域占有方面擁有了超越前代帝王的自信心,而且這種疆域擴展是建立在包容多民族共處一個空間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清朝有別于前代的特點。一旦擁有這樣的自信,清帝下一步必然就要開始收編宋明儒家所擁有的道統(tǒng)。因為清帝不能容忍在皇權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的思想領域,只有把道統(tǒng)整合進“大一統(tǒng)”的框架之內,清帝才能完全克服道統(tǒng)背后的“夷夏之辨”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壓力。因為清朝皇帝畢竟以滿人貴族身份入主大統(tǒng),并不是明代漢人政權理所應當?shù)睦^承者,他必須為自己政權的正當性尋求一個非“夷夏”對立的解釋框架,從某種意義上說,漢代儒家的思想資源可以作為一個相對有利的工具加以利用。所以清帝創(chuàng)造了一個能夠融合多元族群訴求的新型“大一統(tǒng)”思想邏輯。
因此,我們談漢宋之爭,如果只是在思想史內部進行討論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或者說如果只是把漢宋轉型當作一種思想史的“內部理路”,或者把清代思想史視為一種從宋明的“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移,那只不過仍停留在一種表層現(xiàn)象的描述而已,并沒有抓住清代思想史轉變的關鍵意義之所在。可是如果從清代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下來理解漢宋之爭的意義,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我認為,所謂漢宋之爭應該被置于清朝皇帝建立其有別于以往朝代的正統(tǒng)性這個角度來加以理解。也就是說,清代思想出現(xiàn)了向漢代思想復歸的跡象,這并非出于士人的自覺選擇,而是清代皇帝有意規(guī)劃的結果。清帝對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思想觀念的變化有自己的一套整體規(guī)劃,并不是一個思想史內部的轉移所能解釋。比如康熙時代還尊崇朱子學,到了雍正帝時期就開始隱隱意識到“尊朱”不利于滿人貴族政權正統(tǒng)性的建立,因為朱熹極力主張夷夏之辨,反對金人對宋代疆土的侵犯,滿人是女真人的后代,如果一味提倡尊朱,等于肯定朱熹對女真人的排斥和歧視,難以自圓其說。所以雍正帝開始反思宋明士人排斥夷狄所造成的后果,極力消除種族區(qū)隔的影響。乾隆帝開始直接質疑朱熹的言論,有意安排思想界鼓吹反向超越宋代,回到漢代,其實不僅出于思想本身的考慮,而是把漢宋之爭當作一個政治問題加以處理,這也決定了清代思想史演變的大方向。清代思想向考據(jù)學的轉變并非如梁啟超所說是因為帝王屢興文字獄,導致士人紛紛選擇了比較安全的考據(jù)學方法,借此逃避政治的迫害,反而恰恰是皇權有意規(guī)劃和設計的結果。漢代經學背后的依托就是“大一統(tǒng)”的政治邏輯,也是帝王建立其正統(tǒng)性的理論支柱,所以考據(jù)學背后的深層關懷就是如何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尊王”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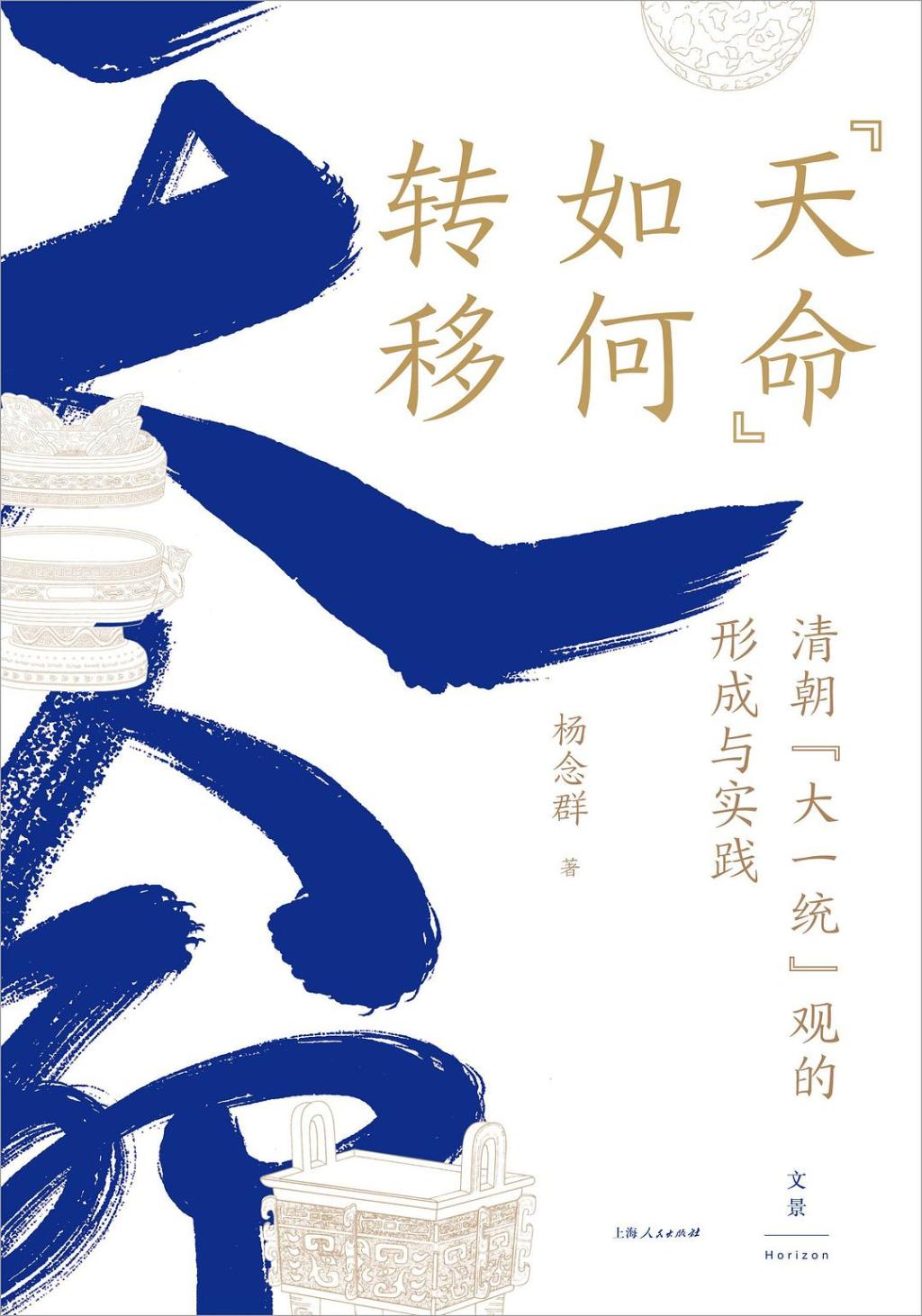
舒煒:您在書中也討論什么叫“清朝的統(tǒng)治”。您采用的“大一統(tǒng)”概念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框架,這本書探討“大一統(tǒng)”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應對清朝歷史解釋中強有力的既定框架。另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tǒng)政治史的挑戰(zhàn)。您比較強調君主帝王的核心意義,政治史很容易變成君主制度或者官制制度史的研究,但這并不是研究所謂的帝王心術,帝王的考慮涉及道統(tǒng)、學統(tǒng)、政統(tǒng)方方面面更幽微的地方。清朝的幾位君主能夠貫穿學統(tǒng)、道統(tǒng)等各個方面,不是只單純考慮治理邏輯的問題。
此外,就多民族統(tǒng)一這方面,您留了一個很大的線索,但沒有著力闡述。這實際上構成“大一統(tǒng)”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如何構想“中國”的多元一體,另一方面就是科舉,科舉有很強的“大一統(tǒng)”的實踐作用,包括您在書里特別提到在西南地區(qū)的科舉和推行教養(yǎng),這都是君主跟學者、士大夫共享一個觀念和行動框架。我覺得您在這本書中關于教養(yǎng)的、關于君主的觀點,都特別值得講一下。關鍵好像您對史學界的通行觀點有所不滿有所批判,是嗎?
楊念群:批判談不上,但多注重帝王之學的研究也是近幾年我特別主張和提倡的,因為帝王的重要性在古代文化基因里就已形成了,最早以周王為中心形成了一套禮儀等級秩序,這個等級體系在不同的時代有所變化,但一直沒有發(fā)生根本動搖。我們討論所有的問題不能像西方那樣,因為西方后來經過民主制度改革之后,經歷了一個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在這個體系之內,考慮更多的是資源如何被平等地合理配置的問題,而我們中國幾千年都是以帝王為中心由上往下分配資源的,帝王承天受命跟老百姓發(fā)生聯(lián)系,沒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夠動搖這個核心,或者瓜分他的權力。不像西方有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慢慢產生影響之后,就削弱和分割了世俗君主的權力,世俗君主必須通過競爭和博弈來與教宗劃分資源。所以我們在中國談所有的問題都必須要圍繞帝王這個中心來考慮。
近幾年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的誤區(qū),好像看待什么問題都要自下往上才具有正當性,這種視角當然有一定的道理,因為我們原來太不注重基層運行的基本狀況了。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史學出現(xiàn)了一個重大轉向,就是社會史研究的興起,紛紛主張從下往上觀察歷史動向,涌現(xiàn)出了許多出色的成果。但物極必反,又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太強調底層社會和民眾本身的意義了,我們圍繞“社會”這個關鍵詞所形成的概念解釋都來自西方,比如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等概念,一旦挪用到中國大多水土不服,卻變成了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因為中國本身沒有市民階級,公共領域就沒有依托。西方市民階級的崛起與資產階級形成了對君主和貴族的抵抗格局密切相關,資產階級通過劃分和確立邊界明確的固定空間比如咖啡館等,建立起了反抗貴族的陣地,所以有人說資產階級革命就是一場所謂咖啡館革命,咖啡館里面就形成了一個公共領域,由下往上攻擊上去,終于推翻了貴族和君主的統(tǒng)治。其中宗教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基督教往往是城市地方自治組織的母胎,很多世俗意義上的市民自治和法律原則都是從基督教里面引申出來的。現(xiàn)在有一個普遍的誤解,似乎文藝復興運動的主題就是要回到古希臘羅馬的人文傳統(tǒng),這其實多少把文藝復興的思想來源給狹隘化了,其實中世紀的宗教思想和制度,同樣是孕育近代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源頭,包括現(xiàn)代個人主義和平等觀念的興起都與基督教思想密切相關。因為只有大家面對同一個上帝才能做到地位平等,由此才能生發(fā)出真正的平等觀念,只有每一個個體都單獨面對上帝才能獲得自由,如果你不面對上帝,必然要面對世俗世界的某一群人或者某一個世俗單位,最后往往決定你命運的人只能是家長或者君主。現(xiàn)在社會史提倡研究老百姓的生活,研究底層組織,當然有它的正當性,但研究前提是建立在西方已經實現(xiàn)民主制度之后,人民已經無可置疑地具有重要性的基礎之上,并以此作為參考坐標來反向觀察中國歷史,這常常容易造成一種時代錯位的感覺。所以民眾的重要性作為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沒人會加以質疑,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民眾的地位始終得不到承認,也就自然缺乏研究其活動的確切理由。因為民眾往往被淹沒在整體等級制的脈絡里面,即使偶有閃光也是曇花一現(xiàn)。在歷史上,如果民眾跟君主相比,君主的重要性肯定大于民眾,因為歷史記載就是以帝王為中心展開的,這是第一個我想要討論的問題。
第二,如果是這樣,它治理的方面就很重要了,也就是科舉制。科舉制是上下循環(huán)的體制,是把上層跟基層社會,包括城市與鄉(xiāng)村打通的體制。我們沒有什么基督教和教會分割權力,我們只能通過循環(huán)再分配權力的過程,使得上下權力打通,讓民眾的利益多多少少有機會得到相對合理的分配,同時為底層的相對自治保留一定的余地,科舉制就是起的這個作用,所以我們原來對科舉制的理解是錯誤的。以往總是從教育的角度把科舉狹隘地理解為是一種考試制度,動不動就說八股文多么害人,科舉制被妖魔化成完全是折磨人的腐朽制度。其實科舉制除了考試之外還是一個政治制度,一個人在鄉(xiāng)里考上秀才就有了一個特殊身份,在村里享受免賦稅或勞役的待遇,在村里地位很高。但秀才出不了村,只能在村里搞搞教學和慈善事業(yè),比如辦私塾,修橋鋪路,等等,或者當一個宗族族長,給老百姓做點事,如果你考中舉人就有機會出村了,可以去當一個縣令,考中進士就可以進入翰林院當中央官員。同時科舉制又是一個循環(huán)體制,因為官僚的祖廟都在家鄉(xiāng),出于孝道的考慮,很多官員一旦退休就會回到家鄉(xiāng),這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huán),這是相對合理的制度。
舒煒:我感覺書中提到的一些概念都很有意思,包括“紀綱”這個詞,“紀綱”給人感覺像憲法似的。這實際上可以結合您以前的專著《何處是“江南”?》來談,皇帝怎樣面對文人士大夫和學者、官僚,他們重新且共同來面對地方社會的時候,可以處于不同的邏輯,但背后還是有一些共同性,比如君主和士人的關系。您在《“天命”如何轉移》中也提及這點。
楊念群:如果從這方面來看,可能《“天命”如何轉移》里關注的問題跟我在《何處是“江南”?》那本書里闡述的觀點有點相互銜接,我曾經有一個想法,就是把帝王帶回到中國古代知識系統(tǒng)的研究里面,帶回到士大夫研究里面來。有一陣子,學界研究帝王和士大夫的關系,往往把他們看成是二元對立的,強調“以道抗勢”和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之爭。一方面我認為清朝帝王把道統(tǒng)收編到治統(tǒng)中,變成治道合一的全能權力中心,另一方面這個收編的過程非常復雜,在這個過程中,我不把帝王僅僅看作權力主體,他還是思想主體,這是我近幾年要往前推進的一個研究方向。我們原來有誤解,帝王好像只是依靠絕對權力攫取收編士人的思想,只會偷知識分子的東西,沒有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實際上帝王在整體的政治運轉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自覺的思想框架和知識體系,這套思想體系甚至在政治層面上比士人的道統(tǒng)更加實用,不能說清帝就是簡單把以往的儒家資源拿來就用,而是經過改造后輸入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才最終成為整個帝王意識形態(tài)構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往我們對清帝獨到的思想意識和知識體系關注不夠,僅僅停留在表面,似乎只要靠耍弄權術,就能把知識分子治得服服帖帖的,這個邏輯某種意義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停留在這一點,就太低估帝王的能力和他本身作為思想主體性而不僅僅是政治主體性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建立起一個比較新穎的詮釋框架。
還有官僚階層的教養(yǎng)問題,同樣形成了一套比較自洽的邏輯體系。官僚首先應該擁有一套依靠道德訓練而形成的自我控制技術,一旦進入官僚系統(tǒng),通過這個技術就能夠轉換成基層治理的方式。如果從中國歷史上看,為什么儒家作為一種統(tǒng)治思想會脫穎而出?正因為儒家的理想是想讓每個人都擁有自我教養(yǎng)的能力,這樣一來王朝的治理成本就會大大降低。最后就變成了我不用人管,自己就好像形成了一套自我約束的機制。當時我看諾思(Douglass C.North)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就發(fā)現(xiàn)他也注意到了如何通過一種軟性的東西對社會進行控制,進而降低治理成本這個問題。如果用法家去主導政治就比較難辦,因為法家的設定就是把每個人都當成監(jiān)控對象,用高成本的手段去控制人的一舉一動,建立各種嚴密的制度約束機制,而儒家則主張慢慢去掉這些監(jiān)控制度的腳手架,讓每個人的內心去遵從某種道德規(guī)條的約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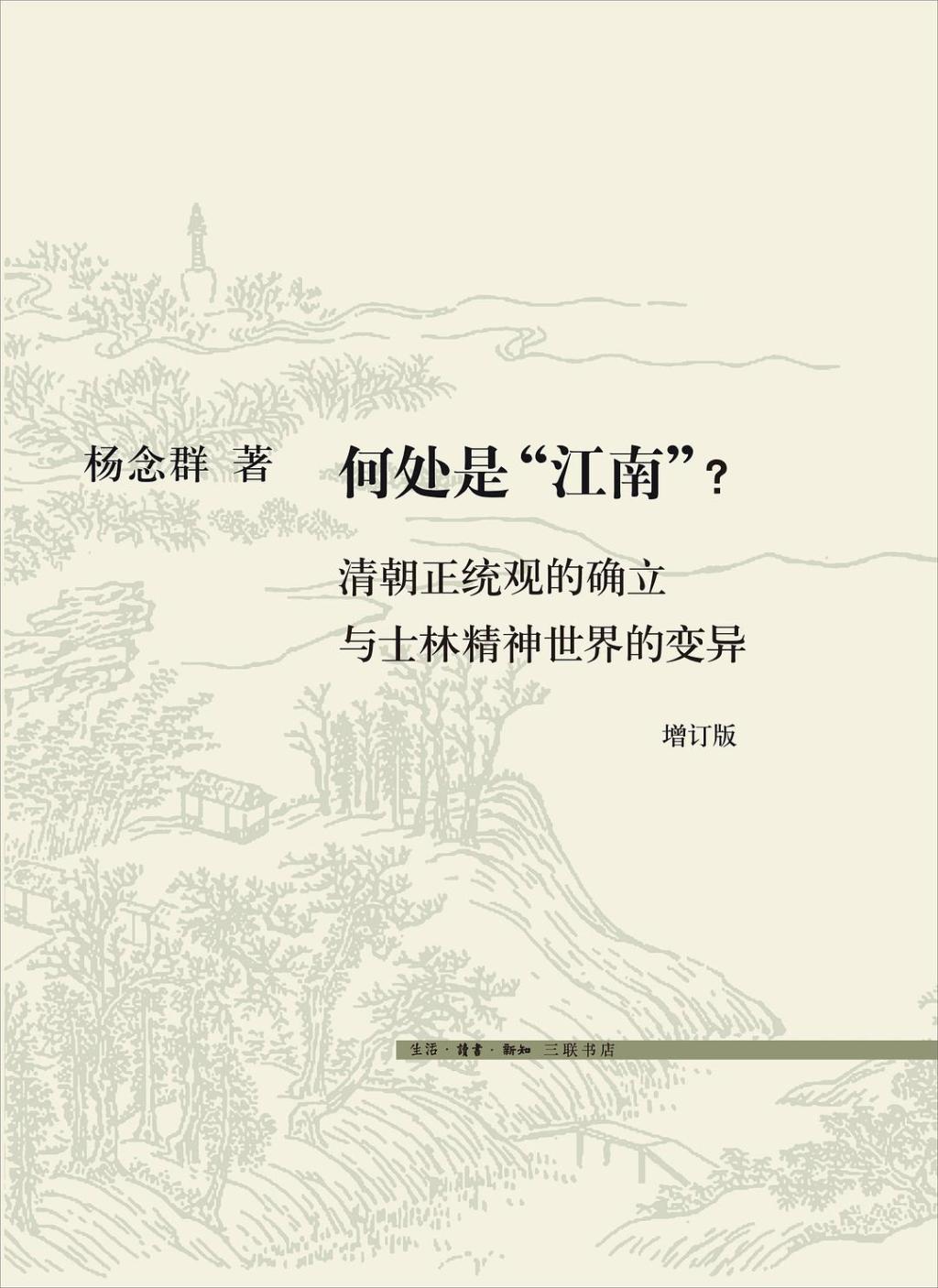
舒煒:我感覺“大一統(tǒng)”完全可以理出很多層次,關于春秋“大一統(tǒng)”學說本身,以及不同君主、學者,各種不同的正統(tǒng)、紀綱這些問題,甚至科舉制度。特別期待您能寫一部更大范圍的類似“大一統(tǒng)”的觀念史。這本書您主要勾勒了清朝在這方面的幾個線索。在此之外,是否有寫作上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
楊念群:難度比較大,因為我只是提出一個大的框架和解釋,至于“大一統(tǒng)”這個詞,我是想把它動態(tài)化,我一直強調要挖掘思想的行動邏輯,而不要把思想僅僅看作若干概念本身之間的相互銜接,對于這點只是我初步做了一下嘗試。我更多考慮的是如何更有效地應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挑戰(zhàn)。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大量引入西方理論,而且意圖把它們本土化,但我們所有本土化的努力大多不很成功。
我個人有一個想法,當然并不是憑我一己之力,而是大家集中力量重新梳理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概念,然后把它激活。除了“大一統(tǒng)”“正統(tǒng)”,還有“文質之辨”“夷夏之辨”“天命”等,這些核心概念都需要重新梳理,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于典籍之中,經常被古人使用,我們不要把它們當作僅僅是經典中沒有生命力的陳舊詞匯,而是需要通過重新解釋,讓它們煥發(fā)出生機。當然對這些概念的解釋并不意味著固步自封在原有傳統(tǒng)脈絡中。當代學者受到現(xiàn)代社會科學的訓練,不可能完全按傳統(tǒng)的解釋對待這些概念。我們需要在所謂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回歸古典文獻,去理解當事人使用這些概念的歷史語境以及行動邏輯,而不是一味盲目套用西方概念去解釋中國傳統(tǒng)。其實只要套用西方概念,你就沒有辦法脫離西方背景來觀察,結果難免還是陷入削足適履的境地。比如很多人都說中國發(fā)生了早期近代的現(xiàn)象,可是“近代”本身就是西方的說法。溝口雄三先生曾經說過要赤手空拳進入歷史,說中國有一個獨特的近代,包括日本也有自身的近代邏輯,結果最后還是落入西方設置的圈套。為什么我們不能暫時先把近代的邏輯拋開?因為中國歷史有自身的演變脈絡,并不是古代和近代之間如何界定的問題,比如我們要談正統(tǒng)“大一統(tǒng)”、文質之辨這些概念,就要按照它們自身再循環(huán)的邏輯去加以認識。不必用西方定義過的“近代”來描述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歷史就是循環(huán)論,我們探討的就是這個循環(huán)的歷史邏輯,同時不要把循環(huán)論妖魔化。我個人認為,中國歷史一直在循環(huán),包括現(xiàn)在也在歷史的許多觀念中循環(huán)不已,那何必非得用進化的思維去看待呢?而且循環(huán)論的邏輯并不一定是倒退的,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循環(huán)的邏輯往往有一個螺旋式的上升過程,其中也蘊含著不斷自我更新的觀念。
“大一統(tǒng)”其實與很多中國古代的歷史概念能夠建立一種互動的聯(lián)系,比如“大一統(tǒng)”和正統(tǒng)的關系就很密切,與文質之辨、夷夏之辨,以及各種經學和理學思想的討論都能形成對話關系,只要激活這種復雜的關系,就有可能重建中國思想的觀念體系。
舒煒:這點特別重要,可以作為咱們的總結。這本書確實是念群教授真正的抱負,希望以此重新激活中國歷史脈絡,甚至重新記錄政治思想很多的詞語或者觀念。當然舶來的概念肯定有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還是需要用自己的話語來重新言說,這是這部書嘗試做出的一個重大努力。最后請念群教授做個總結。
楊念群:我有兩點比較感慨。第一,其實我們這些當代學人大多都受到社會科學比較大的影響,如何找到自身的立足點就變得很重要。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都難免引用一些西方優(yōu)秀思想家的作品,同時我們又要想辦法盡量淡化這些思想對我們研究的過度支配作用,只是把他們當作研究的背景和資源。我曾經用一個比喻來形容社會科學方法與歷史研究的關系,歷史研究就像蓋房子一定要搭一個腳手架,目前這個腳手架根本沒有辦法靠自己來搭,只能靠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但是這個房子一旦搭起來之后,就必須拆掉腳手架。我們現(xiàn)在做研究總是在完成論著的同時,行文中到處留下西學的痕跡,自己的觀點反而無法看清。就像蓋完一棟房子,腳手架卻沒被拆除,好像永遠都擺在那兒,到最后反而看不清楚房子本身了。因為你只看到了腳手架,而腳手架只是你的工具。你把腳手架拆掉之后要再去看房子,哪怕輪廓還不那么清晰。這樣的文章才能算是見識通透。這是我想要說的,在處理現(xiàn)代社會科學方法和我們自身歷史關系的時候,應該采取的基本態(tài)度。第二,通過這本書也是想建立起一個我們對于清史研究新的認識。清朝的統(tǒng)治難度是非常大的,因為清朝始終是一個多民族多語種的共同體,要研究透清朝的特性必須掌握多種語言。現(xiàn)在我們清史研究所要求學生必須經過多語種的訓練。中國的中古研究是有優(yōu)勢的,中古的材料很少,有前輩學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所以中古史的闡釋框架和理論解釋力還是非常強的。相對來說清史研究的解釋力偏弱,就是因為清代一方面離現(xiàn)代較近,同時清代又是一個復雜的多民族共同體結構。對清朝的認識必須有別于以往朝代,所以我們要建立起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就會感到異常困難。我希望通過這本書的寫作,能夠使得“大一統(tǒng)”概念跟清朝歷史特性之間建立起更加密切的關系。如果這本書能夠對更加深入地理解清朝統(tǒng)治性質有所幫助,那我會感到特別欣慰。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