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8
夜讀丨正經人的日記史

作者的部分日記本。作者供圖
姜文是我最喜歡的電影導演,但他有一句臺詞,我非常不喜歡,那就是《邪不壓正》里那句:“正經人誰寫日記啊?”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時,像被人懟頭開了一槍——因為我就是喜歡寫日記的人!
這份筆墨與歲月糾纏的游戲,已伴我近五十年,給我溫暖與撫慰,實在不忍讓它受此污名。
我寫日記,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的,最初當然來自于老師布置的作業。我至今保持的“某年某月某日”“天氣”“星期幾”“寫于何地”的書寫習慣,就來自于小學語文老師楊守樸的教育。她說:“一輩子很長,許多事情都容易忘,用日記把它記下來,特別是那些幸福的有意義的事情。但愿你們都擁有值得銘記的一生!”
最初的日記內容,無非是上學、放學,家婆給了一分錢,李小紅給了我一個糖,大姨父出差送來幾本娃娃書之類。不會寫的字都用拼音,每一篇不忘遵照老師的教導,結尾加一句回到主題的總結:“真是XX的一天啊!”大多數時間,“XX”都是“快樂”“有意義”之類的字眼,因為我覺得老師也許喜歡。
但生活并不總是“快樂”和“有意義”啊!比如孫明紅用鋼筆戳了我的手;我放學溜到河邊,撕了本子折成船,放到小溪里,跟著它們跑到天黑;和幾個男同學鉆到秧田里,把泥糊在身上,曬干,然后一塊一塊地摳下來,說得上有啥意義?至于媽媽和爸爸永不結束的爭吵;數學老師拿不及格的試卷敲我的頭,說他用這么大的力氣教豬都會比我考得好時,我并不快樂。
但這些,我都想記下來,只是不愿意給別人看。于是,我便有了兩本日記,一本交作業,一本東躲西藏。我從那時起,就似乎有些明白,真正對我們有影響的,都是那些不便與人明言的人和事。
初中時,“不便與人言”的事越記越多,而“快樂”和“有意義”的作業日記越寫越機械,無趣甚至多余,終于發展到不再寫的地步。我寄希望于老師發現這種無心木訥的僵尸之作并不受人喜歡,也全無意義。
但語文老師張少云并不這么認為,她覺得我二十幾天沒交日記作業,是一種偷懶和叛逆行為,令人發指——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張老師罰我把沒寫的日記,每一篇寫三遍,20乘以3等于60,就算每篇40個字,對于14歲的我來說,也是件龐大的活兒。
其實只須把秘藏的那本日記交出來,就可以免了這份苦役,但我偏不。因為那上面記錄的東西,讓她看了的后果,顯見會比寫幾千字更令我難受。現在想來,寫得也無非就是些諸如挨了老媽的打,不服,想去少林寺學武報仇;與女同桌一起在教室吃飯聊人生,很開心;班主任堵在校門口,沒收了我新小人書,我很不服之類。
但我堅決不想讓任何人看!
那時的我,還沒想到過“人生意義”之類的宏大題目,只覺得任何雄偉而遠大的前途和人生故事,與我沒多大關系。我只是憑著一種單純的傾訴本能,把日常生活中不便與人分享的喜怒哀樂,都記錄下來,像跟一個好朋友分享。
這個好朋友究竟是誰,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它既無所不在地存在于周邊的空氣中,又無所不知地存在于我的腦海,高興時與我同笑,悲傷時與我同哭,暴怒時撫我平靜,沮喪時逗我發噱。它有時像是令我有好感的女生,有時是早已遠行的外公,有時像一位不再有聯系的知交,有時像是我今天出門后期待遇到的一個知心的人。
而多年以后,我才發現,那個好朋友,就是長大之后的自己。
幾十年之后,翻開那些寫在作業作、軟面抄上面的稚拙文字,那些令人發笑的悲傷和令人落淚的歡喜,又躍然眼前。我甚至能回想起寫下它們時,窗外的花是如何飛,鳥是如何叫,我的心是如何怦然而動的。那些曾以為跨不過的悲傷和邁不過的坎,那些以為永遠都不會離開的人與事,都已悄然變成一聲嘆息和一串省略號。我才恍然驚覺,為何當年那些聽起來平淡如水的歌謠,突然讓自己淚流滿面。
從小學三年級至今,我已寫了滿滿一柜日記,堆在一起,接近我的身高。這是一份獨屬于自己的作品,寫它的目的,不是為了成為一個“不正經”的人,正好相反,寫它的目的,是不希望自己變得不堪。就像在積雪的大地上,看到自己的每一個腳印。雖然每一步都努力認真地希望它走得更直,但回頭望去,卻歪歪扭扭,七彎八拐。
我們的人生,何嘗不是如此?走得正不正、好不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但我每天寫下的那幾百個字,至少表明自己曾經努力過。
光陰就像大海與沙漠,日記就像水和沙,一滴水、一粒沙,不足以裝下我們的整個人生,但至少留下了一些小小化石,留給自己在許多人和事漸漸遠去的時候,去回味,去欣喜,去嘆息。
如果人生是一場宴飲,每一次回憶就是一次添酒回燈,只要回憶還在,宴席便沒有散。這也許就是老年人都喜歡回憶往事的原因吧?
未來,我離開人世,這堆人生殘渣,還真不好處置。讓我親手燒了它們吧?下不去手。1994年某個沮喪的夜里,我曾經想這么干,但剛剛點燃第一本,就痛悔不已。那是我燒的唯一一本日記,是1987年剛到重慶讀書寫的。我至今都在努力,想把那一本補齊,也寫了許多文章,但終歸如同想抓住風一樣徒勞。再后來,想想,寫日記本身,不也是這么一件事么?于是釋然了。
我有朋友曾寫過一個故事,講一個音樂人想找到夢想中最好的音樂,但流浪一生,苦求無果,直至某日跌落懸崖。重傷彌留之際,突然耳邊響起那段音樂,但苦于手邊已無紙筆,于是蘸水將樂譜寫在身邊的石頭上,看著樂譜由濕變干,慢慢消失,他也含笑閉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我的這堆日記,會以怎樣的方式與我告別?
但我希望那一天,我能夠含笑感謝它,它證明了,這個世界,我來過!我度過了值得銘記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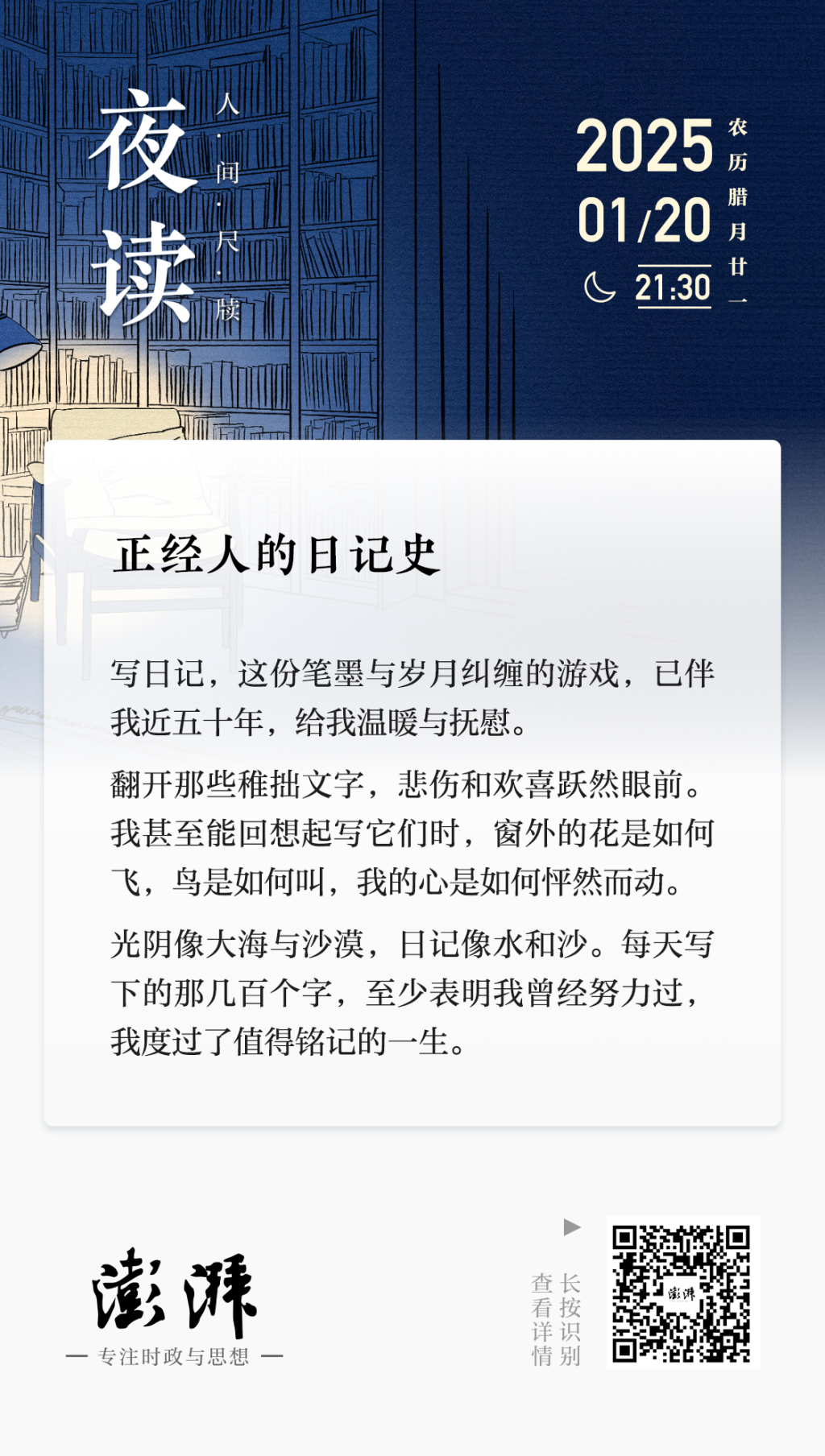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