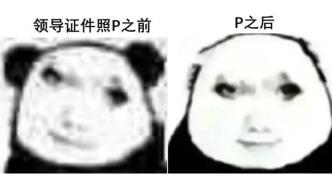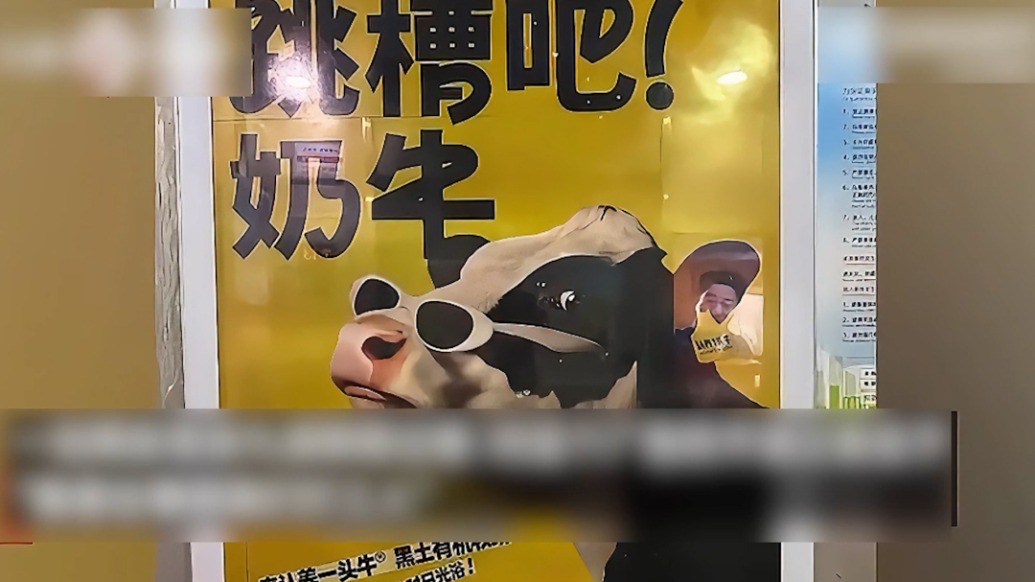- +16
他拍的電影,是打工人最強嘴替
原創 秦萌 新周刊
從編劇到導演,從劇集到電影,到再回歸劇集,董潤年經歷了市場的激烈變化。他是參與者,也是觀察者。
作者 | 秦萌
編輯 | 鐘毅
2023年年底,電影《年會不能停!》(以下簡稱《年會》)因對大廠生態和職場亂象的諷刺,令打工人共情,獲得了超10億元票房和豆瓣8.1分的高分,片中的演員白客更以“窩囊人夫感”出圈,開辟了男演員的新賽道。這部電影的編劇兼導演董潤年在2024年年底推出了他第一次執導的電視劇《不討好的勇氣》(以下簡稱《勇氣》),以脫口秀行業為背景講述女性成長的故事。
《年會》《勇氣》都是現實題材,話題與當下年輕人的關注密切相關。董潤年是如何做到還原打工人真實處境的?他在采訪中講述了自己的調研經歷,并分析了國產劇背后的行業現狀。他認為,傳統電視劇生產時間緊迫,在單位時間投入的資金和人力都不足的情況下,怎樣更真實地還原現實生活,達到一定的審美標準,是整個行業需要面對的課題。

(圖/受訪者供圖)
影視行業面臨的另一重問題,是短視頻的沖擊。董潤年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94年,董潤年15歲,在雜志上看到電影《侏羅紀公園》的一幅幕后照,導演斯皮爾伯格坐在一只巨大的霸王龍的腳邊。董潤年立刻被吸引,到處尋找看這部電影的渠道。有個朋友和董潤年開玩笑,說電視臺在周六晚上9點會播放,他便抱著期待從晚上9點一直等到11點。第二天,這個朋友嘲笑他:這么假的消息你也信。后來,在1995年,他終于獲得了一部翻錄了不知道多少遍的《侏羅紀公園》錄像帶,畫質模糊、布滿橫紋、色彩接近黑白。但他如獲至寶,趕緊又翻錄了一盒,反復觀看,直到把錄像帶看廢為止。
然而現在,“喜歡的電影都在互聯網上,或者在硬盤里,隨時可以看到,但大家反而沒有那么強的愿望要去看了”。他說,相比沉浸式觀看一部長片,大家可能更容易被手機上的短視頻吸引注意力。
這也是電影和電視產業面臨的尷尬處境:中國網絡視聽協會于2024年11月發布的《中國微短劇行業發展白皮書(2024)》預計,2024年國內微短劇市場規模將超過500億元,內地電影全年總票房收入為470億元。這意味著,微短劇的市場規模將有望首次超過電影票房。在這種情況下,電影和電視究竟還能如何吸引觀眾?

選擇和普通人強烈關聯的題材,
增加信息密度和情感強度
《新周刊》:《年會》《勇氣》的劇本創作是同步進行的,并且共享了一套故事背景和職場素材。可否談談你做這兩個項目的不同感受?
董潤年:《年會》《勇氣》都是在2020—2023年期間完成劇本的。(我)做《年會》的采訪時,積累了很多關于職場的具體案例,了解了很多職場打工人的心態。《年會》電影容量有限,很難充分展現職場內容。(我)當時也想做一個關于職場的女性成長劇,劇集的時長更長、空間更大,可以放入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前者是純粹的喜劇電影,后者是可以展現人物成長的正劇。《年會》的職場更夸張,諷刺性更強;《勇氣》里則希望展現更多面向,哪怕是可恨的反派,也有其他生活層面的展現。
《新周刊》:《勇氣》是你第一次執導的電視劇。可否談談做電影和做劇集的區別?
董潤年:技術上差不多,但電視劇體量相對大一些,每天拍攝的量也多。電影在一天中拍的幾場,就算中間隔了許多場,內容也都在一個完整的時空序列里。但電視劇有可能拍了第一集的,緊接著拍最后一集的,這中間的人物狀態發生了很多變化。(導演)和演員說戲的時候,也要講出對人物在全劇中經歷的變化的理解。所以做劇的導演挑戰蠻大的,需要明確人物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什么,心態是什么。功課要做得更細致。
《新周刊》:國產劇懸浮,不理解打工人的處境,這是經常被討論的話題。你怎么看待這種輿論?《年會》《勇氣》是如何保持對打工人生活的了解,確保打工人能夠真實共情的?
董潤年:我們花了一兩年時間調研職場, 潛伏在一些職場App的打工人社區看吐槽,采訪了很多在互聯網大企業里工作的人,了解他們真實的案例,了解他們的心態。我們采訪各個職級的打工人,有年輕、剛入職不久的,有中年、面臨35歲職業危機的,還有一些管理者。特定職位的人有特定的說話方式、做事方式和想事情的邏輯。這樣,在《年會》這種很夸張的喜劇里,我們也讓大家能夠看到某個職務的人就是應該這么說話、這么做事。

(圖/《年會不能停!》)
在影視劇里,但凡一件事沒有邏輯,觀眾就會覺得這是編的,覺得不合理。有趣的是,我們在現實中經常看到一些新聞報道,底下評論說編劇都編不出來,這超越了戲劇的邏輯。其實,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一定由潛意識驅動,未必符合做事邏輯,但一定符合這個人的性格。采訪很重要的一點是去揣摩和了解人物的性格邏輯。相比故事,故事里傳遞的人與人之間的狀態和心理更重要,抓住精神內核,在敘事的結構和層面上可以大膽變化。
大家覺得前幾年的職場劇比較懸浮,其實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審美傾向上,場景、人物造型和表演方式走浮夸風,但創作者的思想很單純,就是希望場景拍出來好看。主角經濟收入不高,但住的房子很大,很大原因是操作方便。在三四十平方米甚至更小的單間里拍戲很困難。機器很大,放進去以后,人就已經沒有地方站了。電影拍攝時間更充裕, 在一個小空間里,拍一天電影只需要拍1頁劇本的內容,可以有更長的時間去調整燈光和攝影機的位置,以及人物的走位。但是電視劇甚至可能有一天拍10頁劇本的情況,沒有時間去做細致調整。而且前幾年行業正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生產節奏非常快,大家想要快速把一個故事寫出來、拍出來,不論是在人物創作上,還是在拍攝上,都顯得有點“急于求成”。
相對電影來說,傳統電視劇生產時間緊迫,在單位時間投入的資金和人力都不足的情況下,怎樣更真實地還原現實生活,達到一定的審美標準,是整個行業需要面對的課題。但這兩年,隨著技術的發展,攝影機的體積更小了,隨著LED燈的發展,燈光師用iPad就可以直接控制多個光源,所以現在電視劇的場景、人物造型都比過去更貼近真實生活。而且,這兩年我接觸到的大部分編劇也都在認認真真做調研、做采訪整理。
《新周刊》:短視頻對你造成了影響,你曾自述希望呈現更快的視聽節奏,因為觀眾已經習慣了1.5倍速的觀影,不如直接呈現一個1.5倍速的內容。你認為現在的影視內容要在與短視頻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需要滿足什么樣的條件?
董潤年:現在在網上倍速看劇逐漸成了一種常態。一方面是為了節約時間,另一方面也說明觀眾感受到這部戲的節奏和信息量不夠。觀眾習慣切片式看劇、幾分鐘了解一部電影的高信息量提純的模式,所以我在思考和嘗試的一個方向就是,在電影和長劇的創作中,提供給觀眾更多信息和情緒的變化。
現在,長劇的觀眾在流失,游戲玩家在流失,但是短劇的觀眾在增加,觀看短視頻、直播的觀眾在增加。觀眾被更直觀、更快速、更碎片化的視頻、小游戲吸引了。短劇行業剛剛興起,一年的收入已經超過了整個電影市場的票房。這種情況下,我嘗試的方向(有兩個),第一是題材的選擇跟觀眾,尤其是跟普通人有強烈的關聯,讓觀眾看到題材就感興趣;第二是增加信息密度和情感強度,這也是現實中電影票房呈現出來的趨勢。我不想做切片式的劇集,即相互之間沒有邏輯、結構和遞進關系的段子的堆砌。我追求的是在更復雜的結構的基礎上,有更高的敘事密度、更有趣的橋段、更豐富的人物、更好的段子。
我們也需要考慮,未來的電影敘事到底是什么樣的。在2024年中國電影金雞獎的論壇上,我聽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觀點,說電影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深度閱讀。現在有很多好電影,但好電影未必有好票房。生活方式改變后,(我們)在家里能更容易享受到各方面的服務和快樂,而看電影加上往返電影院的時間,可能要花四五個小時。現在電影上映,大家可能寧可等到它將來上線,在電視或手機上看。但如果電影上映引起了很強烈的討論,各方有自己的觀點甚至在網絡上進行交鋒,那么作為觀眾就會很好奇,想去看看,以便參加對社會議題的探討。所以,商業電影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視聽娛樂產品,票房高、有影響力的電影甚至變成了一個平臺,承擔的是觀眾觀看后進行的交流溝通、針對性的討論,是我們進行社交的機會。

大家喜歡“窩囊人夫”的溫暖
和沒有攻擊性
《新周刊》:你說你做《勇氣》是受到了《后翼棄兵》的啟發,你是怎么理解女性成長、大女主劇的?
董潤年:《勇氣》算上我一共6位編劇,其他5位全是女性。做女性成長的故事的過程中,我也在進一步學習。比如說,在探討吳秀雅的成長與她跟前男友的感情時,我們有過爭論:前男友鄭昊即便有大男子主義的問題,但是在他的立場上,他沒有做任何實質性的對不起吳秀雅的行為,吳秀雅對現在情感和物質生活的不滿算不算自私。我們逐漸意識到這種討論的前提是好女人應該賢良包容,不該有攻擊性,甚至不應該在物質層面上追求更多,這可能是長久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對女性的壓制和偏見。但是,如果從主人公的主體性出發,她只是想要真正的自我得以彰顯,尋求想要的生活,讓自己開心滿足。所以,我們在戲中討論以及在現實中爭論和思辨的,不是針對某一個男性或女性的討論,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

(圖/《不討好的勇氣》劇照)
做了這部劇,我覺得跟太太的關系也有所變化。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們也更多地聊了過去的經歷,我們發現,哪怕是在一些很小的選擇上,大家也有不同的想法,所以還是要更尊重對方的主體性。即使我們知道對方做了決定會面臨更艱難的處境,會吃苦頭,我們可以盡到告知義務,但不能替對方做決定。
《新周刊》:和《勇氣》里自信又有“爹味”的鄭昊相比,《年會》里的“馬杰克”更是因“窩囊人夫感”而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你在選角上和執導過程中,會刻意去營造這種感覺嗎?
董潤年:完全沒有往這方面去想。白客本人有一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氣質,能讓人平靜下來,符合馬杰克這個角色的底層邏輯。他自身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演員,在喜劇表演節奏上的一些把握很棒。馬杰克在職場里有點受氣,壓抑自己,盡量把棱角磨平,這種狀態是我們一起探討出來的。大家之所以喜歡(他),我感覺是因為馬杰克體現出的溫暖和沒有攻擊性,他一直試圖幫助自己、幫助主人公脫離困境,拆東墻補西墻地到處救火,沒有想害人或甩鍋。而且他還是蠻能干的。
《新周刊》:《勇氣》里有“爹味”的鄭昊不被歡迎,《年會》里有“窩囊人夫感”的馬杰克廣受贊譽,你認為當下人們推崇的男性氣質在變化嗎?
董潤年:有的觀眾不喜歡大男子主義的角色,有的觀眾喜歡“窩囊人夫”的角色,但那是所有觀眾嗎?我們聽到這些聲音,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聽到這樣的聲音、關心這樣的批評,所以更多類似的聲音被我們關注到了?可能很多平臺會有數據,知道是什么觀眾在看我們這些劇,就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分析喜歡這個劇的觀眾到底在什么樣的年齡段,生活環境是什么樣的,住在什么樣的城市。但為什么他們會喜歡這個角色?另外一部分人又為什么不喜歡這個角色?這些需要更精細的調研。
我永遠思考,我們聽到的聲音在真實世界里的占比到底有多少。
運營:嘻嘻;排版:鄭雯涵

原標題:《導演董潤年:商業電影開始有了社交功能》
674期雜志
《視頻化生存》已上市
原標題:《他拍的電影,是打工人最強嘴替》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