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吉川忠夫:寒食散服用注意事項
神明開朗
自三世紀魏晉時代起,中國社會爆發起一股服用散劑的風潮,這種散劑被稱為“寒食散”或“五石散”。通過1927年魯迅先生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的演講記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篇標題略顯冗長的文章,想必有不少人已經知曉了這段歷史。“寒食散”的成分根據處方不同而有所出入,但基本上以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磺這五種礦物為主,有時還會混入其他藥材。因為使用了五種礦石性藥材——石藥,因而被稱為“五石散”。又因為服用后不能食用熱食,只能吃冷食,因此又稱“寒食散”。
服用寒食散的風潮始于魏晉,并于六朝時期廣泛散播開來。這其中的推行者便是魏朝哲學家何晏,此人因以老莊的義旨來注解《論語》而聞名于世。據《世說新語·言語》記載,何晏曾言:“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注釋中引用了秦丞相(有一說認為“秦丞相”是“秦承祖”之誤)的《寒食散論》說道:“寒食散的處方雖然在漢代就已出現,但服用者寥寥無幾,更無人推廣之。魏尚書何晏是第一個服用寒食散而獲得神效的人,從此寒食散便風靡于世,時人紛紛爭先服用。”
如《寒食散論》所說,寒食散確實自漢代就有,曾被用于治療部分疾病,這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一明證。據東漢文帝時代的醫師倉公淳于意所言,齊王有一位名叫遂的侍醫。有一次遂得病,服用了自煉的五石散,淳于意為其診治時,對他說:“你得的是內熱,根據醫書的記載,如果內熱導致小便不通,則不能服用五石。”倉公指出了遂的用藥錯誤,遂試圖反駁,但百日后,他便乳頭長疽而死。此外,西漢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也有用“紫石寒食散方”來治療傷寒的療法,稱將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括蔞根、防風、桔梗、文蛤、鬼臼、太乙余糧、干姜、附子、桂枝等十三種藥研磨成粉,取一勺(方寸匕)以酒送服即可見效。
如上所述,在漢代時,寒食散只是被用來治療部分疾病,而到了魏朝何晏以后,人們服用寒食散只是為求“神明開朗”,即精神上的爽朗暢快,與治病無關。西晉皇甫謐云:“寒食藥的起源眾說紛紜,有說是東漢的華佗發明的,也有說是張仲景發明的……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服用此藥后心情爽朗,體力漸強。于是京城人士口耳相傳,陳年老病不用一日便藥到病除。眾人貪圖眼前近利,而不顧后患。何晏死后服用者仍舊與日俱增,流行之勢絲毫不減。”

那么為何寒食散會如此爆發式地流行起來呢?皇甫謐一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便道明了原因。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不過是幻覺而已。服用寒食散跟吸食鴉片、大麻之類的一樣,會引發強烈的幻覺。在那種幻覺中,人可以體會到“開朗”的感覺,暫時性忘卻一切煩惱與痛苦。而體力轉強則是因為,何晏是“耽聲好色”之人,而寒食散恰好有強精壯陽之效。唐代孫思邈曰:“有貪餌五石,以求房中之樂。”(《千金要方》卷一)何晏的《失題》詩亦有言“且以今日樂,其后非所知”——姑且享受今日之樂吧,明日之后的事誰又能預料得到呢,說不定說的正是身處幻覺中的感受。
寒食散確實有一定的療效,至少當時的人們是這么相信的。西晉的嵇含晚年得子,孩子十個月大的時候狂吐不止,命懸一線。嵇含“決意與寒食散”,不到三十天孩子便痊愈了。嵇含將愛子九死一生的喜悅寫進了《寒食散賦》中:“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還精爽于既繼。”寒食散雖然藥效神奇,但是相應的,毒性也極強。處方或服用方法若稍有差池,將危及性命。究竟能不能給十個月大的嬰兒服用寒食散呢?嵇含再三猶豫最后終于“決意”讓其服用,他之所以會經歷這番思想斗爭,也是因為如此吧。故而說,那些經常服用寒食散、淪為了幻覺的奴隸的人,必須做好覺悟——現實并非幻境,總有一天要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比如東晉哀帝因服用寒食散連政務也無法處理,形同廢人。北魏道武帝成日在活人身上見到妖怪的幻影,惶恐度日,據說許多朝臣因此接二連三地被處死。還有方才提到的皇甫謐,皇甫謐是一名醫學知識淵博的學者,著有《寒食散方》,但他其實也深受寒食散所害。
《皇甫謐傳》中說,皇甫謐剛開始服用寒食散時,神經衰弱非常嚴重,還曾用刀猛刺自己企圖自殺。謐還上疏晉武帝,拒絕了出仕的邀請,在此引用其慘痛自白如下:“我長期與病魔作斗爭,最終半身麻痹,右腳縮小,至今已有十九年之久。再加上我服用寒食散卻沒有節度,更是雪上加霜,受其折磨痛苦不堪已有七年。隆冬里我赤身裸體大口吃冰,盛夏時卻戰栗不停,且伴有嚴重的咳嗽,宛如溫瘧或傷寒……”想必皇甫謐是為了治療半身麻痹癥才開始服用寒食散的吧,結果卻受其副作用所折磨苦不堪言。“這有如噩夢一般的生活由自己一人來承受就夠了”,皇甫謐懷著悲痛的心情執筆寫下《寒食散方》,將寒食散的正確服用方法告訴世人,警戒眾人錯誤服用后果將不堪設想,并記錄下種種副作用的癥狀,具體如下:
“有時會突然異常發作,讓你年紀輕輕就命喪黃泉;我的族弟長互,他的舌頭甚至都縮進了喉嚨里;東海王良夫,癰瘡深深陷入后背;隴西辛長緒,脊肉潰爛;蜀郡趙公烈,一族當中有六人因此而死。諸如此類皆是服用寒食散所致。余命長則十年,短則不過五六年。我總算是死里逃生,但至今仍是人前笑柄。即便如此,世間服藥中毒的患者依舊沒有引以為戒。”(引自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六)
服用注意事項
服用寒食散有諸多注意事項,最起碼下述幾點是必須嚴格遵守的。比如,要盡可能穿得少;還有前文已經介紹過的,只吃冷食等等。寒食散一旦起效就會發作,身體像火燒一般發燙,稱為“石發”或“發熱”。梁朝的張孝秀原本是一名生活在廬山的居士,一心向佛,據說他好服寒食散,嚴冬之時也睡在石頭上。大概是因為石頭的冷氣正好能吸收他體內散發的熱氣吧。還有一則有關宋朝將軍房伯玉的傳聞,據說他服用了十來劑五石散卻不見效,非但如此還引發了惡寒,炎炎夏日也要穿棉襖。醫師徐嗣伯為其診斷說是“伏熱”——熱氣積于體內的癥狀,需要用水讓熱氣從體內發散出來,并且要在冬天進行治療。等到了十一月大雪之日,徐嗣伯讓房伯玉脫去衣裳坐在石頭上,讓兩名助手抓住房伯玉,從他的頭上往下澆水,一共澆了二十石水。這時,房伯玉忽然不省人事了。其家人哭著求徐嗣伯停手,但徐置若罔聞,又往房伯玉身上澆了一百石水。不知為何房伯玉開始抽搐起來,仔細一看,他的背上正冒著熱氣。不一會兒,他便一彈而起,大喊:“熱死我了,快給我水!”房伯玉一口氣喝下一升水。他不但治好了病,之后因為適當地“發熱”,只靠一條兜襠布和一件襯衫就能過冬,而且還日漸豐腴,宛如人偶。東漢名醫華佗也曾用過這種療法給一位婦人治療,不過,那位婦人的病叫做“寒熱注病”,與服用寒食散無關。
原本,如果搞錯了寒食散的處方或服用方法,會導致熱氣積于體內,引起身體不適,需要像房伯玉那樣接受一些粗暴的療法。但即便是普通服用者,也需要通過不停地散步來發散體內的熱氣。當時甚至因此出現了一些獨特的術語,比如,管發散寒食散的熱氣叫做“散發”;為了“散發”而漫步被稱為“行散”或“行藥”。在魏晉名士的逸聞軼事集《世說新語》中我們時常可以見到這些詞匯。宋代鮑照的《行藥至城東橋》一詩還描繪了清晨去行藥的情景——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逈陌,延瞰歷城闉。
有時為了“散發”還需飲酒。但不知為何,雖然原則上只能吃“寒食”,但酒卻必須熱過才能喝。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鄧攸被羯族石勒俘虜,后遭誣陷被扣上失火的罪名,當時他以“弟婦散發溫酒”以致失火為辭進行辯解。如果不知道散發之酒必須熱著喝,恐怕便無法理解這一說辭。此外,《世說新語·任誕》還提到,東晉桓玄被召至京城建康(今南京),赴任途中將船停泊在荻渚。當時王忱前來看望桓玄,其實王忱剛服用過五石散已有些許醉意。桓玄命人備酒,但由于王忱不能喝冷酒,便頻頻吩咐侍從“溫酒來”。桓玄突然簌簌落淚,開始嗚咽起來。原來桓玄之父名“溫”,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將軍桓溫。從禮節上來說,提及對方父親的名字是一大忌諱,甚至同音的字詞都要避免使用。這一點王忱不可能不清楚,卻一再說“溫酒來”,因此桓玄才不禁流涕嗚咽。不知醉醺醺的王忱是有意還是無意,總之是犯了忌諱。可縱使他酩酊大醉也絕不會忘記自己不能喝冷酒,因為此事攸關生死。事實上確實有這樣的傳聞——據說西晉的裴秀服用寒食散后不小心喝了冷酒,便因此斷送了性命。當時人們習慣喝冷酒,所以服用寒食散的人必須異常小心。

服食求神仙
即便寒食散服用起來相當麻煩,并且時而伴有生命危險,但依舊難擋其流行之勢。六朝人將服用寒食散視為一件風流韻事,把它當作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太平廣記》卷二四七《啟顏錄》中還記載了這么一則趣聞。
北魏孝文帝年間,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并且時常聲稱服用后,石藥發作致使身體發熱,說起來神色頗為得意。其中也有非富貴者謊稱服用石藥后發熱的,多被世人嗤之以鼻。有一日,一男子倒在市場的門前,翻來覆去直喊熱,引來眾人圍觀。同行的人覺得詫異,一問,那人便說:“我石藥發作了。”同伴又問:“你何時服用的石藥?怎么現在發作了呢?”那人答曰:“我昨日在市場買了米,米里混了石頭,吃了之后現在就發熱了。”圍觀者聽了哄然大笑,自那以后便很少有人聲稱自己石藥發作了。
但其實,寒食散的爆發式流行與當時人們喜好神仙的風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六朝人心中對永生抱有強烈的執念,他們想讓肉體永葆年輕,想盡可能地延長生命,如果可以的話甚至想得永生。他們熱烈向往已得永生的神仙,對他們而言道教不過是一個用來敬奉各路神仙的宗教而已。當時,“神仙中人——神仙世界里的人”諸如此類的表述被當作最高級的稱贊。其中比較出名的是何晏——人稱“神仙中人”的一位絕美貴公子,膚色極白,魏明帝甚至懷疑他涂了白粉。世人相信何晏的美貌是得益于寒食散的神效。
后來,何晏因卷入政治事件被誅殺,這個意想不到的外因致使他無法延年長生。但人們相信服用寒食散便能何晏一般成為“神仙中人”,哪怕當不成“神仙中人”,至少還能在幻覺中與神通靈,體驗一把成仙的心境。盡管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古詩十九首》之十三)所言,求仙不得反被噬的悲慘結局并不少見,但寒食散仍能風靡一時,想必與這現象背后隱藏著的世人的心愿是息息相關的。據《神農本草經》中有關白石英、紫石英的記載,如長期服用,身體將日漸輕盈,必能延年益壽。
道教中將通過攝取藥物或特殊食物來改造肉體的行為稱為“服食養生”。毋庸贅言,“服食養生”的終極目的自然是成仙。道教書物中記載了各種能讓人成仙的仙藥,比如東晉葛洪的《抱樸子·仙藥》便按功效的順序列舉了以下仙藥,上者丹砂,次則黃金、白銀、諸芝、五玉、云母、明珠、雄黃、太乙禹余糧、石中黃子、石桂、石英、石腦、石硫黃、石臺、曾青……還引用了《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肉體安樂,能延年益壽,升為天神(神仙),上下自由遨行,可驅使眾精靈,身上也會長出羽毛,行廚(諸神的便當)立馬就會送到眼前。”又曰:“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云母、太乙禹余糧,無論哪種單獨服用也能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使毒蟲不近身,猛獸不犯人,惡氣不盛行,可驅妖除魔。”西晉張華在《博物志》中也引用了《神農本草經》,云:“上藥養命,五石可錘煉肉體,六芝可延年益壽。”但被葛洪稱為“上藥”或“大藥”的所謂最厲害的仙藥都是黃金、丹砂制成的,即金丹。那么為何金丹會如此備受重視呢?那是因為它兼具不變與可變兩種性質。草木藥物埋藏在地里便會腐壞,用鍋一煮就爛,經火一燒便會燃燒殆盡,與金丹不可同類而語。換言之,金丹的不變性意味著永恒的生命,可變性意味著人可以被改造為神仙。“所謂丹砂之物,越燒越經久,且變化愈加微妙。而黃金被放入火中煉制百回也不會消減,若被埋在地中則永遠不朽。服用這兩種藥物來鍛煉身體,能令人不不死”,“即便是小丹砂中的次品也勝過草木藥中的上品。草木藥一燒即盡,丹砂用火燒則變成水銀,不斷變化之中又變回丹砂……故能令人長生不老”(《抱樸子·金丹》)。
那么,現在我們的問題核心——寒食散,在《抱樸子》當中又是被如何評價的呢?很遺憾,《抱樸子》并沒有對寒食散進行詳細的記述,只有一次間接地提到寒食散——“服用玉屑,與水同飲,能使人不死。之所以說它不及黃金,因為它往往會令人發熱,類似寒食散的癥狀”(《抱樸子·仙藥》)。從這句話來看,寒食散并沒有被視為一種多么重要的仙藥。大家注意,這里說寒食散的原材料石英、石硫黃等級不如丹砂、黃金,大概是因為它們雖然具有一定的不變性,但其可變性,也就是可變換成其他形式的能力不足。在《抱樸子》中被稱為五石的,不是指五石散的原材料,而是指包含丹砂在內的丹藥的材料。《抱樸子·金丹》中的五石指的是丹砂、雄黃、白礜、曾青、慈石,《抱樸子·登涉》中的五石指的則是雄黃、丹砂、雌黃、礜石、曾青。
金丹是仙藥中的大藥,也只有專門的道教修行者,比如葛洪一類的人物,才懂得如何煉制金丹。金丹的煉制有許多繁瑣的禁忌,并且要求儀式一定要隱秘進行。“調合丹藥必須在名山的無人之地進行,同伴不得超過三人。煉丹之前須先齋戒百日,用五香沐浴,清凈身體,不得接觸污穢之物,不得與俗人來往”;“調和此丹藥時須舉行祭儀,屆時太乙元君、老君、玄女等諸神都將前來。若煉制仙藥者沒有隱身于幽僻之地,使得俗世間的愚人們得以經過或見之聞之,那么諸神將責備煉藥者不遵守仙經戒律,致使惡人散布誹謗之言。如此一來諸神便無法繼續保佑煉藥者,并且由于邪氣入侵,仙藥也無法制成。必須藏身于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用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如此方能制成大藥”(《抱樸子·金丹》)。不僅如此,若沒有龐大的資金,煉金煉丹的原材料可沒有那么容易入手。借杜甫的詩來說,就是“苦乏大藥資”(《贈李白》)。葛洪也確實曾如此自白道:“本人貧乏財力單薄,又生于多事多難的時代,抑郁不得志。且道路堵塞,無法弄到煉丹所需的藥材,故而沒能合成丹藥。”(《抱樸子·黃白》)這么看來,那些非專業道士的凡夫俗子、被拒于煉制金丹的大門之外的“神仙愛好者”們會迷上寒食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畢竟寒食散的原材料比較容易入手,調劑方法也簡單。
被稱為書圣的東晉王羲之也是狂熱的道教信徒。從其尺牘(書簡)當中便可得知他曾服用過多種仙藥。有的尺牘甚至有如《本草》之類的中藥功效說明書一般,其中寫道:“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但也有的尺牘流露著哀傷:“我昨日頻頻感到傷感,實在難以承受,今早服用了散藥望借藥消愁,不料服藥后愈加疲乏。回想起來,足下忠告所言極是。但我已是老人,僅存的希望就是我的孩子們。萬萬沒想到有朝一日我會為她們哭泣不止。我余命不久,且日漸衰弱,這五色石膏散又有何益處呢?只愿散藥能夠逐漸消散……”據推斷這是王羲之接連失去兩個孫女后寫下的文章。無需友人忠告,王羲之便知寒食散有害無益。他之所以服用寒食散也是想用短暫的幻覺來掩蓋深沉的痛苦吧。
多為藥所誤
傳言熱衷于“服食養生”的唐武宗因為藥物發作“喜怒無常”,還有五代南唐的先主“服餌金石,其性多暴怒”,這些皆是寒食散中毒的癥狀。直到后來,那些貪圖享樂的天子當中仍有不少寒食散的愛好者。但隨著針砭藥害的警鐘敲得越來越響,這場波及整個社會的風潮也漸漸消退了。《隋書·經籍志》中收錄了釋智斌的“解寒食散方”等其他類似的藥方,講的都是如何解寒食散之毒,可見當時的醫學家們對待寒食散上癮的問題有多么鄭重其事。其中,唐初孫思邈的一番話可以說是最有力的警告之一。孫思邈是一名醫學家,曾撰寫《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醫書,同時他也是一位神仙家,被稱作孫真人。他說:“我自明理懂事以來,見過無數朝野士大夫受五石散所害。所以寧可吃野葛,也不服用五石散。五石散的猛毒眾人有目共睹,必須謹慎對待。有識之士若發現五石散的處方,應立即焚之,不可久留。”(《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解五石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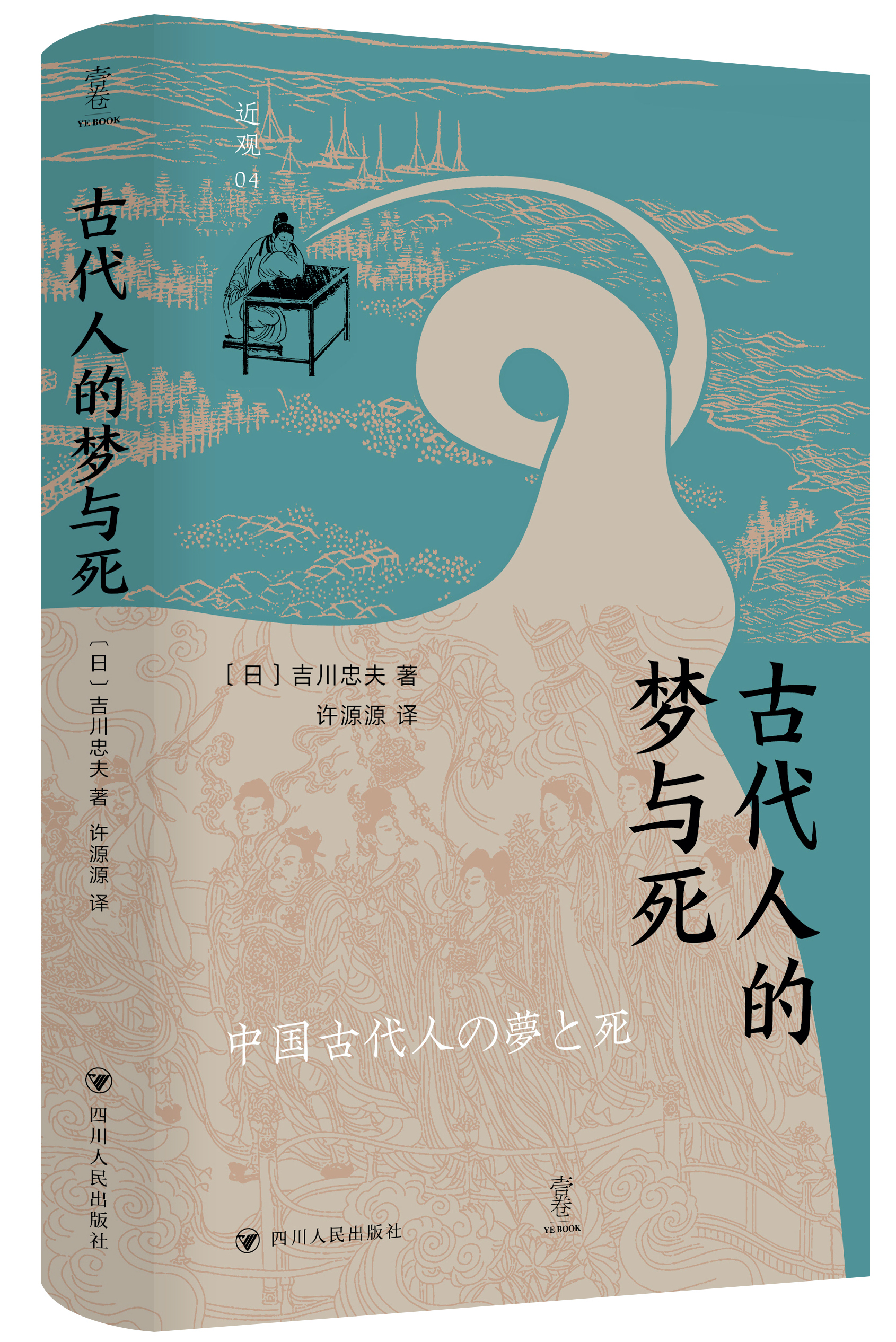
(本文摘自吉川忠夫著《古代人的夢與死》,許源源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