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歪果仁口述中國|貝爾格曼:我在中國當記者
【口述人簡介】
尼爾斯·貝爾格曼(來自德國)
出生于1970年,從小在柏林長大,畢業于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獲新聞與傳播、通信科學雙碩士學位,并輔修心理學與政治學。十四歲第一次隨父母來到中國旅游,2017年再次來到中國,至今擔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德語部的編輯和記者。

在柏林,我的身邊開始聚集起不少的中國朋友,我們經常聚在一起喝咖啡聊天,他們為自己祖國正在發生的一切而感到歡欣鼓舞。那些圍繞中國的發展而引發的討論常常是激昂的。大家經常談及電子商務、經濟和科技發展,像華為之類的中國民族名牌的崛起,還有政府反腐的決心和力度。
中國在許多領域開始嶄露頭角甚至成為領導者,這讓海外中國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國朋友明的眼里,猶如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以及接下來2022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是民族振興的標志。“中國正在努力探索一條與世界共同發展之路,這從中國倡議或主導、參與的上海合作組織(SCO)、金磚國家峰會、‘一帶一路’建設中可見一斑。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是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明的眼里總閃爍著激動,他還提及“中國制造2025”。
中國有句話“心誠則靈”,長久的期待,終于盼到了夢想成真的時刻。時隔三十年后,2017年,我終于再次踏上了這片神奇的土地。
這次,我的身份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德語部的編輯和記者。
此時此刻,當我在電腦上敲下這些文字時,我已在中國生活了大半年。雖然那層神秘的面紗在漸漸褪去,但對中國,我仍然保持著初始的好奇和激情。一切似乎就那么自然而然地發生了,仿佛我只是把工作場所從柏林搬到了漢堡。當然,這個比喻并不恰當,因為在我心目中,中國的生活要更酷炫和有趣一千倍。
從一開始,一群熱情洋溢、樂觀聰慧的同事就讓我初來乍到的不適感不知不覺消失,一切都令人感到親切。我想起了曾經讀過的一句中國古詩:人生所貴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親。
現在我每天的生活是這樣的:
早晨鬧鐘一響,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手機開始迅速瀏覽。我的中國手機從早到晚都是來電及信息提示音。在德國,大家通常使用“Whats App”,人們常常將它與微信進行比較。對此,我經常用一個稍帶夸張的比喻來形容二者的區別:若“Whats App”是腦細胞,微信就是大腦。兩者在實用功能方面差距很大。在中國,通常我只用一個手機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這些我之后還會具體介紹。
每天上班之前,我常常會用手機掃描支付的方式租一輛共享單車。在我住宅樓附近就有一個共享單車停放點,那里停放著五顏六色,型號、款式不一的單車,騎上一輛,穿過幾個小巷,到集市買點水果,然后開始新的一天繁忙又有趣的工作和生活。
我的同事們建立了一個微信跑步群,每天大家打卡,截圖發到群里。雖然我也時不時能收獲大家帶鼓勵的點贊,但在跑步里程上,似乎每天我的女上司都能拔得頭籌。
我很喜歡這種帶有互相鼓勵、鞭策性質的組群,而這在德國比較少見。
因為我的緣故,我所有在德國的親朋好友也都開始使用微信。他們調侃說我已或多或少地變成了一個中國人,我很樂意聽到他們如此評價我,我將這當成一種美譽。偶爾照鏡子時,我會笑著問鏡中的自己:“貝爾格曼,你是中國人嗎?”現在我就餐時總喜歡來點米飯,不再像歐美人那樣喝涼水,甚至練就了“蹲廁”的絕活。我覺得自己唯一還做不到的就是:在炎熱的夏天,像一些當地人那樣將汗衫高高地撩起,露出肚皮在街上晃悠。據我觀察,這種私底下被人們稱為“京式比基尼”的著裝方式,尤其被一些較胖的中年大叔所中意。
在北京,我經常乘坐地鐵上下班,北京地鐵站臺安裝的地鐵屏蔽門給我的印象格外深刻,這既保證了乘客與列車的安全,能有效避免許多事故的發生,也讓候車環境更舒適、整潔、美觀。我的德國朋友們對此也都贊不絕口,因為歐美的大多數地鐵站都沒有安裝玻璃屏蔽門。“為什么沒有呢?”“大概是沒錢吧。”朋友聳聳肩。
讓我發出感慨的還有地鐵站里的安全感。無論是午夜時分的末班地鐵還是清晨的首發車,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而在柏林的地鐵站里,人們總有一種任何時候襲擊都可能發生的隱隱不安感,暴力事件也時有發生。大家別忘了,柏林的常住人口是350多萬,而北京市2017年末常住人口為2170萬。如今在德國,圍繞公民安全感展開了許多討論,我也常想:如果安全感缺失,其他的一切何以安身?
在中國的公交車上,除了司機之外,往往還會配備一位乘務員。這類工作人員可以協助維持秩序,解答乘客線路咨詢等問題。我的中國朋友告訴我,這也是幫助解決社會就業問題。不管怎樣,我都認為這是件多方受益的事情。
因為工作原因,我會經常去中國各地出差。像許多中國人一樣,高鐵出行成了我的首選。我記得在德國,如果列車時速能達到200公里,乘客們就會感到心滿意足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當我坐在時速350公里的“復興號”上時,內心五味雜陳。因為我來自一個擁有大眾、奔馳、寶馬等品牌的國家,那里的人們乘火車還是按部就班地使用紙質車票。盡管目前歐洲,特別是德國產的豪華轎車在中國滿大街跑,但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品牌車開始加入競爭,尤其是電動汽車這塊,中國似乎正在逐步擴大其世界領先優勢。據稱,中國超過90%的自主品牌汽車的鋰電池都在本土生產,而德國受電池生產能力所困,相比之下反而處于弱勢。大概這就是中國媒體常提及的中國能靠電動車來“彎道超車”。
中國的改革開放應該說是給全世界的一份禮物。這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因為我三十年前就曾經到過中國,所以,經常會有德國或中國的朋友問我:那時的中國是怎樣的?
當年剛剛十四歲的我,跟隨我的父母和哥哥來到中國。
讓我記憶猶新的是,身高1.98的父親入住涉外酒店時的窘境。他的身高使得他每次進出酒店房間時都不得不屈身彎腰。而我似乎被餐廳里的各種高分貝的噪聲給嚇呆了。大家都在高聲交談,往往一個高聲喊叫的雜音剛剛襲來,馬上就被不遠處另一個更高音壓下去。今天我終于弄明白了,那此起彼伏的“Fuwuyuan”(服務員)的叫聲,是漢語對餐廳侍應生的稱謂。
那個時候,甚至包括今天,中國人用嘴剝離、咀嚼各種入口食物的方式和能力讓我嘆為觀止。簡簡單單的一雙筷子是餐桌上唯一的食具。人們用筷子將各種食物直接送入嘴里,經過嘴里一系列運作,然后將各種骨頭、魚刺吐出到桌面,講究點的會將棄物放在碟子里。
而中國人“嘴上功夫”的厲害也體現為對“嗑瓜子”的癡迷。餐廳候餐、看電視、坐火車、三五成群聊天時,朋友們飲茶喝酒時,大家手里通常都拿著一把瓜子。
酒足飯飽之后,人們會打著飽嗝,有些人會帶著滿足的神態拍打自己的肚皮。而今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這一餐桌現象已越來越少見。
物資豐沛與人們文明程度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相關聯的。還記得當年父母總在餐館徒勞地希望獲得一杯涼水,而服務員總是一臉的茫然,因為中國人通常喜歡喝與自己體溫相近甚至更高溫度的溫熱水。今天在中國,餐廳服務員會主動問你:水要冰的還是溫熱的?
中國的開放,不但讓更多的外國游客來到中國,也讓更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去感受外面的世界。我曾向一位中國朋友咨詢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他脫口而出:“旅行的便捷。”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86年至今,中國逐步放寬出入境限制、簡化出入境手續,近幾年中國出境游人次都超過1億,這與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年均7000人懸殊之大,讓人驚嘆。
門戶開放自然也造成了一些對西方生活方式盲目模仿和崇拜的現象。三十年后的中國,在我看來,肥胖人數比當年至少多上百倍。讓我有點困惑的是,素來以吃飯講究、擁有千年飲食文化而聞名于世的中國,本身擁有那么多既美味又健康的餐館,為什么仍然滿大街都是外國快餐連鎖品牌?但我的中國朋友很快就回答了我的問題:1987年11月,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了第一家門店,1990年10月麥當勞登陸深圳,一北一南從此開啟了洋快餐對中國餐飲領域的滲透;90年代,在麥當勞或肯德基請朋友吃飯,是很有面子的行為。但現在,至少在中國中產階級眼里,那里只能是偶爾帶小朋友去坐坐的地方。
目前讓許多中國人趨之若鶩的是各類養生保健品,洋快餐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了。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同樣一件事情,在德國可能還在反復討論可行性,而中國可能已將它變成現實。
中國的高效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爭辯。德國柏林新機場勃蘭登堡國際機場,2006年動工建設,原本計劃2012年6月開始使用,現在預計要推遲到2020年交付使用。拖延整整八年,總造價也從起初的20億歐元漲至超過60億歐元,其間柏林航空公司受其拖累,已于2017年8月宣告破產。我難以想象在中國會出現這種情況。
在中國,我遇到了1984年獲得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哲學家、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忠尚先生。能說流利德語的李教授曾長達八年擔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并曾擔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副總編。這些年李教授一直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著作頗豐。他對我說: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正確的,中國首倡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事業。
對這點我體會頗深。中國人通常緊密團結在親朋好友或依據地域構建的各種“圈子”里,并對未來保持樸素的樂觀情緒。“中國人通常知道自己來自何處,又要去向哪里。”我的朋友告訴我。我不希望去想象,當外人試圖去傷害這個“集體”時,會激發中國人何種群體反應。所以,任何攻擊中國的行為應該說都是極不明智的。
在中國,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備受重視。在我看來,中國人的這種泰然自若的實用主義以及集體榮譽感,對大家身處的自私自利、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無疑是一種健康的矯正。中國的發展之路顯然只有通過中國人根據自己的探索經驗來實現,而其成功模式也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
因為采訪的需要,大半年來,我的足跡遍及中國大江南北。在被譽為中國革命老區的延安洛川,我品嘗到了以色、香、味俱佳而著稱的洛川蘋果。如今這里被稱作“蘋果之鄉”,3.5萬公頃土地,每年近90萬噸的產量,讓洛川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現代蘋果產業園區逐步建立起來,這里有優質的蘋果汁、蘋果醋,還有我吃過的最爽口、酥脆的百分之百天然蘋果脆片。當地村民告訴我,當地人95%的收入來自蘋果種植,而且超過60%的果農年收入超過10萬元。
因為焦裕祿而聞名中國的河南省蘭考縣,長久以來一直因為風沙、鹽堿和內澇而成為中國國家級貧困縣。可當我2017年去那里時,當地人自豪地告訴我,蘭考縣已于當年3月份成為河南省貧困退出機制建立后的首個脫貧縣。焦裕祿當年擔任蘭考縣委書記時,為抗擊風沙和鹽堿,大力推廣種植泡桐。今天,作為“泡桐之鄉”的蘭考,顯然受益于當年的這一舉措,因為蘭考泡桐是制作古箏、琵琶等樂器的面板的最佳材料。走在蘭考縣,到處可見樂器加工廠。當地連小孩子都會唱:“要想富,栽桐樹。”
我的一位中國同事對我說:“在歐美,經濟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我們這剛好相反,因此,我們能迅速實施惠及所有人的大型項目。”我想,也恰恰如此,西方國家對中國存有太多的偏見。當我因為辦理工作簽證而在德國進行各項體檢時,得知我要移居中國,個別醫生毫不掩飾地表示不理解:“你為什么要去那個糟糕的地方?”可見,學問并不能根除人們的偏見。
我當然也讀到過關于中國食品安全、霧霾、環保、抄襲的負面報道。面對人們的質疑,我告訴他們:“如果你見過三十年前的中國,再來對比今日之中國, 或許你們就會產生與我一樣的感受。”高速發展的經濟難免帶有不同程度的后遺癥,但這個國家似乎具備天生的自愈功能,外族的蹂躪、鐵蹄的踐踏,她總能如鳳凰涅槃般浴火重生。
我相信她也一定有足夠強大的自我糾錯機制,在自我實踐與西方的錯誤中走出一條自己的改革之路。
三十年前那次中國之行,我父親對另一位外國游客說:“下個世紀甚至千年是屬于中國的。”
對方聽了,不以為然地哈哈大笑:“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十年后,某些國家提出“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中國人的勤奮和實干精神讓世人在震驚的同時也感到不安。但我想說,當我身處遠離家鄉八千公里的北京,無論是在商店、地鐵站還是大街上,總能遇到熱情相助的中國人。有一次我迷路了,一對夫婦主動將我送回居住地,盡管他們自己需要趕往另外的方向。還有一次,在午夜的街頭,見我無法叫到出租車,一位熱心的年輕人通過自己的“叫車軟件”幫我訂到一輛車,甚至幫我墊付了車費。盡管中國人外表通常不茍言笑,但卻有一種植根于骨子里的樸素和善良。
一位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德國女子對我說:“對中國,或許你不必愛她,但一定要重視它。”
我回答她:“可是,我已經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她。”
(楊堅華/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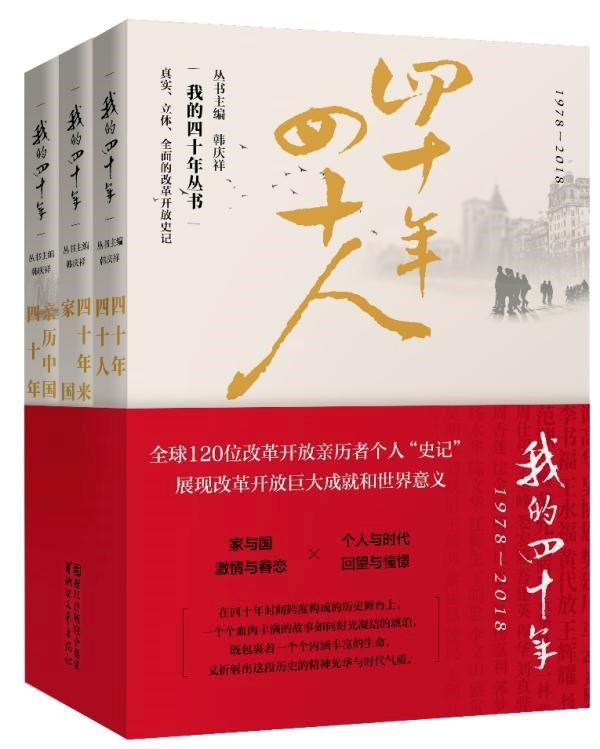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