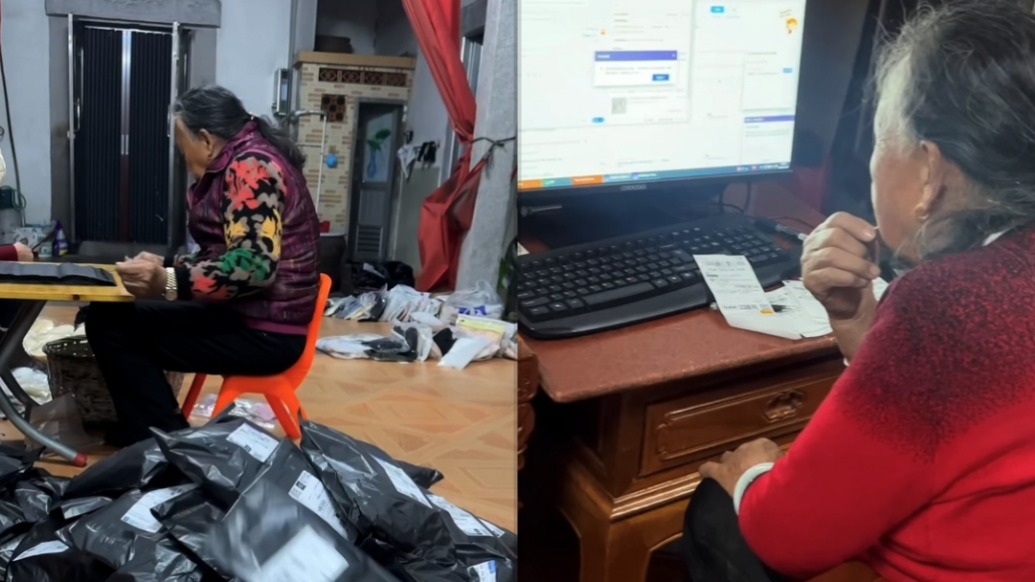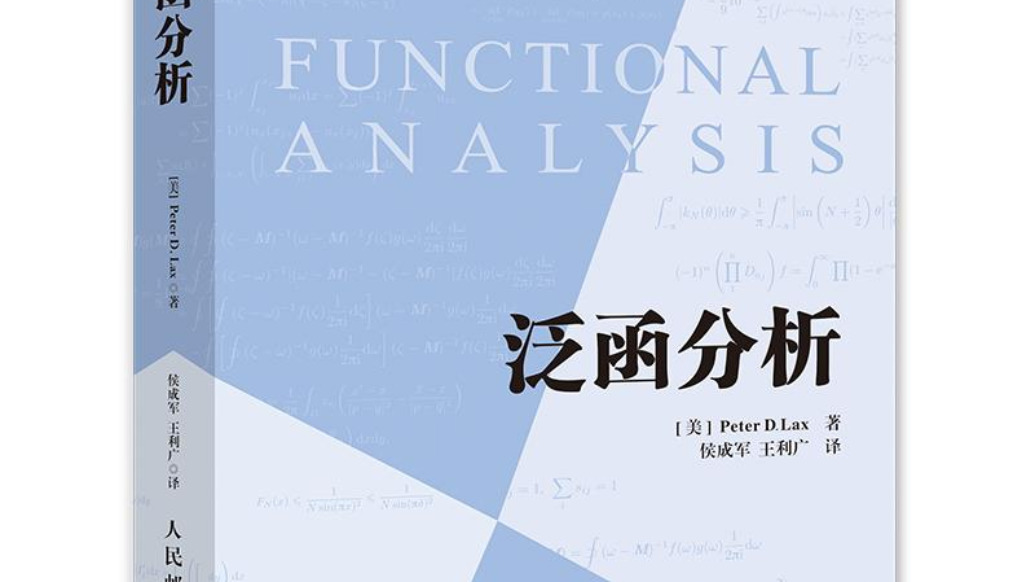- 15
- +1389
奶奶的墳沒有名字
國慶回家,爸爸說要帶我去看奶奶。我本該在暑假時就去看她,但那時正值雨季,上山的路極其難走,就一直耽擱下去了。
爸爸把車停在了山腳下,我們兩個徒步上去。迎面而來的風吹得很澀,樹葉與空氣碰撞,呼啦啦地響著,天仍然藍得那么遙遠,云就飄在遠的盡頭。家這邊其實早就鼓勵人們將逝者的遺體火化,但還是有很多人放不下心里的那一點念想和如同符咒一般貼在心里的陳舊觀念,選擇把親人的遺體裝進棺槨、埋進土里。于是我們路過一座又一座的墳。它們有的被修繕得很是講究,端正的墓碑、琳瑯的祭品,甚至還在外圍砌了一圈圍墻;有的就只是一個小土包,上面長著幾根雜草,沒有圍墻、沒有祭品,也沒有姓名。
奶奶的墳也沒有姓名。
四周被爸爸和叔叔用鐵絲簡單圍了一個四方形,墳前擺著一個酒壺和兩個小酒盅,還有兩枚已經腐爛一半的橘子。爸爸拿出鐮刀,割掉周圍的雜草,陽光曬過的草還透著點清香,頭頂的天也藍得正好,如果沒有眼前這座墳,也許我會把這當成是一次秋游。
我就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該做什么。
我問爸爸:“我們不燒點紙錢嗎?”
“不燒了,這兩天正好是防火期。”他回答。
“奶奶又不喝酒,你們把酒擺在這干嘛?”
“我們沒擺,你爺放的吧。”
我看了看地上的酒壺和酒盅,又看了看四周:“這個地方是本來就用來做墳地的,還是你們買下來的啊?”
“買的。”
“為什么買這兒啊?”
爸爸沒有回答我,像是沒有聽見,手中割草的動作一直沒停下來過。
我蹲下來把酒壺和酒盅擺正,其中一只酒盅通體覆上了一層灰塵,我拿出紙巾把它擦了擦,另一只也同樣沾上了灰塵,但杯口處相對干凈一些。我知道,這是爺爺來過了。
我也知道,爸爸他們為什么把奶奶的墳地選在這里,因為他們不想讓奶奶葬在爺爺那一系的祖墳里。
奶奶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母親,太爺爺很快又娶了另一個媳婦。我不知道她的后媽對她怎么樣,但根據親戚們的回憶,那并不算是一個合格的母親。再加上奶奶是家里的老大,必須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任務,便早早就輟了學,做一些活計補貼家用。也許就是這些原因,奶奶做得一手好飯。
以前我不愿意大老遠地到奶奶家去,但要是說去奶奶家吃飯我倒是很樂意,爺爺會在頭天問好我要吃什么,定下時間,然后指使奶奶去做。
我還能記起在那間小草房簡陋的廚房里,奶奶在鍋臺前面忙活的身影。這邊的大鐵鍋里倒好油,用那根已經有了年頭、被煙熏得發黑的燒火棍扒拉著灶坑里的柴火,等油熱到了時候,把已經搟好的酥餅往鍋里一拍,瞬間就能聽到餅皮發出滋滋啦啦的響聲,油香混合著面香飄滿整個屋子。剛烙好的酥餅表皮酥脆得一碰就掉,捻起一片面皮可以嘗到一股焦香,餅里邊卻是松軟的,一層疊著一層,有的夾著椒鹽,有的是燙嘴的白糖餡兒,這是奶奶為了照顧我們口味不一致而費的周章。
那邊的灶上駕著一口小鍋,鍋里是泛著金黃的小米粥,用小火慢慢熬著,隔著鍋蓋,可以看到粥在不斷地冒著“咕嘟咕嘟”的小泡,每“咕嘟”一下,小米粥就會多一分粘稠與香甜。人們都說粥冷卻后最上面凝結那層“粥油”是一鍋粥的精華,但我那時卻偏偏喜歡去搜刮粥底,就是粥熬好后黏在鍋底的那一部分。奶奶知道我喜歡,會在把粥倒進小盆里之后,用勺子仔細地刮下那一點點黏糊糊的粥底,盛到我拿手捧著的小碗里。爸爸會在旁邊笑我:“什么好東西呀,跟個寶貝似的。”我那時太小,還不知道怎么反駁他,只是撅嘴瞪著他。奶奶也從不幫我還嘴,只是一邊做飯一邊在嘴里念叨著:“好吃不如得意,好吃不如得意。”直到現在,當別人不解地問我“你怎么吃這個呀”的時候,我還會下意識地冒出一句:“好吃不如得意。”
爺爺并不是奶奶的第一個對象(我們這邊管“男女朋友”叫“對象”)。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同村的一個小伙子追求過她,他們兩個從小就認識,奶奶也很中意他,但是奶奶的父母卻嫌棄那個小伙子家庭條件不夠優渥,給不出像樣的彩禮,遲遲不愿意讓他們結婚。后來,小伙子一家搬到了別處,斷了音訊,兩個人再也沒有了聯系。再后來,有媒人把爺爺介紹給了奶奶一家,也談不上什么情投意合,反正雙方家庭都覺得合適,就這樣一直過了幾十年。
爺爺家境很好,據爸爸回憶他小的時候基本沒怎么受過苦,他的文化水平在那個時候也算不錯,雖然沒讀過正經的高中和大學,但爺爺頭腦活絡,記憶力很強,有時甚至聰明得近乎狡猾。這在他玩牌的時候尤其得以體現,他總是贏,他的同伙也跟著贏。
我曾經在爺爺家的柜子里翻到一副牌,和我見過的撲克牌有很大差別,這副牌的形狀是較細的長方形,花色也不是紅心、方片一類,而是打扮古怪的人像,每個人旁邊還寫著字。我拿著這副牌去問爸爸這是什么,他說這叫“五張”,也是一種紙牌。我正拿在手里把玩,想看懂上面畫的到底是什么,姑姑看到后,卻一把奪過來,用一種半開玩笑的口吻說:“這可是你爺爺的寶貝,將來得留著傳家的。”
原來那是爺爺專門用來出老千的牌。
原來他玩牌總是贏不僅僅是因為他聰明。
在爺爺和他的酒肉朋友們在牌桌上呼風喚雨時,奶奶一個人在家里喂牛、鋤地、照看孩子。奶奶生了三男三女,爸爸是老五。大女兒剛剛成年未來還沒有著落,小兒子還在襁褓中哭鬧,六個孩子像六條鞭子,而奶奶是被鞭子抽打得團團轉的陀螺。然而,這并不是奶奶身上最重的包袱。
在把田地里的雜草鏟除干凈、給兩頭奶牛填好飼料、安頓好亂成一團的孩子之后,奶奶開始準備飯菜。再過一會兒,爺爺就會大搖大擺地從那扇大門走進來,頭上扣著他那頂草帽,帶著滿身的煙味,身旁跟著他那幾個朋友,一邊走一邊嗤笑著今天那伙人有多傻,而他們又狠狠地撈了多大一筆。
進了屋門之后,這些人會假模假樣地和奶奶打個招呼,緊接著就被爺爺領進客廳,坐在奶奶已經擺好的桌椅上,等著奶奶把做好的飯菜端上桌,一邊客套著說“嫂子辛苦了”、“哪天來我們家吃飯”,一邊拿起筷子開始大嚼大咽。爺爺坐在正中間,接受著他們的恭維,仿佛一位凱旋的大將軍端起酒杯與他的將士們慶祝戰斗的勝利,然而這勝利是用卑劣的詭計贏得的。酒杯碰撞發出清脆的響聲,一幅賓主盡歡的和樂景象。吃飽喝足,他們靠在椅背上打出一個泛著酒味的飽嗝兒,互相東拉西扯幾句之后,準備起身回家,一邊走還不忘回頭和爺爺定下明天玩牌的時間,爺爺大笑著答應并把這伙人送到門口,回身看到奶奶拿著抹布,收拾大快朵頤后留下的杯碟,沒有過去幫忙,沒有一句慰勞,只是說了一句:“聽著了吧,明天我得早點走,別忘了起來做飯。”說完,就回到屋里坐在炕上,把腿一盤,清點他今天一天的戰利品。奶奶低低地應答了一聲,在圍裙上抹了兩下手,端著裝滿了臟碗的盆走到廚房。想說的話都融進了油污和泡沫,隨著那一盆臟水一同被潑到了屋外,被風吹成干涸的泥巴。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下去,爸爸和大爺到外地去上學,三個姑姑也都各自出去找了份活計,六個孩子里只有我的老叔還尚未長大,跟在奶奶身邊。
一天清晨,奶奶像往常一樣早早地起床,清掃了一下牛棚,到菜園子里摘了些菜。做好了這些事情后,她回到屋里準備叫爺爺起床,卻發現原本還躺在炕上打著呼嚕的人不見了,被子凌亂地堆在一邊。奶奶跑到屋外,喊了幾聲,沒有人回應,又跑到窗戶根兒前往街上看,路上空蕩蕩的,半個人影也沒有。奶奶像是意識到了什么,趕緊找出壓在柜子最底下的錢夾子,果然,里面只有幾張毛票,其余的錢都被爺爺裝進了自己的口袋,和人一起消失了。奶奶拿著那幾張薄的可憐的錢,像一片融化的雪花,癱坐在地上。
后來發生了什么,沒有人愿意和我講。我只知道,一年多后,爺爺又像憑空消失一樣憑空出現在家門口。而老叔因此對爺爺產生了深深的怨恨,十幾歲就離開家出去打工,直到奶奶生病他才回來。
我只知道,不管爺爺如何爭辯如何懇求,爸爸他們仍然堅持要把奶奶的墳地設在遠離爺爺家祖墳的地方。
我站在奶奶的墳前,那些前塵往事在我身邊打了個轉,又被秋天的風輕輕地吹走了。其實我一直都想問問她,你有沒有為自己活過?在我有限的記憶里,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奶奶表達過自己的想法,用“我想……”、“我覺得……”這樣的句式說話,她永遠都在尋求別人的意見,考慮別人的感受。爺爺卻是永遠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他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從來都不吝嗇,但他嘴上又是另一套說辭,“你媽愿意吃這個”、“你奶奶喜歡”,奶奶就在一旁,不搭話也不反駁,伸手接過爺爺遞給她的那點東西,誰也不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歡,因為她從來沒說過。爺爺偶爾有個頭疼腦熱,會像得了什么不得了的病癥一樣急著吃藥、去醫院,給全家人挨個打電話通知一遍,奶奶就陪著他折騰,半夜起來翻箱倒柜地找藥,聽他拿著電話大聲地向兒女們訴苦。
有一次他執意要坐車去外地檢查身體,只因前一天晚上測量血壓時比平時高了一些。奶奶就在爺爺躺在病床上杞人憂天時,拿著證件和化驗單在醫院跑上跑下,不慎摔倒在樓梯上,本來腿腳靈便的她摔傷了膝蓋,疼得坐在地上半天不能動,而爺爺還在病床上等著奶奶來伺候他。之后的幾個月里奶奶都無法正常走路,并且余生都得和拐杖作伴。奶奶雖然傷了一條腿,好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爺爺那無所顧忌的態度也稍微收斂了一些,我們都以為她會一直就這樣過下去。
一天夜里,爸爸被一陣鈴聲吵醒,他拿起手機發現是爺爺打過來的,估計又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小事,接通后剛想問問他怎么了,卻聽到電話那頭爺爺急切地喊著:“快過來送你媽去醫院吧,她頭疼了半宿,剛才暈過去了現在開始說胡話了!”爸爸沒時間多問急忙趕到奶奶家,和聞訊而來的姑姑、大爺一起把奶奶送到醫院急救。醫院走廊里的燈慘白慘白,刺得人眼眶發燙。終于,急救室的門“咯吱”地開了,醫生說,奶奶的大腦里長了一顆瘤,而且這顆瘤在奶奶的大腦里待了很久,已經沒有辦法治愈。情況好的話,還可以再維持一兩年,不好的話,也許就幾個月。
爸爸他們都像受到了當頭一棒,他們不明白,奶奶一直看起來好好的,除了那次腿受傷和經常咳嗽,沒有其他明顯的毛病,怎么會……他們轉過頭去詢問和奶奶朝夕相處的爺爺,爺爺支支吾吾了半天,才道出了實情。
原來,很久之前奶奶就常常會間歇性的頭痛,但她卻什么都沒有說,要么咬咬牙挺過去,要么自己找點止疼藥吃了。而爺爺知道后,也沒有像他自己頭疼難受一樣告知家里人,他看奶奶的癥狀好像也沒那么嚴重,就根本沒把這當成是大事,只是偷偷帶著奶奶去了鄉下,找了一個所謂的“大夫”,也是他以前的牌友,討了點偏方對付下去。可這偏方并沒起過什么作用,奶奶用的最多的還是止疼藥。疼痛雖然能暫時止住,但是,那顆邪惡的瘤卻不是幾片止痛片就能消滅的,相反地,它在奶奶的大腦里日復一日地滋長,終于,在那個平靜的夜里爆發了。
當時我正在哈爾濱陪姥姥,聽到消息后就立刻訂了第二天早上的火車趕過去。我頭一次發現原來火車這么慢,車窗外的樹木像伸懶腰一樣移動,那條鐵軌好像永遠都沒有盡頭。
下了車后,爸爸直接把我接到了醫院,他什么也沒說,只是沉默地領著我走到病房。我走進房門,看見奶奶背靠著枕頭坐在病床上。好像也沒有什么不同,我心想,只是把頭發剃短了。大爺看見我來了,拉著我走到奶奶跟前笑著說:“媽,你看誰來了?你還認不認識她?”又扭頭看向我,笑容擠出的每一根皺紋似乎都在嘆氣,說道:“奶奶的腦子一會兒明白一會兒糊涂,剛才把我們好幾個人都弄混啦。”
我坐到床邊,握住她的手,想了很久卻不知道該說什么,是說“我回來了”,還是“你的病怎么樣啊”,還是“你認不認識我呀”,我的喉嚨像是被鎖鏈鎖住了,哪句話我都說不出來。反倒是奶奶盯了我半天,微弱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大家都笑了起來:“你看,媽還認識。”
這時,我感覺奶奶握住我手的那道力量加強了,我反應過來她應該還要說什么,就又湊近了些。奶奶張著嘴,像是在回想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樣,半晌,她好像是想起來了,兩片干癟的嘴唇開開合合,顫巍巍地抖出幾個字:“吃……吃飯了嗎?”
那一瞬間,我的心臟仿佛被穿了一個洞,但是血液已經流干了,只是一個殼子空蕩蕩地掛在那兒,很冷。下一秒卻又從四面八方涌上了滾燙的血液,直直將它灼燒,我聽到那層薄薄的筋膜破裂的聲音。我想起從前無數次去奶奶家,幾乎每次見面她問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吃飯了嗎?”對于她這樣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來說,填飽肚子是非常重要的事,而她的孫女有沒有吃飯是更重要的事。
讓我更覺得難受的是,即使是這種時候,她還是想著我,想著我爸,想著爺爺,想著所有人。
除了她自己。
上個冬天回家時,奶奶的情況進一步惡化,受那顆瘤的影響,她幾乎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她的拐杖被擱到了一邊,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輪椅。一天里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只能待在床上,有時大家會推著她在屋子里四處轉轉,到窗戶前曬曬太陽,就像一株被精心照料的植物。她的頭發已經長回了原來的長度,有時我看到她坐在那兒,似乎和以前沒什么兩樣,如果沒有那雙渾濁的眼睛和那雙時時顫抖的手的話。
有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去奶奶家吃餃子,奶奶系著圍裙鋪好面板,用筷子攪和攪和裝在小盆里的肉餡,拿起搟面杖麻利地搟起了餃子皮,圓圓的小餅一個接一個地從她手中飛出來,我們圍成一圈幫她包餃子,奶奶搟好了皮,也拿起一張餃子皮放在手心里,夾了一筷子餡放到中間,開始把餃子捏出一個個整齊的褶,就在最后一個褶即將捏好、馬上要收口的時候,她突然不見了,那個還漏著一條小縫的餃子“啪嘰”掉在了地上。我立刻從夢中驚醒,在黑暗中坐了良久,仿佛自己就是那個餃子。
奶奶后來果然不見了,就在今年的三月初一,家里的雪還沒化,這個冬天因為她的離開而被無限地延長。在她尚有清醒意識的時候,還曾拼命地從喉嚨里擠出一個個字,暗示爸爸叔叔他們,爺爺已經是個老頭子了,讓他們不要再把過去的事情放在心上。
我看著面前這個隆起的土堆,想起我與她見的最后一面,幾個月前還坐在床上與我揮手告別的活生生的人,如今成了深埋在地底的一具尸體,也許肉體早已經腐爛了,在那層層黃土下的只剩她的骨骸。我不痛苦,我也不想哭,我甚至驚訝于自己近乎冷漠的平靜,只是感覺胸口箍了一條細細的線,散發的痛覺像一道微弱而持久的電波。也許我是替奶奶不值,我為她的真心錯付而遺憾,我也為她的心甘情愿而生氣。但是我已經沒有機會質問她一句,你能不能為自己活一次?
但我又轉念一想,也許這就是她想要的,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她的滿足來源于她給別人的奉獻,即使生活讓她嘗到的都是苦澀,只要她看到別人快樂,那一刻也能品味到回甘。
風吹起來了,有幾張紙錢忽忽悠悠地飄過來,許是從哪座新墳過來的。這時,對面山腳下響起了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應該是辦喜事吧,國慶期間都是好日子。紙錢在我的面前盤旋,鞭炮聲包裹著我的耳朵,我站在那里,好像站在一個生與死、喜與悲的交匯點,風穿過我,我也穿過風。
爸爸沒有像大多數人上墳一樣,拉著我下跪、磕頭、大哭,我們只是無言地站著。過了一會兒,我聽到他說:“回家吧。”
我說:“好啊。”跟著他走了幾步,我忽然想起來一件事。我悄悄回過頭對著奶奶的墳墓擺了擺手,像每次從她身邊離開一樣,對她做了個口型:“奶奶,我回家啦。”
只是這次她沒有沖我擺手。
我和爸爸走在下山的路上,明天我就要踏上返校的旅程。這是我五年來第一回看到家里的秋天,短短三天,像一個不明就里的夢。山上的樹還是那樣多,我看到秋天逐步走近又走遠,直到樹葉盡凋,有時冷風乍起,秋天似乎再也不來,于是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個季節。
(返鄉導師汪成法,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韓昕穎,安徽大學。家鄉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的一個小鎮上,那里沒有大多數人想象中的民族風情,有的只是最普通的人和事。
文 | 韓昕穎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投稿touhaotougao@sina.com或加小微shhxixi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