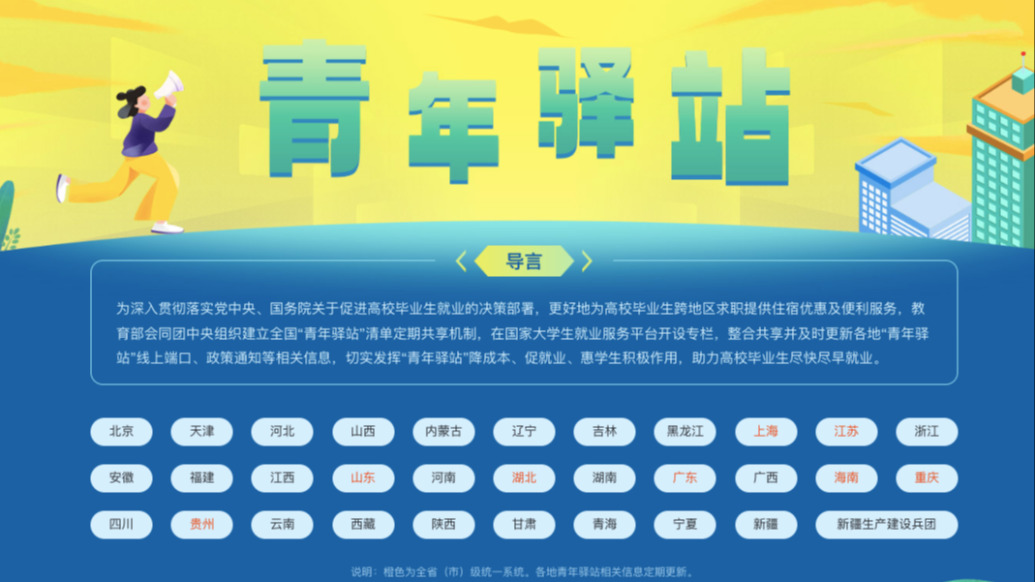- 6
- +1494
村里“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電話打爆,城里家長求入讀
一場演講,范家小學火了。
這是一所位于廣元大山的農村小學。43個學生,13名老師,大部分是留守兒童。當“山區”“留守兒童”“村小”這幾個詞集中出現時,你的腦海里會是一幅怎樣的畫面?

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何帆這樣評價: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公辦名校、國際學校,而是四川這所大山深處的農村寄宿小學。
這到底是一所怎樣的學校,為何一些城里的家長也紛紛打來電話想要孩子入讀?
01
意外走紅
電話被打爆,“你們小學怎么了?”

新年之交,一場跨年演講,讓更多人知道了這所廣元山區的范家小學。
學校不大,一個小操場,兩棟相連的3層樓房,一側是教學樓,一側是住宿區。除去幼兒園,全校共43名小學生,13名老師。其中,大部分學生為留守兒童,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學校,一周回家一次。
羅振宇在深圳舉行的2018跨年演講,長達4個小時,他在尾聲部分講到了這所小學的故事:一想起留守兒童,我們總覺得這是一群前途渺茫的孩子,然而,所有最先鋒的教育理念,在這所山區小學都能看到。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范家小學一夜間火了。
從距離看,范家小學距離廣元市區算不上遙遠。自廣元出發,經寶輪鎮,沿著瀝青山路,一個小時不到即可抵達。學校在一片小型村落的背后,倚著山腳。
那天,紅星新聞記者到達時,校長張平原正在備著一份分享材料,留給他的交稿時間已經不多。他從旁邊的會議室找來了一個取暖器,拖著兩個首尾相連的插線板。他把溫度調到了最高檔,又轉身打開了背后的空調。
“我敢說成都也找不出幾所像我們這樣的學校。”言語之中,張平原對他的學校充滿自信。
那場演講帶來的影響超過了之前所有的媒體報道,“這可是面向全球的直播。”
之后的一個夜晚,在寶輪鎮上的一個小餐館內,校長張平原講述了這場演講之后的幾個小故事——
演講當晚就有不少教育同行發來電視畫面,“他們說范家小學上電視了”。當時,張平原沒當回事;第二天,市區兩級領導電話不斷,問“你們學校怎么了”、“‘羅胖’(羅振宇)是誰?”,其實他和領導一樣迷惑,誰是“羅胖”?
說到這里,另一名老師打趣道,“當時還有說要來學校找‘羅胖’的。”跟著,當地幾家媒體的記者很快到訪,政府部門的慰問也跟著到來。
“這說明我們做的是對的,我們的工作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張平原舉起茶杯,向餐桌前的幾名老師振奮地說,“未來中國的優質教育一定在農村!”
紅星新聞記者到訪的那天下午,這是張平原多次提到的一句話。
02
臉上的自信
“不評三好學生,成績不是最重要”

初到范家小學,紅星新聞記者的印象是這樣的:不同色彩的教室、原木色的桌椅、落地的空調、接入互聯網的電腦和電子“黑板”、人手一塊的平板;隨便走進一間教室,一定會收到孩子們的問好,無論誰,都能跟你聊上天。
老師不在,學生們能自己做著練習,背英語也能當成游戲玩;飯后教室的沙發上他們會一本本翻著書架上的書;課間,小操場能瞬間變成“花果山”;睡覺前,一年級的小個子們也能自己抱著臉盆洗漱,鋪好被子安靜睡覺。
墻面上,各班都有屬于自己班級的“萌寵”,一個動物或者一種植物。比如一年級墻面上的綿羊,象征著善良而友善;五年級墻上的竹子,象征著有氣節而奮發向上;六年級的小蜜蜂,象征著勤勞而奮進。
更重要的是,無論何時,你總能看到孩子們臉上的微笑。
孩子們和校長的自信來自哪里?
張平原2014年起當上范家小學校長,之前的20多年,與許多鄉村教師一樣,他“走出去”的機會不多。“農村孩子起點低,那我們就不追求成績,這個社會除了極少的科學家外,更多的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給他們自信和陽光,給他們良好的素質,他們今后也一定會是優秀體面的勞動者,一樣為社會做貢獻。”
于是,學校告示欄里寫下了學校的辦學目標:辦美麗鄉村學校,育陽光自信少年。
在這里,考試不重要——“學什么就考什么,自己出題自己考,除了小升初的測驗以及市里的抽測,學校都不參與校外的統一測驗。”張平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因為人少,考完當場老師就能改出對錯,再一一給每一個學生講解錯在哪里。
在這里,三好不重要——學校不參與“三好學生”的評選,而是用“美少年”代替,“你可以是運動美少年、勤勞美少年、友善美少年、文明美少年、陽光美少年……總之學科成績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基礎差起點低,但成績是唯一的嗎?八九十分就夠了。科學家要人干,可畢竟是少數,社會的崗位工作又千萬種,好成績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成績不好也有干得好好的。”張平原一開始就想得很實在。
03
一場變革
“農村教育資源少?錯誤認識”

范家小學的課表上,語文、數學等課程集中安排在了上午,下午的時間則集中在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術課程上,另外則是大量的鄉土課程和項目學習。
在張平原看來,玩耍是孩子的天性,校園不該只是一個為了學習的環境,“玩”也該是重要的方面,“玩甚至比學更重要,當然也要讓他們玩得開心、玩得有水平。”
一項鄉土課程從2016年春開始,一直持續至今。
每周三的整個下午,學生們將走出校園,行走在田間。楊秀麗說起了這項課的開端:“一開始帶著孩子們出去玩,采野菜,大家都很興奮,但其實很多都不認識,那就利用這個機會,讓孩子們認識野菜,采回來后再形成文圖,讓他們自己查閱資料,弄清楚每一種野菜的名字和價值,做成一個家鄉的野菜課題,最后大家再一起把野菜炒著吃了。”
之后,《家鄉的植物》《家鄉的野果》《村里的老井》《微型水電站采訪》《留守老人調查》……等眾多課題在隨后進行。“根據不同年級開展不同的課題,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需要采集樣本,然后畫出來,做成卡片,形成文字,再講述出來。不懂的需要自己去求助村民,在玩耍中鍛煉孩子的綜合素質。”
張平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部分同學的植物圖畫甚至可以用手機軟件識別出來。
項目式學習是另一項校園課程,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學習過程。
比如“豆”的學習,就需要學生們找到更多關于家鄉的豆,了解豆的演變,找到與之相關的字、詞、詩句,之后再講這些豆的種子種入土,讓它生根發芽,破土而生。
因為季節不一樣,那次學生們播下的黃豆沒能生長。但發豆芽則是可以的。這并不容易,師生們嘗試了兩三次才終于做成。最后,同樣一起做著吃了。
“都說農村教育資源少,其實這是錯誤的認識,農村的資源遠比城市多,在這里他們能接觸鄉村,走進大自然。”張平原說,這些鄉土課程的開展能充分培養孩子的交流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也增進他們對家鄉的了解和熱愛。


范家小學的學生們在吃午飯。

04
小班教學
師生比43:13,像家般溫暖

更重要的轉變還有教學方式。
因為人少,真正的小班教學在這里成為現實,比如四年級,全班僅有5名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級也僅有12人。“43個學生對應13名老師,這個師生比例是城市學校達不到的。”張平原說,“就連活動空間,城里學校幾百上千人擠在一起,哪有我們寬敞。”
這的確是一個很高的師生比,平均一個老師帶著3個學生。高師生比,更能讓每一個學生都得到老師的密切關注。而每周一次的教室會議上,張平原也要求老師們改變以往的大班授課教案,知識點要盡可能拆分開來,照顧到所有人,學生可以站著,甚至坐到沙發上上課。
六年級的一堂數學課上,老師王畢衛將當堂需要講解的試卷投放到電子黑板上。通過電腦隨機抽到的學生一個個走上前臺,扮演起臨時小老師,王畢衛只在一題結束后,強調一遍相應題目的解題關鍵。一堂課下來,所有學生都能被抽到。
楊秀麗是一年級的語文老師,教材版本的改變讓這些剛剛結束幼兒園的孩子們有些吃力。學期的大部分時間,她的教學幾乎在一對一進行。孩子們從學期剛開始的二三十分,變成了末期所有人都能及格。
張平原認為,在一個絕大部分學生為留守兒童的學校里,父母的缺位是爺爺奶奶每周一次粗糙的關懷彌補不了的。他們大部分時間仍是與同學和老師相處,在這里,班級應該像家一樣溫暖。“而這種相處什么最重要——尊重、體貼和信賴。”
這天傍晚,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哭著推開了三年級教室的門,找張平原哭訴,說,“他打我。”三年級學生齊齊望了過去,安慰他不要哭。正在教室的張平原接話:”誰打的,去打回來。”孩子轉身跑了出去,張平原也跟著出了門:“你們自己解決,解決好了給我說。”但眼前,幾個孩子已經重新玩到了一起。
老師蘇莉回憶起了一個已經轉學的“無聲男孩”。在校4年,這個叫范俊的孩子通過繪畫找回了自信,老師們還特地為他辦了畫展,至今學校的過道上還掛著他的畫。楊秀麗最愛開他的玩笑,“他咿咿哇哇,我們也跟著學他,但他不生氣,大家也都跟他玩。神奇的是有天上課,我在班上問上到第幾頁了,他一下站起來,說6……3。一個音到一個詞,現在有時還能說上一句。”
張平原說:“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05
走出去和想進來
城市家長打電話,希望孩子就讀

顯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
“第一年教育局問我需要什么支持,我提了20萬元。”張平原說,利州區教育局批了下來,這筆錢至今每年都有。20萬元帶來的改變,從一間教室開始。原先破舊的墻面、布滿電線的冰冷教室有了色彩,單一的空曠空間被分成了閱讀區、教授區、寫作區、獨處區。教室內多了書架、小茶幾和沙發,逐漸還有了空調、電子黑板和電腦,乃至現代化的錄播系統和學生人手一塊的平板。
從校長尋求變革、教育部門支持開始,良性循環發生了。
四年前,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辦的中國農村小規模學校年會在四川廣元進行。范家小學,就這么突然映入了與會者的眼簾。受到關注之后,一些社會組織開始進入學校,電腦、平板、網絡課件都源于此。
張平原和老師們也有了“走出去”的機會。多個教育論壇上,范家小學被作為中國農村教育探索的樣本進行一次次分享。
張平原還記得一次云南之行,“一個博士來接我,陪著逛西南聯大的舊址,做大會發言,身邊人隨便一問都是研究生、博士學歷。”他自嘲,“只有我一個大專的。”
云南之行,張平原感觸頗深:“你看當年的西南聯大,在那種艱苦條件下,誕生了多少大家,所以辦學并不在于硬件多好,教書育人還在于教育者的大情懷,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語文老師楊秀麗也不再是一個人埋頭教學,聯盟的建立,讓她和其他學校的老師一起通過網絡遠程參與語文教研。在范家小學教了21年年書的王畢衛也走進國內各個經驗分享的會場。更多老師,都有機會外出培訓。
當然,還有一波接一波的來校考察者們。
從范家小學畢業、升入廣元寶輪中學八年級一班的羅雨欣,至今記得一次接待對自己的改變。她在那次接待中擔任學生講解員。她突然發現,講解之后,自己“一下變得開朗了”。李明杰與羅雨欣同班,他眼里的變化是教室里有了書,課堂能夠走到校外。
升入初中后,李明杰和羅雨欣給人最大的印象是優秀和陽光,現在一個是生活委員,一個是語文課代表。另外兩位同樣是范家小學升上來的李文婧和雷含波,成績都處于年級前列,李文婧還是副班長,喜歡組織活動、性格很開朗。
另一位畢業生李忠林的媽媽在寶輪鎮跑著鄉村客運,路線正好經過范家小學。老師們有時也會坐上她的車,每次她都會向老師擺擺兒子的成績。李忠林媽媽覺得,在范家小學讀書之后,至少兒子“不再內向了”。
張平原很得意,“從我們這里走出去的學生一定不會差,至少能看到陽光和自信,”最近,最讓他激動的是,有遠在河北、成都的家長打來電話,希望入校就讀。


晚間,范家小學的老師在教室里輔導自學學生。

06
正在發生的變量
或是未來農村學校、農村教育改革方向

范家小學所在的茍村共529人,留守在家者基本為老人和小孩。2014年的數據顯示,廣元市利州區全區學生人數200人以下的學校共計14所,其中12所不足百人,農村微型學校占比超四分之一。
“這是全中國農村學校的普遍問題,不單是利州區。”廣元市利州區教育局副局長鮑海兵說,學校規模的萎縮讓老師教學不自信,校長辦學不自信,家長對學校也不信任,“校長開會,這些村小校長都不好意思說自己來自哪兒。”
但張平原的變革成為了一個突破口。為支持這種變革,教育部門引導成了農村微型學校聯盟,每年給每所聯盟學校保底劃撥20萬元,額外還會有25萬元用于聯盟開展活動。城鄉學校及老師的交流也在加大,新招聘70余名教師補充農村學校,對范家小學這類微型學校有名額傾斜。
“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公辦名校、國際學校,而是四川這所大山深處的農村寄宿小學。”——這是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何帆對范家小學的評價,他把評價寫進了自己最近出版的新書《變量》,羅振宇的線索也來源于此。
在何帆看來,范家小學把鄉村小學的劣勢變成了優勢。農村學校的學生流失嚴重,但老師的編制又不能跟著學生的流失轉走,于是師生比越來越高,就能讓老師給予每個學生更多的關注。反觀城市里的學校,都是大班大校,但,小班才應該是未來的趨勢,學校的最佳規模是師生相識。
“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很難公平競爭,要上大學也要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但在這里學業不再是首位的,反而能夠讓農村學生深入接觸素質教育。他們學會吃苦耐勞,孝敬父母、與人為善、熱愛家鄉,這些‘老理兒’就是中國文化這棵大樹的干和根。”何帆說,“對孩子影響最大的社會環境是由同齡人組成的社群,而范家小學給了孩子們最需要的東西:一個平等、包容、自信、樂觀的社群。”
原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麗偉曾多次探訪范家小學,在她看來,范家小學之所以能被廣泛認可,是在于它的理念、制度和實操都能做到貫通和一致。
“這可能就是未來農村學校、農村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口,或者道路和方向。”王麗偉覺得,“原來講到農村教育就會從扶貧的角度講起,認為解決問題的思路就是給他補錢、補資源。范家小學給我們的啟示則是,一種教育改革、教育探索和教育創新。”
(原題為《村里“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電話打爆,城里家長求入讀》)

- 巴基斯坦被断水
- 外交部回应美称中美仍在谈判
- 全国贸易摩擦应对工作会议召开

- 华宝证券:去年股票ETF规模增长近100%,为市场注入流动性活水
- 美股开盘:道指开盘跌0.1%,标普500涨0.1%,纳指涨0.1%

- 中国的一部传统儿童启蒙读物,第一句是“人之初”
- 上海的一所985高等学府,是中国的“建筑老八校”之一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