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細讀海子 | 如果不能帶來麥粒,請對誠實的大地保持緘默
文/魏天無
海子是一個沉重話題。大概因為這種沉重,《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以下簡稱《面朝》)從中學語文必修教材被移到選修教材,最后消失得無影無蹤。
據說,教師們很難回答學生的疑問:一位如此熱愛生活的詩人,怎么會走上不歸之路?但是好像沒有人探究,海子所熱愛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對于今天的我們又有怎樣的意義。
海子的好友、詩人、翻譯家西川說:“一個人選擇死亡也便選擇了別人對其死亡文本的誤讀。個人命運在一個人死后依然作用于他,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三十多年后,依然有許多人借助他的詩歌在思考。
海子本名查海生,1964年5月出生于安徽懷寧縣,自幼在農村長大。1979年,十五歲的他以安慶地區高考文科狀元身份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也從此開始文學創作生涯。畢業后先在中國政法大學校刊工作,后轉到哲學教研室任教,并隨學校搬遷到昌平新校址。海子開設的美學課很受學生歡迎,在談到想象時他曾舉例道:“你們可以想象海鷗就是上帝的游泳褲!”1989年3月,他在河北山海關附近的一條鐵軌上臥軌自殺,留下了將近二百萬字的詩歌、小說、戲劇、論文。
海子當年在昌平的生活相當寂寞,也相當貧寒。有一次他走進一家小飯館,對老板說:“我給大家朗誦我的詩,你們能不能給我酒喝?”老板說:“我可以給你酒喝,但你別在這兒朗誦。”
海子生前,大量的詩得不到發表,便油印成冊贈送友人,卻被人頻頻抄襲見諸報刊,這令他郁悶不已。海子身后,越來越多的人喜愛他、評論他、研究他,他的詩也“順理成章”地進入中學、大學教材。
許多詩人、批評家在文章中都提到,《面朝》是各地房地產商營銷時最喜歡引用的文案之一,盡管他們的房子可能離大海很遙遠,但他們肯定覺得這首詩足以誘惑人們慷慨解囊。
海子生前自稱“物質的短暫情人”,若他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但他是不會抱怨的,因為這就是身為詩人的命運,因為這就是加繆《西西弗的神話》里說的:“如果有一種個人的命運,就不會有更高的命運,或者至少可以說,只有一種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應受到蔑視的命運。”
每個人都要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每個人的選擇都應當得到尊重。我們可能不寫詩,可能不想成為詩人,或者,不想成為海子那樣的詩人;但面對這樣的詩人,面對這樣的寫作,首要和基本的態度是尊重:尊重他人的選擇就是尊重自我的選擇,尊重他人選擇死亡就是尊重我們還在堅守生命。在此,西川三十多年前的話仍然值得深思:“我不想把死亡渲染得多么輝煌,我寧肯說那是件凄涼的事,其中埋藏著真正的絕望。有鑒于此,我要說,所有活著的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這樣,我們才能和時代生活中的種種黑暗、無聊、愚蠢、邪惡真正較量一番。”
大家都知道“詩無達詁”的說法。“達詁”指確切的訓詁或解釋,意思是說,每個人的生活閱歷、思想修養和文化程度不同,對同一首詩往往會有不同的解釋。所以,這個成語可以用來表述解釋的相對性和審美的差異性。我們對詩歌所作的解讀,廣義上都可稱為“誤讀”;甚至可以說,沒有“誤讀”就沒有詩歌欣賞和批評。
但有兩種誤讀需要警覺,一是望文生義,信口開河;一是拘泥于“先存之見”而不自知,也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未能覺察自我的偏見,對文本的“異己性”或“他性”缺乏敏感。這兩種誤讀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離開語境,自說自話。因此,對同一個文本固然允許多解并存,但每一種解釋都應在文本中求得驗證。
朱自清20世紀40年代就主張,“分析一首詩的意義,得一層層挨著剝起去,一個不留心便逗不攏來,甚至于驢頭不對馬嘴”。詩人、翻譯家梁宗岱也曾談道,有些批評家嫻熟于闡發原理,一當引一句或一首詩作例證時,“卻顯出多么可憐的趣味!”原因無非是批評家的理論是“借來的”,他并不了解自己說的話或討論的問題。
學者、批評家藍棣之也提出,“最好的解詩方法是一句一句地解,一行一行地解,一句一行都不可跳過,只有這方法可以把任何一種風格的詩解通。解詩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解釋它的大概意義,這是最能胡說的了,但這種胡說往往被說成是接受理論的方法,或什么‘詩無達詁’”。可惜,現在肯用這種笨辦法、肯下這種笨功夫的人不多。
我們下面采用最笨,也是最簡單的細讀法,一句句、一行行地解讀。
“重建家園”與返璞歸真
《重建家園》全詩如下:
在水上 放棄智慧
停止仰望長空
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
來澆灌家園
生存無須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放棄沉思和智慧
何以為詩—新詩文本細讀十五講
如果不能帶來麥粒
請對誠實的大地
保持緘默 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風吹炊煙
果園就在我身旁靜靜叫喊
“雙手勞動
慰藉心靈”
詩題“重建家園”是個很普通的短語,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現代詩歌一般主張詩歌語言是對日常用語、科學語言的疏離,俄國形式主義也倡導文學語言的“陌生化”。海子的詩題似乎反其道而行之。當然,詩人用它作標題,不可能是隨意的。這里應該注意的是,對這三種語言形態不宜作靜態理解,它們之間存在轉化,尤其是前兩者。最早的詩歌使用的就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勞作的語言,今天的許多日常用語也是由詩歌語言轉化而來,只不過由于使用頻繁,它們已不再被視作詩語了。
“重建”意味著原有家園的毀壞、喪失;沒有家園的人自然不存在家園的喪失,也就談不上“重建”問題。那么,是什么樣的家園被毀壞而需要重建呢?
“家園”是這首詩的核心詞語(意象)。如果把它從詩歌語境中移出,既可指物質家園,也可指精神家園—注意,當我們依憑習見做出如此分辨時,已在動用“智慧”了。不妨設想一下:在遠古蠻荒時代的人的頭腦里,“家園”意味著什么?會有現代人這樣條件反射似的“分辨”能力嗎?
有評論者將這首詩與《面朝》聯系起來,認為它們表達了同一主旨,即對塵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并進一步指出,這首詩更為明確地傳遞出詩人要放棄虛無縹緲的高邁理想,回到現實的意圖,“顯示了對自己既往追求的一種反思和否定”。
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面朝》是否表達了對塵世幸福的向往和追求?從它的最后兩句詩,特別是從“我只愿”形成的轉折意味可以看出,詩人是在衷心祝福親人和所有的陌生人,都能在塵世間擁有各自的幸福,他依然有自己對幸福的理解;在為他人祝福的同時,他也希望他人能為他所追求的幸福而祝福。前面提到的那些房地產營銷者,看中的恰恰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理想而非寫實的成分,是詩句中營造的、猶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妙意境。這一點他們是對的。
那么,認為《重建家園》傳遞出詩人要回到現實的意圖,除了誤讀《面朝》,也誤讀了這首詩中的“家園”二字。解詩者按照自己的先存之見或固有理解,非常“自然”地將物質家園與精神家園對立起來,進而依據下文,將“家園”理解為物質家園,而沒有覺察這其中有什么問題;更沒有意識到,這樣的理解可能正是詩人想要打破的現代人的思維怪圈。每個人的每一種看似“自然”的想法或做法,實際上都是一種“不自然”的產物,是被現代文明/文化塑造成形的。上述解讀的背后,體現的是現代人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習性。
按照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的觀點,人類的語言和文化一開始就是隱喻的,即偶然、不確定的。他讓我們設想,遠古人類最早是用肢體動作、表情和簡單的音節、音調等進行交流,這個過程異常艱難。當這些傳情達意的元素通過反復交流、磨合達到暫定的一致時,包括語言在內的本義開始形成,然后又在本義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隱喻,如此循環往復。他把這種關系形象地比喻為珊瑚礁:舊的珊瑚不斷死亡,而成為新的珊瑚生存的“家園”。所以,海子詩中的“家園”不能單純地理解成物質家園,它本身是個深刻的隱喻。它和大地、太陽、月亮等一樣,屬于人類使用的最基本的語詞,是所有語詞中的詞根部分,積淀著很深的文化意蘊。我們下面分析詩歌時再具體展開。
在水上 放棄智慧
詩的首句就引發了疑問:為什么是在“水上”?為什么是放棄“智慧”?水與智慧有關聯嗎?
孔子云:“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錢穆注曰:“水性活潑流通無滯礙,智者相似故樂之。山性安穩厚重,萬物生于其中,仁者性與之合,故樂之。”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水與“知(智)”確實有關系。此外,水能引起人對時光、生命的思考和探詢。孔子曾在水邊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許,沒有什么比“斯”更能引起人對“逝”的感喟;逝,消逝、喪失,一去不復返。這與這首詩因為喪失家園而重建是緊密呼應的。我們同時聯想到,遠古人類逐水而居,水因此成為人類文明發源地的重要標識,四大文明古國皆是如此。而文明與智慧是相伴相生的。
這句也提示我們,家園的喪失與水有關系。水是生命之源,亦能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舊約 · 創世記》載,耶和華造亞當之后,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使各樣的樹從地里長出來,可以悅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又引河水滋潤它。亞當、夏娃的子孫傳到挪亞一代,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的罪惡很大,便起了毀滅之心,使洪水泛濫。唯有挪亞蒙恩,受命造方舟躲避了洪水。
因此,不論從中國傳統文化還是西方元典來講,水與智慧都有緊密關聯。現代人的智慧又承此而來。放棄智慧之后,是否要做一個仁者,詩人沒有言明。仁者,仁厚之人,包容萬物,喜與萬物同在。這與詩的意旨是吻合的。
停止仰望長空
有人說,“長空”象征高邁理想、不切實際的幻想,詩人以“停止仰望”來表達對以往空想的否定,從而回歸世俗生活。實際上,這一句接上句而來,表達的仍是“放棄智慧”之意。比如,楚人屈原仰望長空,在《天問》中向老天一連發出了一百七十二個問題,表現了詩人對自然、歷史、社會深思熟慮后的見解、質疑。也就是說,人在仰望長空時,往往會引發深沉的理性思考,激起內心奔放熱烈的情感。在海子看來,理性思考即智慧,要“放棄”;奔放熱烈的情感需要“停止”—這一句的重心不在“長空”這一對象,而在“停止仰望”這一動作。全句在說,即使家園的毀滅是由上天引起的(如《舊約 · 創世記》所描述),也不要追究、抱怨,而要平靜地接受這一切。
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
來澆灌家園
生存不僅意味著幸福,也意味著苦難和屈辱;生存意味著承擔,既承擔幸福,也承擔苦難和屈辱,如詩人所言,“做一個詩人,你必須熱愛人類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熱愛人類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須忍受的,歌唱那些應該歌唱的”。生存也意味著平靜;那些意識不到“人類的秘密”的人,自然無法做到平靜。
第一節中詩人表達的是,經由“放棄”而終獲平靜。人只有放棄智慧和沉思,直面生存,才能意識到生存即承擔,“忍受那些必須忍受的,歌唱那些應該歌唱的”。因之,生存即平靜。
生存無須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第二節首句中,詩人為什么使用“洞察”而不使用“觀察”?洞察之洞,即深遠、透徹之意。洞察需要沉思和智慧;而生存是何面貌,大地已完全呈現,并不是人借由深沉、理性的思考,用語言可以表述的。表述往往是詞不達意的。我們只須面向生存本身,回到大地,感受大地。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這一節的最后一句,詩人為什么不直接說“來重建家鄉(家園)”呢?這兩句表述在意義上并無差異,區別在于,原詩語句重心落在“屋頂”上;若作修改,其語句重心則可能在“重建”,也可能在“家鄉(家園)”上。那么,詩人為什么要將閱讀者的視線牽引到“屋頂”上呢?
“屋頂”自然指代的是家。甲骨文中,“家”這個字上面是“宀”(音mián),表示與室家有關;下面是“豕”,即豬。古代生產力低下,人們多在屋子里養豬,所以房子里有豬就成了人家的標志。屋頂的重要在于它能給人以庇護,因為它的功能正是用來承受的:既承受陽光雨露,也承受風暴雷電。而幸福和痛苦也都是人需要承受的。
這一節呼應了首節中對生存的感悟,再次強調生存的秘密在于承擔。
放棄沉思和智慧
第三節一開始詩人就直截了當點明詩意,再次強調,沉思和智慧對于生存本身沒有什么影響。生存類似于道,道若可道,則非常道,而道法自然。生存之道是不可言說的,沉思和智慧并不能解決生存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這里,詩人的生存觀有老莊哲學的影響,帶有宿命色彩。簡單地說就是不要去問,只管去做。
如果不能帶來麥粒
請對誠實的大地
保持緘默 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熟悉海子詩歌的人都知道,麥粒是其詩歌的核心意象,表達著他作為農民的兒子對鄉土中國的眷戀,有評論者因此稱他為“中國農業社會最后一位出色的抒情詩人”。某種意義上,麥粒維持著中國社會和人民幾千年的“生存”;中國長達數千年超穩定的農業社會結構形態,也在根基上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
大地是誠實的,因為它不欺瞞,使人喜也讓人憂,使人生也讓人亡—它按自己的道運轉。
前面說過,生存之道不可言說;不可言說即緘默,也即不要沉思不要探究。語言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說過:“一個人對于不能談的事情就應當沉默。”又說:“確實有不能講述的東西。這是自己表明出來的;這就是神秘的東西。”這幾句話的另一層意思是,語言是無力的,語言與現實亦即生存之間存在鴻溝。“保持緘默”,就是以自己的誠實回報了大地的誠實。
那么,如何理解“幽暗”在詩中的含義呢?緘默即不思不問,渾沌一體。幽暗是天地鴻蒙之初的狀態,也是人未開化、未發蒙的狀態。這讓人聯想到《莊子》所講渾沌開七竅的故事:
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幽暗是渾沌的另一種說法。按莊子的觀點,人在渾沌時不思不問,是最幸福的;一旦七竅皆開,則會死去。《舊約 · 創世記》中夏娃在伊甸園偷吃善惡果的故事,與此類似。耶和華曾吩咐亞當、夏娃,園中的果子可以隨意吃,唯善惡樹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但在蛇的一再引誘下—
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
二人吃善惡果之前,同樣處于渾沌狀態:沒有智慧,不辨善惡,不知羞恥。但他們卻因為有了智慧而受到耶和華的審判,并被逐出伊甸園。亞當所得的審判是:“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于塵土。”
從第一節到這一節,詩人一直在探尋的是生存的意味,亦即“人類的秘密”。在他看來,人應當回到大地,以勞苦所得的收獲奉獻給大地。人是大地的子孫,來自大地也將歸于大地。這就是人的誠實本性。“兩手空空”使詩人愧對大地(他在多首詩中反復表達過這種情緒),而對此所作的任何辯解都是一種喪失本性的墮落。海子這首詩里體現的“反智”傾向,與老莊哲學是一脈相承的。至于這首詩是否有《舊約》關于人的“原罪”意識的影響,僅憑上述分析,很難做出明確的判斷。不過從我們引述的材料中,還是可以看到其中的關聯。許多詩人、批評家指出,海子后期詩歌在語言、結構、寓意等方面,都受到了《新舊約全書》的啟示,是他追求“大詩”理想的一種體現。海子離開人世時,隨身攜帶四本書,其中一本是《新舊約全書》(其他三本是梭羅《瓦爾登湖》、海雅達爾《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
風吹炊煙
炊煙裊裊升起,這是溫情動人、素樸潔凈的鄉村畫幅,越千年而不變。炊煙將閱讀者的視線再度牽引到屋頂,定格在大地上的家園。
果園就在我身旁靜靜叫喊
“雙手勞動
慰藉心靈”
如同炊煙一樣,果園對應著家園。這同樣讓我們聯想起《舊約 · 創世記》傳說。最初人類居住的伊甸園,就是果園(如前所說,此果園與水、善惡皆有關)。洪水過后,挪亞做起了農夫,也是種果園(栽了一個葡萄園)。詩人賦予果園(家園)以人的靈性;大地和人一樣是上天創造之物,皆有靈性。
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夠聽到果園的“靜靜叫喊”呢?貼近大地的人,和大地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在大地上汗流滿面的勞作的人有福了。
最后兩句近似格言,流傳甚廣。如果把它們從全詩中抽出來,可理解為:我用雙手勞動,付出了努力,無論是否有收獲,無論收獲大小,都可以問心無愧,無怨無悔—這與流行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觀念非常合拍,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鳴。這種理解當然不錯,但還需要回到文本語境中去品味。
回溯全詩,這兩句是說,沉思和智慧并不能揭示生存的秘密;思之彌深,失之愈遠。既如此,人靠什么獲得對生存的秘密、大地的本性的理解呢?靠心的體悟、頓悟。心即悟,悟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老莊哲學的重要概念。如前所述,生存類似于道,道是什么?《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又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總之,道是恍惚混融的,是形而上的,不能夠靠眼、耳、鼻、舌、身直接感知,不能夠靠觀察直接把握,靠的只能是體驗。假使到物質世界去直接觀察,可能會背“道”而馳。魏晉玄學家王弼《老子道德經注》說:“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所以道家強調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擾,使內心進入虛靜、安寧的狀態,以直覺式的頓悟把握事物的本體。
解讀至此,海子心中要重建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家園,這樣的家園有無可能重建,大家可能已有了自己的見解。
“大詩”理想與生存的夾縫狀態
海子的詩,特別是短詩樸素異常,很少雕飾,大多朗朗上口,易于傳誦。這種樸素中蘊涵與眾不同的光輝,有一種直抵事物核心的力量。這既來自詩人對東西方元典文化的諳熟,也來自他對“大詩”寫作的孜孜以求,如同《重建家園》所呈現的那樣。
從現代漢詩的發展歷程和海子所處的時代來看,他是一位有遠大抱負和高邁理想的過渡型詩人。這里所謂的過渡,有以下三層含義。
首先,海子生活的時代正處于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不僅詩人的生存遭遇危機,而且也遇到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詩人身份的合理性不斷受到質疑,這些質疑會連帶地引起詩人的自我懷疑,詩人內心總是對既存的一切充滿了懷疑。比如,做一個詩人究竟意味著什么,寫詩這種行為的意義到底體現在哪里,詩是能改變現實、拯救世界還是能救贖自我,等等。這些在以前并不會作為問題,至少不會作為嚴重的問題而存在。
在西方,不要說柏拉圖時代,即使到了19世紀,英國文學家、哲學家托馬斯 · 卡萊爾說:“詩人是世界之光。”美國思想家、詩人愛默生仍然賦予詩人以“君主”“帝王”的形象:“詩人就是說話的人,命名的人,他代表美。……詩人不是一個被賦予了權力的人,他自有權力,使自己成為帝王。”布羅茨基認為:“詩人是文明之子。”但是在海子生活的時代,特別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在經歷了朦朧詩熱潮后,詩歌不可避免地衰落,詩人從“抒情王子”一變而為遭人戲謔的小丑。海子恰好處在一個夾縫之中:從他的理想來說,詩人雖不再是從前代神立言的人,但他堅信詩人和詩歌仍然應該獨享其尊嚴、力量和光輝。他是他的世界里“孤獨的王”。這種夾縫狀態也就是后現代所講的“之間”狀態,處于這種狀態的人是最尷尬,也是最痛苦的,他們要承受來自外部和自我內部的雙重壓力。當然,不是只有詩人才處于這樣的狀態,但唯有詩人對此最為敏感。某種意義上,是詩人表達了處于這種狀態中的人想表達而不能表達的感受,詩人在替我們說話。海子又是在這樣的壓力和痛苦之中,依然堅守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少數詩人之一。
其次,海子的詩歌寫作處在從“我之詩”到“人之詩”的轉換時期。新詩自誕生以來,成長歷程中的一條主線就是有關“小我”與“大我”之辯:或執著于書寫“小我”,或希求以“小我”見“大我”,或簡單粗暴地以“大我”取代“小我”。就以當代詩歌的發展來看,十七年詩歌的總體態勢是將“小我”與“大我”融為一體。20世紀60年代初,貴州詩人黃翔寫了一首《獨唱》,而在那個年代提倡“獨唱”的人,無疑是異端。到了“文革”,主流詩歌里基本上是“大我”,那個代表政治意識形態的“我”壓制、消滅了“小我”的存在。朦朧詩則重新恢復了“自我”在抒情詩中的合法地位,但他們在整體上確實存在以自我的體驗來鞭撻非人的時代,呼喊出“一代人”心聲的寫作指向,扮演的是代言人的角色。再到第三代詩歌,更年輕的詩人普遍以拒絕做“時代的傳聲筒”自居,以沉醉于自我為反叛、先鋒。進入新世紀后網絡詩歌的興起,強化了詩人自我情感的宣泄。那么海子呢,他一直秉持這樣一種信念:消解類似于“小我”與“大我”的二元對立,返歸人原始、本真的渾沌一體的狀態;從詩的角度講,就是要重建詩的家園。海子曾明確表述過他的詩歌理想,這就是人們熟悉的“大詩”理想:
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為一個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
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大詩”呢?它同樣是一種結合,但不是“小我”與“大我”的結合,而是“民族和人類”的結合,是將本民族的情感特色與人類的普遍情感結合起來,以打破或彌合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靈魂與肉體、物質與精神等現代性的二元對立。簡單地說,“大詩”理想就是“普遍詩歌”的理想,它指向人的存在,指向人的精神和心靈世界的深處。就這樣的詩歌理想來說,他站在了塔頂,視線越過了眾人,所以他必然是孤獨的、無人喝彩的。任何一個詩人的寫作都始于自我,但這僅僅是寫作的開始,不是它的全部,更不是它的結局。
再次,從詩歌寫作的精神指向和文本類型上來說,海子的詩處于古典詩歌與現代詩歌的“中間”狀態。這種說法可能比較曖昧,卻是符合實情的。一方面,古典詩歌特別是浪漫主義詩歌以情感抒發為最高原則,后者強調心靈的自由與表達的自由,不受一切清規戒律的束縛。此外,浪漫主義詩歌多取材于鄉間、田野等。這些在海子的詩特別是抒情短詩中有鮮明的體現。另一方面,海子的詩借助自然的種種元素,形成了比較完整、獨特的象征體系。這與象征主義詩歌又非常接近。比如瓦雷里的《石榴》、波德萊爾的《交感》等,通過對自然元素之間關系的描繪,形成一個象征世界,來映射人的本體存在。象征主義詩人在哲學觀上受柏拉圖“唯靈主義”的影響,認為世界可以分為現象世界和本體世界。本體世界即自我世界,現象世界本質上是自我世界的外在顯現。詩人通過對可見可感的現象世界的表現,就可以象征性地表現真正的本體—自我。這個自我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自我,而是與現象世界相對的哲學意義上的自我。海子在他的絕筆《我熱愛的詩人—荷爾德林》中,將抒情詩人分為兩類:一類熱愛生命,但他熱愛的是生命中的自我,認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官能的抽搐和內分泌;另一類雖然只熱愛風景,但他熱愛的是景色中的靈魂,是風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從熱愛自我進入熱愛景色,將后者當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就出離了第一類狹窄的抒情詩人的行列。從這段論述來看,熱愛景色使海子具有濃厚的古典詩人氣質,而把景色當成“大宇宙神秘”的一部分來體悟,又體現出現代詩人對象征手法的熱衷。至于為什么海子會走上這樣一條獨特的寫作道路,就需要結合他的生平來分析。概括地說,海子進入大學之前一直生活在農村,對鄉村、土地有深厚情感,是一位傳統情結很深的詩人。與此同時,在廣泛的閱讀和勤奮的寫作實踐中,他深感單純的抒情已無法達到構建“大詩”的意圖;而“大詩”理想,內在地要求詩人盡可能融合一切有用的詩歌元素。海子的一只腳已經邁入現代的門檻,另一只腳仍然深陷在傳統文明、農業社會的泥土里。
過渡型詩人的意義和價值是不可替代的,難以復制。處于“之間”狀態的詩人某種意義上是分裂的人,他們所承擔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他們總是會為自己設定一個在常人看來無法企及的目標。就《重建家園》來說,海子秉持“絕圣棄知”的信念,渴望返歸人原始、本真的渾沌一體的狀態。海子為自己設定的這樣一種理想追求,顯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不要忘記,詩人的杰出之處,正在于他總是聽從內心的律令或某種神秘的召喚,不可救藥地去追尋那不可實現之物。薩特在評述馬拉美時說,像馬拉美、波德萊爾等詩人, “他們必須是不可救藥的,必須心甘情愿不可救藥,必須終生披麻戴孝”。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 · 韋伯則斷言:“如果我們不是反復追求不可能的東西,那么我們也無法實現看起來可能的東西。”作為農民之子亦即“人之子”的海子,正是以他“重建家園”、重建詩歌理想的矢志不渝的信念,而不是結果,長久停駐在我們的視野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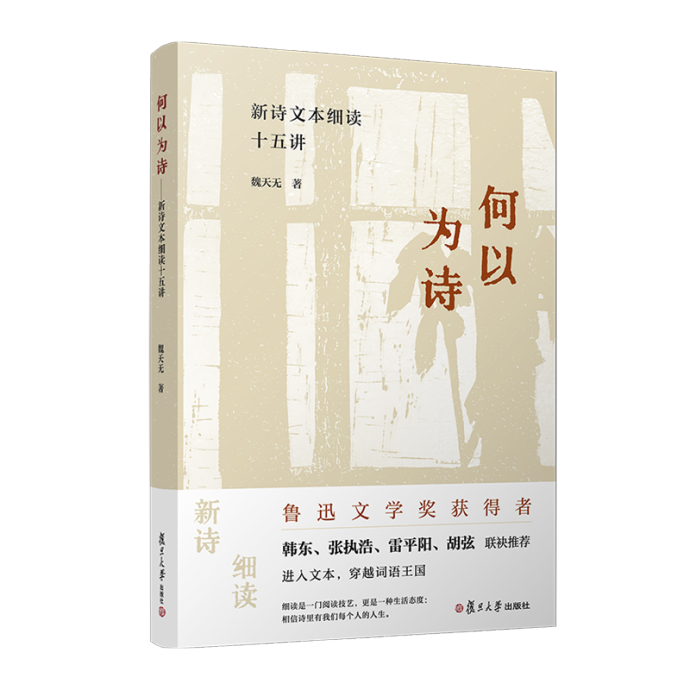
《何以為詩——新詩文本細讀十五講》魏天無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魏天無,1988年本科畢業于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現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華中師范大學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湖北省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曾為美國孟菲斯大學(UM)交換學者(2012—2013)。出版學術專著(合著)六部,評論集兩部(含合作),隨筆集一部。
目錄
引言 什么是細讀?
第一講 揭示現代人深層意識的標本
——細讀徐玉諾
第二講 沉思之詩與經驗之歌
——細讀馮至
第三講 新詩的敘事性及其散文化
——細讀艾青
第四講 傳遞現代人的“現代感覺性”
——細讀卞之琳
第五講 “一切是無邊的,無邊的遲緩”
——細讀穆旦
第六講 詩是心的歌
——細讀曾卓
第七講 “塵埃落定,大靜呈祥”
——細讀昌耀
第八講 在一剎那間攫取永恒
——細讀顧城
第九講 一個人和他的世界
——細讀韓東
第十講 “大詩”理想與詩人的宿命
——細讀海子
第十一講 凝視與凝神中的世界
——細讀余笑忠
第十二講 聲音、氣韻與結構
——細讀張執浩
第十三講 那“孤單地懸著”的,是什么?
——細讀劍男
第十四講 口頭敘事傳統與小如針尖的美學
——細讀雷平陽
第十五講 把外部世界融入內心生活中
——細讀胡弦
結語 細讀之后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