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對一項工作來說,重要的是誰來做以及如何做,而不是做什么
【編者按】
奧地利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維克多·弗蘭克爾以創立“意義療法”聞名于世,對心理學界影響深遠,被稱為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之后的維也納第三心理治療學派。納粹時期,他們全家陸續進了集中營,其父母、妻子、哥哥全部死于毒氣室內,只有他和妹妹幸存。在痛苦中,他開始追尋生命的意義。他曾對友人說:“發生那么多事、那么多磨難,一定有其意義。”于是在這種極端艱難的環境中,他將目光轉向意義,寫下了名著《我們活著的理由》和《活出生命的意義》。
他認為,當今社會面臨一種“存在的真空”狀態,人們普遍患有一種“心靈性神經癥”。針對這種狀況,他提出了意義治療和存在主義分析。在本書中,他將哲學與治療交織在一起,討論了生命、死亡、工作、痛苦和愛情的意義,分析了焦慮癥、強迫癥、憂郁癥、精神分裂癥背后的深層心理。
本文摘自《我們活著的理由:弗蘭克爾論生命的意義》[奧]維克多·弗蘭克爾 著,王琳琳 譯,岳麓書社·浦睿文化2024年4月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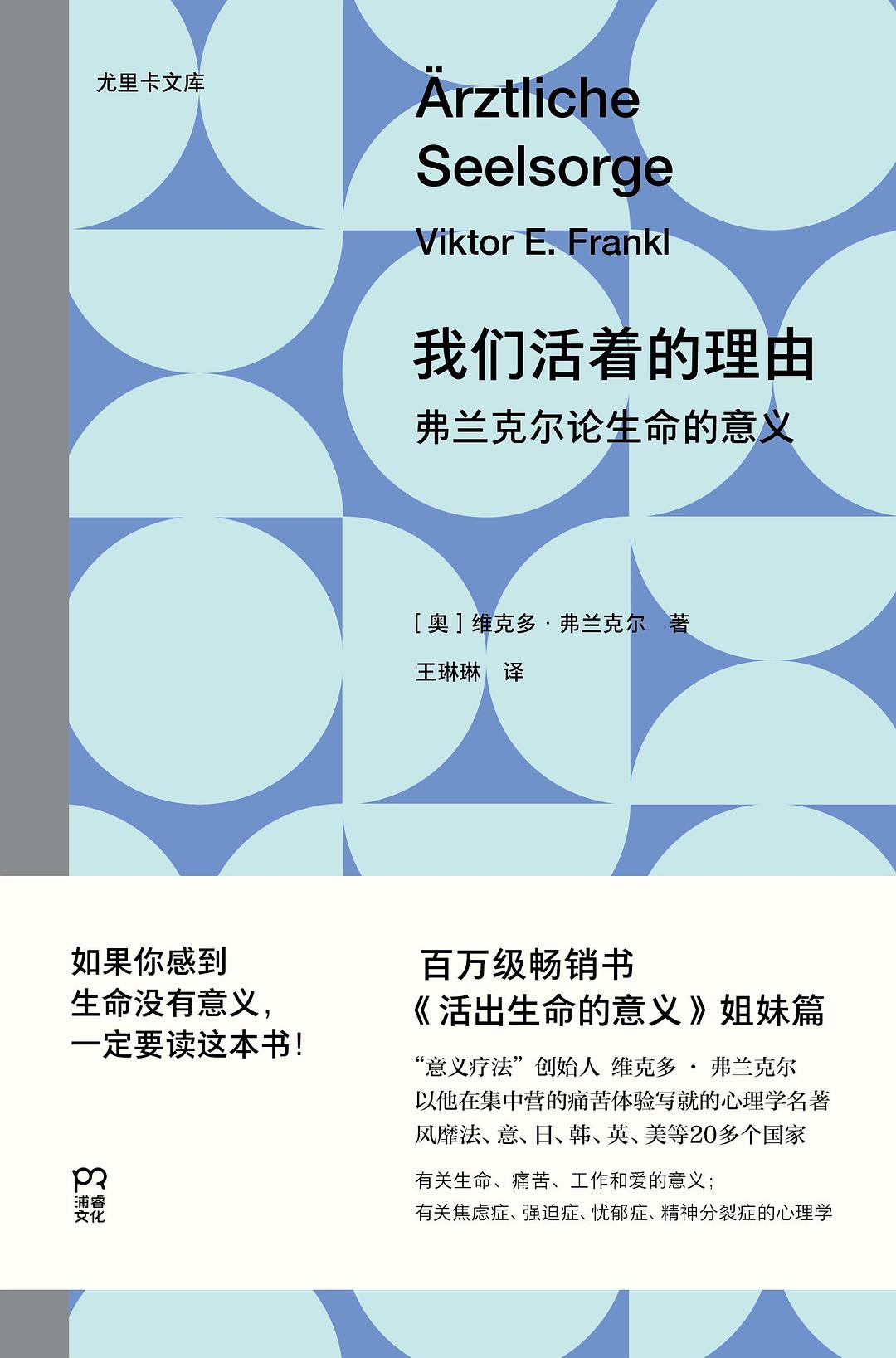
《我們活著的理由:弗蘭克爾論生命的意義》書封
工作的意義
前面我們說過,生命的意義不需要被拷問,只需要被回答,通過對生命負責來回答。其答案并不是通過語言,而是通過行動給出的。此外,它必須與具體境況和人格相對應,并將這種具體性內化于自身。正確答案將是一個具有實際行動的答案,它作為人類責任的具體空間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具體性中。
在這個空間里,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我們說過,意識的獨特性和唯一性非常重要。我們已經知曉,存在主義分析努力朝著責任意識的方向發展的原因,但與此同時,責任意識又首先在具體的個人任務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使命”。如果沒有看到存在的獨特意義,人就必定會在遭遇困境時松弛倦怠。他就像一個被濃霧困住的登山者,在沒有目標的情況下,危及生命的倦怠威脅著他。但當濃霧逐漸散去,避難所在遠處若隱若現時,他就會突然感到神清氣爽,精力充沛。登山者都熟知“攀登峭壁”時典型的疲勞體驗,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錯了路線,也許會陷入錯誤的巖石地帶;直到突然看到通往山頂的路,他知道自己離山頂不遠了,手臂就會仿佛又重新充滿了力量。
創造性價值及其實現是生命任務的重點,其具體實現領域通常會與職業工作相契合。工作是可以代表個人在團體中的獨特性,并讓人從中獲得意義和價值的領域。然而,這種意義和價值是附加在成績(為集體做出的成績)之上的,而不是特定的職業本身。并非只有某種職業才能為一個人提供獲得滿足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任何職業能讓人快樂。如果有人——尤其是那些神經癥患者——聲稱自己換個職業就會獲得滿足,那么這種說法要么是對職業意義的誤解,要么就是自欺欺人。如果無法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那是人自己的錯,跟工作無關。職業本身無法使你變得不可替代;它只能給你提供機會。
一位患者抱怨自己的生活毫無意義,因此也根本不想恢復健康;她覺得如果有一份讓自己感到滿足的工作,例如,如果她是一名醫生或護士,或者是一名獲得某種科學發現的化學家,那么一切就會變得美好了。此處,重要的是要讓這位患者清楚,起決定作用的絕不是一個人所從事的職業,而是她的工作方式;它與具體從事哪種工作無關,而在于構成存在獨特性的人格是否在工作中發揮作用,從而使生活變得有意義。
醫生這一職業的真實情況是什么呢?是什么給他的行為賦予了意義呢?他是按照藝術規則行事,在必要時給這個或那個患者注射或開藥嗎?單純的藝術規則中是不包括醫學藝術的。醫生的工作只是為醫生的人格提供了一個通過人格實現職業成就的永久機會。醫生只有超越純粹的職業規則限制,才能開始真正的人格化的、自我滿足的工作。讓上面的病人如此羨慕的護士工作又是怎樣的呢?做護士要煮注射器、端便盆、搬運病人——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但這些工作本身并不能滿足人們的內心需求;當護士超出規定義務,開始人格化的工作,如她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照護重病患者時,她的職業才真正開始賦予生命意義。只要人們正確地理解自己的職業,它就會賦予每個人這樣的機會。每個人身上都存在著無可替代性、獨特性和唯一性,對一項工作來說,重要的是誰來做以及如何做,而不是做什么。除此之外,我們需要告訴那些認為在工作中無法獲得滿足的人,他們最終可以在他們的職業生涯和私人生活中展現他們的獨特性和唯一性,正是這些賦予存在意義。例如,作為愛的付出者和被愛的人,作為妻子和母親,在所有這些關系中,她對于她的丈夫和孩子來說都是無可替代的。
人在工作中可以實現創造性價值并獲得獨特的自我滿足,然而,人與工作之間的自然關系卻由于工作環境的原因被強烈扭曲。很多人抱怨,自己每天為老板工作8小時甚至更多的時間,必須在流水線上不斷重復同樣的動作,或者長時間操縱一臺機器,總之,他們表現得越是非人性化,越規范,就越顯得忠誠可信,越受歡迎。工作僅僅被理解為一種達到目的、賺錢以維持生計的必要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真正的生活僅存在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業余時間中。然而我們要知道,有些人的工作會使他們非常疲倦,所以他們下班后就在床上倒頭大睡,根本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們只能將業余時間變為休整的時間;這些時間里他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睡覺。在空閑時間中,即使雇主本人也并不總是“自由”的;他也無法逃脫所謂的工作關系的扭曲。在日常生活中,為了賺錢和生計而忘記生活本身的人比比皆是。賺錢已經變成了一種生存目的。一個有錢人可以用他的錢達到很多目的,但他的生活卻失去了理由。在這樣的人身上,不斷賺錢完全掩蓋了他的真正生活;除了賺錢,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懂藝術,也不運動,連他玩的游戲也以某種方式與金錢關聯在一起,比如賭博游戲,其最終目的還是贏錢。
失業神經癥
當工作完全停止,也就是在失業的情況下,工作的意義才會清晰地顯現。根據對失業者的心理觀察,我們提出了失業神經癥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癥狀的焦點不是抑郁癥,而是麻木冷漠。失業者對外界事物變得越來越不感興趣,缺乏主動性。這種麻木冷漠并非沒有危險,它會使這些人無法抓住可能向他們伸出的援助之手。失業者將他的空虛視為一種內在的空虛,一種意識上的空虛。他覺得自己沒用,因為他無事可做。因為沒有工作,他認為自己的生活沒有意義。如同生物學中存在所謂的空白增殖(Vakatwucherungen)一樣,心理學中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失業因此成為神經癥發展的溫床。精神上的閑散會導致“持續的”周日神經癥。
麻木冷漠是失業神經癥的主要癥狀,它不僅是心理空虛的表現;在我們看來,每一種神經癥癥狀也都會伴有某種身體表現,很多情況下是營養不良。就像一般的神經癥癥狀一樣,有時它也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尤其對于已經患有神經癥,只是由于失業而加劇或復發的患者,可以說,失業的事實作為物質進入神經癥,作為內容被吸收到神經癥中,并受到了“神經癥化處理”。在這些情況下,失業是神經癥患者為生活中(不僅僅是在職業生涯中)的所有失敗開脫的一種受歡迎的方式。失業充當了替罪羊,為“拙劣”的生活背負了所有責任。一個人自己的錯誤被描述為失業的注定后果。“是的,如果我沒有失業,那么一切都會不一樣,一切都會很美好。”——然后他們就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事可做,神經質類型的人往往會這樣竭力宣稱。失業讓失業者的生活變成了權宜之計,并誘使他們沉迷于一種臨時的生存模式。他們認為別人不應向他們提出任何要求。他們也不向自己提出任何要求。失業的命運似乎免除了他對他人和自己的責任,也免除了他對生活的責任。人生所有的失敗都可以歸咎于這種命運。顯然,認為鞋子里只有一處擠腳,在某種程度上是好事。如果將一切都歸咎于某個因素,而這一因素又是一個看似命定的事實,那么這樣做的好處是,似乎什么都沒有被放棄,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想象擺脫這一因素后一切就會好起來。
就像所有的神經癥癥狀一樣,失業神經癥也有結果、表達和途徑;我們期望,從最終和決定性的角度來看,它就像任何其他神經癥一樣被證明是一種存在模式、一種精神立場、一種存在的決定。失業神經癥根本不是神經癥患者所描繪的注定的命運。失業者不必陷入失業神經癥無法自拔。即使失業,人“也可以有另外的活法”,他也能以某種方式決定他是否受制于社會命運的力量。很多例子證明,這種性格并不是由失業決定和塑造的。除了上述的神經癥類型之外,還有另一種類型的失業者。他們和失業神經癥患者一樣,處于困窘不利的經濟條件下,不過他們并沒有為失業神經癥所困擾,他們既不冷漠也不沮喪,有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愉悅。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人往往還有其他形式的工作。例如,這些人可能是某個組織的志愿者、大眾教育機構的名譽工作人員、青年俱樂部的無薪雇員;他們經常聽講座和好的音樂,他們廣泛地閱讀,并與好友交流討論閱讀的內容。他們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組織他們多余的空閑時間,這給他們的意識和生活帶來了豐富的內容。像神經癥失業者一樣,他們的肚子也經常咕咕叫,然而,他們肯定自己的生活,一點兒都不絕望。他們已經明白如何讓自己得到滿足,并從中獲取意義。他們已經意識到人生活的意義并非來自工作,失業的人也不必被迫過毫無意義的生活。對他們來說,生活的意義不再與擁有一份職業工作畫等號。真正造成神經癥失業者麻木冷漠,最終導致失業神經癥的,是認為職業工作是生活的唯一意義的錯誤觀點。錯誤地將職業和生活等同,必然會讓失業者感到自己毫無用處。
所有這些都表明,人們對失業的心理反應根本沒那么重要,人的精神自由還有巨大的空間。在我們嘗試對失業神經癥進行存在主義分析的背景下,很明顯,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相同的失業狀況,或者更準確地說,一部分人將他們的心理和性格交給社會命運塑造,而沒有神經癥的人則反過來塑造社會命運。因此,每個失業的人可以自己決定成為內心堅定樂觀的失業者還是冷漠麻木的失業者。
失業神經癥并不是失業的直接后果。我們有時甚至看到,失業反而是神經癥的后果。不難理解,神經癥會對患者的社會命運和經濟狀況產生影響。在同等條件下,一個保持樂觀堅定的失業者會獲得比那些冷漠麻木的失業者更好的競爭機會,在申請工作時更容易有好的結果。而失業神經癥的反作用不僅是社會性的,而且是性命攸關的。因為精神生活通過其任務特征獲得的結構會影響到生物層面。此外,內在結構的突然喪失通常伴隨著空虛體驗以及器官衰退的現象。精神病學上有典型的心理—生理衰退現象,如人在退休后迅速衰老。動物也有類似的情況,如訓練有素的馬戲團動物的平均壽命比動物園里同齡的“沒有工作”的動物更長。
之所以存在進行心理治療干預的可能性,其原因在于,失業神經癥與失業本身沒有根本關聯。如果有人對這種解決方式表示不屑,他們可以參考當下失業青年中流行的說法:“我們不要錢,我們要充實的生活。”很明顯,狹義的非意義療法,即所謂的“深度心理”治療,在這些情況下是沒有希望的。相反,這里所指出的道路只存在于存在主義分析之中,它要求失業者直面社會命運,保持內心自由,它喚起患者的責任意識,使他們可以賦予艱難的生活以內容并從中獲得意義。
正如我們所見,失業和職業工作都可能被濫用為達到神經癥目的的手段。為達到神經癥的目的而工作與為達到有意義生活的目的而工作,二者必須區分開來。因為人的尊嚴禁止他將自己降格成為一種手段、一種單純勞動過程的手段、一種生產資料。工作能力不是一切,它既不是讓生活充滿意義的充分理由,也不是必要的理由。一個人可以在有工作的同時過著毫無意義的生活。也可以在沒有工作的同時賦予生活意義。一個人主要在特定領域尋求生活的意義,而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生命,這無可厚非。問題是,這種自我限制是否建立在客觀的基礎之上,或者就神經癥而言,是不是必要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沒有必要為了享受而放棄工作,也沒有必要為了工作而放棄享受。這種神經癥患者的情況正好契合了愛麗絲·呂特肯(Alice Lyttken)的一本名叫《我不來吃晚飯》的醫生小說中的一句話:“如果沒了愛情,工作就會成為替代品,如果沒了工作,愛情就會成為鴉片。”
周日神經癥
大量的職業工作并不等同于意義豐富的創造性生活;然而,神經癥患者有時會試圖通過完全沉浸于工作來逃離生活。一旦忙碌的工作在一定的時間段中暫停下來,存在層面上的內容空虛和意義貧乏就會顯現。這個時間段就是——周日!我們經常見到,一些人在周日不得不拋棄手頭的工作,他們的臉上帶著掩飾不住的絕望,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也被拋棄了,他們沒有約會,沒有人邀請他們看電影。他們手中沒有“愛情”的“鴉片”,或者暫時沒有了忙碌——那種可以掩飾內心空虛的忙碌,只有工作狂才需要這樣的忙碌。在星期天,當平常的工作節奏放緩時,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意義的貧乏就會漸漸顯露。我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仿佛那些在生活中沒有目標的人總在以最高的速度飛奔,仿佛這樣他們就可以對無目的性視而不見。他們試圖逃離自己,但無濟于事,因為在周日,當平時的忙碌停止時,存在的無目標、無意義、空虛就又會在他們身上顯現。
為了克服這種感覺,他們逃進了舞廳。那里有嘈雜的音樂,這讓他們省去了勉為其難的“舞廳對話”。他們還省去了思考,全神貫注地投入舞蹈之中。此外,“周日神經癥患者”還會逃離到另一項周末活動,也就是體育運動的“庇護所”之中。在那里他們仿佛可以關注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哪個足球俱樂部贏了比賽。兩個11人的隊伍踢球,成千上萬的人觀看。在拳擊運動中,只有兩個人是活躍的,但是他們的競爭非常激烈,這可以滿足不活躍的偷窺觀眾的施虐欲。我所說的這些不是反對健康的體育運動,只是批判性地詢問,體育運動有哪些內在價值。讓我們以登山者的運動理念為例,登山首先需要積極參與,被動地觀看在這里是行不通的。這里比拼的是真正的能力,與身體素質密切相關,例如,在某些危及生命的情況下,登山者不得不落到最后;在心理關系中,“素質”再次被推至前臺,無論登山者有什么心理弱點,比如焦慮或恐高,他都必須學著克服。應該指出的是,登山者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尋找”危險,而是如歐文·施特勞斯所指出的,“嘗試”危險。競爭在很多運動中往往導致對記錄的追逐,在登山運動中卻被轉化為“挑戰自我”的一種高質量形式。攀爬團隊的體驗最終代表了另一個積極的、社會性的時刻。
即使對記錄的病態追逐也證實了人類的特點,因為這些記錄也是展示人類追求其唯一性和獨特性的形式。這同樣適用于其他的大眾心理學現象,例如流行時尚:人們不惜一切代價想從時尚中獲得獨特性;在這里,唯一性和獨特性僅限于最外在的東西。
不僅是運動,藝術也會在神經癥層面被濫用。雖然真正的藝術或藝術生活豐富了人的內心,并將他們引向最本己的可能性,但在神經癥層面被濫用的“藝術”只會使人偏離自我。它更多的只是一種令人迷醉和眩暈的情況。例如,一個想要逃離存在的真空的人可能會去看一本扣人心弦的犯罪小說。他最終會在緊張中尋求解決方案——那些擺脫乏味的消極欲望被叔本華誤認為是唯一可能的欲望。前面已經提到,我們并不是為了擺脫乏味、緊張、斗爭而去體驗消極欲望;實際上,我們并不是為了不斷獲得新的感覺而進行生命斗爭,生命的斗爭更多是帶有意向性的,并在其中獲得一些意義。
對于尋求刺激的人來說,最大的轟動事件莫過于死亡,不管是在“藝術”還是在現實中。市儈的報紙讀者想要在早餐桌前讀到不幸和死亡。然而大量的不幸和死亡報道也不能使他滿足,匿名的大眾對他來說太過于抽象,所以,這個人同時可能會產生去電影院看一場匪徒電影的需求。就像其他成癮者一樣:追逐聳人聽聞的事件成癮的人需要緊張刺激,而緊張刺激又會產生新的、更強烈的對刺激的渴望,從而導致刺激劑量的不斷增加。這其實形成了一種對比的效果,好像死的總是別人。這種類型的人想要逃離的是對他來說最為灰暗的事實,即他自己也終有一死的事實,這讓他無法承受存在的真空。必死無疑意味著一種基于愧疚的恐懼。死亡是生命的結束,它只能讓那些沒有填滿自己生命的人感到恐懼。只有這些人無法正視死亡。他并沒有意識到生命有限,也沒有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自我,而是逃到了一種赦免的妄想之中,就像那些被判死刑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開始相信自己還有可能被赦免。這種類型的人逃到了一種認為自己什么都不會發生,死亡和災難只會降臨到別人頭上的妄想之中。
神經癥患者往往會逃到小說世界中,逃到他們心中“主人公”的世界里。追逐紀錄的運動員至少還想要在自己的功勞簿上休息一下,但這種類型的小說讀者只想要別人滿足自己的需求,即使只是一個虛構的人物。然而,在生活中,從來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功勞簿可以休息,也沒有一勞永逸的事情;生命一再地向我們提出新的問題,讓我們永遠無法安寧。只有自我麻醉,才能讓我們對那些永恒的刺痛不再敏感,生活以此不斷向我們提出新的要求,并拷問我們的良知。誰停下來了,誰就會被超越;誰自我滿足了,誰就會失去自己。所以我們不應滿足于我們創造或者體驗過的一切;每一個時刻都需要新的行動,都會產生新的體驗的可能。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