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暗藍評《愚蠢的核彈》|失控才是最恐怖的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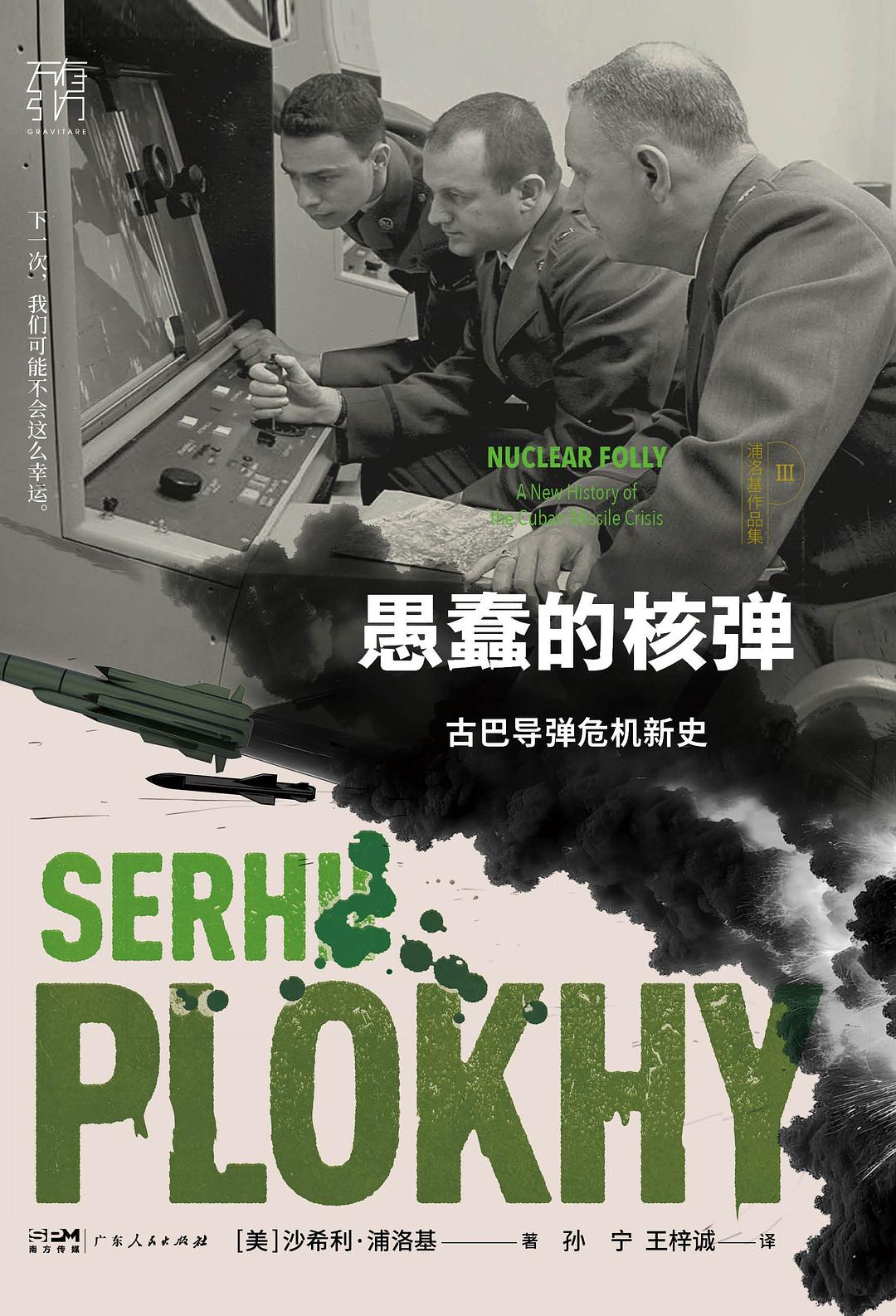
《愚蠢的核彈:古巴導彈危機新史》,[美]沙希利·浦洛基著,孫寧、王梓誠譯,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24頁,98.00元
被譽為“恐怖之王”的斯蒂芬·金不僅以寫恐怖小說見長,他對于“恐怖”相關的文藝作品乃至其所體現的社會心態亦頗有研究。1982年,他憑借評論作品《死之舞》(Danse Macabre)摘下雨果獎“非小說類獎”。有趣的是,這是他創作生涯中第一個重要獎項。
在這部作品開篇,通過對兩部科幻影片——1951年的《地球停轉之日》與1957年的《地球大戰飛碟》進行比較,斯蒂芬·金指出了“恐怖”的源頭:
《地球停轉之日》是少數真正意義上的科幻電影。《地球大戰飛碟》里的遠古外星人是一種更常見的電影類型——恐怖秀——的使者。這里沒有“這是給你們總統的禮物”這樣的廢話。他們只是來到卡納維拉爾角的“天鉤計劃”基地,然后大打出手。在我看來,恐怖的種子正是埋在這兩種理念的夾縫當中。如果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理念之間存在一條力線,那么幾乎可以肯定,恐怖就是在這里滋生的。(Stephen King, Danse Macabre, Everest House, 1981, pp.20-21)
友善與威脅、饋贈與破壞、和平與戰爭——在斯蒂芬·金看來,恐怖正是滋生于這樣互斥的理念并存所形成的力場當中。值得玩味的是,1957年美國的銀幕正在上演“恐怖秀”,于現實則是冷戰進入高潮——這一年蘇聯兩度將人造衛星送入太空,美國自然不甘示弱,但年底“先鋒號”卻折戟沉沙。接下來,二者的角力導致了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機、1961年的豬灣事件,以及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不同于世人往往將古巴導彈危機僅僅看做冷戰中的重要事件,在《愚蠢的核彈》一書中,浦洛基有意從“核歷史”的角度對其進行考察。“倘若兩位領導人對核武器有一種更傲慢的態度,那么我們很難想象古巴導彈危機最終會有怎樣的結果。”(382頁)通過更全面的視角與細節性史料的更多應用,浦洛基論證了這一事件與人類歷史上大多愚行并無不同,“他們幾乎犯下了所能想到的每一個錯誤,幾乎走錯了每一步”(同上);但最終阻止“事先張揚的戰爭”成真的,實際上是廣島與長崎的浩劫,以及發生在比基尼環礁和克什特姆等地的核事故所展示的恐怖。恐怖滋生于互斥力場,使角力持續,但也能確保克制;若恐怖被更愚蠢、更盲目的領導人無視,恐怕會導致失控——失控才是最恐怖的結局。
從《八月炮火》到《愚政進行曲》
《愚蠢的核彈》這部古巴導彈危機新史之“新”,首先體現在敘事框架的拓展。不同于將視角更多局限于美國一方,進而把這一事件處理成“危機-應對”案例模型的慣常做法(如美國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與菲利普·澤利科合著的名作《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浦洛基兼顧了美、蘇、古巴三方視角,同時增添了更多細節,從而方便讀者從歷史而非案例的角度理解這一事件——歷史是真實人物演出的故事,而案例更像“角色扮演”。
從呈現“套路”到復原真實,細節必不可少。對于古巴導彈危機中的約翰·肯尼迪,人們通常將他看做力挽狂瀾的決策者,而浦洛基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細節:“約翰·肯尼迪十分警惕因誤讀對手意圖而引發戰爭的可能性,他對巴巴拉·塔奇曼的普利策獲獎作品《八月炮火》尤為推崇。”(第5頁)他不僅將這本書送給身邊的朋友以及駐扎在世界各地的美軍指揮官,還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前評論當時尚未完結的柏林危機時談到了這本書,“‘通過閱讀一本講述戰爭歷史的書籍,我不禁感嘆,溝通失敗、誤解和相互挑釁在導致開戰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肯尼迪所說的書就是巴巴拉·塔奇曼近期出版的《八月炮火》”(113頁)。
盡管肯尼迪有避免誤讀對方意圖的自覺性,但他實際上并未做到。正如《八月炮火》中德國元帥施里芬無法理解比利時人的抵抗意圖和俄國人的動員能力,法國元帥霞飛亦不能理解德軍的攻擊重點,肯尼迪對于赫魯曉夫的行事邏輯始終一頭霧水。然而諷刺的是,答案其實就在他的鼻子底下——或者說,被他拋在自己“腦后”:
隨著討論的推進,肯尼迪又開始糾結于赫魯曉夫為何要這么做。幾分鐘后,他再次問道:“如果不能提高他們的戰略實力,那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有沒有蘇聯專家能告訴我?”肯尼迪剛拋出問題,緊接著又說:“就跟我們突然要開始在土耳其部署大量中程彈道導彈一樣。我覺得這么做太他媽危險了。”這時,副國務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插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確實部署了。”(154頁)
赫魯曉夫的動機很簡單:在力量不足時確保威脅——與五年前美國在土耳其部署導彈如出一轍。然而牢記需要盡可能理解對方意圖的肯尼迪,也許忘記了理解他者最直接的辦法是換位思考。他和他的幕僚們并不認為蘇聯與美國有何相似之處,哪怕是五年前的美國。大概根本上,他們并不愿意承認那是“自身”的一部分。畢竟,他們是“出類拔萃之輩”,到華盛頓就是為了把只會打高爾夫球的老一輩政客甩在身后,“與此相反,新人們都是強悍的人——‘硬骨頭的現實主義者’,這個名詞往往用作對他們的稱呼,這也是他們自己選定的對自己的描繪”([美]戴維·哈爾伯斯坦:《出類拔萃之輩》,齊沛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3年,71頁)。政治經驗的割裂導致盲目——其實此前的豬灣事件已經暴露出“新人”渴望證明自己的同時依然在走目中無人的老路。當他們日后在越戰中越陷越深,這一點也將進一步體現。
肯尼迪最終也被他喜愛的作者巴巴拉·塔奇曼寫進了書里,成為歷史的教訓之一。在1984年出版的《愚政進行曲》中,肯尼迪壓軸登場。塔奇曼在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分析了“出類拔萃之輩”相較于艾森豪威爾時期戰爭政策的轉變。肯尼迪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傾心于“對戰爭的理性管理”,相信歷史已經進入了一個受理性約束的時代,“然而,事物的另一面卻被遺漏了。戰爭是具有兩面性的……麥克納馬拉并不太了解人性因素,人類行為有時并不是理性的,它們荒誕怪異,難以捉摸,因此沒有成為分析考量的要素”([美]巴巴拉·塔奇曼:《愚政進行曲》,孟慶亮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282頁)。
僅從古巴導彈危機的結局來看,肯尼迪最終的確讓事件峰回路轉,但促成這一結局卻并非他的理性或是熱愛閱讀的好習慣,而僅僅是他在那十三天的舉棋不定釋放了更多偶然。事后來看,這些偶然稍有差池,都將導致這一事件走向完全不同的結局。這顯然不可能是一個理性主義者的有意為之。
權力的新悖論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倒從未以“理性主義者”自居。他喜歡標榜自己的熱情與機智,而古巴導彈危機的起因正是他的靈機一動:
根據他的兒子謝爾蓋回憶,赫魯曉夫在瓦爾納的一個海濱公園散步時,突然靈光一現:他要對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蘇聯的核導彈部署在古巴海岸。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訪問保加利亞期間,我萌生了在古巴部署核彈的想法。”這似乎可以同時解決他面臨的兩個問題,既能保護古巴,又能縮小與美國間的導彈實力差距。“赫魯曉夫的想象力很豐富,當被某個想法吸引住時,他便會把這個想法的實施看作解決某個特定問題的簡單方法,一種‘包治百病’的方法。”這位蘇聯領導人的助手奧列格·特羅揚諾夫斯基回憶道。(62頁)
赫魯曉夫從一開始便在憑借偶然性行事。但與肯尼迪不同,他的偶然由于權力的慣性注定會成為實然。要把導彈布置在古巴,存在兩個難點:一是需要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的同意,二是古巴的地形是否能夠隱藏導彈基地。盡管卡斯特羅最初對這個提議并不感冒,但出于“道德、政治和國際道義”(76頁)立場的考量讓他接受了這一提議。于是蘇方代表比留佐夫元帥便確信一切障礙皆被掃清——盡管“實地考察之后,比留佐夫當然知道古巴的棕櫚樹不可能隱藏占地數百平方米的導彈設施,然而他似乎并不在意這一點”(77頁)——既然雙方的當權者都已點頭,客觀困難似乎便不值一提。
這場危機的結局,在此刻其實已經埋下伏筆:美方注定會早早發覺蘇方在古巴的動向,并采取行動,于是它只持續了短短十三天。但也正是因為底牌暴露得太快,雙方早早便開始劍拔弩張,這十三天從一開始便充滿戲劇性——以及盲目和失誤。譬如10月24日肯尼迪終于下定決心,在晨會上下令追擊蘇聯船只,“然而他不知道早在二十四小時之前這些船只就已經改變了航向,駛離了古巴”(203頁);再如日后赫魯曉夫吹噓的這一事件中蘇方的“戰功”——擊落美方一架U-2偵察機,實際上也是一系列混亂指令的偶然結果(262-263頁)。哪怕是到危機收場時,“烏龍”仍未停止。當雙方已經“談妥”,莫斯科方面卻得到情報,稱肯尼迪將再次通過電視發表全國演講,迫使赫魯曉夫臨時決定把他給肯尼迪的信公之于眾。然而,“蘇聯軍方特工獲得的情報實際上是肯尼迪10月22日演說的一次重播……如果肯尼迪想在星期天(10月28日)發表電視演講,他也不會定在上午九點,因為那是美國人去教堂做禮拜的日子”(310頁)。
所以盡管對于古巴導彈危機,最常被提及的描述也許是時任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的“眼對眼”,但真實情況也許是雙方都在“盲人摸象”。不過肯尼迪的理性主義還是讓他把握到了些許真相。在幾個月前評論柏林危機時他便指出,“那些要以西柏林爭端為借口發動戰爭的人,應該回想一下這句名言——‘制造恐懼的人也無法擺脫恐懼’”(33頁)。一切的起點——赫魯曉夫的靈機一動,只是讓他暫時擺脫了危機,但更深層次的恐懼依然留在他這一邊。于是當肯尼迪終于記起美方在土耳其的導彈,并把這一籌碼放上談判桌,他很快便選擇妥協。只是這一妥協令他顏面盡失,他的“失敗”令一些人開始懷念“鋼鐵領袖”斯大林。如果斯蒂芬·科特金的結論成立——“不論是好是壞,歷史都是那些永不放棄的人創造的”([美]斯蒂芬·科特金:《斯大林:權力的悖論》,李曉江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964頁),那么赫魯曉夫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妥協與隨即失勢或許代表了權力的一種新悖論——一旦它進入慣性狀態,試圖“修正”,反而意味著破壞。
加勒比的孤兒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便是一種完全沒有必要的動作。一連數日,不但差點把全世界投入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火,事實上也把雙方的高層決策人士嚇得清醒過來,一時之間,總算變得比較具有理性了。”([英]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鄭明萱譯,麥田出版,1996年,343頁)霍氏的總結可謂切中肯綮,也正因如此,這場危機對這兩個大國而言其實并無輸贏之分。美蘇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也在共同的恐懼——核戰爭——面前相對適時且體面地收手了。盡管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在不久后退出了政治舞臺,但這其實與這場危機關系不大——就算它是落在他們背上的稻草,也絕不是最后一根。
但仍有深受挫敗之人。“幾十年后,卡斯特羅回憶起自己與同志們在得知莫斯科電臺播報赫魯曉夫給肯尼迪的信時的反應,他說:‘當時我們全體國民都滿心憤慨,而不是覺得寬慰。’”(324頁)在通過古巴一家報紙總編——而非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得知美蘇雙方達成協議后兩天,卡斯特羅在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會面中大發雷霆:
吳丹以剛果(金)政府為例,試圖反駁卡斯特羅有關國家主權的觀點[剛果(金)曾邀請聯合國工作人員進入該國]。聽到這里卡斯特羅憤怒地回擊道:“剛果(金)做出這一決定的人已經死了!被埋葬了!”他指的是剛果民主共和國前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他于1961年1月被西方力量支持的反對派殺害,而當時聯合國維和軍隊就駐扎在剛果(金)。卡斯特羅拒絕了吳丹的請求,不但不接受聯合國針對導彈基地的核查,而且不同意在古巴港口核查運載武器返回蘇聯的船只。這次會議最終沒有達成共識。卡斯特羅一直在講國家主權和羞辱,吳丹則始終在談對國際和平的威脅。(333頁)
這里的爭論,或許會讓人聯想到紐倫堡審判中關于“危害人類罪”與“滅絕種族罪”的爭論。在融合公共歷史與家族秘史的出色作品《東西街: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中,作者菲利普·桑茲討論了當時兩位法學家——主張以“危害人類罪”為納粹分子定罪的勞特派特與主張“滅絕種族罪”的萊特金——面對“法律如何有助于防止大規模殺戮”這一根本問題的分歧。在勞特派特看來,“危害人類罪”即包含了對群體的保護——強調對群體的保護反而會強化部落主義;但萊特金認為勞特派特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忽視了沖突和暴力的現實:個體成為目標是因為他們是特定群體的成員,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個體特質”([英]菲利普·桑茲:《東西街: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源》,吳曉筠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341-342頁)。同樣地,吳丹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立場令他必然要強調“國際和平”,這一立場的無力顯而易見;而就像紐倫堡的判詞中最終并未出現“種族滅絕”,持有更現實主張的卡斯特羅也和萊特金一樣,只能接受失敗的結局。
由浦洛基的角度,從《原子與灰燼》到《切爾諾貝利》,再到這部《愚蠢的核彈》,對“核”這一主題的持續關注確保他能夠提出足夠有益的警世之言——“今天,我們仿佛回到了古巴導彈危機之前的狀態,用丘吉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話來說,就是缺乏廣泛認同的‘恐怖均勢’(balance of terror)”(385頁)。恐怖有其益處,但人類的想象力若能更豐富則更好:在恐懼一場危及所有人的浩劫的基礎上,那些危害一個區域、一群人的災難同樣值得害怕。如果我們無力想象他方的恐怖圖景,那么它遲早會降臨到我們眼前。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