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40年40人|葛小偉:“人性化”的中美關系有助于跨越分歧
北京時間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時,中美雙方同時發布《中美建交公報》,宣布兩國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系。40年彈指一揮間。澎湃新聞聯合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跨越大洋兩岸,對話40位重量級人物。他們有當年建交的推動者、親歷者和見證者,更有40年風雨關系的參與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1978年,在中美建交前夕,葛小偉跟隨身為外交官的父母來到中國,從一個孩子的視角見證了中美關系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如今,那個興奮的小學生已經成長為中美問題專家,致力于促進兩國相互理解。他先后倡議發起了“中美安全對話”“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紐曼華語文學獎”等活動,為促進中美官方和民間交流與合作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在中國生活、求學的經歷給了葛小偉不同的視角,也使他更能從中國人的角度和立場理解中國。“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們都一樣,都是‘人’。我覺得在國際關系領域,我們很容易忘記這至關重要的一點。”他說。在充滿現實主義論調的國際關系研究圈中,葛小偉帶有人性溫度的觀點讓他顯得有些特別。
在葛小偉看來,某些國際關系理論過于狹隘地強調差異與分歧,卻忽略了人性的共通之處。他認為中美應該發展更加“人性化”的關系,培養同理心、增強相互理解,這將有助于在國家層面加深互信,戰勝挑戰,實現和睦合作的美好未來。
一個“美國兒童”眼中的中美建交
澎湃新聞:您曾經在一所中國小學上學,能否談談這段經歷?
葛小偉:我到中國的時候是1978年,1980年離開中國,當時我只有十來歲。那時我的父親在使館工作,實際上當時還沒有美國駐華大使館,只有一個聯絡處,1979年就變成大使館了。
我當時在北京的芳草地小學上學。來中國之前我一句中文都不會說。我記得,那時下課打鈴的時候,學生會說“打鈴了”,于是大家跑出教室,去足球場踢球。過一會,大家又會大聲喊“打鈴了”,又都跑進教室。第二天,當我再聽到有人說“打鈴了”,我便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就是這樣開始學習中文的。
當年的體育課有一個扔手榴彈的項目,是那種練習用的手榴彈,我扔得最遠。因為在美國經常扔棒球和壘球,所以我知道怎么扔。我曾代表芳草地小學參加北京市的一場運動會,我的比賽成績在全市名列前茅,排在我前面的幾個學生年紀都比我大,所以我感到很驕傲。在芳草地的經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澎湃新聞:中美建立外交關系的時候,您正好在北京,對這件事有什么特別的記憶?
葛小偉:當時我還小,所以沒有什么國際關系的概念。我去參加了美國駐華大使館外舉行的一場正式的升國旗儀式。升旗儀式后要放鞭炮,很多國際媒體都在現場報導。大人們可能記住的是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這位首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講話,或者中國外交部長的講話,而我注意到的只是鞭炮,10多歲的小孩子就是這樣的。
澎湃新聞:在中國生活學習的這些經歷對您研究中國的學術興趣有影響嗎?
葛小偉:除了在芳草地小學上了兩年學,1988年我還在北京大學留學了一個學期,結束后又在北京為美國《新聞周刊》工作了兩個月。1988年這8個月,我交了很多好朋友,包括北大排球隊還有哲學系的一些研究生。在和中國人交朋友的過程中,我意識到很重要的一點: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是“人”。這一點,在國際關系領域,往往很容易被忽視。
因為在北京待過,交了很多中國的朋友,我自然而然地對中國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比方說,我認為北京是我的一個老家,我覺得我一部分是北京人,還保持了一點北京口音。
申請大學的時候我決定繼續學中文。我選擇了語言類專業非常出色的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做亞洲研究,包括中國歷史、哲學、宗教等。后來我在密歇根大學讀碩士,期間上了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中國政治課,這對我影響很大。我很快對美國的中國研究,尤其是中國政治的一些學術觀點有了一定的認識。讓我印象很深的一點是,很多學者是用西方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政治,因此導致了一些誤解。我對此感到有一點“憤怒”,所以我就想,或許我也應該讀博士,做更好的中國政治研究。
相較于和我同時代的研究中國的學者,由于我從小在中國待過,我在中國的經歷更豐富一些。從1978年到現在,我一直有機會來中國,所以我親眼看到了中國的變化,這使我能夠從一個歷史的角度來了解中國的現況,我的同事們不一定有這樣的經驗,他們的角度會稍微不一樣。

中美交往需要多軌并行
澎湃新聞:您倡議和發起了“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發起這個對話的初衷是什么?相比資深外交官,青年外交官對話有什么獨特作用?
葛小偉:我先后在密歇根大學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求學,讀書期間,經常會見到來自中國的外交官,他們會跟美方的外交官談判。我注意到,兩方坐下來談話的時候,總是中方坐在這邊,美方坐在另一邊。這些談判的過程常常有點像是在互相“教訓”、批評對方。我認為這些交流有“逆向作用”,所以我便開始思考如何改變這種模式。我稍微學了一些政治心理學,借鑒社會心理學,來了解怎樣幫助不同群體更好地了解對方的想法,減少彼此的偏見和誤解。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在中美關系中做一些類似的“對話”,幫助中美之間多進行一些真正的溝通,真正理解對方的立場。青年外交官是未來的領袖,現在提供多一點非正式的場合給他們交朋友,了解彼此的立場,會對他們將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過去交流的機會主要是在領導層面,而普通外交官之間交流的機會,尤其是在華盛頓和北京之外的非正式場合的交流機會,幾乎沒有。這個“對話”由我和吳心伯教授共同主持,一直堅持至今。
澎湃新聞:您還曾發起過“中美安全對話”,在組織這些活動的過程中您對中美關系有沒有獲得一些新的視角?
葛小偉:通過這兩個“對話”,我越來越了解到,外交官所面臨的工作挑戰真的很大。比方說,他們在做外交工作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的背后還有很多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有很多限制。我希望我們能夠想辦法幫助外交官來開展他們的工作。
在進行“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時所面臨的一個最基本的挑戰是試圖真正從對方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無論是美方還是中方的外交官,他們都知道對方在重大事情上的正式的官方政策,但是他們真正了解政策背后的動機嗎?這就不一定了。因為他們沒有足夠多的機會真正深入交流,真正傾聽對方,了解對方的感情。我認為,要真正促進中美相互理解和尊重,就需要有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的意愿。沒有必要完全同意對方的意見,但是如果你愿意了解對方,就可以減少誤解。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1.5軌對話和二軌對話對推動中美關系有什么作用?
葛小偉:一軌對話,也就是領導層面的交流,因為場合太正式、語言太正式,有時候太過非黑即白,可能會有一定的逆向作用;而1.5軌對話或者二軌對話則不同。以“中美青年外交官對話”為例,雖然我沒有做過量化統計,但十年的經歷證明組織這樣的活動能帶來積極的影響。我和與會人員交流時,他們經常表示參會者之間私下或個別的小范圍交流非常有幫助,他們通過參加活動建立起了個人友誼。這說明我們的外交官們認為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尤其在中美存在分歧和挑戰的領域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和角度,對我們解決問題最有幫助。
澎湃新聞:過去10年來中美之間合作和摩擦都在增加。在您組織的這些外交官對話活動中,與會者關心的議題有哪些變化?是否也反映了中美關系變化的某些特點?
葛小偉: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外交官們討論的話題范圍也變得越來越廣泛。過去,兩國外交官主要討論的是雙邊或地區性問題,但現在,幾乎所有的全球重大安全問題都需要中美通力合作才能解決。所以,全球變暖、國際衛生等問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的議程冊上。我記得有一次特別驚訝地發現有些外交官在討論非常具體的細菌耐藥性問題——可見我們的外交官們對所有的全球問題都要了解!
但應該指出的是,10年來有些情況一直沒變。比如涉及到日本的問題,中美兩方仿佛在討論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這就是意識形態的作用,讓我們對同一個國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觀點和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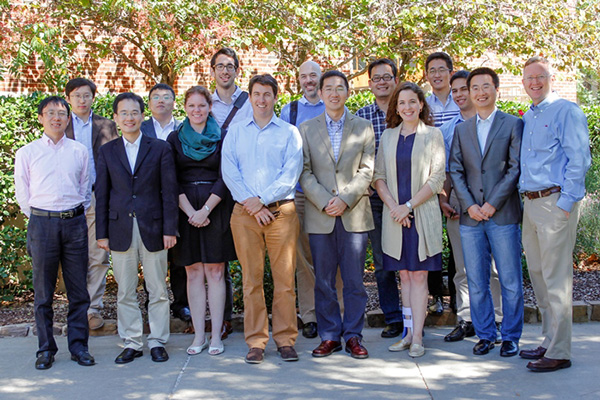
人性的共通之處能幫助中美戰勝分歧
澎湃新聞:您是一位政治心理學家,您認為意識形態差異對中美關系有什么樣的影響?
葛小偉:我的研究強調意識形態、民族身份,以及這些心理因素如何影響國際關系。在美國,影響美國人對國際事務態度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其核心就是特別重視個人自由。在普通美國人的認知里,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挑戰個人自由的。一般的美國人恐怕對中國政府總會有一點擔心,有一點恐懼,他們覺得中國崛起或許會威脅美國人的自由,所以或許會有過分的恐懼。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力量。
澎湃新聞:誠然,中美之間存在很多“誤解”和“誤認”。這些問題能否用“文明沖突”這樣的理論來解釋?
葛小偉:我覺得這樣的“誤解”會讓兩方的人民過分恐懼,有過于強烈的威脅感。這些威脅感會產生不良后果,影響我們對對方的政策,導致“安全困境”。舉例來說,中國人看美國常常會有一種黑白分明的看法,例如“美國是霸道的”。美國人也經常會有這種黑白分明的看法,比如“我們是自由的,他們沒有自由”。如果事實真的那么簡單,黑白分明的話,那么人們應當恐懼。但現實不是非黑即白的。
對于“文明沖突”的說法,我不以為然。因為各個文明之間也不是涇渭分明的。的確,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不是全然一樣,我們的教育和父母教給我們的價值觀有微妙的不同,會影響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們都是“人”,我們最終都有作為“人”的共同挑戰和訴求。
中美兩國互相妖魔化對方的現象確實存在,雖然不是主流,但凡是希望中美和平友好的人都不應該掉以輕心,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對方和我們一樣,人性是共通的,我們要一起努力找到更多的共同點,增進互相理解,而不是讓差異被放大從而誤導我們。

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沖突”理論過分強調了文化、文明之間的不同,忘記了我們的共同之處。這是“文明沖突”理論的負面作用,如果總認為對方跟自己不一樣,那很容易與對方起沖突。
澎湃新聞:您曾提到,由于對中國崛起后中美發生沖突的假設性討論過于密集,會使得中美雙方陷入某種惡性循環。這是為什么?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們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葛小偉:在國際關系的領域內,我們要小心,比如“現實主義”這樣的理論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這很可怕。所以,我希望教國際關系理論的老師,在做研究的時候,教書的時候,要自覺地想一想這些理論有什么后果。
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還是現實主義。無論在華盛頓還是北京最有影響的理論也是現實主義。但現實主義過于狹隘地強調國家利益,而沒有考慮到心理因素、個人因素。有些人覺得人就是一種經濟動物,但是人也有別的需要,比如我們都希望別人尊重我們。得到對方的尊重是人類交往中的基本動機之一。這種訴求同樣適用于兩國關系,兩方都希望得到對方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尊重,都很容易把某些行為解讀為羞辱或挑釁。
作為學者,我們應該幫助各自的同胞理解對方的立場,因為這樣可以減少誤解。我在美國教中美關系的時候,發現很多美國學生根本不理解中國。我的工作就是幫助他們從中國人的立場了解中國的外交。有一些問題很難解決,比如臺灣問題,美國人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是如果他們能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理解一些問題,比方說了解鴉片戰爭的歷史,理解“百年國恥”這種歷史觀,那么或許會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對臺灣問題有那么強烈的感情。
我也希望中國的同事能用這樣的態度幫助中國的學生更深刻理解美方的立場。美國對臺灣問題的政策真的是因為“霸道”?因為想阻礙中國的崛起?想羞辱中國嗎?還是跟他們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有關?總而言之,我們要同情對方,不要總是責怪對方。
澎湃新聞:您認為影響未來中美關系穩定的最大干擾因素是什么?
葛小偉:中美關系已經不僅僅局限于雙邊問題,而是包括了幾乎所有的國際問題,比如國際反恐、環境保護等。兩國之間的相互依賴也變得越來越復雜。
實際上,我最擔心的可能是日本、臺海或者朝鮮半島的某個事件,持續發酵、惡化升級,把美國也拉進去。比如,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結果很嚴重,所幸我們最后還是解決了。假設明天再出現一個類似的撞機事件,但是發生在中日之間,在東海而不是南海,北京和東京能夠控制國內輿論嗎?能理智地管控這個危機嗎?如果沒有管控好,美國會被拉進去嗎?
所以,雖然這些是偶然事件,誰都不會故意這么做,但是還是會有這樣微小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建立互信,沒有互相信任的話,就很難管控危機事件。
澎湃新聞:中美關系40 年中的后四分之一時間里,您每年都有機會和兩國的外交官直接接觸和交流。新生代外交官之間的交往呈現出什么樣的特點?他們對中美關系的下一個40 年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葛小偉:在日益全球化的當今世界,外交官們和普通大眾一樣,彼此之間直接(通過出訪、參會等)、間接(通過電視、電影、社交媒體等)接觸的機會都變得更多了。但是更加密切的交往所能帶來的結果和影響卻不一定是積極正面的。如果我們帶著同理心,學會互相尊重,我們就更加有可能消除偏見,在面對21世紀的中美關系時,找到應對挑戰、繼續前行的方向。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