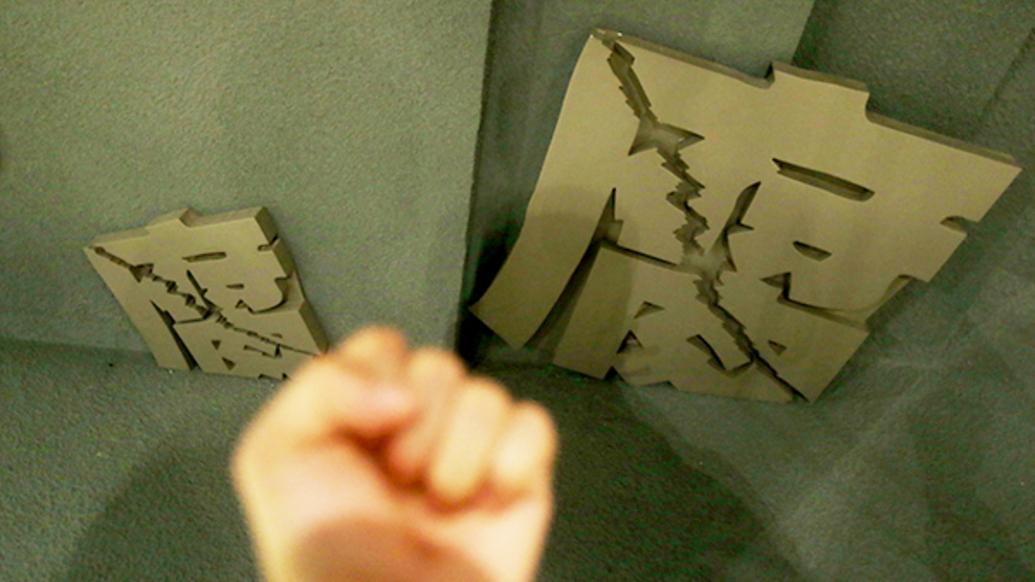- +1139
《刑事訴訟法》最新修正的不足

現行《刑事訴訟法》由全國人大1979年7月1日表決通過,1996年3月17日第一次修正,2012年3月14日第二次修正,本次修正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2018年10月26日表決通過。雖然每次修正都順應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都是亮點紛呈,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少許不足,需要引起人們的重視,以便再次修正時及時修改。
一、缺席審判制度存在的不足
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最大的亮點,是建立了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具體見于其第五編“特別程序”第三章“缺席審判程序”,包括第二百九十一至二百九十七條。
專家認為,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有利于推動司法機關積極履行職責、懲治犯罪、促進反腐敗國際追逃工作的進展,可以使一些案件得到及時處理,使一些證據得到及時固定,避免因時間過長導致證據滅失情形的發生。此外也是為了與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相銜接。
可見,設立缺席審判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過分強調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以至于對該制度的現實可行性考慮不足,有可能導致該制度淪為一紙空文。
首先,在可適用缺席審判制度的案件類型方面,第二百九十一條的規定存在諸多問題。
一是案件類型太少,僅僅限于貪污賄賂犯罪案件、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對其他類型的案件均無法適用。而其他類型的案件,有可能涉案金額更大、被害人更多、社會危害性更嚴重,與貪污賄賂犯罪中法定刑較輕的罪名相比,更應當適用缺席審判制度。例如,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邪教犯罪,受騙群眾成千上萬、詐騙金額動輒幾百億、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集資詐騙犯罪,嚴重反人類反社會的拐賣人口犯罪,似乎更應當適用缺席審判制度。
二是“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的范圍不夠明確。從《刑法》規定來看,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不僅包括《刑法》分則第八章規定的“貪污賄賂罪”,而且包括分則第三章中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甚至職務侵占罪也應當包括在內,因為職務侵占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僅僅在于犯罪主體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實際上,從法定刑來看,這些犯罪的法定刑都比“貪污賄賂罪”中的“介紹賄賂罪”重得多,如果對介紹賄賂案件可以缺席審判,則對這些犯罪也應當可以缺席審判。但是,如果因為介紹賄賂罪的法定刑很輕而將其排除在缺席審判適用范圍之外,則法定刑多重的罪名才可以缺席審判又成了一個疑難問題。
三是規定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適用缺席審判要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這可能由于層層匯報的程序過于繁瑣、流程過于冗長而導致對這些案件難以適用缺席審判。因為,無論是逐級經區縣級公安、市級公安、省級公安、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匯報,還是經區縣級公安向區縣級檢察院、市級檢察院、省級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逐級匯報,其程序和時間都不是一般的繁瑣和冗長,很可能由于程序上的扯皮而延誤辦案時機,而《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區縣級公安辦理這些案件應當經哪種途徑取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核準。實際上,無論哪種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和恐怖主義犯罪,其社會危害性都比貪污賄賂犯罪中的輕罪的社會危害性嚴重得多,其法定刑也重得多,對這兩類犯罪在適用缺席審判的程序方面應當更加寬松才對。
四是用“嚴重”來限制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范圍不夠妥當。因為,從法定刑來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幾乎都是重罪,只有某些罪名中的“一般參加者”的法定刑才是比較輕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而“嚴重”是指具體罪名的法定刑較重還是具體案件的性質或者社會危害性嚴重,具體多重才屬于“嚴重”,無疑也會引起理論上的極大爭議和司法實踐中的無所適從。
綜上,與其根據案件類型對缺席審判的適用范圍和審批程序進行限制,不如根據具體犯罪本身社會危害的嚴重程度進行限制。一般來講,經過公安機關初步偵查和正式立案偵查之后,是能夠初步判斷具體案件的社會危害程度的。
其次,根據第二百九十二條的規定,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方式,或者通過外交途徑提出司法協助方式,或者通過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將傳票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只有對被告人收到開庭傳票和起訴書副本之后,仍然拒不回國參加庭審接受審判的情形,才可以缺席審判。
這條規定意味著,偵查案件的公安機關或監察委員會必須在立案偵查之初,就明確知道并且確認犯罪嫌疑人準確的居住地點(以及一直到開庭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之時對方都不會變更居住地點),并且知道有確實可行的合法途徑可以送達書面訴訟文書,比如,居住國官方肯定會配合送達等,否則,均將由于無法送達書面訴訟文書而不能適用缺席審判。這對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和恐怖主義犯罪案件的公安機關來講,要求將更加嚴苛,很可能案件在公安系統內部或者檢察系統內部逐級匯報審批過程中,由于有內鬼向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親友通風報信而使整個辦案努力功虧一簣,久而久之,將極大打擊公安機關辦案的積極性,從而使缺席審判制度形同虛設。
實際上,文書送達的目的是及時通知犯罪嫌疑人,允許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在通訊技術很不發達的農耕時代,當然需要書面通知,以便通知到位并留下辦案依法的證據。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只要在指定的官方網站上公告足夠長的時間,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網指定欄目滾動公告六個月,并以其他適當方式告知對方有這樣一份公告可在該網站查詢到,就應當能夠推定犯罪嫌疑人已經知道開庭審判的日期和地點,應當回國參加庭審接受審判,而沒有必要經過繁瑣而又代價高昂的書面文書送達程序。
再次,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被告人的近親屬不服判決的,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這條規定顯得莫名其妙。因為,可能實施了犯罪行為并接到出庭通知、應當回國接受審判而拒不回國接受審判的是被告人,判決書確認的應當承受犯罪后果的也是被告人,雖然《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近親屬”的范圍較窄,僅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但這些近親屬與被告人在法律上仍屬于不同的主體,其既未參與實施犯罪活動因而對犯罪活動并不知情,又不承擔刑罰等犯罪后果,沒有任何理由對與自己的權利義務無關的判決書享有上訴權。
實際上,在缺席審判之外的其他程序中,僅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上訴權,被告人的近親屬不可能享有上訴權。所謂“法定代理人”,是指代理未成年的被告人參加刑事訴訟活動的監護人。
由于二審可能影響被告人的刑罰后果,因而在實質上,這條規定賦予了蔑視法律權威、接到開庭傳票和起訴書副本仍拒不回國接受審判的被告人比參加庭審的被告人更大的權利,違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則。因此,如果說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將判決書送達被告人及其近親屬、辯護人”還有一定道理的話,那么規定“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不服判決的,有權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卻毫無道理。
最后,關于缺席審判的規定存在問題最多的,恐怕屬于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該款規定:“罪犯在判決、裁定發生法律效力后到案的,人民法院應當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交付執行刑罰前,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罪犯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理。”該款規定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其一,根據其第一句話分析,如果罪犯沒有到案,則不能將罪犯交付執行刑罰。顯然,這里的“交付執行”,應當是指對主刑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交付執行,對罰金、沒收財產等財產刑的執行,則沒有必要等到罪犯到案之后才交付執行,因為直接扣劃罪犯的存款、拍賣或變賣罪犯的房產及其他資產即可。但是,由于該款規定賦予罪犯推翻生效判決、裁定的權利,法院在罪犯到案之前,未必能夠依法執行財產刑,否則,可能由于無法執行回轉而導致重審之后的判決、裁定無法執行。
例如,在法院依第一次生效判決、裁定拍賣罪犯所受賄的多套房產之后,第三方已經依法取得了房地產證,而重審認為原判認定被告人受賄房產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則事實上無法執行回轉。而根據該條第三款“依照生效判決、裁定對罪犯的財產進行的處理確有錯誤的,應當予以返還、賠償”的規定,在罪犯到案重審之后,是可能需要執行回轉的。
這樣,由于錯案追究制度的存在,法官在罪犯到案之前,對所謂生效判決或者裁定中確認的主刑和附加刑,都不敢依法執行,由此導致只要罪犯拒不到案,法官就不敢執行生效判決、裁定的后果,實際上是使缺席審判追逃追贓的立法目的落空。
其二,該款存在一個邏輯上的悖論,即,法院在罪犯到案之前已經作出的生效判決、裁定到底有無法律效力?
如果說具有法律效力,則為何人民法院應當告知罪犯有權對判決、裁定提出異議,并且一旦罪犯提出異議人民法院就應當重新審理,即使罪犯在第一審判決作出之后已經委托了辯護律師提起上訴?為何該條第三款會規定依照生效判決、裁定對罪犯財產進行的處理經重審之后仍可能被認為確有錯誤?這與根據審判監督程序進行重審的性質不一樣,因為審判監督程序主要是由人民法院的審判監督庭審查認定已經生效的判決、裁定是否確有錯誤以至需要重新審理,而不是可以由罪犯毫無根據的異議來決定應否重新審理。
如果說不具有法律效力,則所謂一、二審法院缺席審理的“生效”判決、裁定從何而來,則缺席審理有何意義?難道僅僅是為了通過首先作出定罪量刑較重的判決、裁定以吸引罪犯回國接受審判?而讓監、公、檢、法辛苦多月甚至數年的勞動成果付諸東流,無疑也是對國家司法資源和納稅人錢財的極大浪費。
其三,毫無疑問的是,缺席審判程序并非審判監督程序,而新法除了規定只要罪犯提出異議就應當重新審理之外,并未就重新審理的具體程序作出規定,則所謂重新審理,是由原一審法院重新審理,還是由原二審法院重新審理?是適用第一審程序,還是適用第二審程序,或者參照審判監督程序來決定應當由哪個法院適用哪審程序進行審理?
在《刑事訴訟法》本身沒有規定的情況下,無論是由哪個機關作出何種立法解釋或者司法解釋,都將不符合《立法法》的規定,因為,根據該法規定,對這種涉及罪犯人身自由權甚至生命權剝奪的重大事由,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制定法律來規定,其他任何機構都無權作出相關規定。
其四,僅規定罪犯有權到案提出異議要求重審,卻又沒有規定具體程序,也將導致司法機關無所適從。例如,由于沒有規定允許到案的具體期限,則假如罪犯在判決、裁定生效之后十多年才到案,是否仍然有權提出異議要求重新審理?由于沒有規定已經到案的罪犯提出異議的截止期限,則在法院告知其有權提出異議之后,罪犯故意遲遲不作決定的,比如,考慮了十年仍然不作決定,是否會喪失以及何時才能喪失提出異議的權利?雖然隨后的立法解釋或者司法解釋可能作出規定,但這種解釋是違背《立法法》的,因為《刑事訴訟法》本身并未規定罪犯提出異議的最長期限,無論作出何種解釋,都是對罪犯權利的不正當限制。
其五,該第二款僅提及罪犯“到案”,卻未提及是主動到案還是被國際追逃抓獲歸案,但無論何種情形,都未涉及能否對到案的罪犯采取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的問題。
一方面,刑事強制措施僅僅適用于法院審判之前,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跑、竄供、毀滅或偽造證據,以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而不適用于判決、裁定已經生效的罪犯。對后者只存在交付執行的問題,不存在繼續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以保證刑事訴訟活動順利進行的問題。況且,由于缺乏法律明文規定,對這種罪犯采取強制措施將明顯無法可依,比如,對罪犯進行拘留、逮捕的法定期限、應當由哪個機關作出決定、由哪個機關執行等,目前都沒有明文規定。
另一方面,對“到案”的罪犯拒不采取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也不妥當。因為,既然他有權提出異議要求法院重新審理,則在實質上仍屬于判決、裁定并未生效的被告人,仍處于法院重新審判之前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因而仍有必要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以保證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否則,完全可能出現在法院重新開庭審理之后,被告人又潛逃至境外的情形。
況且,為了防止罪犯濫用其提出異議權而故意拖延時間不作是否提出異議的決定,在客觀上也有必要對其采取拘留或者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例如,由于法律未規定罪犯提出異議的期限,并且提出異議是罪犯的權利,則在理論上,即使罪犯一直考慮了十年,法院也無權決定剝奪罪犯繼續考慮的權利。此外,如認為對這種罪犯不能采取拘留或逮捕等強制措施,則無異于否定之前國際追逃的所有艱辛和努力,無異于無端浪費納稅人的錢財。
總之,由于立法的自相矛盾,司法機關無論怎樣做都將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其六,賦予罪犯不需要任何合理合法根據即可提出異議要求重新審理的權利,既不符合刑事訴訟相關理論,在國際上恐怕也沒有先例,無異于否定缺席審判制度本身。
從該第二款的立法意圖來看,除非已經到案的罪犯追認之前生效判決、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否則只要罪犯已經到案,無論是主動投案還是被國際追逃抓獲歸案,之前所進行的缺席審判程序統統歸于無效,都應當重新開庭審理,這顯然違背《刑事訴訟法》增設缺席審判制度的初衷。而對于具有嚴重暴力傾向的恐怖主義犯罪規定罪犯有權提出異議要求重新審理,也與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犯罪普遍從重從嚴處罰的慣例相違背。
二、重大立功或涉國家利益可以無罪的規定與《刑法》不協調
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實,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公安機關可以撤銷案件,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也可以對涉嫌數罪中的一項或者多項不起訴。”這一規定可能存在如下問題。
第一,與現行《刑法》的規定不協調。在《刑法》中,案件涉及國家利益或者重大利益,并非法定或者酌定從寬處罰的情節,更非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法定理由。相反,《刑法》第三條中明文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換言之,只要實施了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就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沒有任何例外,否則,就有破壞“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則之嫌。雖然《刑法》第六十八條中規定了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從寬處罰制度,但其對重大立功僅僅是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沒有規定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該條規定的出臺,將使司法機關無所適從,不知應當適用哪部法律。
第二,根據此條規定,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有三: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立功表現,或者案件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而沒有犯罪性質或者嚴重程度等方面的限制。換言之,無論多么嚴重的犯罪,只要符合這三個條件,都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而不僅僅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這在《刑法》中是不可能找到相應依據的。
這種規定雖然有利于國家與犯罪人交換某種利益,但是對法治建設到底有何種影響,恐怕難以評估,至少不利于人們確立對法治的信仰,因為人們只能從現象上觀察到有嚴重的強奸、殺人、搶劫、販毒甚至恐怖主義犯罪等罪犯不被追究刑事責任,卻未必知道國家能從該次交易中獲得哪種利益,而拿公平正義的法治原則與罪犯做交易,本身即是對公平正義的法治原則的破壞,也是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損害被害人應當享有的公平正義,對被害人很不公正。
第三,該條規定有架空審判權之嫌。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來講,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檢察機關負責審查起訴,法院負責審判,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其中,審判權是人民法院專屬的權利,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由公安或者檢察機關行使。而犯罪嫌疑人是否自愿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是否具有重大立功表現、案件是否涉及國家重大利益,都是應當經過人民法院依法審判才能確定的事項,不能由公安或者檢察機關自行判斷決定。
第四,該條規定也與《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相矛盾。根據《刑事訴訟法》,雖然公安機關有權撤銷案件,檢察機關有權做出不起訴決定,但只能適用于依法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以及情節輕微或者顯著輕微因而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而不可能適用于嚴重犯罪案件。
例如,其第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
可見,公安和檢察機關只能根據《刑法》的規定來判斷能否不予追究刑事責任,而不能根據《刑事訴訟法》本身的規定進行判斷,此條規定與上引兩條規定相矛盾。
此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條的規定,對有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被害人,被害人既可以先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對結論不服時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
那么,對人民檢察院根據該條規定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書,是否仍應當送達被害人?被害人是否仍有權申訴或者提起自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將違背該條的立法本意,并且將導致法院無論作出何種判決都不適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則否定的依據何在又不得而知,而且被害人完全可以根據第一百八十條去主張其申訴或者提起自訴的權利。
三、修正條款中存在的其他小問題
除了以上兩個主要問題之外,修正條款中還存在一些小問題,簡要例示如下。
第十五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該條規定是典型的廢話,因為,在司法實踐中,對這樣的人向來是從寬處理的,不可能反過來從重處理。即使沒有該條規定,也絲毫不影響司法機關從認罪態度好的人從寬處理。
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機構可以在人民法院、看守所等場所派駐值班律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托辯護人,法律援助機構沒有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由值班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建議、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對案件處理提出意見等法律幫助。”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看守所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并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約見值班律師提供便利。”
該條規定存在的問題在于,由于法律援助機構僅僅是“可以”派駐值班律師,而不是“應當”、“必須”派駐值班律師,因此不派駐值班律師并不違法。顯然,在尚未派駐值班律師的地方,自然談不上被告人有權約見值班律師之類問題;而有的地方有值班律師有的地方沒有值班律師,也將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獲得無償法律援助取決于其犯案的地點和運氣,從而顯得不倫不類。
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由審判員三人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進行,但是基層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
此款中,規定“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共三人或者七人組成合議庭”估計是筆誤,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得出由五人組成就不可以的結論。其實只要是多數加單數,比如三人、五人或者七人均可,多數是為合議,單數是為表決,因此,這里的“或者”比較可能是“至”的筆誤。實際上,由于我國并未實行真正的陪審制度,因此完全沒有必要規定可以由七人組成合議庭,五人共審一案已經夠多了。由于“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一般仍是由三人組成合議庭,連五人共審都極少見。
該條第二款存在同樣的問題,不過,由于該條中是“三人至七人”和“三人或者七人”混用,似乎又是有意為之。若是有意區分,則立法理由值得商榷。
第二百九十六條規定:“因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無法出庭,中止審理超過六個月,被告人仍無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申請或者同意恢復審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況下缺席審理,依法作出判決。”
此條規定的問題在于太不明確:是只能由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或者同意,還是也可以由被告人的近親屬申請或者同意?其實,將“法定代理人”與“近親屬”之間的頓號改為“或者”即可防止這種疑問。但是,如果被告人與近親屬的意見完全相反,則是應當尊重被告人的意見還是尊重其近親屬的意見,又會產生爭議,可見立法技巧有待提高。
四、結語
雖然本次修正亮點紛呈。例如:第三十九條第三款刪除了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的律師會見需要經偵查機關批準的規定,第七十五條中刪除了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可以在住處之外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規定,這對于保護特別重大賄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非常有力;第八十一條中明確規定批準或者決定逮捕時應當考慮哪些因素,第一百零八條對“偵查”所作的定義更加準確,第一百七十條對《刑事訴訟法》和《監察法》之間的銜接處理,以及增設認罪認罰程序和速裁程序并詳細規定具體細節等,都可謂立法亮點,——但是,對修正中存在的問題,也應予以適當注意。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