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唐曉渡:無論張煒的小說成就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他本質上都首先是一位詩人
所謂伊人
作者:唐曉渡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3-11
唐曉渡的詩歌批評具有廣闊的精神視域, 但卻存在著一個絕對立腳點,即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放棄對詩歌存在的獨特依據的探詢和堅持。對他而言, 詩歌的本體依據或存在理由是“ 探索生存、情感經驗和話語方式的可能性, 發現那些只能經由詩所發現的東西”。
—— 陳超
唐曉渡向來以思想深刻和綿密見長……有著突出的面貌:一是極強的問題意識,善于慧眼識相,鞭辟入里。二是精細的對話風范,有一種虔懇、內斂的開放,有一種如切如磋、絲絲入扣的話語方式。三是謹嚴的“行規”,批評的自足與對象保持辯證客觀的平行。據豐富而求貫通,由精密而行張力。
——陳仲義
(唐文)所揭示的“時間神話”之說,切中了本世紀以來知識分子思維模式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并對當前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某些現象做出了坦率和尖銳的批評。文章由于其深刻性而給人諸多啟發。其觀點和膽識對清理 20 世紀的思想,具有較大的意義。
——首屆“文藝爭鳴獎”評委會
唐曉渡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推動朦朧詩潮的核心成員之一,在其后的主要詩運浪潮中從未缺場,努力影響中國當代詩歌走向……他的詩評因此透放著多元的精神品質,其充滿詩性哲學的思辨被硬朗堅執的痛苦張力所浸透……唐曉渡已成為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詩評家之一。
——第二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評委會
張煒:為什么是“詩人作家”[1]
文/ 唐曉渡
雖說很早就讀了張煒的《古船》,但直到2000年我倆才第一次見面。這里有一個小故事,我對煒兄本人甚至都沒有說過。那年秋天我受邀去法國里爾參加第一屆世界公民大會,問了邀請方,知道張煒將與我同行,且文學界的受邀者只有我倆,不免心中忐忑。因為1995還是96年煒兄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詩人,你為什么不憤怒》,發表后被廣泛征引。我對此一現象頗不以為然,于是1997年寫《九十年代先鋒詩的若干問題》時,就在反對“現實在握”的上下文中趁便對此做了針砭。在我看來,問題不在于詩人該不該憤怒,該不該“拷打良心的玉米”,而在于為什么似乎只有詩人才需要憤怒,才需要“拷打良心的玉米”?為什么沒有人向那些幾乎無須“拷打”就能發現大大的“良心”問題的領域,比如新聞領域,或者進一步,就造成社會性“良心危機”的根本所在提出同樣的要求?更讓我不忿兒的,是許多人在責難詩人時那種不屑的,甚至揚揚自得的口氣或神色,仿佛他們可以自外于良心,仿佛他們就是一再請求“拷打”,卻被一再延誤的“良心的玉米”本身。這番話連諷刺帶挖苦,雖不是針對煒兄本人,卻也免不了連帶的嫌疑,擔心他看到或聽說過受不了,所以忐忑。結果在候機樓門口見到,張煒一個笑容就把我的擔心全部化解了。那是某種心意相通、“一潭清水”式的笑容,非常寬厚非常誠懇的笑容。那一刻我突然醒悟到,張煒所謂“詩人你為什么不憤怒”,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自問,而不是對詩人的指責。我們之間已無須就此再多說一個字了。
更令我難以忘懷的,是那天到了巴黎以后,凌晨快兩點了。煒兄忽然給我房間打電話,說讀了我在飛機上給他的一篇又臭又長的訪談,想好好聊一聊,問能否現在就過來。我自是立馬應下,同時深深感動于他的激情:類似的激情20世紀80年代我也曾有過,但十幾年下來,好像早就耗得差不多了,而在他身上居然還完整地保留著!那次我們都聊了些什么,聊了多久,現在已全然記不得了,但煒兄冷靜外表下如火的激情,卻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不必說,這種持恒的激情,是一個詩人才會有的激情;而其后不久讀到的《九月寓言》更使我確信,無論張煒的小說成就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他本質上都首先是一位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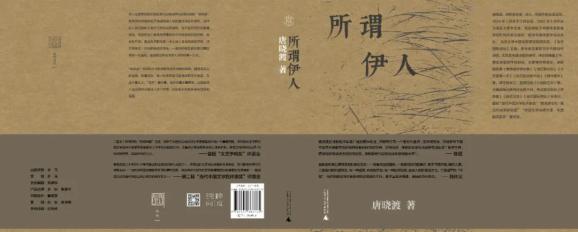
《所謂伊人》書籍設計展開圖
由此,前些年在一篇談張煒散文的短論中涉及他的“身份”時,我不得不“發明”了一個復合詞,叫“詩人作家”。一個朋友看到后頗不以為然,說你既已明言此一說法參照了昆德拉有關作家和小說家的區分,而在昆德拉看來,所謂“作家”,除了有其獨到的思想和一種無法仿效的聲音外,還有一個特征,就是可以運用任何文體形式寫作,其中當然也包括詩歌;那么,還有什么必要疊床架屋,再在前面加一個“詩人”呢?又說,張煒在小說和散文界早已聲名蓋世,就不必非當全能冠軍了吧。當然,后面那句更多只是個玩笑,但還是揭露并自我反駁了前面那句中暗藏的小心眼兒。因為我所謂“詩人作家”非關成就,只關乎某種寫作性質和語言狀態;就構詞法而言,則既非偏正結構亦非并列結構,而是在復合中使“詩人”和“作家”相擁相濟,要在突出張煒的寫作,乃是一種出自心靈、為了心靈并創造心靈的一體化“詩性寫作”。這樣的寫作超然于一切有關寫作者的身份界定之上,并使所有拘泥于文體特質的辨析統統淪為第二義。
當然,同樣基于昆德拉的區分,說張煒是個“詩人小說家”也未嘗不可,但我總覺得有所欠缺。欠就欠在一體化的特征不夠突出。考慮到傳統和接受的因素,在中國當代語境中,一個小說家往往更多意味著一個能把故事講得精彩紛呈的人,他的思想——如果他有思想的話——就溶解、隱藏在他的故事及其講故事的方式中;而對一個作家來說,僅僅會講故事還遠遠不夠,他更多致力的,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通過叩問人性和人的命運,勘探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生存、文化和精神地圖。從《古船》開始,三十多年來張煒在小說中一直在做這件事,最能體現他在這方面成果的,不必說是十卷本的巨著《你在高原》。他的散文同樣屬于這規模巨大而又持續深入的勘探的一部分,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在例如《我跋涉的莽野》《世界和你的角落》,尤其是《游走:從少年到青年》等集子中對個人心路歷程和精神地圖的自我勘探,包括他對膠東和古齊國地域文化系統而廣泛的發掘。那是他的根脈所系,是他自我辨識和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小說家也涉筆散文,可更多只是將其作為處理故事邊角料的一種方式,但對張煒卻不能作如是觀。他的散文從一開始就不是他小說的副產品,倒不如說二者相輔相成,構成了同一場壯闊的精神漫游。他在散文上所花費的心血,所表現出的精湛技藝,所取得的成就,較之他的小說一點也不稍遜,甚至可以說,從中能更分明地聽出他那“無可仿效的聲音”。那是他個人的聲音,一種融合了他所堅持的社會正義而又更富彈性和張力,更能體現其“美學正義”的聲音,其鮮明的節奏、多變的調性和波涌的旋律感,正與其澄澈深邃的思致運行、結實柔韌的語言織體互為表里。雖豐富程度或不如他的小說,但其靈動,其純粹,毋寧說更勝一籌。
我與沉默的橡樹
作者:張煒 著
出版社:山東畫報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19-05
不過,更能突顯這一特質的,要我說還是他的詩。必須承認,盡管早就注意到張煒小說和散文在語言上顯著的詩性特征。盡管《你在高原》任何意義上都當得起“史詩”的稱譽,但若不是煒兄近年來寫詩的熱情大熾,我大概也想不到對他使用“詩人作家”這一指稱。前幾年出版的《家在萬松浦》就不說了,這里只說剛出的《我與沉默的橡樹》。看看每首詩末簽署的日期吧,其中絕大多數作品,包括兩首小長詩,都寫于短短的一個半月之內。我知道張煒的寫作生涯始于詩歌,其實許多作家、小說家也都是這樣;問題在于,寫了這么多年小說散文,且取得了如此卓越,如此有說服力的成就以后,為什么又回過頭來寫詩,并且是以如此的規模和密度?轉移陣地,謀求什么“全能冠軍”肯定不會是張煒的思路,那他這么做的道理又在哪里?他本人曾說過所有文體中寫詩最難,依此邏輯,就是要嘗試再次攻堅克難啰。這樣看,倒是和今天這個會的主題“精神高原”若合符契,因為“高原”不僅意味著高度,更重要的是意味著登攀,而張煒一直在登攀。不過,這里的“精神高原”應該還有一重意涵,即“精神家園”,否則令人感到“高處不勝寒”,就又不是張煒了。對應“高原”的關鍵詞是“高度”和“登攀”,對應“家園”的關鍵詞則是“漫游”和“尋找”,張煒同時呈現了這兩種精神向度,兩種話語姿態。如果說可以據此貫通張煒的全部作品,那么,透過他在詩中發出的那更加個人化、更無可仿效的聲音,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辨認出前面所說的那種“美學正義”,而且可以發現某種被濃縮了的“精神圖式”。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詩集開篇的同題小長詩《我與沉默的橡樹》。毫不奇怪,這首詩的第一章就是“尋找”;以下次第為草頂泥屋、這一餐、思念、辟谷、墾與播、落葉和花,等等,計十四章。孤立地看,它們只是一個個日常生活的具體場景和特定感悟,但只要把它們串起來,讓它們動起來,就成了同一精神世界中不同節點和要素的隱喻,就能據其切換,大致勾勒出內在于張煒全部作品的抽象圖譜。這首詩的最后一章是“五個兄弟”,初讀時有點納悶:為什么僅僅、必須是五個呢?直到抬右手扶額才恍有所悟:對堅持手寫的張煒來說,這可不是他登攀/漫游中最親密、最可信賴的五兄弟嗎?如此收束也格外強化了這首長詩的“元寫作”性質:五棵蓬勃挺拔的橡樹,在這里不僅對應著五根手指,還象征著一個扎根大地,沐浴天風,與萬物彼此吐納往還的生機無限的精神世界。

“1973-2021:詩之約——張煒《不踐約書》新書分享會”現場
相信所有朋友都已注意到,鄉村情境、自然意象,尤其是植物意象,在張煒的作品中占有特別大的比重(這本詩集中甚至包括了一首中等長度的《半島草木篇》),以致有人懷疑這是否表明他過于留戀正在消逝的農業文明?甚至引申懷疑他的批判立場中是否有太多道德主義的成分?我完全不能同意此類把問題簡單化的觀點,其根據首先不是來自什么更高深或更體恤的理論,而是我第一時間的閱讀感受。那是一種靈魂受洗、“澡雪精神”的感受,讀他的詩更是如此。幾年前讀到《家在萬松浦》時,我曾長時間驚訝于其風格的潔凈;反復品味后我意識到,這潔凈其實更多源于詩中那無所不在的寂靜。在這種近乎無語自在的寂靜中,一棵草籽在地下悄然萌動,一朵野花在溪邊獨自怒放,一只松鼠躊躇著從樹端滑下,而你的心也在不覺中變得曠遠。那一刻我腦海里油然浮起一個略顯激憤的聲音,他在追問,追問勒內·夏爾之后,戰后歐洲還有哪一位詩人能讓人們聽到蟲鳴的聲音、莊稼拔節的聲音,總之大自然的聲音。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領會到“自然”的不可或缺,領會到相對于寫作,所謂“自然”不只專指某一領域或某類題材,同樣不只專指某種清純的情懷;更重要的,是指人與萬物在筆下同在,并依循各自本性,在種種有意無意的沖突、壓抑、遮蔽中生生不息,那樣一種對稱于世界本相的精神生態。對真正的寫作來說,揭示這樣的生態乃是分內之事,換句話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盡管遠非所有的寫作者都能做到,盡管達至此一境界有多種方式和途徑,然而,忽略以至無視此一根本,卻肯定算得上一個寫作者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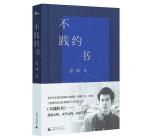
不踐約書
作者:張煒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1-01
立足這樣的根本看過去,張煒作品中最易受人攻訐之處,也正是他最無可替代的價值所在;某種自在的寂靜穩居核心,是其“精神圖式”中最柔弱,也是最有力、最富生長性的部分。就個人趣味而言,我其實更喜歡像莎士比亞那種不避俚俗、矛盾糾結、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作品;與此相平行的,則是對一切疑似精神潔癖的本能反感和警惕,生怕它們妨礙、遮蔽了自己對當代復雜詩意的發現。我不能說張煒的作品從未令我產生這方面的困擾;奇怪的是,疑惑的浮云從來不能久駐,我總能很快在仿佛被催眠般喚起的潔凈中安頓好身心。這是在贊美他語言的強度和魅力嗎?當然,但同時也在贊美他彌漫其中的生命能量。要形成如此豐沛的能量,再杰出的才華、再豐富的閱歷也不夠,還必須有賴思想的深長。“一個除了沉思一無所有的人/菜葉是靈苗,是生命的原形”——張煒的這兩行詩,于此恰好可以視為他的自況。某種程度上,正是對存在深長的本真之思、原初之思,持續從內部塑造著集智士、勇士與修士于一身的張煒,并源源不斷地為他的作品注入清靈素凈的活力。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這樣的“思”本身就是“詩”。就此而言,與其說張煒的詩是他作品的一部分,不如說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一直在書寫,并將繼續書寫下去的大詩的一部分——詩既是他開始其精神勘探的原點,為什么就不能成為其歸宿之所呢?
鐵與綢
作者:張煒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2-02
注釋:
[1]本文根據2019年5月在北京師范大學“張煒和他的精神高原”研討會上的發言錄音改寫而成。
延伸閱讀
詩歌和風水(代后記)
文/ 唐曉渡
在去年舉辦的“越界語言:詩/ 行為藝術的現場”對話交流活動中,日本當代著名詩人吉增剛造使用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來隱喻詩和詩人,以及詩與當今社會的關系。他說詩之于他猶如雙手捧著的一滴水,一不小心就會傾覆或蒸發,因此必須倍加呵護和珍惜。
由此想到希臘當代詩人埃利蒂斯使用過的另一個有關詩的隱喻。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辭中他把詩比作詩人掌中的太陽。在他看來,“手捧著太陽而又不致被其灼傷”,是詩人的智慧。
又想到愛爾蘭當代詩人希尼。他有一首詩同樣可以視為詩和詩人的隱喻,并且同樣與水有關。我說的是《卜水者》。那個手持V形樹杈、在遼闊的大地上到處叩問水源的“卜水者”形象,顯然也是希尼心目中的詩人形象。
又想到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想到他那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著名詩句“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們歌唱”……
金。木。水。火。土。所有這些都是元素性的意象,或指向海子所謂“詩的元素”。吉增先生或許正是有基于此,而進一步提出了“詩和風水的關系”這一命題。這一命題看起來有點“玄”,遠不如“詩歌在商業化社會中的生存和走向”這樣的命題(這本是那天對話的主題)來得直切,但在我看來更有趣。不僅更有趣,也更能觸及詩的真義。事實上,每一個在今天還堅持寫作的詩人,都不可能不考慮詩的“風水”問題,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詩歌堪輿學”。
當我們說20世紀80年代是“詩的黃金時代”時,我們同時也在指斥當下的詩歌風水不好。二者或許都是實情,但如此看待詩和風水的關系是太狹隘、太外在了。沒有誰會事先為詩備下一塊“風水寶地”;反過來,只要堅持并善于發現,再貧瘠的土地也未必不能成為這樣的“寶地”。無論詩與社會(“商業化”只是其特殊形態)的關系有多么格格不入,無論其社會地位“邊緣化”到什么程度,都不應妨礙我們領略發現本身的快樂,不應妨礙我們學習詩的發現所據以的智慧。這種智慧肯定不會教導我們憤世嫉俗,而會教導我們把所有的“不”理解為“是”,教導我們始終敞向眼底心中涌流的好景致,教導我們平心靜氣,安之若素;不必忍耐,但要等待。
《所謂伊人》封面平面圖
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可以說詩人是人類生活,尤其是精神和情感生活的“風水先生”。他不斷勘明并指出我們在這方面的缺失,試圖重建被種種或來自強制,或來自成見的力量所毀損、扭曲和遮蔽了的個人和世界間,包括其自我內部的“元素性”關聯,以調節和維護生命本身的“自然生態”。然而,這只是我所謂“詩歌堪輿學”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近乎一個悖論。我們都知道一個醫生往往診治不了自己的病,那么,一個詩人怎樣才能當好自己的“風水先生”呢?
寫《卜水者》的希尼同時也寫過一首《挖掘》。在那首詩中,詩人被引喻為一個挖掘者。這一形象和卜水者的形象看上去有點沖突,其實正好相輔相成。它當然表征了寫作的勞動內涵,但更重要的是其“深”的維度。如果說“卜水者”致力于在貌似沒有水的地方發現水的話,那么“挖掘者”就致力于讓我們在當下即刻品嘗到源頭活水。“鐵锨鋒利的切痕/ 穿透生命之根覺醒著我的意識”——正是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詩歌把自身呈現為生命中的一片好風水,并照亮我們被“商業化”的粗糲物質外殼和五顏六色的泡沫所禁錮,但永不會泯滅的內在渴意。
2004年春,天通西苑
(本文選自《所謂伊人》,唐曉渡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出版,2023年11月)
所謂伊人
作者:唐曉渡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純粹Pura
出版時間:2023-11
《所謂伊人》是著名詩歌批評家、詩人唐曉渡的一部隨筆散文集。主要涉筆作者長期關注且交誼深厚的眾多國內前輩及同代詩人,如楊煉、憶明珠、昌耀、北島等等,也記錄了與作者有重要精神關聯的國外詩人、翻譯家和漢學家以及一批當代小說家及其作品。記述了作者對自20世紀80年代初親歷的當代詩壇的風云變化的觀察、思考和感悟。唐曉渡置身當代中國詩歌變革和發展的前沿,既是參與者,也是記錄者,讓讀者從第一視角感受當代詩壇的風云變化,對當代漢語詩歌的發展歷程有更深的了解和思考。
唐曉渡,詩歌批評家、詩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54 年1月生于江蘇儀征,1982 年1月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供職于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作家出版社,現為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研究員、《當代國際詩壇》主編。多年來主要致力于中國當代詩歌,尤其是先鋒詩歌的研究、評論和編纂工作,兼及詩歌創作和翻譯。主要著作有詩論、詩歌隨筆集《唐曉渡詩學論集》《與沉默對刺》《今天是每一天》《先行到失敗中去》《鏡內鏡外》等,譯作有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等,主編或編選各種詩選數十種。先后參與創辦《幸存者》《現代漢詩》《當代國際詩壇》等詩刊。曾獲“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教育部名欄·現 當代詩學研究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批評家獎”等獎項。
張煒,當代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棲霞市人。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2020年出版《張煒文集》50 卷。作品譯為英、日、法、韓、德、塞、西、瑞典、俄、阿、土、羅、意、越、波等數十種文字。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書》《你在高原》《獨藥師》《艾約堡秘史》等21部;詩學專著《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楚辭〉筆記》《讀〈詩經〉》《蘇東坡七講》《唐代五詩人》等多部。作品獲優秀長篇小說獎、“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茅盾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南方傳媒杰出作家獎、京東文學獎等。近作《尋找魚王》《獨藥師》《艾約堡秘史》等書獲多種獎項。新作《我的原野盛宴》反響熱烈,《不踐約書》獲第六屆長詩獎·特別獎。
原標題:《唐曉渡:無論張煒的小說成就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他本質上都首先是一位詩人 | 純粹新書》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