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 +190
對談|王笛×張明揚×李磊:不要把陌生人社會極致化
【編者按】
本文為2023年上海書展期間“歷史寫作的現實思考——王笛《歷史的微聲》《那間街角的茶鋪》分享會”的錄音整理稿。澎湃新聞經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刊發。

對談現場
李磊:各位讀者大家晚上好!歡迎來到思南文學之家,今天晚上這場活動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主題是:歷史寫作的現實思考——王笛《歷史的微聲》《那間街角的茶鋪》分享會。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李磊,王笛老師在我們出版社有一個作品系列,是我來做責任編輯。王笛老師是澳門大學講席教授,張明揚老師是歷史作家。今天晚上主要由兩位老師,就現在比較熱的公共史學和非虛構歷史寫作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是公共史學?
李磊:公共史學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公共史學這個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請王笛老師。
王笛:謝謝李老師,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安排這個活動。在我進入學術領域早期,即1980年代,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公共史學這個概念,我注意到公眾史學/公共史學,是我到美國留學以后。美國非虛構的寫作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流行起來,很多記者、文學家、獨立作家都在寫非常有趣的歷史書,當然也有一些專業歷史學家。為大眾閱讀服務的歷史寫作,根據我的觀察,就是公共史學。不像寫學術論文有一定的格式,先要有導言、第一章、第二章……層層的遞進,最后是結論。而且必須在導言說主要觀點,想論證什么問題,到結束以后,通過這個研究得出什么結論,第一點、第二點,等等。但是公共史學沒有受這些格式的影響,而是更接近文學的表達。像寫小說,但是有據可查,把錯綜復雜的歷史資料交織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敘事,不像學術那么呆板。像巴巴拉·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一個月的故事,錯綜復雜的故事,無論是政治、外交、軍事、人物的塑造都是通過文學式的描述,《八月炮火》得了普利策獎。她寫作的時候要查檔案、實地考察,做很多口述,在資料上花的功夫并不比做嚴肅的歷史研究少,但是更多的是考慮怎樣把這些資料建構,怎么把故事陳述出來,怎樣把故事寫得有趣,讓一般的讀者能夠讀下去,感興趣,而且得到啟發。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是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但是她的歷史寫作也是非常精彩的。寫巴黎和會,一般會枯燥無味,但是她的《締造和平》,把巴黎和會各國之間的矛盾斗爭,通過故事、細節,讀起來引人入勝。例如,她描寫簽訂合約那天,中國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不公平的合約。她專門描寫了在談判桌邊有兩張椅子是空著的,那是中國代表團的席位,實際上這是無聲的抗議。我們過去寫歷史不會注重這些細節,我們都是講大問題。而把文學和歷史結合起來的寫作,不僅僅是注意世界舞臺上的縱橫博弈,同時也要有細節的描述,要有人物的塑造,這樣才能讓讀者讀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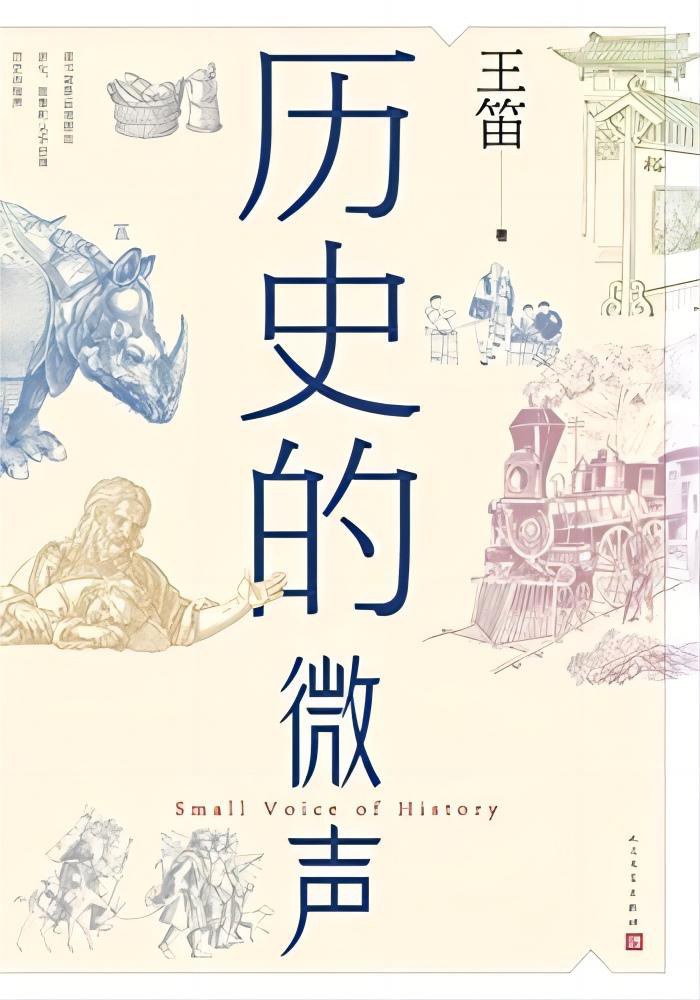
《歷史的微聲》
李磊:好的公共史學,可以起到啟迪公眾的作用,例如王笛老師的《歷史的微聲》《那間街角的茶鋪》《袍哥》等書。明揚老師之前說應該復興公共史學的敘事傳統。王老師講得非常詳細,明揚老師可以補充公共史學的概念,可以就你閱讀王笛老師的作品或者你自己的作品闡述公共史學的表現。
張明揚:王老師是站在歷史學家的角度來說,剛才也提到在美國很多記者寫非虛構歷史,我也是一個記者出身,就從記者的角度來說吧。王老師剛才提到了《八月炮火》,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在我看來,可能是最優秀的一本非虛構歷史寫作,是符合我們對非虛構所有想象的一本書,資料收集能力,采訪能力,細節描述,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塔奇曼一下筆就充滿了時代感,仿佛身臨其境,讓人產生情緒上的勾連共情。
中國近十幾年來公共史學、非虛構歷史寫作的熱潮,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就來自于西方作品,這些年引進了這么多一流的西方非虛構歷史,讓我們中國讀者包括寫作者知道原來歷史可以這么寫,這么好看,并且是符合學術規范上的好看。
是否符合基本的學術規范,這是公共史學和廣義上通俗寫史的區別。我們以前寫故事,寫歷史故事,二十年前中國就有了,他們很多以搞笑為主,資料引用得很不嚴謹,不是嚴肅得歷史寫作。公共是它的寫法,但是還是必須符合歷史學的基礎標準,比如要有引證,說任何事情需要有出處。歷史如果有空白的地方,可以合理地推理,合理地延伸,也就是李開元先生說的所謂歷史偵探。但歷史上有定論的東西一定不能任意發揮,這就不是公共史學和非虛構歷史了,那是歷史小說。
歷史學也好,歷史學家也好,是否承擔啟蒙公眾的社會責任,這可能有爭議。我傾向于認為這是歷史學的責任之一。好的非虛構歷史寫作或者公共史學,可以把學術界的新想法、新觀點,用一些相對通俗的方式準確地傳遞給大眾,這也是幫歷史學承擔基礎的社會責任。
我看王笛老師幾本書里,就能傳遞某種歷史觀,歷史學要不要關注普通人物?除了王侯將相之外要不要關注普通人,歷史敘述中底層視角重不重要,這些都是歷史學的基礎功能,告訴我們歷史學干什么。通過這樣的寫作,告訴公眾,真實歷史是怎樣的。歷史觀是很重要的詞。這些年,公共討論里很多人喜歡大談國際問題,宏大敘事,動不動就熱淚盈眶,但是對身邊的事情和身邊的人缺乏關注,缺乏關心,缺乏情感。如果多讀王笛老師的書,這方面是能得到啟發的。學習歷史、閱讀歷史寫作的時候不能僅僅是帝王視角、宏大敘事,觀察世界也是如此。
李磊:那么,公共史學寫作的難點,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呢?
王笛:公共史學寫作的難點,主要還是如何解決歷史資料與文字表達的矛盾。因為一方面宣稱是史學,那么一定要有史料的根據,一定要根據歷史的記載來進行寫作和故事講述;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僅僅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傳統寫作,就會顯得枯燥無味,就會羅列資料。那么,就需要我們的寫作者仔細考慮怎樣進行表達,包括語言,組織結構,故事講述方式,等等。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并不是容易的,有時候需要反復的斟酌和試驗,要吸取文學家的一些表達手法,要引人入勝。結合傳統歷史學像司馬遷的文學性,讓歷史表達和文學表達相得益彰。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公共史學雖然是面向大眾的,但是也不能太迎合大眾。寫作者必須思考他的寫作所要達到的目的,要向讀者傳達怎樣的信息,而不是什么好看就寫什么,而是覺得什么能給我們的讀者以啟發與思考,那么這些東西就是值得寫的。
張明揚:有兩點。其一是學術規范。公共史學寫作當然沒有學術寫作那么多清規戒律,但也要遵守基本的規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信口開河,寫什么都要有史學依據。而很多人在進行通俗歷史寫作時,為了讓行文更有趣,往往喜歡生造人物的心理活動,隨意發揮,這些都是必須要克服的危險沖動。
其二是公共性。公共史學寫作也好,非虛構歷史寫作也好,除了歷史本身之外,自然也要遵循一些公共寫作的基本規律,比如流暢性,比如要有必要的情感投射,比如要有人物的故事,這些都必須得到寫作者的尊重。在這一點上,不可有學術寫作的沙文主義傾向,還是那句話,要對陌生的領域保持開放性,保持好奇心。
人與人之間怎么連接?
李磊:剛才,明揚老師說要對身邊的人關注、關心、有情感。王笛老師的《那間街角的茶鋪》,主要寫1950年之前50年成都的市民生活,寫到很多成都市民、鄰居之間的交往故事。我特別想請兩位老師聊一聊,在由陌生人組成的城市里,人與人之間怎么連接?
王笛:在現代社會,人們的居住模式發生了變化。過去,北京是四合院,上海是石庫門,成都有大雜院,鄰里之間不可避免愿不愿意都會有很多交往。我在《那間街角的茶鋪》中間寫到,你跨出屋門就會和鄰居發生關系。街上是各種小販,大家坐在門口,做日常的事務,坐在那里乘涼、看街景。但是隨著現代化,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城市的重建,絕大多數的居民開始搬進公寓樓。一旦進入公寓樓就是獨立的空間,你在同一層的鄰居,有時候幾乎都沒有來往,人與人之間就變得陌生。過去,炒菜沒有鹽,你可以去鄰居家借點鹽、油,這是非常自然的,現在完全不可能發生這種關系。
我們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模式,幾乎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是社會學的研究。關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所研究的時代,《那間街角的茶鋪》是1950年之前,傳統的交往模式。傳統的交往模式是人們坐在街頭兩邊,人們到街上去,到市場,去橋頭,去茶館,待在那里喝茶聊天。哪怕我們是陌生人,我們不是鄰居,我們不認識,但是可以坐在那里和陌生人進行聊天。這種傳統,從相當程度上保留到了今天,如人民公園鶴鳴茶社。人們可以非常放松,你可以很自然地加入談話,別人不覺得奇怪,也不覺得突兀。人與人之間,大家的距離就是一張茶桌,這個茶桌把大家聯系在一起。這種生活方式,這種社會的交往,在過去長時間的日常生活中間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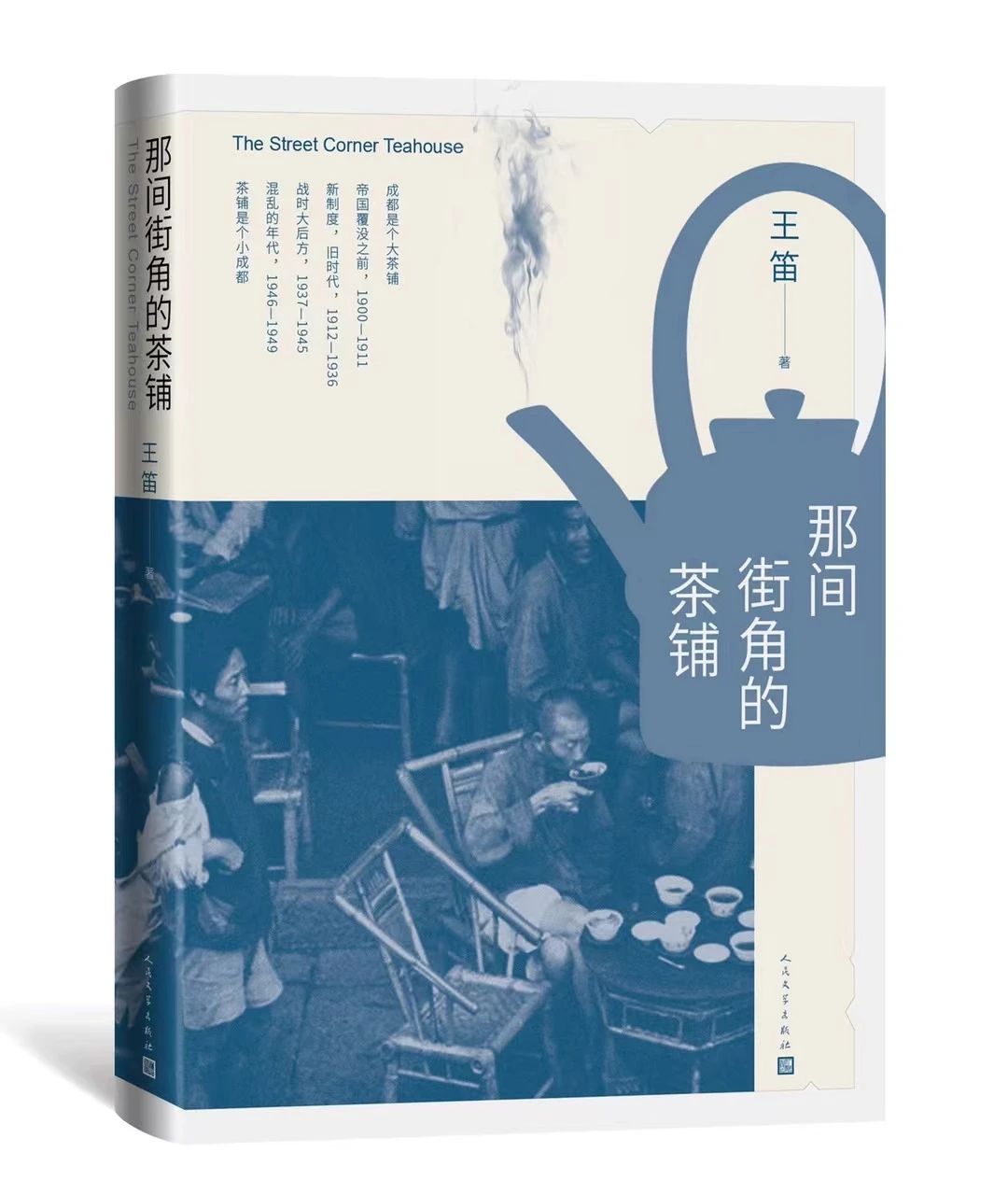
《那間街角的茶鋪》
張明揚:我們現在很喜歡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是從鄉村的熟人社會過渡到現代的陌生人社會”這是進步。大體上我同意,但是中國人理解會有點偏頗化,把陌生人社會極致成原子社會。人和人之間要有非常強烈的邊界感,你不跟我說話,我也不能跟你說話。人和人之間,我要強調獨處,強調個人價值,這些西方都沒有問題,但是中國人極致化了。西方雖然是陌生人社會,但是有很多其他補充,比如有社區活動、社區組織,有公共沙龍,還有很多派對,他們在對陌生人社會的弊病進行補充。中國人已經看到陌生人社會的小小補充,比如鄰近感。上海疫情,大家發現每個人是原子,碰到某些大災難的時候,人都會覺得孤立無援。這時候通過鄰居,通過微信群,重新建立聯系。中國現在也在反思,不能把陌生人社會極致化,我們特別需要公共生活,不能把陌生人社會理解成沒有公共生活,沒有讀書會,沒有讀書沙龍。我們中國人有時候會發現,到國外開一個派對,陌生人之間聊得很愉快,中國人反而落寞。很多人會說,個人價值,是西方來的。偏偏你們到了西方,西方人聊的開心的時候為什么你反而被邊緣化了,說明你把西方的有些東西給誤解了,包括西方的社區組織。西方人說有一個強大社會,我們中國人說強政府小社會,政府的責任,但是也有我們個人的責任,我們個人把社會把陌生人社會誤解得極致化了。在日本居酒屋,陌生人聊天很正常,《深夜食堂》就有這方面的表現。中國就覺得你是騷擾我。在日本居酒屋,有點像茶館,它是坐在一起的,大家可以聊天的,甚至會認為看到居酒屋日本人這樣聊天是很美的東西。為什么落實到中國社會,就覺得陌生人聊天好沒有邊界感?我們把西方來的東西誤解,極致化,把陌生人社會理解成原子社會。如果一個社會變成原子社會挺可怕的。我們需要茶館,哪怕茶館這個介質不存在了,但是需要它代替公共生活,這是不可缺少的。
王笛:現在由于互聯網的使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確實拉大了。過去我們想要消磨時間,要社交,我們必須到公共空間,到酒吧,或者到茶館,或者是到咖啡館。在互聯網時代,你可以在家和陌生人、和世界上任何角落的陌生人交流。你可以不知道他的性別、年齡、教育背景,你們可以聊任何問題,可以敞開聊,跟你家里人或者好朋友不聊的事情,也可以在網上盡情地聊。另外,獨處變得非常容易。過去獨處會覺得很難,但是有了互聯網,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人與人的溝通形式被改變了。
過去我們要人與人之間溝通必須到公共空間,是雙向交流;但是大眾媒體興起以后,包括報紙、收音機、電視,這些都是單向交流,你是接收者,你不能跟輸出者直接地進行對話;但是網絡興起,又變成雙向交流,你可以在與世隔絕的家里,和任何人不管是對話,還是思想的交流。
現在就面臨這樣的問題,加上三年疫情封控,三年時間是非常長的時間。特別是小孩長大以后,在這三年中間缺乏人際交往,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有了社恐,他寧愿和手機進行對話,情愿通過網絡進行交流,而不是面對面通過語言。甚至在大學生中間也能看得到社恐。現在怎樣讓人走出封閉的世界,所謂封閉的世界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小天地,怎樣走出去發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立怎樣的公共空間。這種公共空間吸引人們走出自己的小天地里,融入到大天地,和人與人發生聯系。這是社會管理者、教育機構、家長、老師需要共同關注的問題。
書寫小人物和普通人
李磊:王笛老師《那間街角的茶鋪》,寫到成都市民也包括成都郊區的人,他們的生活無論是語言還是行為都新鮮活潑。《歷史的微聲》則是您對民眾史觀的闡述。您多次說,日常才是最重要的,日常生活才是最值得珍視的,民眾的創造力產生了中華文明。您這么多年堅持寫小人物和普通人,能從您的這一史學觀的形成源起,給我們做一下分享嗎?
王笛:關于為什么要寫小人物和普通人?過去我主要強調的是要寫出一個平衡的歷史,就是說帝王、精英只是歷史的一個部分,而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不應該被歷史忽略。而現在我更多的是強調在歷史中寫小人物,還有一個歷史的接受問題,就是說長期以來民眾受到過去歷史寫作的影響,認為自己人微言輕,這個對自己的認知,自我的尊嚴,社會的責任,等等,都有消極的影響。因此我想寫小人物,可以讓民眾去認識到自己的價值,有自信,知道在人格上自己不比任何人更少,做一個自由的人,獨立思考的人,能夠挺身而出反抗不公的人,而不是被馴服的唯唯諾諾的人。
李磊:明揚老師,《棄長安》中,有一段,你寫到一個小人物,但是沒有展開。不在關注范圍還是缺乏記載呢?你覺得,寫小人物的難點在哪里呢?
張明揚:小人物當然值得展開,很多時候是資料不夠。我覺得,非虛構寫作恰恰比傳統歷史敘事更應該強調配角的概念,有意識地去寫最佳配角。其實這也是電影和小說的通常做法,只有主角沒有配角的文藝作品就不成立啊,這就是為什么說非虛構寫作需要吸收其他藝術形式的方法。
我在寫《棄長安》的時候,當然也會面臨小人物特別是普通民眾資料缺乏的問題。我們對安史之亂普通民眾慘狀的了解主要來自杜甫的詩,比如“三吏三別”,詩是可以入史的,這個要盡量的用;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與皇帝寵妃宰相他們相比,詩人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普通人,至少是精英階層中的普通人,那是不是可以通過多關注詩人的個人命運來折射當時普通人的命運呢?我覺得是可以的。有很多讀者就問我,詩人真的那么重要么,你為什么要在《棄長安》中寫那么多詩人?坦白說,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讓詩人來稍稍彌補對安史之亂中普通人的失語與“不在場”,詩人固然是精英,但他們也不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他們在戰亂中的顛沛流離與小人物并無二致。你或許還可以這么想,連詩人都這么命運跌宕了,何況戰亂中的真正小人物呢?
王笛老師書里提到過,中國史學傳統上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想寫小人物資料就特別少,只能上窮碧落下黃泉,想盡辦法找。我寫《入關》的時候,遼東當地老百姓究竟是怎么民不聊生的,有很多面上的記載,但具體到人就付之闕如,所幸,還是可以找到一些當地人造反的資料,對于古代的普通人而言,往往只有造了反才有資格進入歷史。
以詩證史
李磊:陳寅恪《柳如是別傳》,是以詩證史。《那間街角的茶鋪》引用了成都的民謠、竹枝詞。《棄長安》,引用了李白、杜甫等人的詩歌。歷史寫作使用詩歌,如何做到補充資料的不足,又防止文學創造的主觀性?
王笛:當歷史研究缺乏細節的時候,缺乏心理狀態的描寫的時候,詩歌可能可以提供一種有用的補充。當然,如果歷史資料有比較完整的記錄是最理想的,但是往往我們進入到微觀歷史,進入到日常生活,研究普通人,需要歷史細節的時候,資料幾乎都是找不到的,這樣詩歌給我們提供了一種選擇。我20年前發表過一篇英文論文,使用的基本資料便是竹枝詞,描寫19世紀成都城市的日常生活。在我的成都街頭文化和茶館的研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竹枝詞。這是由于歷史資料的缺乏,而竹枝詞提供了豐富而且真實的描述。竹枝詞不像一般的詩歌,它的描述是非常直觀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歷史的記錄。當然我們應該意識到詩歌是人的創作,但是如果詩歌是我們所描寫的那個時代的人所寫的,那么可以視為是對那個時代的反應,可以當做歷史資料來使用的。
張明揚:我在《棄長安》里寫到很多詩人,一方面是以上提到的,是一種對小人物命運的“平替”,把他們當作安史之亂的普通人來寫;另一方面,就是以詩證史了。
在某種意義上,詩比正史更能體現時代風貌,尤其是具體到個人,對時代變遷的細膩感受,這種感受是一手史料。比如,李白和杜甫的人生際遇,在盛世驟然轉換至亂世中的不知所措與茫然,都可以在各自的詩中看到。
讀書和教育
李磊:《歷史的微聲》,我最喜歡的是,書里面寫了很多位歷史學家,王笛老師講了偶爾的跟他們的個人交往,介紹了他們的思想,主要是民眾史觀方面的,這對于我寫高密非虛構很有啟發。請問王老師,除了您的老師羅威廉,對您影響最大的歷史學家是誰?
王笛:我是專業研究者,要大量閱讀前輩的研究,《歷史的微聲》是我過去三十多年的一個閱讀史。特別是學術雜志,出了新書會邀請我,不管英文還是中文,對這些書進行評述。在三十多年的時間內積累了很多,這本書是第一次把它總結到一起。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到我的知識儲備,為什么寫《跨出封閉的世界》《街頭文化》《茶館》《袍哥》,我是怎樣思考的,為什么認為這些研究有意義,怎樣把看起來沒有多少歷史意義的小題目變成嚴肅的學術研究,而且相當大的一部分還能寫得超越歷史研究的圈子,甚至大眾也能夠讀得下去。如果要了解我的學術發展脈絡,我得知識儲備,我的研究方法,《歷史的微聲》就是一個最好的途徑。
里面所收的書評,可能一般的讀者讀起來會有一定的困難。為了克服這個障礙,我決定花一定的功夫。第一部分全部是新寫的,我回顧了我從小學一直到現在的閱讀道路,主要是在大學以后的閱讀,以及到美國以后受到中西方學術訓練的大量閱讀。除了專業閱讀,而且對文學、人類學、社會學的書籍都有涉獵。李老師問到底誰對我的影響最大?很難說,因為許多歷史學家都對我發生過影響。
舉個例子,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業界之外并不熟悉,他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我寫《袍哥》的時候首先閱讀他的《土匪》《原始的叛亂》《傳統的發明》等著作。他研究邊緣人群,也寫歐洲的革命,寫時代的變遷,既寫大歷史,也寫小歷史。他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是不一樣的,屬于“新馬”,他堅持批判精神,即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從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的養料。
李磊:《歷史的微聲》主要是講閱讀和思考,明揚老師可以談談對這本書的看法嗎?并請明揚老師,接著王笛老師關于教育的觀點,談談你的認識。
張明揚:《歷史的微聲》最好的一部分是王老師寫他的閱讀史。王老師提到一兩百本書,其中提到的書,我讀了80%左右。買這本書,跟著這個書單走特別棒。王老師還看很多小說,我碰到很多讀書人很喜歡標榜自己不看本專業以外的書,這是一種思想的封閉。讀書要雜,也得有自己的專業,這兩個東西互不沖突。讀書,在專業以外稍微雜一點,也是一種避免自己陷入學術信息繭房的努力。
王老師書里提到非常經典的著作,哪些作者對我有影響?王老師書里提到的作者,大部分對我有影響。還有一本書,您沒有提到,我特別喜歡您的《袍哥》。我個人蠻喜歡看這種題材的,比如就看了不少杜月笙相關的書,我總是覺得,游民社會也好,豪強也好,都是正常社會的一種補充。
至于教育,王老師已經說得非常好了。你讀書本身,就是一種對所謂內卷教育的反抗,你開闊自己的眼界。國內孩子最可悲的是,他們不太讀書,只讀教科書或者只讀老師推薦的東西,連學者都不認為讀雜書是浪費時間,但是有孩子認為讀雜書是浪費時間。教育首先閱讀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強調閱讀為中心,不把閱讀作為教育中心,我們扭轉教育是很大的問題,從多讀書多開闊眼界開始,不要只讀所謂的有用的書,對考試有用的書。現在孩子讀書的風氣下降的蠻厲害的,我個人還是比較憂慮的。
李磊:王老師和明揚老師給年輕人讀書有何建議?
王笛:現在短視頻、短信息的誘惑,讓人很難靜下心讀書,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要抽時間讀書,因為讀書給你全面的知識,比較深入的思考。當然,讀什么書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可以是小說,可以是學術著作,可以是專業的書,隨你喜歡,讀書要喜歡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勉為其難,特別你不是為了工作讀書的話,一定要選你喜歡的,這樣才能真正堅持下去。
張明揚:我特別同意王老師說的興趣導向。我們不要把讀書作為固化強化自我定見的東西,不能讀到特別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東西就是好,凡是讀到跟自己價值觀不一樣的東西就是不好,還是在讀書中不斷地調整突破自己原來的想法,還是保持開放性,在書里接受書對你既有思維的挑戰,然后與它進行博弈。
讀者互動
李磊: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于海教授,也來到了今晚的讀書分享會現場。我們請于老師講幾句。
于海:我到現場是向王老師表達我的敬意,我今天把你的書帶過來了(指《街頭文化》)。我十多年前看你這本書的時候,就覺得你這個歷史學家真的厲害。你做的學問不是一般的歷史學家能做的,我看你是從歷史中看到空間,從空間中看到社會的空間社會學家、空間政治學家、空間文化學家。其實街頭是看不到什么東西的,有幾本經典著作是寫街頭的?最經典的一本是美國人懷特的《街角社會》,但是《街角社會》的重點不是在街角,而是社會。他所創立的參與式觀察成為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我要比較你這本《街頭文化》和《街角社會》。他是社會學家,你是歷史學家,你寫出了一本空間社會學的書。我也寫上海空間,主持了很多上海城市空間的研究,因此深知你研究的重要。本書目錄的第一部分,分別為城市環境、商業空間、日常空間、社會空間、慶典空間等,這是何等自覺的空間意識?常人從街頭看到什么?看到來來往往的人,一閃而過,可能一輩子不再見面。但是你看到了空間里的文化,看到日常空間里的家和鄰居,看到家的結構,你寫茶館,實際是講社會空間。檔案中有茶館,卻并無“社會空間”;街頭有紅白喜事,也無“慶典空間”,你大海撈針,把辛苦淘到的歷史材料還原成一部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而且這一切是通過空間這個棱鏡來透視來分析來組織。不妨設想,如果把《街頭文化》所有歷史史料的來源全部遮蔽,沒有人懷疑這本書是現場田野成就的空間社會學的作品。
讀書不光是閱讀,大家要朗誦。朗誦作品片段,常常是莊重的儀式性活動。當福柯去世時,德勒茲在現場朗誦福柯《性經驗史》的段落,這是從希臘下來的傳統,這是文明和典雅的傳統。我今天愿意做一個朗誦者。我今天所要強調的觀點很簡單,王笛老師不僅會講故事,會用史料,但他更能做的是提出理論、提出概念、提出思想,這才是學者真正的本事。我們不要被王笛老師會用史料,會講故事來淹沒了他更大的本事,即抽象概括。作為學者提煉或者概念化或者理論化。王老師在歷史史料中最敏感的是社會學的敏感和空間學的敏感。社會生活一定是空間化的,而空間里一定是有社會故事的。這個社會故事可以是慶典儀式,可以是家常里短,也可以跟政治有關,跟權力有關。我要朗讀的段落,就是關于社會權力的,書中寫到:
社會的許多領域中政府權威的缺乏,為當地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其活動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茶館講理被人們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個公共場所處理爭端,實際上是在公眾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決者或調解者必須盡量按“公平”行事,否則,民眾的輿論會對調解人的聲譽不利,這也就是“吃講茶”成為社會調解的同義詞的由來。另外,即使調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發生,一般人們在這樣的公共場合還是盡量保持理性,而且萬一斗毆發生,有眾人的勸解,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段落不僅文字非常流暢,而且講出很好的道理,回答了茶館怎么成為調解的地方,怎么可以成為社會權力施展的地方的問題。在茶館這個空間場景中,來茶館不是或不只是簡單喝茶,茶館作為訟案調解的社會空間,當事群眾有了,事理有了,權力關系也有了。
《街頭文化》獲得了美國城市史學會的獎,美國社會學會也應該為它發獎。
讀者:王笛老師您在三十多歲時去了美國,讀了大量英文。許多著作原著看著比較好,翻譯過來,因為一些原因,做了調整甚至刪減。我中文閱讀速度比英文快十倍,我想知道外文書的原汁原味,但直接讀英文,成本太高,有沒有好的建議?您的成功經驗是什么樣的?
王笛:我在美國待了25年,仍然是中文比英語好,中文畢竟是母語。現在好多好的英文書翻譯成中文出版,有的中間人為做了刪改,包括我自己的書如《袍哥》等。不過,好的英文著作翻譯過來的,哪怕做了一些刪改,但是基本內容和思想觀點還是保留下來的,所以不必非讀原著不可。當然,如果是你覺得這本書太重要了,感覺到有些關鍵的地方,特別是你對刪改的地方特別好奇,你可以找到英文版,翻到那一頁進行對比,不必從頭看到尾。絕大多數書刪減的畢竟很少,讀中文版還是節省很多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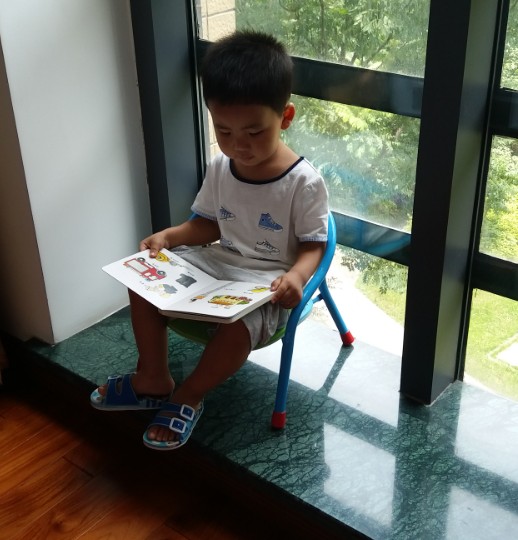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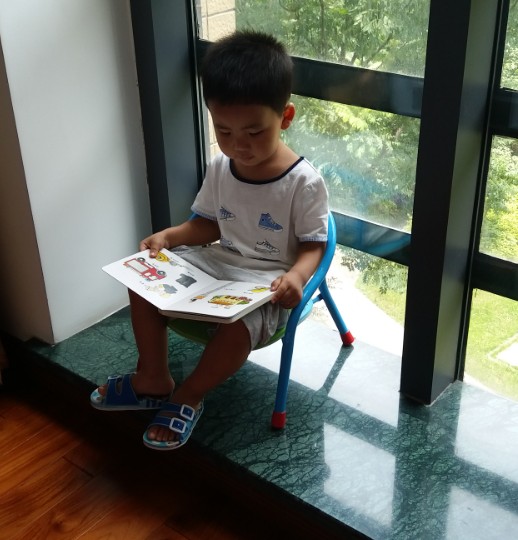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