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一位心理學專業的抑郁癥患者決定進行意義感研究|鏡相
本文由鏡相 X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合作出品,入選高校激勵項目“小行星計劃”。如需轉載,請至“湃客工坊”微信后臺聯系。
采寫 | 劉蕾岑
指導老師 | 莊永志
編輯 | 吳筱慧
編者按:
2023年7月5日晚,歌手李玟因抑郁癥輕生離世的消息令不少人感到痛心。網絡上一片嘩然,大家難以接受像太陽一樣在舞臺上發光、溫暖粉絲的偶像,也有難以消化的憂傷。但其實抑郁癥作為最常見的精神疾病,離我們的距離并不遙遠。據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我國有將近9500萬抑郁癥患者,而50%的抑郁癥患者是學生。抑郁癥患者并不是社會的另類,他們生病的原因、感受以及努力自救的過程值得每個人關注。下文講述的是一位來自985高校心理學專業的抑郁癥患者,曾經的她每天的生活圍繞吃飯睡覺、學習做題、考試排名連軸轉,可考了年級第一之后,她開始問自己: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沒有意義?于是,她將意義感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這是她和抑郁癥斗爭的故事,也是她堅持意義研究、探索人生意義的故事。
2023年2月10日,時隔半年再見沈琪,她的皮膚白了不少,大嗓門笑稱休學后“天天擺爛在家,胖了好幾斤!”
半年間,沈琪因身體原因辭掉了高強度的實習,又發現自己的研究方向“基礎心理學”并不適合找新工作,于是她自學編程,考了教資,“實在不行,就去高中當心理健康老師”。
沒有科研壓力,沈琪自稱現在每天能睡滿8小時,已在逐步減藥。距離復學還剩九個月,雖擔心舊癥復發,她還是準備重拾落灰一年半的心理學文獻,再次面對“意義感”的課題。
2022年3月,南京市部分區域提高疫情風險等級,隨即學校管控徹底擾亂了沈琪的看病日程。
她有抑郁癥,還有鼻炎,治療刻不容緩。4月,為方便治療,她從校內宿舍搬到學校對面的小區。在新租的占地15平米的立方體里,一張雙人床占據了大部分空間,一臺小茶幾,放有調酒用的吧勺和一瓶梅酒。陽臺的晾衣桿上,飄著一對洗凈的白色襯衫。
沈琪是1998年生人,來自冬天被嚴寒和海風夾擊的秦皇島,平常戴副625度的酒瓶底,走路一跳一跳,帶點模特步的范兒。她是Z大2020級心理學系的直博生,畢業論文和研究方向都與困擾她的“意義感”有關。
她曾向導師發誓,2022年11月,一定參加博士中期考核,爭取拿到優秀評級。這需要她高效率地看完75到100篇文獻。
由于經常失眠、乏力,她并沒看幾篇需要正襟危坐、圈點勾畫的學術論文。反倒是抱著Kindle把馮友蘭的《活出人生的意義》、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和日本推理動漫《名偵探柯南》看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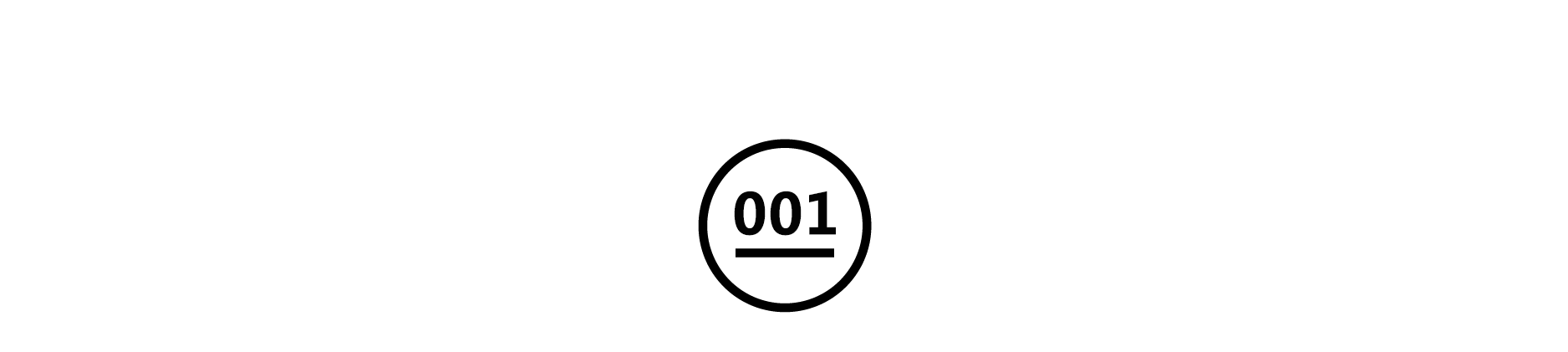
從流水線生產到火山噴發
說起那些讓她感到無意義的階段,沈琪一邊大笑,一邊掰手指頭清算:“初中是枯燥流水線生產,高中是巖漿劇烈涌動,本科是火山連續噴發,直博直接是宇宙大爆炸。”
“流水線生產”期間,為了備戰中考,沈琪每天的生活就是圍繞吃飯睡覺、學習做題、考試排名連軸轉,從早上6點一直到深夜11點。她考了年級第一,同時也發現,自己過去熱衷的游戲變得索然無味。偶爾想笑一笑,不知該開心什么。
那時她還不知道“無意義感”這個詞,也不懂得用心理學術語“快感缺失”(Anhedonia)來描述自己的狀態,更不曾想到這可能是“抑郁癥”的前兆。
巖漿是在衡水第一中學劇烈涌動的。高考作為一種終極意義,被細化成一個個落實到天的小目標,壓力和熱血,冰火兩重天。為給學習騰出時間,身邊的同學省去了睡前換睡衣的環節,直接穿著背面印有“追求卓越”的校服入睡。沈琪身體弱,經常心慌頭疼拉肚子,有時捎上習題冊跑校醫院,喝上兩支葡萄糖,猛吸40分鐘氧,一邊忙不迭地做題。
“這道題首先劃去絕對項,用排除法排除A和D,剩下的再看遍材料,關鍵詞圈一下,這塊勾出來,好的,選C。”機械化的思維套路讓她有些麻木,有時她累得想哭,但比起停下來細想為何要反復練早已熟知的知識點,她還是想先完成眼前這份會影響成績排名的答題卡。老師說,高考是人生輝煌的跳板,高考成功的人是光鮮亮麗的“人上人”。高中三年來,她一直靠老師的話鞭策自己,但所謂“輝煌”、“人上人”只是腦海中一團意義不明的虛影。
2016年,沈琪考入Z大社會學院,在同為Z大2016級心理系、后來在牛津大學讀碩的馮悅的印象里,沈琪是那種“課前爭當課代表,上課始終第一排”的優等生。
那年11月,北大心理學副教授徐凱文發表《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的演講,一時轟動。演講說:在功利主義教育觀的導向下,中國大學生患有類似抑郁癥的“空心病”,不知學習是為了什么。他引用了錢理群教授關于“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論斷,談了“教育商品化”的問題。
大一下學期,Z大的新生還未分流,在課程《心理學概論》的最后一課,老師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意義焦慮”,研究年輕人“擔心人生沒有意義,因此十分焦慮”的現象。沈琪聽著有些入迷:這時的她終于有時間,也有科學手段去質疑——自己長時間來的辛苦和努力,到底有沒有意義?
但她不曾料到,在確定將“意義感”作為本科畢業的研究方向前,她先撞上了抑郁癥。從大三下學期做學年論文到直博做課題,這三年,是沈琪和抑郁癥斗爭的三年,也是她堅持意義研究、探索人生意義的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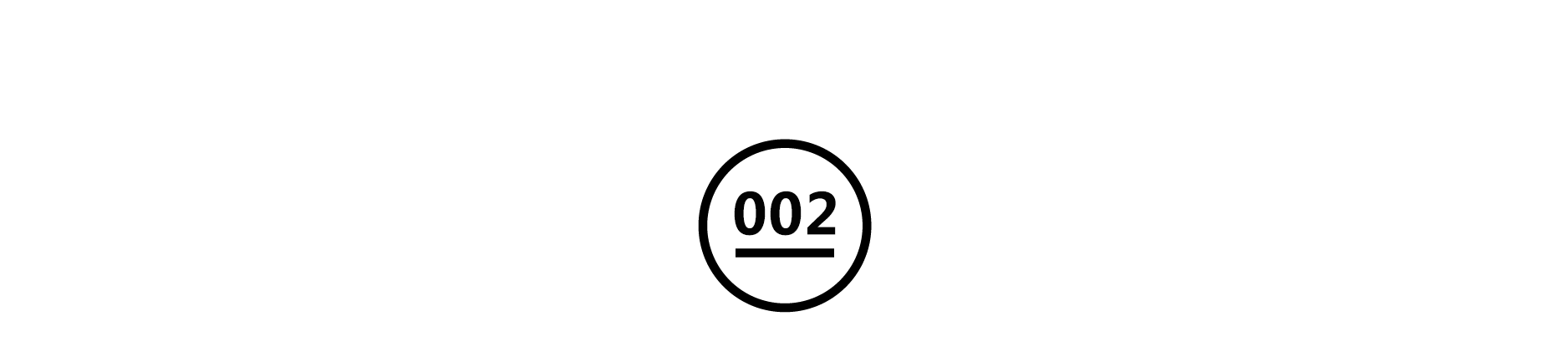
抑郁癥來了
自初中起,爭吵不斷的家便是沈琪排斥的地方,到了大學,家依然時不時刺激她血壓升高:
秦皇島,親戚聚會。那時沈琪的男友還沒念博士,親戚們認為他配不上保研直博的她,勸她“嫁一個出身大城市的官二代”。
沈媽會將沈琪在初中、高中的所有成就,一一列在一張A4紙上,攜著一臉不情愿的沈琪前往各桌,高聲朗讀紙上的榮耀。
家里,爸媽曾嫌棄她沒考上北大。
......
她會用“地獄”形容自己的家庭,也會在每次和家里吵架時首先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孝順、沒人情味。
大一,她時時因為家庭矛盾而失眠,開始嘗試通過專業的正念冥想法入睡。正念冥想要求人靜下心,調整呼吸、集中精力,可她越是鉚足勁強迫自己入睡,越是焦躁難安。
大二,她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交換。伯克利的教學不僅讓她認識到“有的人天生就在其他人奔赴的羅馬”,也讓她發現,很多在實驗室驗證成功的療法,真正運用到實際生活,能夠發揮的效力接近于零。實驗室會控制變量,但生活中,身心疾病、階級、閱歷、性格、社會關系和家庭關系,影響著個體的治療程度。這意味著,心靈意義上的療愈沒有可復制的范本,每一個個體對抗精神疾病的故事,都是現在進行時的生命實驗。
大三下學期是Z大心理學系壓力最重的一個學期,學年論文、升學壓力全都壓在這一段。上野千鶴子在東京大學入學式的致辭在國內走紅,“你們應該都是抱著努力就有回報的信念來到這里,可是等待你們的,是一個努力也未必有回報的社會。”這句話在沈琪的心里砸出一圈圈漣漪。
不久,沈琪的手里多了一張顯示中度抑郁狀態的診斷單,她還記得確診時,醫生“嘶”的一聲:我第一眼看你,感覺挺開朗的呀?
確診后的那段日子,失眠的不僅是沈琪。男友是大她一級的河北老鄉,名字里帶一個“鶴”字,沈琪喜歡叫他鶴先生。2016年,鶴先生帶領同鄉的大一新生熟悉Z大,人群中一眼看見開朗自信的沈琪,恍惚間一見如故。得知女友確診后,鶴先生輾轉反側,第一次意識到愛情不止甜蜜。
2019年秋天,沈琪進入大四,已獲得直博心理系的資格。她享受閱讀文獻、攝取知識和自由思考的過程,年級第一的成績也讓她期待做出一番漂亮的研究成果。她進入Z大社會學院教授王飛的課題組,導師研究年輕人的“無意義感”。沈琪也選擇“自我控制與意義感”方向作為本科畢業論文的主題,研究自律為何會給人帶來意義感。
如果翻看沈琪的QQ空間,她畢業論文寫作過程的賽博剪影是這樣的:
2019年 大四上學期
10月18日 圖書館 知道自己最近精神不好,特地選了短小精悍的論文進行閱讀。結果對電腦屏幕發了兩小時呆,于是去操場上狂跑5公里發泄。
11月26日 宿舍 做噩夢,夢見自己渾身扭曲,怎么吶喊也發不出聲音。引用曼玫《抑郁生花》的句子,“我不想再害怕你、抗拒你、逃避你、消滅你。”
12月5日 教室 前夜睡眠差影響記憶,下午兩點和導師討論學術,居然把一篇文獻的研究結論完全記反了。但吃安眠藥會讓第二天頭疼。
......
2020年 大四下學期
3月25日 因疫情隔離原因 居家 早上六點自然醒,起床這會兒總算沒頭疼了——昨天一天基本沒學習,我以為今天的狀態緩過來了。結果才看了半個多小時的論文,我又偏頭疼,頸椎也疼。這是條件反射嗎?!
......
這樣的狀態斷斷續續,直到她完成本科畢業論文。
時間來到2020年6月,沈琪即將本科畢業,17號這天,Z大2016級心理學系12個學生在食堂將三張四人桌拼成一個長桌,當作畢業聚餐。沈琪聊到自己在吃抗抑郁藥,坐她右邊的馮悅為了安慰她,搭了一嘴:“其實我已經吃了半年的弗洛西汀和喹硫平”。還有位童姓男生透露,一天吃三片富馬酸喹硫平。患了抑郁的同學知道,他的抑郁癥已經非常嚴重。
大家數了數這屆心理系的抑郁癥患者,合計有四五位。

沈琪的抗抑郁藥物
這位童同學本是天文系的,但因為總來旁聽心理系的課,也被算作心理系人。童同學曾向馮悅坦言心理疾病嚴重影響了自己的學習,放眼四周,一些掛科的同學其實也是如此。于是他邀請馮悅一起向學校學生代表大會提交提案,呼吁加強對學校心理治療的重視,但最后由于繁忙,提案無疾而終。

作為直博生,我似乎不喜歡搞研究
讀博兩年,抑郁癥不止不休。
整夜失眠。
凌晨,宿舍,安眠藥依然不管用,沈琪聽信某公眾號聲稱藍莓的花青素可能有抗抑郁功效,于是花費一百多元購買藍莓提取物,輔以收聽冥想APP,但仍無法入眠。她當然知道保健品無法醫治疾病,還是試了——這是心理專業的她干過的最離譜的事。
不是沒有嘗試過心理咨詢。接受咨詢師干預時,她會不由自主地識別咨詢師此時向她使用的治療策略:同感、矛盾性提問、自我披露、與來訪者建立長期的情感聯系......沉浸感全無。曾有位咨詢師過多輸出觀點,她則在心里默默回憶課程內容:心理咨詢師應該注重使用傾聽療法,而不是“三分聽七分說”。

沈琪在宿舍,借助插花、喝茶助眠
她一直在等候“減藥”的時機,如果某天狀態不錯,臨睡前有點困意,晚上就會少吃半片安眠藥。減藥一旦失敗,病情便會惡化,會比現在任何一刻還難熬。但她在意的是“我在吃藥,說明我這個人是不正常的,是精神殘疾。”
代替藥的是烈酒。在放任自己一口氣悶了四兩40度的波本威士忌后,她糊里糊涂地用香熏蠟燭將手中用來調酒的壺燒了個洞,清醒后當作笑話講給別人聽。
波本威士忌,加檸檬或不加檸檬,加氣泡水或加白開,按1:1和1:2.5兌,都是不同的口味,若是兌上紅石榴糖漿,會變幻出漸變色。沈琪仰頭干完一杯梅酒,麻溜地從床頭柜里掏出護肝片,摳一片扔嘴里:“酒喝太多了,需要護肝。”和著水一骨碌咽下去。

沈琪調的漸變分層酒
酒不比藥管用,但酒讓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需要依靠藥物入睡的病人”。
由于直博需要上研一、研二、博士的課程,她的博一課表很滿,還好周末跳拉丁舞可以將她暫時拽離現實。舞步踩上音樂節拍,她伸出手,是全班最柔緩的姿態。向朋友介紹拉丁舞步和模特一字步的區別時,她會在嘈雜街區旁若無人地輕輕躍起。
至于研究——只要狀態不錯,學習都是她的優先項。可她一看文獻,看一句忘一句,沒兩小時就犯困、胸悶。嚴重時呼吸急促,手不自覺地微微發抖,需要躺床上歇好一會兒。
她分不清,如今做研究的低迷狀態,是受抑郁癥的生理影響多一些,還是根本就是因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有時她回望,忍不住揣測也許自己更適合曾經反感的應試學習模式:每天完成被安排的任務,每件事都有標準答案。相形之下,研究生之路則空洞而遙遠,大多數是“幾年之后要發一篇文章”式的一聲令下,往后每一步都要自主探索和設計。
社會學院的書記勸她,“學習”是向內輸入、學習知識的過程,而“研究”是向外輸出、生產知識,你在本科階段喜歡學習,并不代表你適合做研究。導師也常問她,你是不是潛意識里并不想讀博,只是迫于家里的升學壓力,已經將家人對你的學業期待內化了。
她回答不上來。
學不進去的大部分時間托付給了勵志動漫,主題關乎夢想、斗志與羈絆。有時她深受劇情鼓舞,有時又黯然傷神。看動漫就像去做了一場心理咨詢,咨詢結束后的即刻感到療愈和動力奮發,可回到現實,再次面對一地雞毛仍束手無策。
我到底是誰?我喜歡什么?我有拼盡全力也想達成的目標嗎?我有賭上自尊的事業嗎?揮之不去的問號。
2021年8月,南京疫情反撲,城市情緒低落。醫生新開的處方要求她每天戶外活動不少于2小時,最好有半天能室外活動。可當時拉丁舞課程正因疫情停課,戶外運動更是難以開展;作為一名直博生,在書桌前久坐是基本。這種反差讓她覺得荒謬。
被迫在宿舍隔離的日子,每天盯著確診數據上爬,睡醒一刷手機就是有關新冠疫情的通告與新聞,她沒來由地感到不安全。“沒有意義”的感覺,又一次滲入了生活的縫隙。
12月,沈琪的博導邀請她參與課題項目“大學生無意義感的內容及其形成”。她的任務是把學界有關的經典文獻閱讀、整理一遍。
然而沒多久就讀不下去了。沈琪和鶴先生的雙方父母見面了,沈媽要求女兒在家鄉辦正式婚禮,因為如果只辦訂婚宴的話,“沒啥親戚來,來了也不咋給錢”。那晚,沈琪多吃了兩片安眠藥,她很傷心,自己的終身大事“被爸媽當作回錢的工具” 。
狀態又掉了,經常是當房間地板上明亮的方格子輪轉成忽明忽暗的夜色,她才從床上爬起來,陪鶴先生吃當天第一頓飯。直到2022年3月初忙完結婚,整頓好心情,她才開始認真思考該如何準備11月的研究生中期考核。
想在中期考核拿優秀,不僅要求博士生交出一個完整的實驗方案,最好還做出一個證明方案沒有硬傷的階段性成果。
可是,心理學研究的過程與結果具有不確定性,容易投入多但最終難以對數據進行合理的解釋,這在沈琪看來如同白干:“不應該討一個結果嗎?”她的本科論文就遇到數據難以處理的瓶頸,到了博一,她仍在反思該如何解釋那些數據。
沈琪本科論文的假設是,人們在努力的過程中更有意義感,就算目標沒實現,人也會感到很快樂。經過反思,她發現自己對學術名詞“Procedure”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誤將其翻譯成“純粹的過程”。實際上那篇外文文獻對此的釋義是:“Procedure并不是純過程,而是每一步都能看見目標進展的‘階段性結果’。”這個邏輯是,人無法從純粹的過程中獲得快樂,如果在過程中沒有一點結果實現的話,人還是開心不起來。
博士期間,她總在閱讀文獻時琢磨論文里提到的理論、方法等是否可以用作于自己的論文研究,本科期間那種不為研究結果而讀文獻,純粹求知、自由思考的享受感逐漸不復存在。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她的研究方向“意義感”并非學界主流。即使她確實是適合做研究的人,這個方向未必容易發文章,未來就業也難。天平的另一端,她已經24歲,理想生育年齡僅剩6年,對她而言,這意味著自己需要在6年時間里順利畢業并找到穩定工作。
這一串焦慮的因果纏成她繞不清爽的線團,又像是在走鋼絲,偶然發現自己可能并不適合腳下的賽道,卻又不敢退回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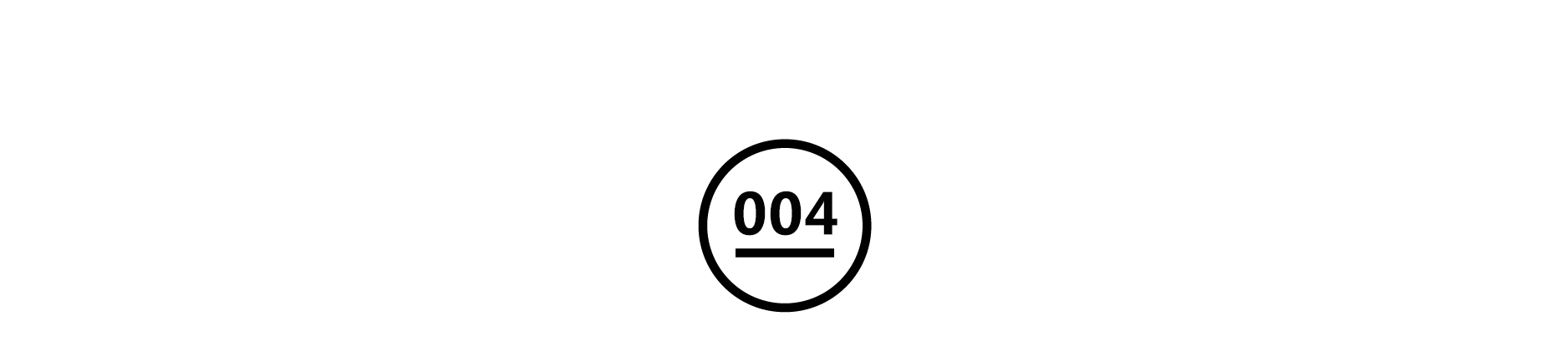
鼻腔手術
2022年4月初,柳絮紛飛的春末,沈琪的慢性鼻炎復發,但這一次比往年更嚴重。
從單純鼻塞到偏頭痛到整個頭都痛,從微微鈍痛到尖銳的跳痛,變成下樓梯顛一下都會痛,再到炸裂般的長時間頭痛。早晚氣溫較低時,鼻子堵塞,在快要窒息時,她感覺死神在身側一閃而過。
考慮到疫情期間外出學校看病要走諸多流程,她和鶴先生搬至學校對面的小區租房。
鼻腔鏡的檢查結果顯示,沈琪偏曲的鼻中隔與鼻甲擠壓在了一塊。手術通知單趕著4月的尾巴來了。
術后清醒過來,疼痛從咽鼓管區域逐漸蔓延到耳朵,連吞咽唾沫都費勁。一般止痛泵的流量開到5檔,她要求開到8檔。止痛泵停后,護士幾分鐘內沒現身,她不顧鶴先生的阻攔,一邊哭一邊拍好幾次呼叫鈴。換泵時,護士說,之前有個20歲出頭的男生,在術后嚎了一晚上。
第三天凌晨清醒,她猛然想起,整整兩天,自己常吃的抗抑郁藥、抗焦慮藥都沒有吃。她很心慌,鶴先生也醒了,護士讓她吸了氧。
凌晨兩三點,瀕死感達到頂點。她斜躺在床上,雙手抓住鶴先生的手放在胸口。在鶴先生看來,她的眼睛一半睜開,像在做夢,嘴里嘟囔像說夢話。而她當時的感覺,正陷在一種說不出的難受,既不是疼,也不是癢,像缺氧。整個人輕飄飄的,靈魂似乎正在逐漸離開身體。她把手舉起來:我有沒有在發抖?
鶴先生急忙按鈴喚人,醫護人員匆忙的腳步聲漸近,他在她耳邊一遍遍重復“沒事的”。。
四周聲音漸弱,世界搖搖晃晃,力氣從指尖流出,沈琪失去了意識。
2022年5月1日清晨,沈琪從術后痛感中蘇醒,護士拔掉鼻腔海綿的一瞬間非常疼。鶴先生告訴她,前一晚的她,神志不清地交代后事,說她有哪些財產在哪兒,說他離開她的時候要帶上些什么。鶴先生調侃她:“你說這么多,卻沒把銀行卡密碼說出來。”
熬過了“生不如死的術后恢復期”,為慶祝健康和自由,她穿著病號服在醫院四處游蕩,又在日記《病痛、瀕死感與未來一年的選擇》中寫道:“憧憬痊愈后的美好生活,是支撐我挺過術后恢復期的強大精神動力,但是,這是很認真的思考,不是單單為了麻痹自己。我經受了這種痛苦,是為了什么?為了之后繼續回到大學,繼續抑郁焦慮沒有動力,不知道該做什么研究嗎?顯然不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戛然而止,我回顧這24年的人生會后悔什么,是沒有讀完博士嗎?顯然不是。”
初中,尤其是高中以來,她被灌輸的價值觀是,要努力學習,實現階級躍升。心理學的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將人做事的動機分為外部和內部兩類,從外部動機向內部轉變有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如果不做此事,擔心受到懲罰;第二階段是如果不做此事,會感到愧疚和后悔;第三階段是一種認同感;最高級的是同一感,即感到所做之事理應是我的一部分。“我很好學,但從衡水一中到Z大985本科,我努力讀書的動機都是處于第二階段。”
高考已過去6年,時間的卷尺一天天舒展開,她無數次站在高光底下,但也一直啃食著抑郁癥長出的惡果。
這一次,她想把從小到大,為了“追求卓越”“成為優等生”這些目標而錯失的機會,都補回來。
她決定休學一年。

逃避可恥但有用
學心理學這些年,沈琪越來越能理解爸媽,越來越疲于和他們爭辯。她認同一個觀點,人在加工信息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父母的愛不可能是無私的。我不敢說他們不愛我,但比起愛我,他們更愛自己,更愛自己的面子。”面對爸媽下達的要求,她學著優先考慮自己的感受,“他們用愛的名義對我造成傷害,我就是不舒服,也許沒有必要太自責”。
至于理解自己:沈琪看過奧地利精神病學家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書中提到,人天生會有一種不足感,終其一生,人都在試圖超越這種自卑。
在從本科到博士的心理學研究實踐中,她逐漸發覺,屢次失靈的正念冥想法,其核心要義并不是形式和儀式,而在于對周圍的覺察和對自我的無條件接納,“了解自己對于‘煩’是如何具體化的、如何去拆解和描述此刻正困擾我的煩躁,然后接納自己睡不著、學不好”。
剛確診中度抑郁癥那會兒,醫生說這個病不太好治,心理學這個專業讓沈琪覺得自己很可能屬于好治的那一批,但她不是。后來,她又了解,80%的抑郁癥患者會不斷復發。她自認為性格開朗,又在努力改善病情,有望成為那痊愈的20%。
“事實證明,其實我就是那治不好的80%。”沈琪歪一歪頭,嘴角向下一撇,順手將手邊玻璃杯里僅剩的檸檬水一氣喝光——鶴先生將她的烈酒藏了起來。
休學后,她新找了一份實習,想試試學術外的工作,2022年7月底早上9點到崗。“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可我又不覺得我這是逃避。”
也許是一種新的選擇。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沈琪、馮悅、王飛、童同學皆為化名,照片均由沈琪提供)
實習生:方益
歡迎繼續關注本期“小行星計劃”專題:

海報設計:周寰
目前鏡相欄目除定期發布的主題征稿活動外,也長期接受投稿。關于稿件,可以是大時代的小人物,有群像意義的個體故事,反映社會現象和社會癥候的非虛構作品等。
投稿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
(投稿請附上姓名和聯系方式)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