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隱喻、說話、闖入:鄭在歡小說中的三種力量|新批評
從“駐馬店傷心故事”中走出的鄭在歡,在最新小說《動物癡人》中用歡脫的語風講述一眾打工男女和一只羊在北京郊區上演的人間悲喜劇。青年評論家賈想在讀完這篇小說后認為鄭在歡的寫作由“土的寫作”走向了“風的寫作”,來到了一個離地的位置,與日常生活的重力進行無休止的斗爭。
他從小說中的隱喻出發,認為:小說這個文體的魅力,在于小說中處處是“難以解讀的符號”,在于在虛與實之間、具體與抽象之間游走,在于永不定于一尊、永不斬釘截鐵的曖昧。
文丨賈想
讀完《動物癡人》(《當代》2023年3期),我想:鄭在歡寫飛了。寫飛了不是說寫壞了,而是描述他的寫作目前所處的一個位置。幾年前,我感覺他的寫作正在從沉重的駐馬店掙脫出來,從“土的寫作”走向“風的寫作”。
現在看,他的寫作確實乘風而起,來到了一個離地的位置。與日常生活的重力進行無休無止的斗爭,是小說家的宿命。因為虛構就是反重力,就是上升與墜落的辯證法。這么看,鄭在歡認領了他的宿命,當然,也是認領了這個職業的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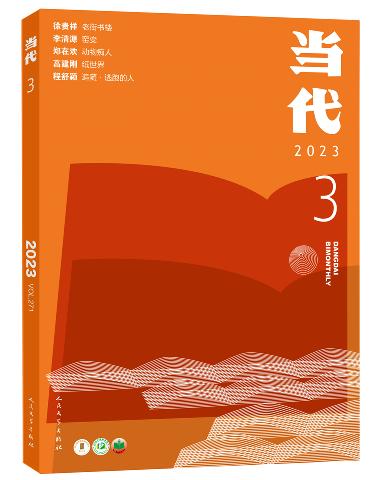
《當代》雜志2023年第3期刊發了鄭在歡的最新小說
從《動物癡人》當中,我看到至少三種力量:一是隱喻的力量,一是說話的力量,一是闖入的力量。這三種力量共同的效果,就是將一個演繹城鄉二元對立的故事給抬升了起來,從社會學的層面,抬升到了美學的層面。談美學問題而不是社會學問題,分析形式而不是做內容概括,是文學評論的職責所在。
隱喻的價值連城,在于提供了一個垂直的深度,將語言和語言所表達的現實,分解為表象與本質。這樣,我們在表達一個事物的時候可以同時表達其所隱喻的事物,在敘述人間的時候,可以同時涉及天堂與地獄。對于現代的小說家,隱喻始終誘惑著他們。
在《動物癡人》當中,鄭在歡動用了隱喻。具體而言,叫做動物隱喻。這方面的歷史就更長、更龐雜。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只取其中的兩個動物隱喻:羊的隱喻與狗的隱喻。
羊總是隱喻著良善、柔弱、服從,狗經常隱喻著強勢的一方,兇狠、霸道。在鄭在歡的故事里,羊,作為一個被飼養的動物,與農村來的樸實善良的騷虎住在一起;狗,作為寵物,與城里專橫霸道的小房東住在一起。二者隱喻著地位完全不同的兩個主人。
騷虎與小房東,擁有兩套完全不同的“動物觀”。來自鄉村的騷虎認為,“世界不是人類的,是動物的。”他相信人也是動物之一種,是與動物平等的存在。他尊重每一個動物的獨立性、主體性和生命權。

鄭在歡部分作品封面

而小房東的動物觀,完全是高高在上的、人類中心主義的動物觀。他認為人與動物有本質性的差異,人的價值遠高于動物,動物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主體性和生命權。
故事推進到后面,騷虎的羊意外闖入了小房東的家,為此小房東的狗咬死了羊。從這里開始,故事就不再是羊和狗之間的沖突,而是它們所隱喻的那些身份與觀念的沖突——低位者與高位者的沖突,樸素的“齊物論”與人類霸權主義的沖突。
這就是隱喻的力量:在講述一個特定事件的同時,也講述了一個普遍性的事件;講述經驗世界的同時,還講述了觀念的世界。但隱喻的缺陷也在于,它將故事中的形象從具體的時代與現實背景中抽離出來,變成了一個“可解讀的符號”。
隱喻越有力量,故事就越容易全盤滑入觀念的層面。小說這個文體的魅力,在于小說中處處是“難以解讀的符號”,在于在虛與實之間、具體與抽象之間游走,在于永不定于一尊、永不斬釘截鐵的曖昧。隱喻,在快速換取小說深度的同時,犧牲了這個文體的曖昧。
鄭在歡是河南人。河南人喜歡“噴空”,一個“噴”字,可見對說話的狂熱。在小說里面,說話的有意思之處在于話的真假難辨。也就是前面說到的“曖昧”。

《風柜來的人》劇照
話作為一個非物質的東西,假亦真時真亦假,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這就為藝術表達提供了足夠的自由。這種語言,特別“誠”的時候就會放光明;特別“不誠”的時候,就會引發恐懼。真與假、光明與恐懼、善與惡之間的轉換,是小說語言最根本的美學秘密。
鄭在歡的才華,就在于他掌握了語言的這個秘密。他在小說中,多次讓人物使用這種真假難辨的話,引發人物的轉變、事件的轉折。行動,當然是推動情節最好用的方式。
但在厲害的小說家那里,比如巴別爾(讀一讀他的《鹽》吧)、博爾赫斯(那圖窮匕見的《刀疤》),他們可以只用一句話,就把善惡、真假和整個世界的秩序顛倒。真正的語言大師每說出一句話,都像向天空拋出了一枚不確定性的硬幣——沒有落地前,印在硬幣兩面的天使和撒旦,誰都沒有勝算。
故事有兩種,一種是戲劇性的,一種是非戲劇性的。絕大多數的小說,是逃不開戲劇性這個課題的。戲劇性,本質上就是兩個字:“闖入”。“闖入”,一是要求故事存在互相區隔的、不同的敘事層面,二是要求一種突然性、意外性。在這個意義上,戲劇性,就是指故事突然從一個層面突入另一個層面所造成的效果。
《動物癡人》,很好地實踐了這個戲劇性的法則。鄭在歡在故事中,設置了很多硬性的區隔:市中心的二環與城郊的六環(空間區隔)、房東與租客(貧富區隔)、直播世界與現實世界(真假區隔)。他自如地在這些區隔之間制造著戲劇性:讓燕燕從黑暗的六環“闖入”二環明亮的沃爾瑪;讓騷虎的狗“闖入”房東的地盤;讓龍哥所在的虛假的、表演的世界,“闖入”騷虎所在的平靜的、樸實的世界。小說就是在這一次次的“闖入”當中,推向了高潮。

鄭在歡在書房
需要專門談的,是龍哥對騷虎的“闖入”。龍哥看到了騷虎身上“愛護動物”的吸金標簽,來到騷虎家里,做了一場天花亂墜的直播秀。
我所注意到的是,鄭在歡借由這次“闖入”,將一種新的節奏注入了小說,那就是資本新一輪高速積累所產生的癲狂的節奏。這是新的形式感。這就是我對處理當下題材的作品的期待:不僅要呈現新的經驗內容,還要呈現出維持新的經驗內容的那個形式。
故事講到最后,龍哥從直播世界來到騷虎、張全、小房東、燕燕等人所處的現實世界。他像病原體一樣,將直播世界(資本世界)的那種“繁榮的表演性”,傳染給了張全、小房東、燕燕。隨之傳染給他們的,還有“假話”。他們因為沉入了語言的表演、沉入了虛假的屏幕,而被現實除名,消失在了藝術的荒誕性之中。只有騷虎,這個自始自終不說假話的癡人,因為保留了基本的動物性,而逃開了被荒誕所吞噬的命運。
假的人,因為無限逼近虛假而消失;只有真的動物,因為保留了動物性的誠實而活了下去——這就是作為小說家的鄭在歡,所作出的判決。
原標題:《隱喻、說話、闖入:鄭在歡小說中的三種力量|新批評》
本文為澎湃號作者或機構在澎湃新聞上傳并發布,僅代表該作者或機構觀點,不代表澎湃新聞的觀點或立場,澎湃新聞僅提供信息發布平臺。申請澎湃號請用電腦訪問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